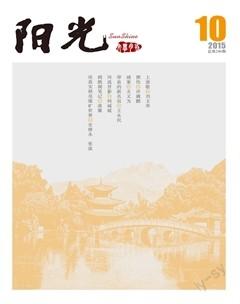我的父亲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每当听到或下意识地哼起崔京浩演唱的《父亲》那首歌时,我就情不自禁地热泪潸然,父亲清癯的面容,整天忙里忙外的羸弱身影总在我的眼前叠现,我仿佛又回到了与父亲朝夕相处的艰辛却又充满温馨的欢乐时光——父亲离开我们有二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减轻我那撕心裂肺式的痛。对父亲的那份愧疚,我至今仍难以释怀。
父亲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去世的。那天是星期日,我搭车、转车还步行十余华里,从单位赶到家乡探望病中的父亲。母亲告诉我,父亲这次很难挺过去,医生都不愿意下药打针了。见到我回来,父亲很高兴,立即穿上外衣,从床上坐起来。我见他面容憔悴,气喘吁吁,比以前更瘦了。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父亲说:“等你病情好转时,你和妈还是到学校和我们一起住,互相有个照应,也省得我一心挂念两地。”“不用了,还是在家老去好,万一死在单位,麻烦就大了。”父亲断然拒绝。我知道,父亲除了不想火化外,主要还是为我着想:老家是个大村,有一百多户几百号人。按当地风俗,在外地去世的人,是不能摆放在公用的祠堂中受祭的,否则会有人说闲话,甚至刁难。望着父亲,我潸然泪下。
父亲吃了一个我带回的砀山梨,就没有吃午饭。趁着吃午饭的机会,我与母亲悄悄商量了父亲后事的安排,叮嘱她,父亲病危时立即派人通知我。午饭后,父亲精神特别好,他让我到堂伯父家把刚修好的族谱拿来,让我把谱上所载的祖父、祖母、父、母等相关内容读一遍给他听后,点了点头。然后对我说,他去世后,丧事从简;母亲百年后,他希望能与母亲合葬。我含泪点头答应。他又从身上掏出几张纸币,抽出两张崭新的五元钞,让我转交给两个小孩。余下的钱都给了母亲,母亲习惯性便秘,让她去买几盒黄连上清片。歇了一会儿,他就催我赶紧回学校去,我看他意识清楚,精神还好,又担心学生,于是就赶着回学校了。没想到,与父亲这一别,竟成永诀!
也许是心灵感应吧,当晚我梦见父亲去世了,竟哭出声来。妻推醒我,问道:“怎么了?”我说:“不好!我梦见父死了,今天不回学校就好了。”妻安慰道:“别瞎想,不会的。”天不亮,就听到有人敲门喊我,我从床上一跃而起,一开门,是屋下的两个堂兄弟,我一见到他们,就知道大事不妙。果然,他们开口就说:你父亲晚上去世了。尽管有预感,一旦证实,我仍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好在妻还镇定,尽管她是上海人,乡情乡俗还懂,赶紧到厨房煮了两碗面条,煎了几个鸡蛋,招待了两位报信的堂弟兄。送走了他们,我们赶紧收拾东西,一家四口搭乘学校食堂采买的农用车赶回老家。母亲告诉我,当晚屋下叔伯弟兄们在父亲病床前聊得很晚才散去。父亲临睡前还吃了药,带着生的希望安详地走了!
父亲没有童年的欢乐,当别的小孩还在父母怀里撒娇、任性的时候,父亲就成了孤儿。六岁时,祖母因患“大肚子胀”的病而去世,八岁时祖父又离他而去。父亲只得靠自己打拼谋生,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其艰难可想而知。父亲二伯的儿子堂兄伯根将父亲带到离家十余华里的邻村八子塅石大屋财主石三合家为其放牛,好歹总算居有定所,不至于四处流浪冻死饿死于荒山野岭。父亲这一去就是十五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才重回家乡。在石家,父亲由放牛娃而长工,最后成为育秧、拔秧、插秧、犁、耙、平、锄等样样农活都精通的老把式。对于石家的这段佣工经历,父亲很少也不愿提及。其间倒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父亲的堂兄伯根一直尽着长兄的职责,他把父亲的工钱攒起来,在老家为父亲买了一间正屋,置了一亩多水田,好让父亲成年返乡时不至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是伯根大伯的精明和善良,父亲回乡时也许一无所有,真的无安身之所。毕竟外面的诱惑还是很大的,何况是没有父母关爱管教的孩子。每念及此,父亲对伯根大伯的感激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伯根大伯没有后人,所以每年清明、除夕回家祭扫先人时,我和子女都在伯根大伯坟前烧一些纸钱。子女虽在外地工作,我坚信只要他们有机会返乡,肯定都会坚守这份承诺的。另一件事是解放战争期间,本县油坝小苏港夏家洲土匪夏干、余洪鱼等自称“四老爷”(抗战时期新四军的一支部队曾在这一带活动过,当地人称之为“四老爷”。当地一些土匪也就自称“四老爷”,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到财主石三合家劫财。石家长工还有石姓族人仗着人多势众,拿着锄头之类的农具驱赶土匪,父亲冲在前面,一土匪掏出手枪,逼住父亲,拽下锄头,用枪托猛击父亲额头,父亲顷刻倒地,血流如注。同伴见状,停止了追赶,土匪乘机逃脱。同伴们急忙用锅底灰摁住父亲的伤口,好久方才止血。值得庆幸的是,土匪们没有开枪,否则父亲就性命难保了。后来给父亲改棺(当地风俗,人死后先将棺材在山上暂厝三年,然后才改棺入土安葬)时,我分明看见父亲前额凸起豌豆大的一块,大概是当时骨髓从裂缝中溢出而形成的骨质增生吧。
一九四九年,父亲从八子塅回到老家。一九五二年在好心人的撮合下,父亲与母亲结婚。面对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父亲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无论是与人换工还是组内互助,他总是出工出力出技艺,干活效率高,质量好,备受人们称赞。一九五三年,家乡成立了初级合作社“中华社”,父亲被乡亲们一致推举为社长,村西边的续阳叔被推举为副社长。父亲目不识丁,又因拥有一亩多水田,土改时被划为下中农,而非贫农。之所以被推举为社长,完全是凭自己的实力苦干出来的。一九五三年,父亲还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赴县城参加县政府的授奖表彰大会。我后来还见过一个白色陶瓷的肥皂盒,就是那次受表彰的奖品。可惜父亲没有一点儿文化,不然或许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续阳叔后来成为大公社的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党委书记,最后在副区长的任上退休。他的人生道路比父亲顺畅得多。对此,父亲倒还淡然,一副乐天知命的模样。
父亲青壮年的时候,假如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凭他的吃苦耐劳,凭他的一手老把式的技艺,即便是在家种田,也定会收入丰厚,生活滋润。何况父亲还是一个多面手,动手能力极强,看一样,学一样,会一样。他不是专业篾匠,菜篮、箩筐、畚箕等生活生产用具,都是自己动手编制,从不求人。他不是专业瓦匠,却会砌猪圈、粮仓。他还会摸黄鳝、逮泥鳅,捕鱼捉鳖。农副牧渔,三十六行,没有他不会的。在某些领域,其手艺不输给专业工匠。偏偏生不逢时,“大锅饭”让父亲徒有绝技,英雄无用武之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做一天都是十分工,三至五角钱。家庭副业、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经商做小生意是“投机倒把”,均明令禁止。再加上母亲不是天足,一九五八年大集体时母亲在蔬菜组种菜,又染上了湿疹,以致一碰上青菜就浑身起疹,奇痒难忍,尤其是双脚,经常溃疡流水,行走都很困难。这可苦了父亲,既要主外,干活挣工分;又要操内,砍柴种菜,料理家务。父亲忙里忙外,每天都是干不完的活儿,做不完的事。但他毫无怨言,整天都是乐呵呵的,他坚信凭自己的实力完全能撑起这个家,正是凭着这份坚定、自信,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家庭的温馨和谐。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年代,全村饿死的就有几十人,有七八户绝户,像我们这样一个弱势家庭,居然能从死亡线上挺过来,这不能不归功于父亲的顽强能干和母亲的坚韧贤惠。
一九六一年,为了度过春荒,政府允许个人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父亲在山边滩头一口气开了十几块荒地,全部种上生长周期短的荞麦,菜园地也栽了不少芹菜。收获时节,看着一担一担的荞麦,一家三口心里都乐开了花。别人家三餐都吃荞麦糊,我家则可以顿顿吃上荞麦发糕。发糕一出锅,我就左一块右一块,一个劲地狼吞虎咽。这时父亲总是双手托腮,欣赏他的劳动成果是如何让我大快朵颐的。
父亲是一脉单传,我的出生,无疑成为他最大的快乐。父亲对我的百般呵护关爱都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中:那充满慈爱的短暂一瞥,那带着体温的轻轻抚摸,从街上带回的五分钱一个的“扁担头”(长烧饼),别人给他却省给我吃的一把南瓜子,无不凝聚着深沉博大的父爱。让我快意的还有,经常坐在父亲的肩头走村串户,看戏看露天电影,到外婆和舅爹家拜年。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饱饭都令人羡艳不已。没有钱买鱼买肉,父亲就利用出工休息时间摸黄鳝;发大水时,就去戽鱼;放水灌溉后,就在塘涵出口处逮泥鳅。父亲用他的精明,用他不知疲倦的忙碌,精心呵护着这个家,全力支撑着这个家。父亲很少骂我打我,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我是因为我偷跑到池塘里玩儿水、滑入深潭差点儿淹死,父亲知道后用竹梢狠狠地抽我双腿,直至血肉模糊,自此之后,我再也不敢背着大人偷偷去玩儿水。
少年、青年时放牛、佣工的艰苦劳作和艰辛生活,成家后长时间超负荷的忙碌,大大透支了父亲的生命。但命运喜欢捉弄人,联产承包,正是父亲大显身手的大好时光,他却英雄迟暮,力不从心。不到六十岁,父亲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再也无法承受那繁重的田间劳作了。我与妻商量,把父母接到单位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时光里,随着我们工作单位的调动,我们全家在两个农村中学之间往返迁徙。当时我的月工资是三十六元,妻的月工资二十多元,我们加在一起的六十多元月工资,供养一家六口人,相当拮据。我们常常是寅吃卯粮,当月的工资还上个月欠食堂的伙食费,再打借条从食堂借支当月的饭菜票,下个月发工资后再还。尽管如此,父亲仍然心满意足,能与儿孙一起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这精神上的愉悦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替代不了的。因此,无论我们的生活怎样艰难,他都从不埋怨,逢人就夸儿子、儿媳如何好,孙子、孙女如何聪明听话。见此,我们内心的愧疚也得到些许减轻。其实,我们当时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非常大,连两个小孩的学习都无暇顾及,对父母的关心真是少之又少。每念及此,内心总是隐隐作痛。尽管父亲身体不好,但他从不闲着,尽可能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洗菜、烧饭,打扫卫生,从不让我们动手。他看到学生倒在水池边白花花的剩饭,非常惋惜,不顾我们的劝阻,每到学校开饭的时候,他就带着篮子和锅铲,到学生宿舍的水池边收集学生倒掉的剩饭。回来后,他将剩饭洗净晾晒,晒干后的饭粒晶莹透亮。老家有人来时,他就将这些干饭粒送给他们做喂猪的饲料。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剩饭,他还自作主张圈养了一些家禽,包括鸡、番鸭以及番鸭与家鸭的后代骡鸭等。他仿佛又找回了从前的感觉,整天忙里忙外,乐此不疲。
也正是捞剩饭这件事,引发了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面冲突,我也因此铸成了不可饶恕的大错。那年我带文科复读班的班主任,一天,一位学生家长来学校看望孩子,因是熟人,我就留他在家吃午饭。刚刚开饭,一位老师就急匆匆跑来告诉我:“王老师,你父亲走不动了,坐在那里,快去看看吧!”我赶紧跑过去一看,父亲坐在一块石凳上,一篮剩饭就摆在脚边,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旁边围着一圈又一圈端着饭碗看热闹的学生。见此情形,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我黑着脸,一言不发,拎起篮子转身就走,让妻扶着他回到家中。送走客人之后,我没好气地冲父亲吼道:“叫你不要捞,你偏要捞!你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你让我怎么面对学生?”也许他从未见过我对他发这么大的火,也许他真的觉得影响了我的工作和面子。过了几天,他平静地对我说:“细伢,我跟你说件事,我这身体比以前差多了,万一死在学校,回老家上祠堂都有麻烦,我和你妈商量了,我们还是回老家过。”我惊诧莫名:“回家吃水都是问题,你们怎么生活啊?是不是那天我说了你几句,你就要赌气走啊?”“不是,我们考虑好久了,我一定要死在老家才安心。”“现在不走,等过了年再说。”事后我又告知了小舅父和在安庆的大舅父,希望他们做做工作。但父亲去意甚坚,谁也劝不住。春节之后,请大舅父出面,请来亲房的堂兄,开了个家庭会议。让堂兄负责挑水,粮食、柴火等生活必需品供应都一一安排妥当。把父母送回老家安顿好后,临别时,父亲还安慰我:“你别介意,我真的不想死在学校,在老家寿终正寝比什么都重要。”父亲回老家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又把母亲从老家接回到身边,我们一起又共同生活了十九年。母亲临终前两天,也是日夜吵着要回老家,在被送回老家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去世了。叶落归根,狐死首丘,莫非真有预感?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当时为什么莫名其妙地冲父亲发火,是虚荣心还是不满父亲捞剩饭,抑或是自己的性格暴躁、一时冲动?是,又都不是。依父亲的精明豁达,他也不会过于计较我的任性以至于执意回老家。对我,他一直很迁就包容。即使我做错了,他也认为正确。父亲执意回老家,一是如他自己反复说的,要在老家寿终正寝,免得死后为我增添麻烦。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姑伯叔婶,爱人家在上海。万一与乡亲发生纠纷,单打独斗很难占上风。在乡村,有时法理往往难敌乡情乡俗。其次,捞剩饭以及那天的场景,他也意识到,多少会让我有点儿尴尬,会对我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调到这个学校的时间还不长,他知道,校领导比较器重我,而其他同事多少有点儿不平衡。这也许是他执意回老家的最重要原因。为了我,他宁愿舍弃一切,这就是我的父亲,处处为我着想。俗话说“眼泪总是往下淌的”,没有谁比我体会得更加深切。这也更加重了我的负罪感,毕竟是我的任性让父亲执意回了老家,而且回家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父亲临走之时,我偏偏又不在他身旁。想想父亲对自己的百般呵护与关爱,想想父亲为支撑这个家忙碌了一生,想想父亲在刀尖上谋生活的半辈子漂泊,我真是欲哭无泪。
父亲的人生遭际,是同时代普通农民命运的缩影。他的一生,同那个风云不断变幻的时代紧密相连。同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一样,父亲是平凡的,但又是伟大的;父亲是卑微的,但又是高贵的。尽管他目不识丁,但他的言谈举止,立身处世,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父爱如山,沉稳厚重;父爱似海,博大深邃。
我爱我的父亲。
王敬波:男。安徽某中学教师,发表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