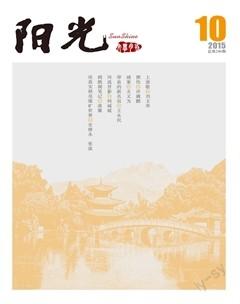河流昔影
在水上,放弃智慧,停止仰望长空,为了生存你流下屈辱的泪水,来浇灌家乡平静的果园。
——海子·题记
水 凼
大水离开,像往年一样,会留下一些礼物,当然不是那些没有漂走的树叶,也不是长在凼底的水草。白天,一把把锄头在彼此监视下守候,当水缓缓流退使水凼露出一丝形状,锄头噼里啪啦在其周围争锋,挖掘一个个小小的口子,摁上竹制的鱼篓——鱼便成了小镇人的礼物。
我的眼睛已在早春挖的水凼上滴溜溜转了几天,那上面闪动的波光嵌着一只只眼珠,不只是我的眼珠。涨水之前,我挖了平生第一个水凼,它不大,但符合我的欲望,能获得十来斤鱼就心满意足了。铲子磨破了我手上的皮,虎口处流出了血。铲子软了,吃不住泥土,但更加硬硬地磨擦我的手。我把它扔下,其他人的铲子一片欢笑。
河滩上的铲子已纷纷撤离,一个个水凼张着大嘴望天,迎接雨水的到来。我的铲子显得孤零零,在旷野被黄昏的残霞染红。我以为我的手在大面积流血。我将怨气全部发到铲子上,似乎被它欺负了。这实在不应该,虽然铲头与铲柄脱离过一次,但铲刃没有卷起,柄也没有断,这样的铲子算是非常优秀的了。父亲将铲子接好后,要替我将未挖好的水凼完工。铲子在父子之间跑来跑去,最后它选择了一双嫩手。
水凼挖好,我比别人多花了数倍的时间和精力。我大吁了一口气,然后扛着铲子,三步一回头地回家。回家后就想象,就梦想。有一天早晨,看见水凼消失在河水之下,顿时内心盈满了幸福。我的意念在河水中驱赶鱼进入水凼,意念同时织成一张网,围住水凼留下鱼。听见母亲对父亲说,要是水凼里有鱼就好了。母亲的声音里有一种叫做期待的东西将我撞击得很兴奋。父亲的耳朵里有一条饥饿的虫子爬了出来,使得他的回答怪里怪气的,他说情愿没有大水,庄稼地就能保住……水凼那么高的位置,水能上去吗?挖得那么浅,会有多少鱼呢?
父亲的话惊醒了我的梦。原来我在挖水凼时,那么多铲子发出讥笑,是因为水凼位置高,水上不去,待不久;原来父亲要替我挖,他是想将水凼挖深一些。这时,我的目光投向水凼之上的一汪水,希望变成了焦虑。我暗中有个很坏的祈愿,涨起的水高过水凼。可那样必然会使庄稼受灾。这想法,让我感到自己有罪过,于是又很忏悔。在涨水的日子,我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白天的想法,到晚上又变了;梦中的想法,到第二天成了相反的想法。
铲子已不再被我关注,它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我已把锄头检查了几遍,它要及时地在水凼朝下游的地方挖一个恰到好处的口子。鱼篓也已准备好了。锄头与鱼篓没有放在一起,但它们之间由我传递待命的消息。盼望水在白天把水凼呈现出来,口子越早挖开装上鱼篓越使鱼少跑掉一些。可往往水凼在夜里露形。每个锄头发现这种情况,都是不高兴的。除了极少人守夜,让锄头处于警惕状态,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睡觉,让梦连接着水凼。
我想守夜,因为实在害怕这一夜水退得厉害。母亲说,淹死了怎么办?父亲像是饱食了多日,竟然也反对我去守夜,而他自己又不去守夜。我决定半夜的时候悄悄溜出去。可是,锄头不见了,鱼篓不见了。我以为父亲去守夜了,一边骂他抢占胜利果实,一边冲向水凼的地方。结果没有看到父亲,而看见了别人的身影。锄头在星光下奏出一阵阵美妙的声音。我返身往家跑,路过厕所,锄头喊住了我。父亲将它藏在厕所里,而鱼篓在什么地方呢?柴堆上的一粒星光召唤了我,我冲过去夹起了两只鱼篓。
很庆幸,我在水凼刚刚露形的第一时间挖了一个口子,将鱼篓装上了。我的所有的心思开始浓缩到鱼篓中。鱼篓在天亮的一刹那被我快速提起,另一只鱼篓装到口子上。鱼篓脱水的声音不对头,我听见有人抛过来一句,有多少?我一看鱼篓,空空如也。回答了一句,有三条,两条小的,一条大的。大的大概多重?我不再回答。别人的鱼篓在我面前清晰起来,白花花的鱼一闪一闪,闪得我心头痒痒的,酸酸的。
什么时候弟弟过来了,我吼了一声,你来干啥?弟弟笑着,伸头朝鱼桶里瞅了一眼。我小声说,不要急嘛,鱼在凼底睡觉,还没醒来呢。弟弟却站到别人的水凼旁看鱼儿跳跃,将我给忘了。我反复起篓装篓、装篓起篓,只得到了几条小鱼。我被鱼篓脱水的声音击打着,精神沉重,心中绝望。我喊来弟弟,让他接收水留下的礼物。弟弟却不服从,他认为水凼里水快退完了,不会再有鱼。我狠狠地反驳他,水凼里的水退干净,至少要三天……
锄头服从了我的意志,将凼口给堵了起来。我留下一句,这水凼是属于我的,然后提着鱼篓回家,肚子饿得咕咕叫。接下来几天,我不再去看水凼——它是我的耻辱!母亲安慰我,明年提前找个好的位置,全家人都去挖,挖个大大的水凼。我哭了,哭得很伤心。父亲递给我一只脸盆,他要我去把水凼里的水全部舀出,小鱼小虾也是不错的收获。
我跳进敞开的水凼,踩着几公分深的水,使劲地舀水,泼向凼外。黑泥慢慢现了出来,一条条小鱼和一只只河虾在黑泥上蹦跳,然后一一落进寂寞了一年的鱼桶。
沙 井
季节的手掌在秋天收完果实显出本有的干枯。河流细若纹路,被烟尘遮蒙。期待一场雨,一场能让河水洗净手掌泥垢的大雨。一只只木桶在河边徘徊、逗留,面对泛着青苔和微生物的浅水,最后还是由瓢低下了头,舀起水,装入桶中。
我扛着铁锹站在沙石裸露的河床上,四顾茫然,努力判断哪里可以挖一眼井,不仅渗水量大,而且离家比较近。每天都得吃水,能从较近的地方挑水回家,这是我必要的选择。我开始挖井,一两锹挖下去,出现了散发着臭气的黑泥,立即放弃。泥井中的水带着腐殖气,不到万不得已不敢吃。
连续挖了几个地方,还是接触到了淤泥,心里就很不舒服。抬头,目光穿过柳叶飘飞的河岸树林,竟然一时找不到自己家的门,心里更加急躁起来。半天儿后,终于挖了一眼沙井,水在铁锹下慷慨地渗出,多情地往上涨。铁锹在水中兴奋地发出哗哗声响,像在饱饮一顿。这时,木桶追逐木桶,涌向我挖出的沙井。
大家一起等待混浊的水沉淀,枯涩的眼神闪动欲望。水尚未澄清,就有一些饥渴的瓢蠢蠢欲动,被我的瓢制止了。井是我挖的,我的瓢就理直气壮。但很快无数的瓢将我的瓢打败了。不断加入的瓢,不以为这井是我挖的就该由我优先舀水。已有人在这个沙井的旁边另挖一个沙井。我告诉他不要靠得太近,否则我这井就没水了。他不理睬我,继续挖,挖了一个更大的井。我很生气,但没有发怒,因为那井引走了一些瓢,给这井减轻了压力。
井水清澈后,木桶向瓢发出舀水的指令,水倒进木桶的声音,悦耳动听。一只瓢伸进井中,另一只瓢也伸进井中。小小的井,瓢与瓢碰撞,争吵,人影重叠,覆盖,井水消失了。半桶水,拎回去不成,至少还得将另一只桶盛上半桶,这样我好挑回家,倒进那个静守在灶台旁的水缸。
挑一担水需要很长时间,不如在等待的时候再去挖一个新的沙井。我右肩挑着空桶,左肩扛着铁锹,径直走向离家五百米的地方。河道在那里转弯,尽管别的河段河水似隐若现,不时断流于沙石之下,而河湾处最干旱的日子也蓄留着水,数平方米,几十公分深,它将全镇的妇女召唤了过来,差不多每户人家都在此洗菜、洗衣服。
白天,这里的水不能直接挑回家食用。空空的水缸自然会驱使人们去把水面上的星星月亮挑回来,即使是漆黑的夜也得去。小鱼小虾溜进瓢,跃入桶,将一缸水弄出腥气。半个月水缸得清洗一次。父亲晚上回家,朝水缸里瞅一眼,二话不说就去挑水。我不用解释自己不是偷懒而是河里没水可挑,乖乖地提着马灯走在父亲身旁,给他照亮,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向那个河湾。河湾处有一盏灯扑闪着,远远的传来水欢畅地进入木桶的声音。河湾又亮起一盏灯,我手上的灯。
父亲用瓢舀水的时候,我说可以直接将桶摁入水中,向上一提就有半桶水,可以省力省时。父亲没有那样做,他认为将桶摁入水里必然发生搅动,离开水面沉淀物会泛上来,把水弄脏。这样,别人会骂我们。父亲一瓢一瓢地舀,舀满了两只桶,他站起来,从我手上接过扁担。他执意要亲自挑,我实在拗不过他,就像我拗不过老天爷一样。
还是来说那天下午的事吧,我在干干净净的阳光下沿河道行走,走向河湾。在我之前已有人挖了一个比较大的沙井,我接连几天让桶加入嘈杂的队伍寂寞等待。我从人们身体的缝隙中看去,欣赏不同颜色的瓢在沙井之上舞动,耳旁是人们对井水的夸赞。季节的寒意在加重,而井水却一天比一天温暖。此言不虚,我将瓢插入井中,手接触到了水的肌肤,让人感动的温度停留指间。需要感动的人,催促正在感动的我动作快一点儿。
我将铁锹挖下去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刷地射过来。有人出面反对,不允许我破坏泉眼。我的第二锹代表我不相信他们所言这里只能存在一口井。可我还没有挖第三锹,一个人抡着扁担冲了过来,我赶紧扔下了锹。我只得服输地坐在木桶旁,搓着手上的沙子,一边观察一位姑娘洗衣服——她是我的同学。我竟忘了挪动身子,结果有人插队将桶放在了我的桶的前头,我后面的一个人向他的桶里悄悄扔进了一把沙子。
早晨起床,揉着惺忪的眼睛,打着哈欠,想起昨天回答母亲的话,妈,水缸里还有水,明天再挑吧。父亲很晚回家再没有力气去挑水,第二天他在用水的时候即使发现水缸已见底也没工夫去挑水。我皱着眉头走到屋后,突然产生了幻觉一般,只见河水滔滔,将所有的沙井淹没了。这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比我起得早的母亲,没有到我的床头叮嘱我去挑水。
草 须
只有铁耙知道草须的坚韧;拔草须的手在凛冽的寒风中也炼成了铁耙。实际上手和铁耙很像,铁耙的齿和手的指头达成了兄弟般的默契,铁耙挖着紧抓草须的泥土,手指插向草须,拎起来,抖掉上面的土碴,扔到一旁。
摊开在鹅卵石上晾晒的草须,散发药草的气味,把冬天的河滩弄得病恹恹的,时而又有些亢奋。云彩压得很低,雨雪随时都会降下来。草须或许曾进入某个乡间郎中的方剂,但它们不是药草,铁耙和十指还没有盲目到目不识草的地步,尽管无知于艰辛生活的背景。草须只是一种做饭的柴火,并且是最差的一种柴火,依赖于用最差的柴火将饭菜做熟,将水烧开,可见居民日常的能源已濒临枯竭。
铁耙在几个哥哥之间传递,有一年传到了我的手上,说明我的手骨可以打成铁耙了。在这之前,哥哥在前头挖草须,我跟在他身后拔草须。他常常扭头很不高兴地说,快一点儿,有气无力的,没吃饭啊!饭是吃了,但没吃饱。我懒得回答他。我遇到了一丛没有被铁耙挖动的草须,我便生铁耙的气,并跟草须较量上了,双手刨土,拔草,再刨,再拔。将早餐的食物育出的力气用完了也没有拔起草须。哥哥见我与他落了一段距离,跑过来,瞪了我一眼,铁耙的五根尖齿闪着锋利的银色光芒。
我的手从草须的根部抽出,感觉火辣辣的疼,血冲开沾在指头的泥土,流出来。哥哥看了一眼没当回事,我也没当回事。干活磨破手上皮肉流血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逼视咬我手指的草须。这时候,愧疚的铁耙涌出一股我为报仇的怒气,它在我哥哥的吼叫声中,重重地挖向草须的根部,然后向上一撬,草须颤抖了几下,露出败迹。我冲上前,很轻松地将它拔了出来。
铁耙传到我手上时,它已经掌握我拔草的能耐,因而它的力度控制得非常好。我自己挖自己拔。弟弟养得娇,我指挥不了他,也就不指望他。我现在跟铁耙的关系,是任何人也离间不了的。相较于他人的铁耙,它的确不算好铁耙,五齿的长度和间距都不太理想,它容易被那些顽强的草须绊住,堵塞齿隙,挖向地上被弹回,深入不了土层。他人的铁耙发现我的铁耙的拙劣,就有了欺负之意,把应该属于它的位置强占过去。我叫铁耙守着一丛草须,自己跑上前夺下他人的铁耙。我说,这是我的地盘,你凭什么来挖?对方说,这是公家的地盘,谁都可以挖!
我似乎听到了我的铁耙的叫唤,便回到它的身旁,拿起它使劲地挖。突然遇到了类似树根的东西,铁耙被卡住了,我弄了半天也拔不出来。我垂头丧气,盯着它发呆。这时候,一只只铁耙都在嘲笑我的铁耙无能,挖草须的声音在河堤之下的河床上回荡,风吹不散。我的目光回避着那一只只得意的铁耙,望着枯草萋萋的河堤的坡面。河堤上的草是挖不得的,谁挖它谁就是破坏水利。铁耙的品质有好有坏,但它们都坚守着一个底线,可以在河床上肆意争抢草须,而不打堤草的主意。河床上的草,是河堤上的草蔓延过来的,由于土质比较松,秋水退潮之后,很快就长出了一片草,但很快又在秋霜和寒风中枯黄。河堤上的草就叫草,河床上的草根须长,所以叫它草须。
一只铁耙的停滞,意味着其它铁耙会有更多的收获,在家家需要越冬柴火的小镇,铁耙的忙碌与竞争空前的高涨。就在我的铁耙告诉我无法将它从树根的牙口中拔出,让我赶快回家搬兵时,一只铁耙的身影投了过来,它将我的被困的铁耙的四周的土挖开了,挖出一个坑,我的铁耙终于露了出来,它果真挖在盘结的树根上,挖破了其中的一根,深深地扎在里面,却被其它树根死死缠住,不能离开。
我感谢主动来帮我的人,并有些不好意思。他不仅费了很大的力气,额头上汗珠滚滚,并且他会因帮我而耽误挖草须。后一点更重要。我决定用草须回报他。他说,你先不要说用草须来感谢我,我们得把铁耙取出来。于是,我跟他并肩一起使力,“啪”的一声,铁耙取出来了,可是却断了一根耙齿。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天空暗了,河床在转动。我回家怎么交待?我家只有这只铁耙啊!帮我的人穿上外套,看了一眼断齿的铁耙,转身走了。他的铁耙在他的肩头冲我露齿笑个不停。
缺了一个齿的铁耙,始终是我的一个伤痛,我对它补偿的方式,是用手指头更加卖力地拔草须,拔不动时也不怨怪铁耙没有尽责。我把手指头打造成了锋利无比的铁耙,收获的草须也就不比别人少。这一点得到了父母的肯定。母亲在灶口恨不得掘地三尺,却找不到一种可用来当柴火的可燃物,她急得团团转,眼看就要煮成一锅夹生饭了,这时我抱着一捆草须放到了她的身边。母亲热泪盈眶。我说,妈,你哭什么?母亲说,烟熏的。没有晒干的草须,烟烟大于火焰,弥漫整个屋子。
父亲把晒干的草须挑回家,堆放在柴房里,并塞满了灶口,他的心情特别好,说就是大雪封门十天半月也不愁了。听见这话,我又拿起铁耙。该在下雪之前再去挖些草须,不是吗?
何诚斌: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历史文化中心研究员。作品散见于《安徽文学》《短篇小说》《小说月刊》《奔流》等。中篇小说《好讼镇》获安徽省江淮文学奖,《线团》等多篇小小说收入漓江出版社年度小小说选本。出版散文集《老儿戏》(当代世界出版社)、《心随万物转》(敦煌文艺出版社),长篇小说《小柏和外星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跳蚤穿上红衣裙》(吉林人民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