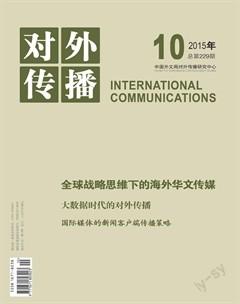外媒阅兵报道议程设置分析与应对
王聪
中国9月3日在北京举行盛大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中国首次以抗战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同日,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本文对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三大外国通讯社从2015年8月3日到9月3日期间关于中国胜利日阅兵的英文稿件进行了内容分析。同时,鉴于新华社英文报道是三大外通社除自采稿件以外,中国新闻最大的消息来源,本文也将外通社部分自采稿件与新华社稿件进行对比,研究外国通讯社对此次阅兵稿件的报道总体倾向和报道角度,为进一步改进和创新国内重大新闻事件的对外报道框架提出建议。
通过调研发现,西方媒体娴熟运用议题设置技巧,为中国的胜利日阅兵报道设定了主题和基调,将公众注意力引入特定话题之内,将阅兵与南海争端、中国军费增长等敏感议题联系,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如果西方公众仅从以上途径获取中国抗战阅兵的相关信息,恐怕很难了解中国举行阅兵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对二战胜利作出的历史贡献,相反会受到外媒这些看似客观报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大外国通讯社的议程设置分析
8月3日至9月3日期间,新华社涉及胜利日阅兵的英文稿件将阅兵本身、其他抗战及二战纪念活动作为稿件主体内容,主题主要涉及阅兵活动预告、阅兵当天的消息及特写、相关英文评论,以及外界对阅兵活动、中国对二战贡献的评价等。另外少部分稿件涉及参阅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北京空气质量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议题,可见新华社对阅兵、其他抗战及二战纪念活动的报道话题分布较为集中,主题突出。
外国通讯社在话题分布方面则相对分散。路透社在8月3日至9月3日期间所发60条涉及阅兵的稿件中,仅有10条将阅兵活动本身作为稿件主题内容,其余稿件主要涉及中外关系、中国经济、两岸关系、中国内政和南海问题等话题。法新社同期发稿70条中,19条将阅兵活动作为主体报道内容,其余稿件主要涉及中外关系、中国经济、南海、北京空气质量等话题。美联社同期发稿56条中有20条将阅兵活动作为主体报道内容,在三大外通社中比例最高,其余稿件主要关注中外关系、中国内政、两岸关系和中国经济话题。可见外媒在报道阅兵、其他抗战及二战纪念活动方面视野更广泛、话题分布更加泛化,在大多数稿件中,阅兵仅仅作为次要主题甚至是新闻延伸背景出现,在近六成的稿件中,阅兵(parade)一词出现的频率不超过3次,涉及阅兵的报道内容在整体占比上也居少位。
值得注意的是,外媒即使在阅兵主题的稿件中,也特别注意引入包括南海问题、中国军费增长,以及所谓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等在内的多个次级议题。
美联社8月23日发表了题为China rehearses for
military parade with fighter jets, troops from Russia, Cuba(来自俄罗斯等国的战斗机和军队参加了中国阅兵彩排)的报道,显示出了外媒对中国阅兵活动的一种复杂,甚至矛盾的角度。一方面,文章承认中国阅兵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又影射中国向邻国,尤其在领土争端方面显示强硬立场。文章称:“在中国对东海及南海领土宣称主权之际,9月3日的阅兵将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称此次阅兵目的在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并展现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政府表达了对北京在领土争端中强硬姿态的担忧。这也使得外国军队参加此次阅兵,在政治上的气氛很紧张。”
法新社则在题为China cuts military manpower, but showcases strength at WWII parade(中国在二战阅兵中宣布裁军的同时展示军事实力)的滚动报道中连续将“Very nationalistic”(极度民族主义)作为滚动报道结尾的小标题,并引用西方专家的话,将出席中国阅兵式的“海外参与度不高”(limited international guest list)的原因归结于阅兵本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nationalistic and militaristic)倾向。相比之下,习近平主席在阅兵前的抗战胜利纪念大会上宣布的30万裁军的消息,虽然被法新社放在标题和导语显要位置,却在下文被解读为中国军队发展向海军和空军方面倾斜,以及解放军提升军队效率的手段,丝毫没有与纪念大会“和平”的主题挂钩。
美联社9月3日的阅兵全景式报道China marks
Japan WWII defeat, shows rising power in parade(中国纪念抗战胜利,阅兵展示力量崛起)同样将阅兵与国内一股“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a prickly strain of nationalism)挂钩,称“这种情绪在国内非常流行,然而它也让海外对中国新的军事实力的使用心生疑虑,中国一直以来希望将自己推销成一个有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形象也因此失分不少”。
此外,三大外通社普遍都在报道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报道阅兵期间北京的交通管制和为改善空气质量而采取的限行措施,强调普通市民当天被勒令禁止靠近阅兵通过区域,并以市民的口吻表达对阅兵花费及庆祝活动带来的生活不便的不满情绪收尾。
法新社更专门采写了一篇题为Tale of two parades as ordinary Chinese barred from display(同一个城市,不同的阅兵:普通市民被严禁现场观看阅兵)的报道,采访了一名名为Hua Yong的异见分子,称当局胁迫其返回700公里以外的老家,只为保证阅兵当天的社会秩序。
综上可见,在重大报道题材方面,外媒通常不转发新华社英文稿件,而是更倾向于自主采访,以将新闻事件纳入自身议题设置范畴,通过对事实的精心选择和排列组合,选择性地添加新闻背景,用大量诱导式的语言,在“自然而然”和“潜移默化”中流露出倾向性,实现其各自的宣传意图。
显然,接触这些外媒报道的西方读者对本次中国阅兵的了解,是在这些主流外国通讯社“提示”下进行的,因此,外通社的报道内容设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范围内受众对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对二战胜利的历史贡献的正确认识。
新华社的舆论应对和主动出击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不仅应是“信息源”,也应是“引导源”。
具体来说,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外媒在议题设置方面争夺主动权。
1.针对外界关切,密集发声,有力回应。针对海外质疑我阅兵意在秀肌肉、海外参与度不高等议题,单独播发有针对性的澄清性消息和言论稿件,回应外界关切。新华社对外部在本次阅兵报道中播发的《中国展示的武器显示了防御战略》《来宾名单显示中国阅兵是覆盖面最大的二战纪念活动之一》便属此列。
2.突出独家解读和背景分析。增加新闻报道内容的独家性,“逼迫”外媒不得不转发新华社稿件,同样是可以帮助夺回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信息时代,新闻信息的获取已经不是专业人士的专利,想要得到独家消息,需要在新闻线索和线人发掘方面下苦功。
另一种更可靠的办法是,在同一新闻事件报道中,采取独家的报道角度及观点。新华社对外部本次阅兵报道中的一条关于阅兵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首次以作战体系模块化编组的小稿子里,就引用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的话——“此举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军队按照实战化标准训练的理念,展示了我军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正是这句看似普通的引语被路透社9月3日当天的阅兵报道连续滚动转载6次,成为当天少见的有外媒转载的英文稿件。
3.寻找新出口、直达终端受众。无论是回应外界关注,还是发掘独家内容,如果新华社稿件落地仍然需要外通社作为中转站,那么在议程设置和影响国际舆论方面始终有可能会受制于人。单一落点的弊端在战役性报道中尤其明显,不少精心策划的稿件由于外媒的选择性忽视和别有用心的截取,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更直接的办法是在新闻报道“最后一公里”中寻找能够直达终端受众的新出口。推特、脸谱等海外社交媒体无疑是此类新出口中的上上之选,是打破“西强我弱”的世界媒体格局的突破口。
在此次阅兵的对外报道中,由于时效突出、内容丰富,新华社阅兵报道迅速成为海外社交媒体关注热点,多条推文被《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截图转发,同时被RT、BreakingNews等媒体大号转推。更重要的是,阅兵直播数十条推文的阅读量高达数百万次,直接抵达海外受众。可见,海外社交媒体作为中国外宣报道的新阵地值得深耕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