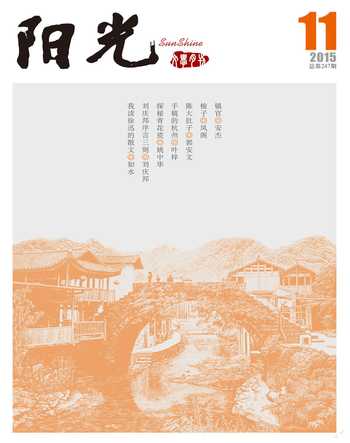刘庆邦序言三则
敢将十指夸针巧
姚喜岱做了二三十年编辑工作,现在仍然在编辑岗位上辛勤劳动。年复一年,经喜岱的手所编发的稿子,恐怕可以用无数来形容。做编辑工作的同时,好在喜岱自己也写了不少稿子。这部《心底映象》作品集,就是他从众多作品中自选出来的。喜岱终于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作为和喜岱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向他致贺!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一说到好的编辑,总愿意把编辑工作与给他人做嫁衣相联系,作比喻,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而我对这种比喻一直有所保留,不愿完全认同。任何比喻都有局限性,这个比喻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它散布的是一种哀怨、自怜和悲观的情绪,仿佛编辑都处在被动和无奈的位置。“为他人做嫁衣裳”,出自南唐诗人秦韬玉《贫女》中的一句诗。整首七律描绘了一位手艺超群、品格清高的穷家女儿形象,她一边为自己嫁不出去伤心发愁,一边还得“苦恨年年压金线”,为富家女儿做嫁衣。这样深究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把编辑和贫女相类比是不合适的。或许有的编辑确有贫女那样的愁苦情绪,但绝大多数编辑并不如此。别人且不说,据我对姚喜岱多年的了解,编辑工作是他的向往,他的追求,他对编辑工作一直很热爱。他把当编辑看成是学习的过程,劳动的过程,享受的过程,也是自我完善的过程。喜岱在一篇文章里就明确说过,当编辑“不是被动的工作,而是创造性的劳动”。
如果用“为他人”和“做嫁衣”不能概括、评价喜岱对编辑工作乐此不疲的态度,以及在编辑岗位上所做出的突出成绩,我更愿意把诗人同一首诗中的另一句诗送给喜岱,那就是:“敢将十指夸针巧。”这真是一句好诗,可惜很多读者把这句神来之笔忽略了。诗的意思是说,小小的绣花针是灵巧的,而穿针引线者的十根手指比绣花针还要灵巧。在人和器的关系上,诗句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明任何高超的技艺都是源自人的心灵。这个意思与我对喜岱的看法是吻合的,喜岱用心对待每一篇稿子,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在这部书里,喜岱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他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些心得,并总结出了“严、密、细、真、实”五字经。在文章中,喜岱结合自己的编辑实践,从五个方面逐一谈了自己的体会。这些体会虽然不是长篇大论,却有理有据,言简意赅,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这样的文章,不仅当编辑的可资借鉴,作者读一读,也会对编辑的心路有所了解,并加深理解编辑工作的甘苦。
喜岱的这部作品集由三个部分辑成,分别为“记人”、“记事”和“记怀”。“记人”里所收录的作品,我以前几乎都读过。我在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的时候,设计过一个栏目,叫“煤海英才”,为煤炭战线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立传。这些人物包括煤矿先躯、劳动英雄、共和国煤炭部的部长、科技专家和文学艺术家等,每位人物一个版。这个版由喜岱负责编辑。陆续推出一系列英才人物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想把这些人物的事迹结集成书。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的想法未能实现。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有些英才人物是喜岱采写的,他在本书中收录了进来。其中有抗日英雄节振国,煤矿泰斗孙越崎,从延安成长起来的著名作曲家刘炽,全国闻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邓玉华,独具风采的煤矿诗人秦岭,如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节目主持人瞿弦和,等等。每个人物都写得细节丰沛,情感饱满,生动感人,既有励志作用,也有史料价值。
在“记事”一辑里,我读到喜岱所采写的一些关于煤矿事故的通讯,还有骗官大案的庭审纪实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写实风格和文学色彩,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破碎,还结结实实地存在着。在安全生产的力度不断加强,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这些作品仍不失警醒意义。
“记怀”里的大部分作品,我是第一次读到。这些作品是喜岱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写自己的身世和对人生的一些感悟。我和喜岱同岁,我们都经历过“十年动乱”,都下过矿井,当过矿工,有着差不多相同的经历。读喜岱的这些作品,让我感同身受,并引发起对往事的一些回忆。我甚至觉得,喜岱的煤矿生活资源比我还要丰富,值得很好的挖掘。比如他的老矿工岳父及其七个子女的命运,就是一部书的素材。如果不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至少可以写成一部中篇小说或长篇散文。
如果喜岱不打算写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就不说了,要是打算写的话,我给他的主要建议是,一定要放松,要有一个自由的心态。编辑工作做久了,容易专注于字句,写东西容易手紧。而手一紧,文章就紧,就失去了力度。任何自然、优美、有力度的文艺作品,都是在放开手脚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不知喜岱兄以为然否?
内在生活
近日集中读了萧习华新的散文集《水流云在》,我来谈一点粗浅的感想。
人类世界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参与建设物质世界的人比较多,而参与建设精神世界的人相对少一些。与两个世界相对应,人类的日常生活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生活,另一种是内在生活。外在的生活对每个人来说几乎具有强制性,只要我们还生存着,外在的生活就必须日复一日地进行。相比之下,内在的生活有一些选择性,像选题作文一样。你选了这个题目,做一做当然好。你不做这个题目呢,也不会影响生存。
所谓外在生活,就是物质生活,客观生活,表面性的生活。内在生活呢,就是精神生活,主观生活,发生在心灵时间和心灵空间里的生活。过外在的生活容易些,在惯性的作用下,人们每天的外在生活不知不觉就开始了。过内在的生活就不那么容易,不是谁想过就能过的。有人知道内在生活挺不错,也想过一过内在的生活,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外在生活挤占了,以致无暇静下心来过内在的生活。比如一些企业管理干部,持续不断的管理工作常常使他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一旦放松下来,他们还是愿意选择外在的娱乐性生活,以调整自己的身心。萧习华不是这样,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做煤矿企业的管理工作,从基层做到中层,又从中层做到了高层。在做好外在的管理工作之余,他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始终没有放弃内在的生活。进入内在生活领域需要一个抓手,一个途径。笔就是他的抓手,写作就是他的途径。他写诗歌,写散文,写报告文学,还写小说,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绩。这部散文集就是他心灵生活的最新成果,内心世界的最新呈现。
这部《水流云在》由三辑组成,分别为“长河帆影”“山水琴音”和“煤乡风雪”,写故土情怀、游历感悟和矿山风云。习华的生活底蕴丰厚,写作态度诚恳,文字朴实而富有诗性,每个小辑里收录的作品都很好读。在今年端午节放假期间,我每天都在读习华的作品。“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有习华的作品陪伴着我,使我度过了一个充实的节日。我18岁到矿上当工人,自以为当矿工比较早,对煤矿生活也比较熟悉。看了习华写矿工生活的散文,我知道他17岁那年就下井当上了一名采煤工,煤矿生活的经历比我还要丰富。我写了大量矿山题材的作品,对矿山环境的描述多停留在我所熟悉的中原或北方煤矿。习华长期在四川的煤矿工作、生活,他写的一些川地煤矿的细节我从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比如《一壁坟茔山河在》这篇散文里写到的威远煤矿,是1940年始建,孙越崎为第一任矿长。大饥荒时期的1960年产煤量最高,达98.89万吨。也就在这一年,全矿工亡矿工41人。矿工死后,家人在附近的崖壁上面凿一方孔,放入骨灰盒,孔口置一块小小墓碑,碑上刻有逝者的名字和简单铭文,以志纪念。墓室数百上千,纵横排列,井然有序,让人肃然,震撼!如今完成使命的威远煤矿已经关闭,可坚守在崖壁上的矿工没有离开,他们还对煤矿久久地凝望着,直至永远。
让我为之感动的还有习华写亲人的一些篇章。《飞扬的红盖头》写的是他的祖母,《父亲的冬日》和《父亲不说话》写的是他的父亲。我历来看重写亲人的散文,甚至把此类散文看作判断一个作家文品和人品的试金石。我看出来了,习华是怀着深切的感恩之心,饱蘸着情感的泪水,在抒写这些不得不写的散文。也可以说,习华的这类泣血之作,也是立碑之作,他在用自己的文章为亲人立碑。
有一年春天,《中国煤炭报》的记者们在四川都江堰煤矿工人疗养院开会。会议后程,记者们都到九寨沟观光去了,我留在疗养院里写小说。某日下午在奔腾不息的岷江边散步,我看见一位脸上留有煤瘢的老矿工在开荒种高粱,就上前与他攀谈了一会儿。攀谈中得知,老矿工种高粱不是为了自家吃,而是用于喂鸽子。他喜欢看一群鸽子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老矿工的话让我想到,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种高粱的体力劳动是一种外在生活的话,那么,他在种高粱过程中对于鸽群在天空中飞翔的美好想象,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同样的道理,萧习华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也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互相滋润,互相促进。也就是说,他的繁忙的外在生活,不但不会让他放弃内在生活,只会给他的内在生活增添更多的素材。而内在生活的持久修炼,会使他的内心更丰富,情感更饱满,为人更真诚,工作更勤勉,人格更完善。
历史性的成果
不可否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来自煤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煤矿遍地开花,煤炭产量以翻番再翻番的方式叠加增长。因当初的采矿还主要依赖密集性的人工劳动,在煤炭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煤矿工人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形成一支战斗在地层深处的、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让人始料不及的是,煤矿不仅出产煤炭产品,还自发地生长出一批书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他们创作的闪耀着乌金之光的作品,频频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亮点。
当然,从业队伍的扩大,煤炭产量的增加,与作家的生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好比物质的富裕并不一定催生精神的丰富,前者和后者不会成正比。可后来矿工群族成分的构成,一改过去大都是文盲的状况,的确加入了一些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知识青年。这些青年不满足于物质生活,还热爱精神生活;不仅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也不甘平庸。他们拿起笔来,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渐渐地,他们成了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他们的作品走向了全国,有的还走向了世界。不管是从全世界的范围内考察,还是与中国煤矿文学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比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煤矿涌现的作家是最多的,煤矿文学作品的繁荣也是前所未有的。别的不说,仅从六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和一届全国煤矿长篇小说“乌金奖”的获奖作品来看,说蔚为大观恐怕一点都不为过。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骄傲的宣称,中国作家所写的矿工生活的小说,并不比左拉、劳伦斯、戈尔巴托夫等外国作家写的有关矿工生活的小说差。
不过回顾起来,我们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煤矿文学的评论相对有些薄弱,未能与文学创作并驾齐驱。虽说也有一些不乏热情的评论,但由于评论者的视野、学养、理论资源、语言存量以及天赋所限,所写的评论只是粗浅的、随机性的零打碎敲,既没有形成系统,也没积成规模。有的评论视角甚至仅仅停留在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层面,与文学评论所需的专业艺术水准相差甚远,只能让作者和读者哑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相辅相成,如果二者结合得好,配合得好,可以互相激发,互相滋养,互相提升,收到比翼双飞的效果。而煤矿文学创作和评论一头沉一头轻的状态,显然是不平衡的,对双方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煤矿作家协会早就注意到了评论跟不上创作的问题,我也曾提议专门召开了一次加强文学评论工作的座谈会,意在组织和团结煤矿的评论队伍,提振一下评论作者的积极性,并动员更多的作者投入评论写作。不能说我们的努力一点效果都没有,实在说来,收效甚微。然而煤矿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仍保持着不错的势头,不断有作品和作家出现。在新兴媒体风起云涌的今天,作家写出了作品,总是希望得到评论界的关注,以推介给读者,实现其作品的文本价值。作品出版后,他们满怀希望,像是打开了信息接收器,随时准备接收作品的反响。可他们东瞅瞅,西望望,石头是石头,大海是大海,石头沉到大海里,没得到什么动静。时间一长,他们就失望了。
希望重新燃起,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史修永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那里成立了一个中国煤矿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中心,由他主持当代中国煤矿文学的研究工作,希望得到我的支持和配合。我一听就觉得很好,“众里寻他千百度”,心情不禁有些兴奋。研究煤矿文学,本来应该是煤矿作家协会份内的事,煤矿作家协会的前身也的确叫过中国煤矿文学研究会,但由于人才、钱财、精力专注和学术氛围的缺乏,这项工作一直未能很好的开展起来,更不要说深入下去。而在中国煤矿的最高学府中国矿业学院成立煤矿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心,那是再合适不过,不论是人才的优势,经费的支持,专业水平的保证,还是信息的采集,现代手段的运用,都让人有理由对他们的研究充满期待。我一再向史修永表示祝贺,并祝愿他们的研究咬定青山,持之以恒,早出成果。
如今成果出来了,史修永的这部《多维视角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就是一份结实厚重的成果。我以前曾多次为煤矿和煤矿以外的作家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写过序,还从没有为一部文学评论集写过序。我知道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学养不足,理论水平和抽象概括能力都不高,生怕说不到点子上。可这次我还是鼓足勇气,把为这部书写序的责任承担下来。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不要怕,学无止境。写序之前必先读史修永这部书,把读书的过程当成一次学习的过程就是了。不是我谦虚,通过阅读史修永的这部书稿,我的确得到了不少启示,学到了不少东西。史修永以宏阔的思路,远大的目光,真诚的情怀,通过大量阅读、分析、归纳描述矿工生活的文学作品,勾画确立了煤矿文学的版图。他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着力,把煤矿文学的版图放在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版图中加以考察,找到了煤矿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并发掘出煤矿文学特殊的生长环境、不同的精神文化诉求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证明煤矿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应有的正视、认可和尊重,给丰富多彩的煤矿文学以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赋于煤矿文学以文学史意义。史修永改变了过去对煤矿文学的评论多停留在感性层面的做法,他一上来就以理性、学术、科学的态度,系统地探索煤矿文学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深刻的生命意蕴,无疑,史修永的这部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代煤矿小说研究的一项学术空白。
史修永不像有的评论家那样,从外国的文学理论中拿来一个模具,将中国的作品往模具里装,把作品变成随处可以变形的填充物。史修永的研究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充分尊重每一位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创作个性,阐释的是作品的题中之义。他不仅评论单部作品,难得的是,他还把几部作品放在一起,找出作品的共性,从而捆绑式地挖掘出煤矿文学的独特性。比如他以《沉沦的土地》《红煤》《富矿》等小说为研究对象,所撰写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中国当代煤矿小说》,论述了煤矿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并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此论文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以“环境、主体与科技”为主题的第四届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并被收入由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
史修永在本书的后记里写道:“这只是一个开始……其中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不断拓展。”这是我愿意看到的话。不难预见,史修永和他的研究团队会善始善成,修史修永,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八部,译成外文作品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四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 《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和长篇小说《红煤》分别获第四届、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首届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