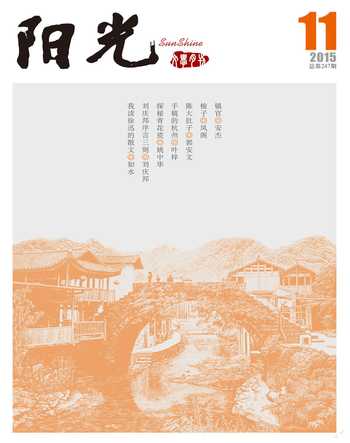孬子的老屋
我的对于童年满满当当的记忆,都与葛家老屋有关。老屋的惶惶光景里,盛满了我最温情最柔软的念想。
我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不!是他们把我丢在这里。他们像对待弃婴一样,把我连同老屋一起抛下了。我已经是一个鹑衣百结,茕茕孑立的老者,被爱遗忘,被烟火陈旧。我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又像脱了粒的稻壳,更像一个找不到坟茔的孤魂。我在与我同样形销骨立、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屋里,整日的漂移、游荡、趔趄。
是的,他们都走了,都走了……
他们只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他们看我时不用眼珠子,而只用眼梢子乜我。
他们都叫我孬子。
我有一个充满稠腻的暖意的童年。童年里,有一个不苟言笑的祖母。我的祖母像一片被日子漂得茎梗分明的茶叶。我没有母亲。
在我八岁的记忆里,有一条瘦硬魆黑的小路。小路长长窄窄,曲曲弯弯。它是老屋的脐带,也是我全部记忆的脐带。它一直躺在我的记忆里,就像延伸在暖春的蕊处,那么柔软与温润,那么绵长与缱绻。
而我的对于泥土的敬畏,就来自这条脐带。是的,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从泥土中来,还要回到泥土中去。
我说过,小路是窄窄弯弯的。其实,它可以不必这样憔悴与孑弱,它可以宽宽扁扁、大大方方,当然,如果没有那些坟茔的话。
我好像还说过,我没有母亲。没有母亲的孩子常常会忘了天黑是要回家的。
当溏心儿蛋黄似的夕阳回到山那边的家时,暮色把一切都慢慢地消融吞没,慢慢地把一切都吃深吃透。哦,我忘了说了,我有一双灵异的眼睛。当夜泼漆一般把一切都洇入黑暗,我的灵异的眼睛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物件。子喜和子禄在他们母亲的叫魂声中仓皇逃回家中,独我像没有灌浆的空壳,在沟渠野地里流连忘返,在老鸹窝的树下游弋晃荡。可是,我那脸上注满忧郁和皲裂般皱纹的祖母,总有办法将我找到。
祖母爱怜地抚摸我,从额头到脸颊,都要抚摸一遍。我倔强地将头歪向一边,我在躲避祖母的手。她的手粗糙,像小刀片。祖母用她的刀片把我的脸颊过了一遍后,总要顺手拧我的鼻子,把我的鼻涕和涎水擦到树上。她弄疼我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树上有一双阴鸷的眼睛,一只老鸹蹲在树上,它在看着我,一动也不动。都暖了那么多天了,它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呢?
因为不断地冒出三两冢坟茔,小路显得特别瘦弱、拥挤。我一个箭步,接连从好几冢坟茔上跳过。哈!我跑到祖母的前面了。
祖母突然大惊失色,她惊悚地看着我,一激灵,丢下我,踅回到那些坟茔的前面,低着头,双手合十,我听见她对着光秃秃的坟茔喃喃自语:地下公,地下婆,莫怪哦,我孙子小,不懂事,莫怪哦,莫怪,莫怪……
她对着我跳过的那些坟茔,一个一个地说,低声地说,怕扰了地下安睡的灵魂似的。她颤栗着身体,然后自顾自走了,丢下我愣在那儿,再不肯理我。
我抬头,只见月影诡谲,一股从未有过的忌惮马上堰塞了我的喉咙,潴在了胸口。再看祖母,浓郁的夜色已经将她的背影吞噬……
我对母亲的记忆与水有关。
不管你信不信,我清楚地记得我出生时候的事。母亲肚子里的水好大啊。洪水滔滔,波涛汹涌,恶浪滔天……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母亲肚子里的水。而我的颈部被一根绳子箍得很牢,我在水里像鱼一样地游弋,可我一点儿都不像鱼那样的优雅。我不断地游啊,游啊,我极力想摆脱我颈上的绳子,我太想早日游到岸上,于是我双脚不停地蹬啊,蹬啊……终于我上岸了,却把母亲给蹬到山上了。
我看到过我的母亲。我说过,我有一双灵异的眼睛,我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物件。不知为什么,她从不看我。她老是重复一种动作,她在不断地找地方脱裤子,眸子里有一种深深的急切……
母亲的眸子好明亮啊,精致饱满,棱角分明,像月光下的清泉在汩汩流淌,丢一粒石子进去,月亮在泉水里闪着影影绰绰的光呢。
老屋也有这样的眸子。老屋的眸子晶莹剔透,闪亮清澈,像母亲。
我说的是老屋的水。
老屋怎能没有水呢?如果没有水,我无法想像老屋的样子。那一定是混浊、蜷缩、龌龊而萎靡不振的吧!那一定像被炕煳的烟叶,还像被榨干的油渣吧!
因为有水的滋养,我的老屋像一个注满相思、铅华洗净的少妇,饱满充盈而又温情缱绻。
门口的月牙塘是父亲的烙伤。
我虽然没有母亲,却有一个身体硬朗、模样周正、沉默寡言的父亲。我家的物件都像祖母一样,上了年纪。我记得有一张竹床,两头已经破了几个小洞,床面和四周已经被一种叫光阴的东西磨得哧溜溜的,闪着黑亮黑亮的光。这竹床是父亲的最爱。夏天的夜晚,父亲总是将竹床早早搬到月牙塘边,早早地占据那棵得三人合抱的柳树下面的风水宝地。男人女人田间地头、乡野村事的,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父亲却蹙着眉,沉默地叹气,轻轻地,好像怕捅破了透明的空气,又好像怕触碎了稚嫩的蛹。可是我却能听得见。我不仅有一双灵异的眼睛,我还有一双灵异的耳朵。星星也一定听见了,我看见有一颗星星因为不忍再听父亲的叹息,欻——的一声划过星空,落到那遥远的天际去了。柳绦儿好像无动于衷,她们低垂着头,只顾与塘水调情,与鱼儿接吻。风是她们的情人,风一来,她们就媚态百生,婀娜腰肢,犹如小姑的长裙摇曳。
我忘了说,我还有祖父,只是他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另娶了一个年轻女人,生下了像柳绦一样多愁善感的小姑。
小姑拖曳着长裙,在柳树下望着月牙塘发呆。小姑有柳叶一般的眉,有月牙塘一般的眸。
我走近她,我想对她说,你真美。
走开!你这孬子!小姑丢下恶恶的眼神,离开了——别走呀!我不是孬子,我只是想对你说,小姑,你真美!
唉……父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声。父亲的哀伤消融在如母亲眸子一般的月牙塘里。
我始终相信母亲一定能懂父亲的哀伤,不然的话,母亲怎么流下了那么多的泪呢?你看,我母亲的泪水都已经汇聚成一条小溪,从老屋中间穿过,从我家灶台边淌过。
祖母颠着小脚,撅着干瘪的屁股把一把柴火塞进灶膛,一边不慌不忙地转身到小溪里洗净葱蒜。
父亲蹲在小溪边刷牙,洗脸,对着溪水抚摸胡子拉碴的下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子福的祖父教一句,子福就跟着念一句。父亲缩回头脸。
父亲踯躅着,将蹅满泥巴的脚探进溪水。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子福又念了。父亲有点儿不好意思,脚蹅在溪水里,进退不得的样子。
我对母亲的记忆只能到这儿了。多少年后,每每回忆这般光景,总会让我掩面长泣,我只能任由泪水从指缝间细细地流出来……我想母亲的时候,就去给她培土。我相信母亲一定能听懂我的话,她不会骂我孬子。我的泪水虽然不及母亲的多,但也一定能盛满她的手窝吧。
关于母亲,我不忍再说。
老屋是有灵魂的。堂轩就是老屋的灵魂。
子荷的祖父在堂轩前面的场地边种了一片白里包着黄蕊的茴香花,她的母亲在蚕豆里加上茴香、桂皮、黄酒和盐,先大火煮开,又用小火烹一个钟头。子荷的袋子里常常装着一把这样的茴香豆。她坐在堂轩大门靠右边的石凳上。她只坐右边的那个石凳。她一粒一粒地往嘴里丢茴香豆。
其时我的祖母整日里围着锅台打转。她琢磨着怎样用糯米粉炸成各式点心用以讨好已经成为公家人的祖父。元宵果、麻球、麻花,她天不亮就起床,将这些黄灿灿、香喷喷的家伙装在竹篮里,让我在天上刚刚露出熹微之色时送给祖父。小祖宗,你走快点儿嗨,你别让那个女人看见了嗨。见到他,你就说,家里没钱捉猪秧子了嗨……
祖父是一个公家单位的伙夫,我记得见到祖父的时候,他已经烧开了一大锅水。他见到我,将祖母半夜为他炸的那一篮的家伙轻轻地丢在一边,在氤氲的热气中拿过一个火柴盒,从里面窸窸窣窣的擒出两毛钱。快走,快走,去买点儿炮仗放。他竟不问问我一个八岁的孩子,一个人是怎么过的河,才没让那些黄灿灿的家伙被水濡湿。他怎么就不问一句呢……
我果真去买了炮仗。我一路放着炮仗,放完了,我也就到家了。
子荷往嘴里丢茴香豆,那样的清香诱惑了我,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和她交换。子荷有一对黑溜溜的眸子,小鼻尖上滚着一颗晶莹的汗珠。她是一颗青涩的果,又像暖春后瓜园里趟出来的瓜楞儿,一触即碎。我坐到左边的石凳上,我装着不看她,我的手插在裤洞里,摩挲着大腿上的肉。我有炮仗哦……子荷不看我。咚咚锵,咚咚锵,我唱起歌来。孬子,子荷掷下两个字,马尾辫在背后甩得好欢实啊!
我从地上抓起一把沙砾土,我撵到她,像糊腻子一样塞进子荷的嘴……
猪秧子到底还是有了。不过,祖母还没等到猪秧子甩膘的时候,就回去了。她回到了她来的那个地方,她也做地下婆去了。
祖母的那个肩胛骨上还没来得及甩膘的猪秧子,给了老屋人一场饕餮大餐。咚咚锵,咚咚锵,堂轩一连几天热闹非常。
我嘴巴油润润的,腮帮吃得鼓鼓的,眼睛却到处睃个不停。我瞥见我的父亲,突然猥琐下去的父亲,他竟和黑白无常坐在一桌抢肉吃。我摇一摇头,我分明看见父亲正趴在祖母的黑漆棺材上哭号……
我真想戳瞎我的眼睛——凡是被我那双灵异眼睛看到的人都是活不长的。这次,我竟然就这么看走了我最后一个亲人。
父亲出殡那天,我没有一滴眼泪。
可是凌乱的脚步却碾碎了门前的茴香花,茴香花哭得梨花带雨,东倒西歪……
从此后我爱上了睡回笼觉。我睡得涎水直流,睡得又熟又糯,软糯得犹如刚出锅的糍粑。
我再没有糯米汤圆可吃了。这玩意儿我是真的喜欢。搛起,吹一口气,咕咚一声,我能清晰地感知它闯过喉咙,热到心窝……再也吃不上了。
我也没有能教我读诗的祖父。
子福、子喜、子禄、子荷,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四兄妹。他们还有一个异母哥哥,叫子贵。子贵的母亲早早地就和我的母亲做邻居去了。他们有个满腹诗书的祖父。单听他们的名字,就知道给他们取名的人一定是不简单的。
他们的名字就是他们祖父取的。他们都是我的堂兄妹。
他们的祖父把家道振兴的希望寄托在子福、子喜、子禄身上。他教他们认识堂轩大门内墙上的图案。我只知道那墙上有四朵荷花,我在月牙塘里看过的。我忘了说了,我家的堂轩是观察公第十九代孙修耀公所建。
你修耀公可了不得呀!他们的祖父开口就这样对他的孙儿说,好像修耀公是他们一家的修耀公!
你们看嗨,他指着堂轩大门上的马头墙的内墙,对着他的三个未来大学生孙儿说,那墙全是水磨青砖镶嵌,正中是“观察流芳”四个字。观察公是我们潜山葛氏的始祖,晓得了不?
他们的祖父眼里满含热望,把能给他光耀门庭的三个孙儿望成了熟玉米,望成了三个红火球。
你们再看嗨,两边还有文武加官进爵的砖像,修耀公会护佑你们的嗨。再看中间的那一排凸出的阳雕,打鱼、担柴、耕田、读书,那是“渔樵耕读” 的意思嗨。往两边看哈,燕子衔泥、大象驼瓶(太平)、喜鹊钻梅,跟着是梅花鹿与仙鹤,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嗨?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们家族给你们的希望嗨,它们分别代表贵、福、喜、禄、寿嗨。子贵和子荷是指望不上了,就看你们仨了嗨……
“氏本葛天传上古,籍从观察宦舒洲。”当我坐在千节虫一般的水车上,跟着他们的祖父摇头晃脑的时候,他们就指着墙上的字,那是我们的名字,瞧,我们的名字在墙上!贵福喜禄寿,子贵、子福、子喜、子禄、子荷。你不行的吧?
我好想我的名字也能嵌在墙上。
我眼睛湿润了。我感觉口干舌燥,心房像有油锤在一下一下地夯……我一甩头,甩掉了不争气的眼泪,我看见了一撇从窗外洇入的阳光,照在中堂“齿德兼优”的匾额上。我一口气穿过前堂的十根大木柱,追着那一撇阳光。我惊奇地发现,等我跑到中堂,那一撇阳光又洇满了上堂轩的“乡评善行”的匾额……
老屋是有灵魂的。堂轩就是老屋的灵魂。
关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繁华落尽,热闹消弭……都走了,全体都走了。
都走吧,永远也别回来!就是回来,也不要咔嚓咔嚓个不停,我讨厌那方方正正的一闪一闪的橡皮擦一般的盒子。它们是能摄走人的魂灵的!
我一撇一捺地踉跄在老屋空旷的四周。
老屋被抽筋剔骨,被扒得赤身裸体,灵魂再也找不到躯壳,看不到一撇灯火……
堂轩摇摇晃晃,风雨中,它像一块被扯烂的酒幌子,被撕扯着,被推搡着……
但还有一撇漂移的影子。
那就是我。
他们说我是孬子,留下来的都是孬子!
葛良琴:女。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现在某中学任教。已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若干篇。散文《老屋里的三个女人》曾收入黄山书社出版的散文集《回望乡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