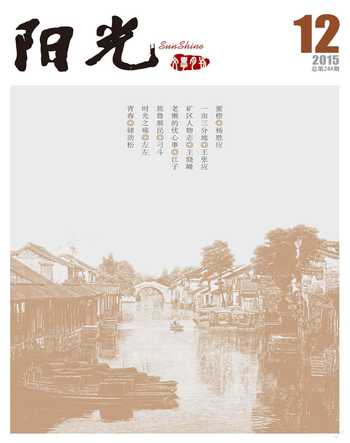相得益彰的成功合作
白丁
开篇的话
我一直认为,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在他的创作中应当占有重要位置,这篇中篇小说可以说是他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趣,更体现了他对底层民众特别是矿工群体的关注。刘庆邦小说的审美情趣和创作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刚劲,一是柔美,前者主要反映在煤矿题材的小说中,后者主要体现在农村题材的小说中。换言之,刚劲风格一般由矿工形象来表现,而柔美风格则大都由那些女性来展示。综观刘庆邦早期创作,大都是煤矿题材,属于刚劲一类,许多故事情节有暴力色彩,人物性格剽悍,情节扣人心弦,叙事也很硬朗。他的成名作《走窑汉》如此,《拉倒》《血性》《玉字》如此,后来写的《神木》和《卧底》也属于这一类,似乎煤矿的生活非用这种风格来表现不可,可以说,他的反映煤矿生活的小说大都从《走窑汉》脱胎而来,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二:一,刘庆邦是从矿井深处走上文坛的作家,他19岁来到煤矿,那炼狱般的生活给了他非常的精神震撼,也给了他不断闪耀的创作灵感。尽管后来他写出了《白煤》那种温和的小说,更有《梅妞放羊》《鞋》《黄花绣》和《女儿家》等充满阴柔之美的小说,但我认为,作家早期的作品更能体现其精神实质。所以,《神木》应该成为刘庆邦小说的代表作。
刘庆邦和李杨不期而遇,小说《神木》变成了电影《盲井》,接着,《盲井》在2003年第53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艺术贡献“银熊奖”,又荣获2003年第2届美国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叙事片奖、2003年第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银奖等十多个奖项。是小说成全了电影,还是电影让小说名声鹊起?在许多人看来,是电影让默默无闻的小说一炮打响,让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一夜成名,像《红高粱》和《暗算》让莫言和麦家连同他们的同名小说名扬四海。勿庸讳言,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在传播上有着小说无可比拟的优势,它的确可以让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大众的青睐,但说到具体作品,情况又很复杂,许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后,都无法保持原著的精神和风格,以致引起作家的不满和批评界的指责,有些作家不希望甚至拒绝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我是在读过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之后去看电影的,给我的感觉并不强烈,或者说,先读小说再看电影不如先看电影再去读小说更好。就连名著改编的电影尚且如此,对其他电影的改编我也并不看好。麦家认为,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他说:“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导演通过修改原著来展现自己的水平,这块硬伤一直存在。”他还认为:“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在多次观看电影《盲井》和阅读小说《神木》之后,我产生了将二者做个比较的想法,我觉得这样做也许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最初的念头还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那篇题为《图像比语言更丰富——兼论第六代导演及李杨的电影〈盲井〉》的文章,是作者杨扬在美国Weber State University 的演讲,载《上海文化》2005年第3期。此文也把小说和电影作了比较,文章写道:
网上有文章说,《盲井》的成功体现了文学对电影的拯救。言下之意,《盲井》的成功要归功于小说《神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李杨的作品在第六代导演作品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故事性很强,这种成熟的叙事方式毫无疑问受到了小说的影响,因为从《盲井》的轮廓看,基本保持了小说原来的面貌。但电影和小说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事实上,在《盲井》拍成电影之前,知道刘庆邦《神木》的人并不多,正是通过《盲井》,很多人知道了小说《神木》。电影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是有很强的话语优势的,一部小说拍成电影放映,可以让这部小说连同作者一起走红,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存在。美国作家佐普写了不少作品,但无人知晓,电影《教父》走红,佐普才成为公众人物。电影的成功有小说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电影自身的价值。
我在电影和小说中来回穿梭,觉得电影《盲井》基本忠实了原作,除了个别地方的增删和改变外,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小说的精神一致,没有使小说走样,也就是说,基本没有“伤害”到原作,并且由于电影艺术的特殊效果,还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感染力,也张扬了小说的神采,随后产生了较大影响,获得了荣誉。但我关心的并不是小说和电影谁沾了谁的光,谁的功劳大,我就是想通过二者的比较,来看看各自的成功与不足。我认为,从小说到电影,应该是刘庆邦和李杨一次相得益彰的成功合作。
关于取舍
《神木》是一篇将近七万字的中篇,详尽地写了两名罪犯的两次犯罪活动,从引诱“点子”上钩到最终将点子杀害,两次的犯罪活动实施的手法基本一致,但是过程却完全不同,结局也不一样,这种重复在小说中能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通过比较,展示了小说(故事)的魅力。详尽的叙述,让读者更能理解作者的意图。特别是小说开篇就提到了罪犯行骗行凶的过程,等于把谜底交待了,欧·亨利式的结局不复存在,还会有悬念吗?这对读者是一个考验,对作家更是一个挑战。在电影里,开始就是清晨出工的情形,也是第一个点子死期的临近。小说可以娓娓道来,但电影的节奏不能拖拉,所以,电影从杀害第一个点子开始是必须的,开头便营造了血腥恐怖的一幕,容易吊起观众的胃口,这也是小说与电影的区别所在。85分钟的时间里要容纳70000字的内容,电影必须做出适当的剪裁。可是,从人物的塑造来看,小说显然要胜过电影一筹。小说中,在两次犯罪活动中有一个间隔,即杀害第一个点子后,他们各自回家过年了。其间,宋金明的心灵经受了折磨,他回顾了自己是如何走上这条道的经过,面对用人头换来的不义之财,特别是看到老婆为他一下子挣了这么多钱而担忧的时候,宋金明也不想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他竟然哭了,暗下决心,从此洗手不干了。同乡赵铁军出去半年没有音讯,过年也没有回来,极有可能被别人当成点子打了闷棍,这也让他产生了罢手的念头。显然,这为他后来救助元凤鸣做了铺垫。在电影里,李杨不会不理解刘庆邦的意图,处处拿唐朝阳的冷漠凶残和宋金明残留的善心做比较,比如宋对自己儿子学习的关心,比如他看见元凤鸣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点子让人难以下手,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前后两个点子是父子关系后,他更是非常震惊,担心绝了人家的后,不得已,他只好拖延计划实施的时间,让那个寻父的孩子尽可能地享受生活的快乐,包括找女人“开壶”,临刑前大吃一顿,以至于最后与同伙同归于尽,也要救那个孩子一命。这些都体现了宋金明身上未泯灭的人性。小说中,宋金明在回家过年期间,借给嫂子四百块钱,让她供儿子读书。他自己一个人悄悄地离开村子,就是不想连累任何乡亲。这些内容显然对阅读小说的读者是很有必要的,一来可以增加对这一人物的理解,二来,在两起剑拔弩张的犯罪活动中,小说的笔触深入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中间这段的插入也起到了缓冲和调节的作用。电影却把两起犯罪活动连在了一起,第一起犯罪的结束就是第二次犯罪的开始。另外,在小说中,第二次引诱点子上钩的时候,罪犯遇到了同行,那人的手法与罪犯张敦厚(即唐朝阳)如出一辙,这一段表面上看是一场虚惊,其实,读者不难看到,使用这种犯罪手段的还大有人在,这便揭示了生活的残酷,危机四伏,不知有多少人跌进了这样的陷阱。但在电影里,这些情节却不得不割爱,无疑是一种缺憾。
电影还增加了一个情节,在集市上,两个罪犯和元凤鸣走散了,到手的点子意外失踪,让两个罪犯非常着急。当然,元凤鸣最终还是找到了。没有想到,他是去为叔叔宋金明买鸡去了。我以为这个情节的增加似无必要。也许是想表现元凤鸣的单纯善良,但多少有些生硬和牵强了。
在电影《盲井》里,两名罪犯在第一次得手后去嫖妓,在昏暗的歌厅里,因为小姐不让宋金明动手动脚,宋金明恼了,理直气壮地去找老板娘,结果又给他换了一个听话的小姐。唱歌的时候,他们唱“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这样的歌词让影片具有了讽刺意味,这些情节其实是当下某些现实的折射。可是后来他们又唱起《社会主义好》那首老歌,并且改了歌词,我以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还有做爱的场景,过于暴露,也是蛇足。
关于细节
小说里有个细节,第一个点子唐朝霞被杀害后,两个罪犯拿到赔偿金,拎着死者的骨灰盒赶往另一个地方。半道上,他们坐下休息,如何处理这个骨灰盒,小说和电影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小说是这样写的:
唐朝阳把唐朝霞的骨灰盒从提包里拿出来了,说:“去你妈的,你的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了,不用再跟着我们了。”他一下子把骨灰盒扔进井口里去了。这个报废的矿井大概相当深,骨灰盒扔下去,半天才传上来一点落底的微响,这一下,这位真名叫元清平的人算是永远消失了,他的冤魂也许千年万年都无人知晓。
这一细节让人震撼。那个叫元清平的男人,被人害死在井下,变成一把骨灰装在盒子里,还是被抛入了报废的深井,而且半天才传上来一点儿落底的微响,引起了读者的悲悯之心。电影里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看到,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两名罪犯从远处走来,一边走一边闲聊着,其中一个人随手将手里的一包东西扔在了一堆垃圾里。这漫不经心的一扔,表现了罪犯对死者的漠视,但如果不留意的话,观众竟不知道他扔下的是什么。这与小说不同,作家在小说里写道:这一下,这位真名叫元清平的人算是永远消失了,他的冤魂也许千年万年都无人知晓。这是作者的声音,无疑是带有感情的一句话,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于不动声色中表达了作者对死者强烈的同情和对罪犯强烈的谴责。电影里却一笔带过了。
电影里有个镜头,元凤鸣被带去“开壶”,接待他的是一个名叫小红的女孩,在小说里,他们那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在电影里,他们却在向家里汇款时在邮局相遇了。我觉得这一细节用得比较好,表现了两个人心地的善良,没有忘记家里的亲人,发了钱,便往家里寄去。他们的钱都是血汗钱,都是拿青春和生命换来的。特别是小红,在经过元凤鸣身边的时候,把手搭在他的肩头,那一摸,以及元凤鸣对她背影的凝望,包含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
此外,电影还增加了一个细节,即元凤鸣床头的美女图。这个细节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像他这个年龄的男孩,产生这个性意识是正常的。再说,这个细节对元凤鸣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有帮助的,后来他和小红的事虽然让他蒙羞,但毕竟还是做成了,美女图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关于结尾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王明君(即宋金明)做了一个假顶,也就是让上面的石头悬空,用一根柱子支撑着,只要把柱子打倒,上面的石头全落下来,就能把人砸死,也就形成了真正的冒顶。他想用这一招把元凤鸣“办”了,并且还告诉了同伙张敦厚(即唐朝阳)。后者不以为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他走到假顶底下,想试试柱子牢不牢,王明君正在假顶下面站着,他警惕地跳了出来,却用镐尖将张敦厚的脑袋扎破,张敦厚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临死前抱住王明君,想把他拖到假顶下面,在这个时候,王明君让元凤鸣来帮他把张敦厚打死,还告诉了元凤鸣,张就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可是元凤鸣不敢上前,王明君只好抡起镐,在张敦厚的头上连砸几下,把他结果了,然后把他拖到假顶下,自己也站在下面,交待元凤鸣,告诉老板,他们是冒顶死的,让他找老板要两万块钱,然后回家,好好读书,哪儿也不要去了。元凤鸣毕竟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没有按照王明君的交待找老板要钱,而是实话实说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就离开了煤矿。
而电影中,是张敦厚在看到王明君迟迟不肯动手的情况下,首先干掉了王明君,正当他向元凤鸣走去的时候,尚未咽气的王明君又把张敦厚干掉了。这里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了内部的一场相互残杀。元凤鸣在老板让他在赔偿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几次拒绝签字,欲言又止(也许他想说出真相),在马大姐的劝说下,才签字领到了赔偿金。这个结尾的改动,与原著有了较大出入。刘庆邦的意思是想突出元凤鸣的单纯,他的这个结尾让小说的悲剧色彩更加浓重了,可是在电影里,元凤鸣却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赔偿金,这一改动虽然安慰了读者的心,却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电影中让两个罪犯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突出的是一种因果报应的主题,而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君身上人性的复苏和闪光。电影对小说结尾的改动,无疑是把人性的较量转化成了两个罪犯的相互残杀,两相比较,当然是小说的结尾更佳,它使主题得到了应有的提升。
可是我又不得不质疑,王明君制造的假顶真的是想杀死元凤鸣吗?小说里语焉不详。王明君在杀死张敦厚以后,选择了同归于尽,难道没有其他更自然合理的选择了吗?比如打倒柱子,制造张敦厚被砸死的假相,这样就可以和元凤鸣一起找老板索要赔偿,一走了之,岂不更好?但是仔细分析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明君在杀了同伙之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与张敦厚之间因元凤鸣的出现发生了冲突,让他们从合作伙伴关系演变成为敌对关系,心力交瘁的他似乎和张敦厚有了一个了断,当时他想的更多的是让元凤鸣能得到一笔赔偿,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生死。或者说,他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从前面提到的过年时他在老婆面前流泪,想洗手不干的情节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心理),他不想再把这种戏演下去了,他就是想一死了之。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许才能给小说的结局一个自圆其说的推断和结论。
关于作者
2009年3月24日下午,刘庆邦携新作《红煤》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在线与网友交流。说到他的小说《神木》改编成电影时他有一段话:“《盲井》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神木》而改编的。《神木》发在2000年《十月》杂志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都转载了这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有的打工者还给《中华文学选刊》寄信,用红布写成条幅,上面写着‘感谢刘庆邦关注底层的打工者,要求选刊选载这篇小说。之后由导演李杨改编成电影,这部电影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最后又在美国、法国、荷兰、香港、台湾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中国矿工的形象已走到国际上去了。”由此可见,小说《神木》在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前就走红了,并非没有多少人知道。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神木》是刘庆邦小说中的精品,即便不被改编成电影,它仍不失为一篇力作。通过电影和小说的比较,我们也可以做出结论,即电影基本忠实原著,绝大部分情节来自小说,包括细节和对话。在网上,我曾搜索到一篇《盲井》观后的文章,作者甚至这样说:当影片结尾才抛出来的“本片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的字样,彻底颠覆片首“编导:李杨”的志得意满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是文学拯救了一个留洋学生拍摄的处女作电影。”而《上海文化》刊登的那篇文章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是电影让小说风靡全球,因为电影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是有很强的话语优势的。其实,我倒认为,电影和小说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载体,作为《盲井》的电影,导演、制片、编剧都成了李杨,整部电影成了“李杨作品”,只是在片尾打上了“本片改编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的一行字,看起来是有些不公。但是,《盲井》毕竟是电影而非小说,它已经成为另一种文学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它是李杨的作品也无可厚非。在说到小说《神木》时,它自然是刘庆邦的作品,与李杨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话又说回来,小说在先,电影在后,没有小说就没有电影,因此,电影作为一种成品,它又不属于李杨一个人,而是与刘庆邦的一次合作。
李杨被称作第六代导演,他1959年出生,后来去德国深造。第六代导演“经历了电影从神圣的艺术走入寻常生活,成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现实过程,所以,他们的观念和作品内容都较前几代导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的影片没有通过制造幻觉的快感向市场妥协,而是更多地关注那些出于禁忌而“不可言说”的社会现实,更显出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真诚。在题材选取上,他们关注当下都市、边缘人物;在叙事策略上,他们常常在剧中人物身上融入自己的经历,或多或少带有自传色彩;在影像风格上,他们强调真实的光线、色彩和声音,大量运用长镜头,形成纪实风格。他们注重以电影为媒介来考察当代都市普通/边缘人的生活状态,新一代青年在历史转型时期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在他们的镜头下被真实地记录下来。”(百度搜索)在《盲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第六代导演的技巧。而这种技巧的使用正好与小说《神木》的风格相吻合。另外,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神木的来历,多少有些诗意了。在中文词汇里,找不到“盲井”。《盲井》的英文片名《 Shaft》,除了有矿井的意思,也可解作欺骗、陷阱或光线、棍子等。电影取名《盲井》,我以为比《神木》更通俗,更达意,也更符合电影的要求。
结束语
《盲井》可以说是李杨在电影艺术的一次成功探索,从观看效果来看,我不得不承认,它的确打动了反复阅读过小说《神木》的我,它张扬了小说原作的优势。李易祥、王双宝、王宝强三位演员各具特色,河南方言的使用,粗糙的画面和自然音响,真实地表达了生活状态,让人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以上这些视听效果都体现了第六代导演的艺术追求。但是,我又不能不说,由于电影艺术形式的局限,它又无法细腻地传达出小说的神韵,比如小说中一些非常精彩的心理刻画,还有作者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旁白”,包括一些生动的描写,都被电影忽略了,我们只能用“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来诠释了。
《南方人物周刊》 曾发表文章,介绍了《盲井》拍摄经过。文中说,刘庆邦对李杨的敬业精神多有褒奖:刘庆邦说,他是被李杨身上的真诚打动的。“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在承担责任?太少了。李杨非常不容易。”刘庆邦1951年出生于河南,李杨1959年出生于西安,他们同属于50年代,在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甚至审美情趣上比较接近,李杨选择了刘庆邦,是他的眼光,也是他的幸运。而刘庆邦的小说《神木》变成了电影《盲井》也是一种幸运。因此我说,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是相得益彰的成功合作。再进一步讲,由于他们的联手,我们这些读者或观众也算是幸运的了,我们享受了这道艺术佳肴。
白 丁:男,江苏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九期学员,现居江苏。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中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写作为主,小说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被《作品与争鸣》《小说选刊》等转载,获得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芳草文学奖。文学评论在《文艺报》《文学报》《北京文学》《阳光》《创作评谭》《文艺新观察》等刊发表,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
——神木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