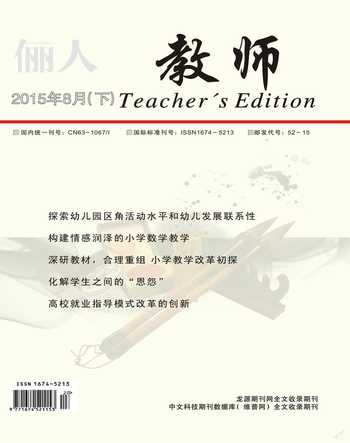生命在身份倒错中流逝
霍超群
【摘要】爱玛的沉沦经历了“幻想—拒绝—放纵”三部曲。探微“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二者因称谓不同所导致的人物性格矛盾,可为爱玛之死找到巧妙的新突破,在这个视角下,爱玛悲剧的产生并非其行为失控的终极形态,而是理性“回归”的一次悬崖勒马。
【关键词】爱玛 包法利夫人 身份倒错 悲剧
福楼拜有一句名言:“生活的本质就像是一盆漂浮着许多毛发的汤,可是你还得把它喝下去。” 在《包法利夫人》中,每一个角色都让人“难以下咽”:爱玛情欲旺盛得令人发指、夏尔的平庸使人恨铁不成钢、无名文书莱昂的怯懦令人生厌、风月老手鲁道夫的寡情薄意遭人鄙夷……这些血肉鲜活的人物让我们深刻看到法国十九世纪的社会现实:虚伪与逼仄的环境让人的心灵蒙尘,堕落的人世间保藏着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长久以来,关于主人公爱玛悲剧的讨论往往离不开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两个方面,而“悲剧的最高层次莫过于性格悲剧” ,评论者多从爱玛身上挖掘出她不安现状、耽于浪漫、空虚淫荡的性格缺陷,但较少有人从 “身份倒错”视角对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命运进行探析。
一、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一个身份倒错的女人
爱玛与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笔下同一个人物的两个不同名字,但她们的身份却截然不同:爱玛是个生命力充盈以至于精力过剩的乡下姑娘,有着姣好的脸庞和喜爱幻想的心,她热衷阅读,渴望纯洁的爱情;包法利夫人则是爱玛出嫁后随丈夫夏尔·包法利姓氏“约定俗成”的名字,她有义务延续家族血统,维持家庭正常开支。换言之,爱玛是自我悦纳的“自己”,包法利夫人是别人眼中的“她”。
那么二者的身份究竟给爱玛带来怎样的迷失与困惑呢?婚后的她仍然想过着“爱玛”的生活:“结婚以前,自以为有了爱情,可是,婚后却不见爱情生出的幸福。”可见爱玛并没有从夏尔身上找到她所希冀的浪漫,婚姻生活更是“不能再平静的平静”。但爱玛即便是“恨自己给他幸福”,也会履行包法利夫人这个名字带给她的责任:她会在家中画画和弹琴,让丈夫为拥有她而自命不凡;她很会管家,把出诊账单寄给病人时,会附上一封措辞委婉的信。日子过得虽然平淡,却并不拮据。
一场舞会改变了爱玛的命运。在舞会上,爱玛遇到了一见钟情的子爵,从而陷入了虚无缥缈的幻想当中:爱玛不甘做平凡的包法利夫人。而风月老手鲁道夫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更是让爱玛因“包法利夫人”的称呼而恼羞:“‘啊!您看!,鲁道夫的声音充满了忧伤,他说,‘我不应该过来。爱玛这个名字,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让我情不自禁地说出口,可是您却不允许我叫!包法利夫人!……唉!每一个人都这样叫您,可是您却不允许我叫!包法利夫人!……唉!每一个人都这样叫您!……其实,那并不是您的姓氏,那是别人的!”鲁道夫为了引诱爱玛上当,故意变换爱玛的称呼,造成他想爱的是“爱玛”并不是“包法利夫人”的假象,而这个芥蒂却是爱玛最在意的,她渴望掀起生活的波澜,却碍于“包法利夫人”的名字,不敢釋放自己的欲望。这种因为同一个体不同称谓所导致的身份倒错,亦实亦虚地暗示了爱玛内心错综微妙的种种矛盾,也只有这个既是爱玛又是包法利夫人的女人才深切体味到个中的隐痛。
二、幻想—拒绝—放纵:爱玛沉沦三部曲
爱玛的身份迷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堕落过程。她的堕落始于幻想,幻想离开死水微澜的丈夫,幻想抵达流光溢彩的巴黎,幻想和子爵相守相依。但是这种幻想还只停留在隐秘的内心,她对现实生活也没有极端的反抗。可是仅仅是精神出轨怎么能满足这个沉溺于梦幻的女人呢?巴黎舞会的奇幻之旅让她看到上流社会的奢华排场,丈夫矫正畸形足失败的事业“污点”让她怒火中烧,鲁道夫对她高雅气质的迷恋让她重拾妖娆女人的资本。于是我们看到爱玛对“包法利夫人”身份的拒绝:当夏尔在舞会上想亲吻她的肩膀时,爱玛无情地说道“别把我的衣服弄皱了”;当夏尔治疗失败企图得到妻子的爱抚时,爱玛残忍地大喊“走开吧”,懊恼为什么会嫁给如此平庸的丈夫;而在与鲁道夫初次色授神予后她居然没有一丝愧怍,反而是“微妙的东西渗透全身”,“我有了一个情人了”的呼唤让一个无耻的淫妇形象跃然纸上。就这样,她由一种轻微的“浪漫幻想症”堕落到对自身的社会姓名极度不认可的态度,这表面上是对无能丈夫的唾弃,实际上流露出她在追求欲望过程中的与自我价值不符的野心和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爱玛的沉沦历程并非“一往无前”,这当中也有短暂的挣扎与反思。文中有两处细节可见端倪:期初爱玛偷情后会“看看天边有没有人走过,看看小镇里的每一个窗户有没有人在窥视她”;她的脸偶尔会“比树叶还要苍白”、“身子比树叶抖得还要厉害”。她毕竟是有夫之妇,社会舆论和道德规范对她尚有约束力,所以此时她并没有抛开一切,失去理智。而另一个细节则是爱玛收到父亲鲁奥老爹写的信,信中所言情真意切,久违的父爱让爱玛为之动容,“觉出久居鲍鱼之肆的腥臭味” ,亲人真切的问候让爱玛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爱的力量让她想要摆脱生活的困囿,与夏尔“重归于好”。
然而,要爱玛成为现实中的“包法利夫人”仍然是那么困难。她宁可去做众人诅咒的堕落的女人,在肉欲的快乐中沉沦也不愿成为众人赞誉的贤妻良母:夏尔手术失败的噩耗让她从身份倒错的忏悔中彻底清醒!而夏尔这次的失误仿佛解除了爱玛内心淫荡的封印,她变得明目张胆,情欲旺盛得惊人。此后,她不再辗转于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二者身份的痛苦中,她甚至想和情人远走高飞,她甘心抛下自己年幼的女儿……当爱玛“修炼”成以一种纯粹官能、散发情欲的姿态存在着,那么她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一个不计后果的境地,情人的温柔缱让她如坠云端,她曾经敬畏的道德约束、家庭责任通通只能偃旗息鼓;她也不再为夏尔的平庸而生气,甚至没有吵闹,她更懒于揭开她对夏尔厌倦的本质,她的日常生活陷入僵木——在释放情欲和等待释放情欲之间。她的沉沦图式应运而生。
三、奢华的生命形式与残忍的理性回归
正如上文提及,爱玛的堕落使得她对欲望的追求丝毫不受理性的限制,暴露着最原始的、赤裸裸的面目,因此她最终为情欲驱使而毁灭的结局也就昭然若揭。在身份倒错之后爱玛的行为变得失去控制,甚至是不可理喻。她“越来越纵情于人生享乐,变得易怒、嘴馋、淫荡”,她时常对丈夫发脾气,但实际上她根本不想再在夏尔身上花功夫;另一方面她在莱昂面前情欲惊人:“她迅速脱掉衣服,拉开束腰胸衣的细带”、她“浑身颤抖着扑进莱昂的怀里”,为的是通过肉体的刺激唤起所谓的新奇的幸福感,然而事与愿违;于是她机械地写情信,她坚定不移地相信:一个女人得永远给情人写信;在渐趋平淡乏味的幽会中,她的社会功能开始衰竭,她分不清虚假的奉承和现实的冷酷,她大大方方补贴情人,不惜欠债累累,最终变卖房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爱玛的愚蠢,她居然为了取悦她的情人与家庭割裂,于世俗所不能容忍。然而,爱玛的所作所为难道仅仅是“愚蠢”二字能概括的吗?她分裂的人格所造成的失控行为,理智显然已经无法加以劝阻;膨胀的情感饥渴,最后汇聚成洪流,冲垮了所有伦理道德的藩篱。有人认为她最终选择自杀是其失控的终极体现,而笔者认为,爱玛的悲剧是失控“复归”理性的一次悬崖勒马。
爱玛的一生都在追求浪漫,但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爱情,而是自己想象的空中楼阁,她永远“生活在别处”:起先,她拒绝做“包法利夫人”,因为她发现婚后的生活如一沟绝望的死水,但是她还对丈夫抱有幻想,希望她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而当丈夫事业受挫,鲁道夫的出现正好填补她对异性的绝妙想象,她在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中间选择了爱玛,舍弃包法利夫人的头衔,她甚至渴望和他私奔,重组新生活;当鲁道夫无情抛弃了她,她又找到了籍籍无名的法律文员莱昂,此时她不再小鸟依人地依偎在他身边,她想要控制他,让他成为“爱玛的情夫”而不是“莱昂的情妇”,错位的社会身份让她的理智失去控制,可是她越不想做包法利夫人,危如累卵的债务就越会明晰地提醒着她:“你就是包法利夫人,你已经无从选择。”
最后她终于认清了,也可以说是屈服了,而当她可悲地接受自己的这个社会姓名时,她怎么面对过去那个荒淫空虚的自己呢?如果认清自己的代价是倾家荡产,这个代价会不会太大了呢?可惜呵,尽管爱玛用“最奢华的生命形式” 了结一生,也无法卸下盲目追求欲望的生命所承受的沉重与艰辛!
参考文献:
[1][法]福楼拜著、朱华平译:《包法利夫人》,广州出版社2007年版。
[2]李艳:《爱玛之死——论<包法利夫人>的欲望叙事》,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3]周兰桂、刘时容:《“情感饥渴”与“阅读迷失”——名著<包法利夫人>爱玛悲剧的另眼细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4月第2期。
[4]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法]乔治·巴塔耶著、刘晖译:《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