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来信”和“镜中”的破裂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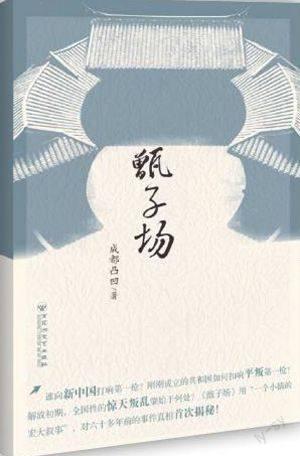


一部成功的小说不只是再现和表现历史,不只是呈现当下的生活或者历史的回声,重要的是它以话语的方式延伸了我们每一位读者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
[作者简介] 霍俊明,诗人,诗评家,任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鲁迅文学奖评委。
《甑子场》
成都凸凹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定价:37.00元
每当看到著名诗人流沙河为洛带古镇题写的“甑子场”这三个性格张扬的大字,我就一直追问“诗人”与“地方性”的历史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特殊关联。尤其是对地方性文化更为特殊的巴蜀之地而言,诗人写作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在于这一特殊的地方和文化场域对生长其间的诗人个性的激发,更在于个性风格突出的诗人与地方和历史之间别开生面的互动性修辞。
一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四川封闭阻隔的地形地貌,人们很容易认为这里滋生出的文化和民风必然也是封闭保守和自我循环的。但事实上巴蜀文化自身就是移民文化,从而带有文化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以及异质性,比如凸凹这部长篇小说《甑子场》中的客家文化。这种封闭与张扬之间的互动也正是巴蜀文化和写作的显豁特征。
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诗歌热潮中成长起来的成都凸凹而言,写作上的地方意识、先锋精神、异秉特质、方言土语(一种地方性的个人化“口音”的表征)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甑子场》中有着全面的展示。小说中的“龙洛镇”这一看似封闭守成的空间却又有着不断向外生长的种种可能性——打鱼人收拢和缩小渔网正是为了抛出和打开。凸凹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同的一点在于地理文化学意义,他在文本中不断强调蜀地的气候、地形、天气、建筑对人物、故事尤其是人情世态的特殊影响。而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成都天气确实每一次都对推动小说的进程和揭示人物关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开头部分的天气与鱼儿心态的呼应关系,“二月间的天气,在阴柔、多雾的成都平原是微冷的,但蜀地难得的太阳加上少风的盆地季候,又为人们的体感揉进了微微的热。真是一个在户外喝茶的好天气!”还有,三月的天气与扣儿婆婆心态的反差,“透过粗糙的松木窗棂,她抬头看了看窗外摇曳着竹影的天。她没有看见那令她抬头的鸟鸣声所在,鸟儿应该是栖身在只漏了一根枝丫在窗缘的院坝边那棵粗大的风水树——红豆树上。她没有看见鸟儿,却从看不远的空气中看见了雾,从微动的树叶间看见了风。这是成都平原惯常的天气:没有太阳,没有雨,风小小的,烟雾杂糅,也是小小的,天就这样阴蒙蒙着,不急也不躁。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她没有出门,她没有出门也知道,满山满坡的桃花正含苞待放。马上就跨进三月了,加之今年的天气大,后人说,山下的桃花瞅着瞅着就褪红了”。
二
小说的空间设置尤为重要。
这些带有特殊地方性知识的空间在当代小说传统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恰恰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同样是川味风格浓郁的李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大河”文学的“改写”“重写”印证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尴尬命运。和郭沫若、茅盾、杨沫等诸多作家以及卞之琳、冯至等诸多诗人对新中国成立前自己创作的作品进行改写和重写一样,李劼人因唯物主义、阶级论和社会学知识对小说进行改写体现了中国作家的集体悲剧性宿命。例如李劼人的《大波》开头以蜀通轮船在长江溯流而上取代了最初的对成都平原气候、风俗的描写。这不仅是对小说和作家的伤害,也是中国20世纪文学政治文化伦理的强大折射。
美国的大学教授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中考察了1910—1950年间以茶馆这一公共领域为切入点的四川,而凸凹小说中围绕着人物展开的会馆、书院、茶馆(茶社,尤其是“女子茶社”)、粉坊、街道等公共空间以及与扣儿密切联系的私人空间值得进一步观照和审视。扣儿这一特殊的女性形象呈现出的个体欲望及其与命运相纠结的“身体”修辞学,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们的注意。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去探寻河流的源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川籍作家,凸凹一直在蜀地的山地、河流、平原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探寻“地方性”的文学精神和历史源头。而成都凸凹“地方性”写作又绝非像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那样简单——出生地、籍贯、工作地都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身份。确实,文学对地域的呈现并不是直线和硬性的,而是要融入作者诗性的发现、创造、命名、想象甚至某种合理的虚构。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基于此,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域的历史更多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编织”出来的,而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地理环境、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值得研究。所以这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成都凸凹这位“蜀地”作家通过文本的想象、命名创造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蜀地”图景和西南诗学的精神气象。成都凸凹通过“地方性”的文学抒写,通过充满了心理能量、文化势能和精神图景的文学形象和场景重新呈现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洛带”。这也为其他写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不无新意的“地方性知识”和具有重要诗学价值的有效入口。实际上成都凸凹这种个人化、命运化但又极具历史性、象征性、想象性的场景也同时完成了类似于田野化考察的过程。文本化的场景和空间重新打开了被历史、社会和时间风暴所封闭的出口和伤痂。
与空间相应的则是语言。“普通话”写作之外的“口音”和“地方性”文学知识也在成都凸凹这里得到印证。而这种一体化之外的文学“口音”和“方言”的获得不只在于凸凹对地方学和文化版图的确认,以及对四川方言和人物志、风俗史的不断抒写,更在于这种还原和再造的“地方性”知识在最大限度上呈现了小说与地方和个人之间最为本源性的关系。正是因为与普通话写作具有差异的口音,而带有了可贵的边缘性、民间性和地方性。
三
《甑子场》中涉及的各色人物不乏传奇性,而年轻作家徐则臣的一句话值得关注。他认为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单凭讲述传奇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徐则臣强调的是每一代作家都应该从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属于自己的小说作物。而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而言,怎样写和写什么都变得日益艰难。这种难度不仅在于写作自身不断提升的难度,而且还在于作家以何种方式和角度认识当下无比新奇的现实以及逐渐烟消云散的历史。与当下更多写作现实题材的作家不同,成都凸凹转身到了历史烟云的深处。被很多人忽略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或者很多人认为二者之间是彼此独立的,而成都凸凹则通过文本的方式沟通了历史与现实。也就是说历史和现实实际上是彼此打开的,历史是现实化的过去,现实是过程化的历史。这样,小说就不乏现实感和历史意识了。
“历史”和“现实”在中国20世纪小说中更多体现为国家、革命、阶级、政治的宏大叙述性元素和权力关系对文学和作家的主导和规训。因此,小说被认为是一门客观呈现历史和斗争的文学知识,而相应的小说本体依据、作家的个体主体性都遭受了空前的贬抑甚至无情放逐。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所言,历史陈述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想象力的产物。这提醒我们历史具有被不断想象和书写的修辞性质。而在此意义上历史必定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被不断“改写”和“重写”——“时间远去,雾霭重重,但我还是不希望在我笔下出现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故技与窠臼。我知道我写这部非虚构小说会面临诸如此类许多无法选择的选择,但不管官方资料多么振振有词或语焉不详,不管民间口实多么生动具体或天马行空,我只采信亲历者。”而中国关涉“历史”和“时代”的小说在更多时候不是呈现为罗兰·巴特倡导的充满“想象力”写作,而是呈现为与之相左的“意识形态”化写作。同时,这些写作者都是当时“时代”和“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们倚靠个人经验的写作不仅是难以赓续的,而且这种去除了想象力和知识分子精神的写作也注定是“短视”和“短命”的。这些作品在一个短时期内呈现了历史的一段面貌,但是从文学的层面讲它们丧失的却恰恰是文学精神和生命力。同时,由于强大政治文化语境以及不断僵化和窄化的文学观念影响甚至规训,这种面对“时代”和“历史”的写作更是沾染上了明显的社会学知识以及“庸俗化”的反映论调。这使得这些作家笔下的“现实”和“历史”与真正的历史之间形似神离,甚至最终违逆了历史本来的面目和复杂“现实”的真实内里。
成都凸凹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我”一直处于历史与现实、虚构与真实的不断龃龉、摩擦之中。在不断的预叙、回叙和插叙中,在史料和想象性场景的拉锯迂回中,读者甚至已经很难辨别“原型”与“人物”之间哪个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确实,这呈现的是想象与现实不断叠加的文本。无论是凸凹担任编剧的《滚滚血脉》,还是他的《镇上的公园》以及这部《甑子场》,再加之其他的地方志、历史档案、官方报道和民间传闻以及历史叙事(比如《全国剿匪大事记》《龙泉剿匪记》、况浩文的《一双绣花鞋》),一个历史中的人物(比如朱向璃)和事件(“龙潭寺惨案”)竟然会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出现在试图再次叙述者的面前。如何叙述历史性的事件已经成为写作者的难题,因为无论你试图完全地还原,还是极尽修辞和叙述方式之能事,二者都不可能让小说与历史等量齐观。小说只是一种修辞方式,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本也同样是一种修辞方式,区别只在于修辞的方式和程度不同。有时候很多长篇大论的小说还抵不上一篇作家的日记。对于川西叛乱以及镇反运动的历史叙述而言,吴宓值得注意。1951年3月,时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教书的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绾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见证人式言之凿凿的陈述,而是短短数语所衔接和省略的历史过程。著名先锋作家格非说:“如果你不能去接近和表现现实,那么你就去写诗。”确实,小说较之其他文体更具有与历史和现实对话的权利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常识”。但是就此我们想追问的是——是否小说文体较之其他文体真的更具有抒写历史的能力?正是出于对历史叙事难度的考量,凸凹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写作方式。无论是他小说连环对接结构(不断连接线索又不断藏匿起绳头)的匠心独具,还是同一人物在不同视角和叙述姿态下的反复现身,都使得小说如何叙述成了重中之重。与“主流”作家和“宏大”的社会学、经验式的“历史”写作之间拉开距离之后,凸凹以“介入者”和“旁观者”相融合的姿态来观察、测量、审视、揣测历史的烟云和现实的地表。他也最终在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立场上使得文学的本体性和作家的个体主体性同时得到了维护。换言之,正是因为凸凹始终在用“文学自身”说话,所以他笔下的“时代”和“历史”就是想象的历史、修辞的历史、个人的历史,从而也更具象征性、寓言性和精神性——“不可靠,是记忆的最大特征。”但是有些历史难题是小说不能解决的,比如“陌生人问我,为什么社会变革总会以一大批乡镇长的死为代价呢?”
实际上凸凹仍然摆脱不了“历史真实”的焦虑,比如正文前的主要人物表中对故事人物的原型和本名以及相关真实事件的反复强调,比如真实历史人物的登场和对场景的描述,比如在书中穿插美国摄影师在1941年拍摄的龙泉驿、洛带镇甑子场的照片,比如在故事叙述中穿插当下城镇化时代的拆迁经历,以及对深圳富二代、大学生志愿者、村党支部书记的描绘。
四
与空间描摹和历史态度相应,凸凹这部小说的“时间”问题值得注意。
时间尤其是与自然时间法则具有差异性的“历史性时间”“社会性时间”在这里具有了延宕和推迟性。以往的小说在提到关于历史进程、时代进步的新旧时间时往往是采取了进化论——即现在是好的,以前是坏的;现在是红的,以前是黑的。换言之更多的叙述者采用了一刀切的二元对立时间观。这甚至成了多年来写作的“时间性真理”。而在《甑子场》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反复地对“解放”“解放日”“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疑问和确认,“扣儿虽然只上过几年私塾,好孬也算得上是识文断字的人,连扣儿都看不出解放不解放的区别,更别说本土本乡的大部分居民和农民了。大伙儿不仅看不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区别,甚至连解放这个词也闹不明白,更有甚者,连解放两字都没听说过。现在想来,一点不奇怪”。成都凸凹从历史性时间、社会性时间、革命性时间与普通人生活时间的不对等状态中更为深层地揭示了“革命”与“普通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进而还原了历史的原貌。
这部小说是一部历史化的寓言,反映了人性和欲望。凸凹对不同类型人物的死亡方式表述皆有不同:死、去世、镇压、处决、自杀、被杀、死于平叛炮弹、死于不明枪弹、牺牲、死于非命……而小说的主干则集中于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矛盾和纠葛。扣儿“靠病活着”以及她的“身体”在几个男人间的不同状态,甚至包括被男女身体器官化的甑子场地形结构似乎都在印证法国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历史文本的身体性特征——尤其对女性和女性写作而言更是如此。这部小说也揭示了男性写作的历史观,比如凸凹在小说中描写“所有突然爆发的大事件,往往都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偶然小事引发的,而这件小事,又往往与一个女人有关。古今中外,有很多案例,或者说很多女人,支持这个定律,比如妲己、貂蝉、杨玉环、海伦,比如扣儿”。与此同时,在一些暴力性的场景和欲望化细节中,这部小说印证了革命和暴动就是男人的狂欢,死亡就是男人的节日。
五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诗人小说”或“诗性小说”。
在当下中国,写作一部小说要具有“诗学价值”,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中国当代文坛,不乏从诗人身份转换成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比如阿来、苏童、孙甘露、池莉、韩东、李浩、乔叶等。而落实到成都凸凹这里,他的“诗人小说”最为吸引我的是他文本中的精神气息和诗意化的语言。
较之当下很多小说家粗糙无比的语言,凸凹小说的诗性化语言很值得关注,比如“左耳和右耳,左梦和右梦”,比如小说中不同人物不断出现的白色的、银白的、黛色的、黑色的、青色的、红色的、桃色的各种颜色“雾”的象征意义。
以莫名其妙的来信作为小说的开头和线索并非先例,但是这串联起来的60封书信所带有的精神气息让我想到的是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作为一个湖南籍诗人,张枣很多重要的诗作和精神成长阶段却恰恰是在巴蜀期间完成的。春秋来信,来自何处?寄与何人?而个人的情感生活一旦与“春秋”这样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时间背景联系在一起,自然就有了化不开的情结和未知的命运。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扣儿被一束梅花所吸引、蛊惑进而揭开小说的草灰蛇线。小说的开局正与张枣诗集《春秋来信》中那首代表作《镜中》的诗意氛围、精神气息和命运轨迹具有某种一致性,“来人推了门进来,将一大把梅花放在靠墙的平柜上,说了声五爷我走了,就走了。很快,浓郁的花香塞满了冬日房间里的每一个空气缝隙,也塞满了扣儿的鼻孔、袖套和领口。梅花,是她喜欢的花,看起来舒坦,闻起来也舒坦。甑子场没有这么好的梅花,平原的梅花就数龙潭寺的最好。意外见到乡梓梅花,她喜,但没有将喜形于色。她知道,鱼儿正尖细地观察着她。她不是装假,她是不想让他顺着她的‘形往下想。她自己也不想往下想。但是,她依然抵挡不了梅花随着窗外吹进的偶尔的轻风向她发起的一阵阵进攻。她深呼吸了一下,又一下”。这一束特殊气息的“梅花”及其对人物波诡云谲关系的重要提示只能出自“诗人”之手。这是一种“残酷的诗意”。“梅花”对于扣儿的命运来说就具有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这一束小小的梅花竟然改变了一个人惯常的生活轨迹。这看似不可能的细节却在真正意义上还原了女性是“情感动物”的本质。为着一束花,她的命运突然转变,这是好?是坏?可能连扣儿自己都难以分辨。当我们再想起张枣的这首诗《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来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 面颊温暖,/ 羞涩。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 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那一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该是如何让人唏嘘感叹、悲伤莫名。而扣儿娘家房前屋后栽满了梅花,“梅花谢了,家就凋敝了”。
原来,花事就是人事。
在“春秋来信”和“镜中”的氛围里,成都凸凹以诗人的方式将那些缝隙和碎裂处放大给我们看。历史和时间的整体性法则至此结束。
一部成功的小说不只是再现和表现历史,不只是呈现当下的生活或者历史的回声,重要的是它以话语的方式延伸了我们每一位读者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和话语方式。凸凹在后记中曾经自我追问,这是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当代小说?爱情小说还是战争小说?悬疑侦探小说还是诗性寓言小说?跨文本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新写实派小说还是魔幻现实派小说?爱恨情仇还是政治幻觉?乡村叙事还是城镇物语?史诗呈现还是底层书写?
我给出的答案是,这是一部“诗性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