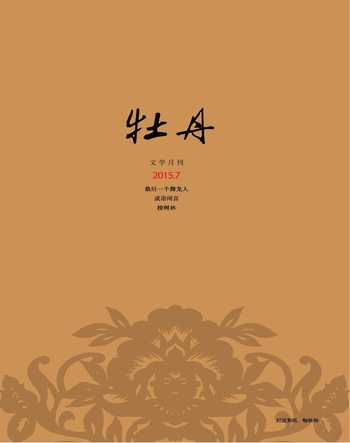记忆深处的往事
龚小萍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灯火闪烁,夜风习习的珠江边,遥望着远处不停变幻的色彩迷离的“小蛮腰”婀娜多姿身影的时候,记忆把我拉回那个哈出白气的严冬的早晨,码在稻场的草垛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寒霜。
当我被父亲从热被窝里叫起来的时候,屋外的天与我一样,还处于朦胧的浓睡之中,透过屋顶上的亮瓦,也只是些蒙蒙的灰光。父亲把我叫起床,硬生生地对我说:“跟我去赶街。”
尽管当时正在美梦之中,但对于“赶街”,我还是有着极大的兴趣的。我快速地爬起床,穿好衣服,用父亲洗过脸的温水胡乱地抹了一把脸,就眼皮沉重地跟在父亲的后面出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父亲去赶街,我们要去赶的街叫大堰垱,那里是离我家20多里地的一个集镇。在那里,可以买到很多我们大队部(那时不叫村)的代销店里买不到的东西。那天早上,父亲挑了一大担的红薯和米糠,是去用这些红薯和米糠换回一些小麦面粉(我老家叫灰面)回来吃。虽然我的家乡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里的鱼米之乡,但具体到我居住的山村,却是一块贫瘠的丘陵,唯一的盛产,就是如今叫我一看到就没有了胃口的红薯。这灰不溜秋的东西,喂饱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父亲挑着100多斤的红薯和米糠前行,我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跟在后面,此时月亮变得很白,地上的霜也变得很白,我与父亲的身影,在白白的月光下,像两个黑色的剪影,飘行在这个静谧的白色世界。
对于一个喜欢“赶街”的少年来说,当时的记忆应当是刻骨铭心的,可我因为一直没有完全清醒,一路前行的情景却那样的模糊不清。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两条腿急速地更替,除了父亲粗重的喘息声,就是我自己越来越快的心跳声。父亲重担之下,踏在土路上发出的“噗噗”的脚步声,似乎正引领着我走向某个未知的世界。
在我年少的记忆中,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父亲一直都郁郁寡欢。从小到大,我极少看见过他发自内心的开心的笑脸,更别指望他会在某个闲暇的时分,为我和弟弟妹妹讲上一个笑话或故事。他和母亲每天都是在匆忙中下地劳动,以此换回我们一家人的口粮。晚上收工回到家里,则如同一尊伫立着的雕塑,满脸都是愁苦的神情。在那个年月,对于生存在山村里,为吃饱饭都会犯愁的民众来说,又有什么真正值得他们高兴的事儿呢?
我们在疾行中迎来了晨曦,迎来了仿佛一把手术刀般将黑夜的皮肤徐徐划开的微弱的太阳光。在已经露出鱼肚白的天上,月亮惨白地移向西天,其神情似乎是很不好意思与太阳光对视。我和父亲迎着太阳光坚定走去,我突然发现我已经跟随父亲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界。四周不再是一垄一垄的红薯地,而是一丘连着一丘的稻田。冬天的田野里光秃秃的,一捆一捆的稻草散落在中间,田里因而显出一种空荡,大地仿佛被剥去了衣服,袒露出一览无余而又青筋暴涨的肌肤。这时候,我听见父亲闷闷地说,大堰垱到了。
此时,我才彻底清醒过来,意识不再模糊,四周的景物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大堰垱除了是个墟镇之外,贫穷也同样在这个地方蔓延着,那些散落在田地边上的房子,也基本上都是土坯筑就起来的,冬天闲下的人无所事事,也都裹着件破棉袄,袖着手蹲在向阳的南墙根上,无精打采地晒着太阳。
因为红薯和米糠比面粉便宜,父亲不惜消耗大量的力气,翻山越岭徒步20多里挑来的一担红薯,最终只能换一小包面粉,可能也就10来斤的样子。另外的米糠,父亲换了几块钱。当父亲将一切都收拾停当的时候,太阳也才露出地面一丈多高。这时候,父亲选了交易市场一处向阳的地方坐下来,摸出口袋里的叶子烟,卷上一支抽起来。阳光下,我竟然看见了烟雾中的父亲挂在眼角的泪,是晶莹、硕大,星星一样的一滴泪。显然,父亲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他的眼泪,目光望向远方,像是在憧憬着什么。后来我想,父亲一定是在想,他用红薯换来的这些灰面,在母亲灵巧的手中,能给一家人带来多少的快乐。
父亲抽完烟,突然扭头对我响亮地说:“平娃,走,吃饺子(我们老家把馄饨叫饺子)去。”这是我老早就在心里盼望着的一句话,也是我丢下香甜的瞌睡,不惜徒步20多里地跟着父亲赶街的目的。我立即山呼海啸般地扑向父亲。父亲领着我进到涔水河边的一家小面馆里,花5毛钱为我要了一碗饺子。当面馆里的阿姨端上来的时候,我一阵狼吞虎咽。我不知道顾客稀少的面館里,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我的吃相,只听父亲在一旁不住地对我说:“平娃,慢些吃,慢些吃,没人会跟你抢。”
直到今天,父亲的这句话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其实也知道,当时是没人跟我抢,父亲不会,其他的过路人更不会,但我知道,那是一个少年饥饿的肚皮在跟我抢。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路边的稻田里畅快淋漓地撒了一大泡热气腾腾的尿,在等待我撒尿的时候,我又听见父亲在一旁喃喃地说:“这要是咱家的田就好了。”
如今,村里如我一样大量外出务工的人,为守候那片故土的父亲留下了很多的田地,直流灌溉的稻田里也收获了堆积如山的金灿灿的稻谷和成百上千斤的小麦,家里栽种的红薯与米糠都成了母亲喂养的猪仔们的可口的美餐。我相信,我年迈的父亲,也一定不会再在意他的儿子撒在别人田里的那泡热尿了。
这巷弄狭窄而悠长,满铺青石条,两边的民居都是白墙黑瓦的徽式建筑,沿袭了古朴大气的徽风。墙面斑驳,仿佛写尽岁月沧桑的水墨画。幽深逼仄的街巷里寂静安然,没有一个行人。路面洁净,墙角石缝已然长满青苔。
左折右拐,沿着墙上小小路牌指示的方向行良久,一路上只见到一位老人,静静地坐在一扇门旁的小凳上,一只猫,也静静地偎在老人的脚边。这座建于光绪二十三年的老宅,简洁朴素,一如隔壁民居。大门也不大,浅浅地缩进一个梯形,门扇两开着,门楣上一款素气的匾额:兰蕙书屋。一个女子坐在门旁的桌后,织着毛衣卖着门票,也没有多余的言语。
迈进大门,是一个不小的庭院,纵深长,最尽头立着一尊胡适的塑像,这一座塑像上,他身着西装,外罩风衣,神采斐然。与之前广场上的那一尊的沉静安然截然不同。东侧的胡适故居是一幢结构严谨、精美典雅的徽派建筑。门前,立有一块“全省重点保护文物单位”的石碑。故居为三开间,前后进,通转楼式,共13间,石库门楼画幢雕梁。大门楼上镶嵌着精致的砖雕和门楣飞戗,砖雕上刻有“三顾茅庐”、“黄鹤楼宴”、“寿星弈棋”等戏文典故,栩栩如生。进门是客堂,全木质结构,红漆大柱,典型的徽州人家格式。墙上挂的都是胡适结婚时亲友送的条幅对联,浓浓的书香。迎面照壁上一幅山水画卷旁,“揽月春云常得句,山光水色自成图。”的楹联正是上庄秀丽风景与荟萃人文的凝练概括。抬眸,黑底匾额上“胡适故居”四个烫金行楷大字耀眼夺目。下方是一席古色古香的红木八仙桌、太师椅,桌上老旧的座钟与东瓶西镜依稀是那些古老日子的痕迹。
细细端详,屋内门窗、栏板的木雕刀笔流畅,镂刻精致,清一色的兰草主题。“兰为王者,香不与众草伍”的清境和房主的立世风格油然复现。“我从山里来,带着兰花草”,是适之先生铭心刻骨的怀乡之情吧。
客堂左侧是胡适母亲冯顺弟的住房,这是一个我所敬仰甚于胡适的女子。正是23岁丧夫的她以温婉包裹的坚韧,遮弥风云举重若轻的母爱,塑造并成就了一代文化巨擘。
右侧是胡适结婚时住过的房间。据说,这些均按胡家的原样布置。站在简陋的婚房,想着胡与小脚女子江冬秀的一世婚姻,想着那路旁小小墓园里的没有尽头的等候,无以分辨的纠结复杂心绪让人窒息。
穿过狭长侧门,是正房后厅。摆设一如前厅,只是木墙上方悬挂着1941年胡适50大寿,由著名书法家程宗鲁书写的“持节宣威”横匾。持节宣威,能换来内心的安宁与慰藉么?
西厅屋是“胡适纪念馆”,陈列着胡适生平事迹,墙上挂满胡适与家人的照片,还有胡适友人的照片。客厅正中,摆放着一尊胡适的汉白玉头像。两边的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横匾是“智德兼隆”。这是蒋中正给胡适的题词,也是对胡适一生的评价。
复杂的心境中,悠悠走遍了整个院落。出得门来,日已西斜。
据说,上庄有99条巷弄,似迷宫一般,初来之人是进得来却出不去。我们并不辨方向,只是沿着曲曲折折的长巷,阡陌纵横的石道,穿过素白的马头墙,黝黑的屋脊瓦,在清一色徽派建筑里,感受时光的温暖和毫不容情。
背着夕阳,走出了迷宫样的村落,心绪却还在那座墓园,那座石桥,那座眺望的塑像上。
晚餐在上庄一家酒店,事前预订了適之先生大加推崇的绩溪一品锅。大大的一锅,春笋打底,一层红烧猪肉、一层油豆腐包、一层鸭肉、一层圆子、最上面是均匀排列的黄灿灿的蛋饺,上面点缀着鲜红的腊肉和红烧鸡块。据说适之先生不论是在北大做校长,还是客居美国,每有贵宾到访,他必亲自下厨,张罗这道家乡名菜。成菜后,又亲手端上桌,并向大家介绍说:“这个菜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徽州菜、绩溪菜、家乡菜,大家不要客气,务必要尝尝”。这种对家乡的眷念,怕就是佩声一直固执地认为他定会回来的原因吧。
生在河南,长在河南。很小的时候,听大人们说:谁谁谁说话撇洋腔,烧包死了,我因此对这些撇洋腔的人嗤之以鼻,心想我长大了可不做这种人。
渐渐长大,才知道这种所谓的“洋腔”就是普通话。
作为河南人,说的河南话,大家都说,顺理成章,祖祖辈辈都这样说的,那个“普通话”,感觉离我好远。
曾为教师,声母、韵母、四声之类的知识我也知道一些,可是在茫茫人流,日常交谈之中,这些知识也只是知道而已。因为身边的人说普通话的很少,不去外省不用担心。
儿女们长大,相继上了大学,我发现他们的普通话说的都挺好,并且我感觉普通话也确实好听。而我的普通话水平还停留在“知道”的阶段。
女儿到上海求学,我去送,在那里我听到许多人在说普通话。我以为他们是外面的人,说普通话很自然,我们都在中国,河南人说河南话也很正常。
来到深圳。深圳是个移民城市,这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大家都说普通话。偶尔说个其他地方的方言,大家就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有很不入流的感觉。我们逛街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再说河南话了,只好闭嘴不吭声。和别人的交流就由女儿开口了。可是,女儿工作,我需要买菜和日用品,我就简单地学说了一句:“这个多少钱?”那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别扭,很想说我们的家乡话可是又不合适。一次,在一个超市的门口,我听到几个人在说河南话,并且和我们家乡话很近似,我就赶快上去搭话,一问,原来是我们的老乡,在那里卖菜。哎呀,我感到那个亲切呀,嘿嘿,终于有知音了!不断地去那里跟他们说话聊天。从深圳回来的时候,在新郑机场一下飞机上了往市区的大巴,听到大巴上售票员的河南话,感觉那个舒服,我自己就像解放了一样!
再到深圳的时候,女儿就鼓励我多说普通话。她详细给我讲普通话和家乡话的区别,例如说:“美丽”就不能说“没丽”,“出国”就不能说“出锅”,“普通话”不能说成“扑通话”如此等等。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普通话练习。
在深圳有几个好朋友,有山东的、东北的、四川的、湖北的、江西的、武汉的等等,我们经常在一块玩,大家都说普通话。这一段时间,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带有不少的家乡音,可是说起来流畅多了。
回到了家乡,说普通话的机会少了。可是,我发现在家乡普通话正在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现在的学校,已经要求教师用普通话教学。现在的许多学生都会讲普通话。而我呢,虽在家乡,对于普通话,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时不时地还会说上几句。有时候我会拿一本书用普通话大声地朗读,我不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可我知道,普通话是和外面世界接轨的必用工具,普通话是我们的国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了我们的国语!
我和秦晓不是一个村却同属一个大队,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都在一个班,她品学兼优,一直是我的班长。秦晓不仅学习优秀,而且长相如出水芙蓉,扎着一双灵秀的大辫子,是一个人见人爱的才女。
我们初中毕业那一年,正赶上洛阳第一届牡丹花会节,在秦晓的组织下,我们同学每人兑了3元钱,包了一辆公交车,到洛阳赏牡丹。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出去旅游,心情是那样豪放,一路欢歌笑语抵达九朝古都。白马寺里,第一次见到老外,第一次与老外用英语对话,第一次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龙门石窟,伊水河畔,陶醉于九朝古都厚重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旖旎的山水之中。看到秦晓站在国色天香的牡丹丛中,定格在相机的镜头里,犹如牡丹仙子下凡,周围盛开的牡丹花也有了几分羞涩。我心中第一次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赏花回来,我们临近初中毕业,30多名同学抉择在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有的继续深造上高中了,有的经商下海成了“倒爷”,有的扛起锄头“修理地球”,有的接爸妈的班当了工人,有的投笔从戎入伍从军,同学少年各奔东西。我和秦晓去了两个不同的高中学校,为更高的理想去拼搏了。高二那年,没有约定,没有沟通,我和秦晓慕名到几十里外的太行山下百中求学,她再次成为我的班长。
那些年,高考前还有第一道门槛,叫做“预考”。在预考中秦晓失利了,我虽勉强过关,之后却因几分之差与高等学府失之交臂。听说秦晓因此大病一场住了医院。“黑色七月”过后,我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情去家里看望了她,互相慰籍,畅谈心扉。她决定不再高考,把厚厚一沓白马王子们的求爱信付之一炬,然后选择去当代课老师。我虽名落孙山,却还想东山再起,于是选择了复读。一年后,正当全国人民庆祝第一个教师节之际,我被省城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十年寒窗苦总算没有付诸东流。听说她找了一个国企干部,很美满,我就没有打扰她的平静生活,背起行装穿上那条发白的牛仔裤求学了,那一年我19岁。
三十年光阴转瞬而过,几年前,漫不经心走在解放路上,忽听有人惊呼我的名字,急忙环顾四周,发现对面立着一个女子。我惊呆了,一拍脑袋叫道:“天呐,秦晓!”
每到槐花飘香的时节,我就会想起去世的姥爷。
姥爷一生经历非常丰富,年轻时当过兵、种过地、挖过河,开过磨坊、油坊,当过工厂业务员,后来成了乡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改革开放后,姥爷把乡里的一个门市部承包下来,开了一个副食批发部。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拮据的年代,姥爷靠那个批发部,接济着他的子女和孙辈们,我们表兄弟姊妹14人才得以有饭吃、有学上。因为姥爷的批发部里需要人手,所以我们利用假期经常去帮忙,我是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也是与姥爷感情最深、在姥爷身上受益最多的一个。
有一年的寒假,我和表哥在批发部里帮忙。一位顾客订了一百多包点心,要我们第二天一早包好有急用(那时候的许多商品,诸如茶叶、糖果、点心之类的,全部靠手工用纸张包装起来),我和表哥为了赶进度就降低了包装的标准。姥爷进货回来看到后,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后他一边跟我们返工,一边教导我们,不管干啥事,都要认真,都要做到最好。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在油灯下一直忙到凌晨三点多。多年来,姥爷那晚的教诲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后来,在姥爷的店里帮忙,姥爷还要求我们对常用商品的价格要做到“一口清”,称瓜子、茶叶、糖果等商品要做到“一抓准”。
印象中,姥爷身上的衣服总是洗了再洗、补了又补,几乎是洗得掉了色、不能再補了才换新的。其实姥爷经营的批发部在当时来说,绝对算得上“高收入行业”,可姥爷却从不铺张浪费。因为牙不好,一日三餐几乎都是炖得烂烂的土豆、豆腐、面条,很少吃肉。姥爷自己生活节俭,但在晚辈的教育上,花钱却从来不含糊。姥爷年轻时,每次出差都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学习用品。读小学时,我经常拿着姥爷送的旋笔刀、文具盒等在同学面前炫耀。有一年的仲秋节前夕,姥爷给喜欢体育的我和两个表哥,每人买了一双青岛双星足球鞋,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那一双八块五毛钱的运动鞋,现在再贵的名牌产品也无法与之相比。不仅对自己的家人这样,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了难处,姥爷也会热心相助。有一年春天,附近村里一个乡亲突然生病住院急需用钱手术。家人来不及返回村里借,就找到了姥爷。姥爷二话不说,拿出两千块钱帮他应了急。
姥爷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而我们回报他老人家的却太少太少。记忆中,我只送给姥爷两件礼物,一是参军后用机枪弹壳做成的拐杖,二是用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为他买的两瓶杜康酒。姥爷去世前半个月,我探亲休假时还和他一起划拳喝酒,姥爷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好好工作、踏实做人,想不到那竟然成为我与姥爷最后的一次交谈……
姥爷的批发部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每到夏天的时候,树上结满一串串白色的小花,清风吹动,暗香袭人。姥爷总会在树下摆张小桌,放个茶壶,支把躺椅,置几方小凳,有老友来时边喝边聊;无友来时独自品茶闭目养神。老树、老屋、老人、老椅,恬静安逸的画面,既成为街头一道水墨似的风景,也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
蒙医生的全名没几个人记得,只有一些辈分高的老人会喊他的小名“蒙腊狗”。
自从当医生有名气后,再也没人叫这诨名了,大家都很尊重地叫他蒙医生。他家并非世代为医,只是自小家穷,念了几年私塾,先去跟了镇上一个骟猪的师傅学了骟猪的手艺,后又跟镇上一个兽医东奔西跑,几年下来,他也就能独自给猪看病了。
整条山沟,就他一人在学医,遇上村里有新媳妇生孩子,山高路远,去镇上医院来不及,多是找了他来凑合接生,他又当起了妇产科医生,也有人临时在地里忙活时,肚子疼什么的,也叫他来,他也不多说,放下锄头,就地看起病来。常常三下五下,还真把人给治好了。更有那年老的人躺在床上,猝然起不了身,也是他挎着药箱飞奔而至,东摸西瞧,手到病除。
一来二去,就这样通过无数次突发事故的临床实战,蒙医生的经验多了起来。有时,他正给牲畜看病,又遇上人有急病,分不了身,到底是人命比畜生命主贵,他只能选一个对象,索性就只给人治病了。
找蒙医生看过病的人,都会回头再找他,一方面是他开的药确实有几分灵验,另一方面也和他的性格有关。
蒙医生不像县城大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医生那样面容严肃,不苟言笑,让人望而生畏。他个头不高,扁圆的脸上老是挂着笑眯眯的神情,一看就是没有啥脾气的好好先生,事实上,他也的确是。
他也从没穿过那种象征医生职业的白大褂,终年是乡下人穿的随便衣服,流行啥就穿啥。无论他的病人是刚从地里忙完回来的邋遢庄稼汉子,还是着装干净的乡镇干部,他都一视同仁:同样的笑容,同样的用心,聆听病情,认真开药方,耐心地叮嘱。
乡下人看病么,要求也不那么高,病医得好,态度好,就认了。因了这点,来找他的人更多了,他的名气愈来愈大,就连离这几十里路远的其他乡镇的人也来慕名求医。
于是蒙医生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即使是农忙时节,他也从早忙到晚,坐在自家的八仙桌前,面前一张长板凳,挤满人,门槛上也坐满了人,连墙角里也蹲有人,那看病的队伍一直排到小卖部门前。
他的生意好,也带动小卖部的生意,烟啊酒啊跟着消费起来,小卖部的老板自然求之不得,也在店门口摆起几张长凳子,方便看病的人坐。
蒙医生看病极有耐心,他对每个病人都是慢悠悠的,闭目摸脉、仔细观察舌头、缓慢询问、不时点头,遇到那爱开玩笑的熟人,他在开完药时也顺带说几句玩笑话,逗得在座的病人哄堂大笑,大伙似乎都不是来瞧病的,而是来喝茶消遣的,医生有趣,病人也高兴。
时间拖得再晚,病人也没得怨言,回去挨家里媳妇责问,就会振振有词地反驳:“我在蒙医生那看病呢,人多得很!”一句话,媳妇也无话可说。
蒙医生的生意好,还仗有一点,他开的药不贵,这对乡下人来讲,最划算,也最实惠。
撞上有些乡下人手头紧,看完病,给不起药钱,向他恳求等年底猪儿卖了,或是来年蚕茧卖了再给。蒙医生听了,也不变脸,还是笑眯眯地答应:要得嘛,要得嘛!病人喊他先用笔记起账,他摆摆手,递上药:“先等病好了再说,有钱记得还就是了!”病人听到这话,往往感恩戴德,嘴里不住念阿弥陀佛,只夸他的好,站在一旁的人见了也无不交口称赞。
就这样十传百、百传千,蒙医生的大名自然传开了。病人多,蒙医生一个人忙不开,他就让他的大女儿打下手,他的儿子还小,念小学的小屁孩,整天不是关心着上山抓鸟,就是琢磨着下河摸鱼,对父亲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毫无兴趣。
那天,蒙医生看完病人,已是深夜,他去猪圈解手,他媳妇见他久久不上床,便出门去看,只见他倒在地上,脸色煞白,旁边的猪都吓得蜷缩在角落,他媳妇慌了神,忙叫醒儿子和隔壁的邻居们。
蒙医生出殡那天,天上飘着毛毛雨,三大姓的村民们都到齐了,长长的送葬队伍蔚为壮观。
自打蒙医生去世后,山沟里出外打工的人更多了,只留下老人小孩,到后来,打工赚到钱的人家不是在镇上就是在县城买了房,将老人、娃娃接走了,于是,这山沟,渐渐人烟稀少,只有狗声热闹了。
这山沟,便再也没出过像蒙医生那样的医生了。
责任编辑 谷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