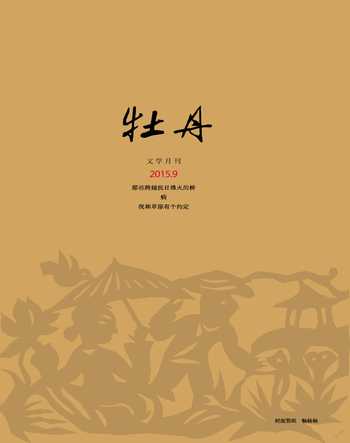光源
郑吉平,白族,1969年2月生,贵州省大方县人,中共大方县委党校副校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5年7至8月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曾获2003年度《民族文学》新人奖,有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最后一块田》,著有长篇小说《嗄呦寨》。
正月十六早晨,靠山村村长蒋银八兀自把一颗苦瓜脑壳吊在床沿上吸烟。老婆挡都挡不住,黄家坝那个老黄就闯了进来。他正搜肠刮肚的想着生财之道呐,也就被老黄打断了。
啊?
蒋银八一声惊喳,合着一根烟不该落地,被老黄手疾眼快一把接着,颠过烟屁股那一头,恭恭敬敬地交还给他。
蒋银八撑起身来,说,老黄,再说一遍,你要干什么?
老黄说:开旅店。
我妈!蒋银八张了面前的老头儿一眼,心里头骂了一句,说,老鬼,你索性划开肚皮给我看看,——真想看看你一颗心子到底和别人有啥二样!
老黄嘿嘿地笑,说,有啥二样,还不都是肉长的。
蒋银八说,那,别人一辈子老老实实地当农民,你为啥一下儿想做这样,一下儿又想做那样?
“你看你都做了些什么行当哟——”
蒋银八眯着眼粗略算了一下,天!他喊了声,陀螺般旋了下屁股,两条腿就挂在了床沿上,拍着两膝说:
正规不正规的,一共十来种!
啊?老黄说,怕不得吧?
蒋银八索性一样一样给他数了出来。老黄也自感觉意外,摸了摸草不剩几根的萝卜头,咂舌道,妈呀。
大正月间,老黄提着那两瓶用九龙山野生山萝卜泡出来的“奢香花酒”,正是来找村长写一张纸盖一颗印,上乡里面办营业执照——您且记牢这个话头。
老黄家族的宗谱很正规,一出世他老爹就给他取了名字在谱上登记,老黄的谱名叫做黄克勤。因他一张马脸,上面撒着不多几粒麻钉,故而打小就被人呼了“黄瓜”的绰号,逐渐地人们忘了他本名儿,大人细娃都只知他叫“黄瓜”。生产队时会计造花名册,造到他时,觉得“黄瓜”不应是他本名吧,就问“黄瓜”的真名叫什么,不曾想,连着问了五六个人,愣没哪个晓得“黄瓜”的名字是什么。千万不要忘了,那年头阶级斗争一竿子插到底,平时喊个把绰号问题不大,可一旦把人家的绰号写上册子,哪怕老黄才三脬牛屎高一个孩子,动辄那可能就要上纲上线的,所以会计不敢马虎,慎重地登门找“黄瓜”本人求告。老黄当时摸了摸脑勺,竟然没能够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来,一时间尴尬得好像当场被会计拿着他偷偷在集体地里掰了两个包谷——好一下儿才恍然地回忆起来,一回忆起来,乃欣慰地说:“想起来了!会计,我想起来了!克勤!我叫克勤!克勤克俭的克勤!”
可见那时节农村人多没身份。“黄瓜”还算很不错的雅号,另有那叫“毛狗”、“母鸡”、“牛崽”、“猪儿”的,甚至还有连“猪狗”都不如的,什么“尿棒”啊,“狗屎”啊,要么是别人呼出来的绰号,要么,他爹妈一开始就没把他当人,才出世就赐了这么个名儿,不过也很可能是,他们认为小娃的名字取得越贱,他生存能力越强。如果你一辈子没得出息,哪怕活到一百岁,人家也猪啊狗啊屎啊尿啊地叫你,叫得矢志不渝,叫得肆无忌惮。老黄,这样的称呼可从来不属于哪一个老农,人不会叫,叫了他也不敢受,一旦恍惚应了一声,恐怕至少要忐忑不安地睁着眼睛过一晚上,甚至两晚上。尽管我们的媒体惯称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叔叔”、农民“伯伯”——一介老农受别人一个“老”字似乎无所畏惧,但他岂敢身受!或许您不知道,我们农村人最在乎这个“老”字,爱拿它与辈分裹搅,果真你的辈分比我老,我心甘情愿地叫你“老爷(爷)”、“老祖公”、“老外婆”、“老菩萨”,但如果没有可信的依据来证明我们的辈分高下,你若叫我“老郑”,我是断断不敢答应的,因为我不晓得“老郑”在这里其实只是对年长者的一种普通称呼,而误以为意思是“姓郑的老辈子”。你问我为啥不晓得而误以为?因为,我是农民,我没得文化,我见识不多,我谨小慎微,我猜忌。倘在春节期间,你喊我一声老郑,我还以为你想敲诈我:让我给你发压岁钱呐。当然,农民其实也希望得到尊重,比如,当你买他的粮食时,他很怕你说他的粮食不好,因为,每一颗粮食都是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地壅出来的;农民也喜欢托老,比如,我们和那些关系不错的人,互相之间经常嬉皮笑脸地以“老娘”、“老子”自居——和种粮食一理,这也是令我们非常有成就感的——岩脚小二,但凡爱托老的婶子嫂子让他喊她老妈,他无一不喊,聪明人以为他傻,说,小二,你吃她们亏了,小二说,我吃亏,我老爹不吃亏哩:整得人家哑咪咪。从“小二喊妈”,看得出我们农村人……有时也会有超常的思维和理念。
老黄就是我们靠山村一个具有超常思维的农民。正因为他超常的思维,给他带来非同寻常的经历,也就赢得一个“老黄”的称号——你们政事单位或工矿企业才有的那种文屁儿朝天、不敢指着名儿戴的绰号。
“黄瓜”之所以变成“老黄”,字没变多,话没变长,无非就是改了一字,但,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如果老黄能够坚持将国民教育接受到底,现在他名字应该在某一级单位的退休花名册上,那么,别说“老黄”了,就是叫他一声“黄老”,也是大有可能的。要说老黄的童年和少年,十分不幸,也十分万幸。不幸在于,他老爹是个地主。20世纪中叶——老黄种过烤烟,他说,一株烤烟的烟叶,分为脚叶、中叶和顶叶,中叶么,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嘛——咱农村革命群众,尤其是刚刚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连老婆都还来不及找上一个的农民革命群众,谁会见得地主了,谁不朝老黄的老爹吐口水了,谁不骂老黄是地主崽子了,幸得老黄老娘早些年死了还好了,又幸得老黄姐姐妹妹没得一个还好了,要不然……人、财都要被摊公了。可想老黄童年时代过的是什么日子。老黄12岁的时候,他老爹吃不过批斗,一个打雷下雨的晚上,悄悄抛下老黄,投堰塘死了。没曾想,他这一死,却改变了老黄的命运。
那堰塘是一个重要水利工程,肩负着灌溉下面两三千亩槽子田的任务。当时,田里的秧子正在抽穗,经管堰塘闸门的人恰是生产队长的儿子,因见连日晴好,也就没放下闸门,一家人都给他老外婆庆生去了。当夜一场雷雨下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人们老早起来看田,一槽田安然无事,再上堰坝一看,四五十米深的山塘只差指甲厚一线水就漫下槽子了,一时额手称庆,俱说亏得队长儿子早些时放下闸门,否则的话,几千亩的米箩算是完了。队长儿子见塘水没往槽子里泄,也自以为他原本就把闸门放下去了的。老黄不晓得老爹哪儿去了,一连哭了十天,亏得好心的婶婶伯娘看顾。我们知道,人死在水里,三天后会自行漂到水面,但老黄的老爹干嘛头十天了还没漂起来呢?
那一夜雨,实属百年难遇的大暴雨,周边农业受灾的地方很多,因此,十天后,县里组织的参观团来学习我们的水利工程。队长要让各级领导和客人看到渠水绕山转的场面,当场让儿子开闸放水。队长儿子抽不动闸门,以为坏了,赶忙潜下水去检查,一掏水口,掏出老黄的老爹来。老黄的老爹头十天了还不漂起来,原来是卡在水口里了。
当着县、区、公社三级领导和来自各地的参观者,队长沉着冷静,现时编了个老黄老爹学黄继光舍身堵水眼的英雄事迹。当时比较注意抓典型,县里面的领导当即说,一个曾经对人民有罪的人,通过思想政治改造,现在敢于为人民献身,这是多么好的典型,放着这么好的典型,怎么不早上报?
黄家又出了一个英雄,老黄顿时成了烈士遗孤,不仅生活有了着落,而且马上被县简师破格录取。读了一个月简师,接着读短师,半年后,进入初师,读了三年初师,紧接着就读中师了。如果老黄持之以恒坚持接受国民教育,读完中师是要保送高等师范院校的。但老黄为了早日生儿育女,带着当时和他的同桌、现在和他同眠的老伴儿,偷偷跑了回来。
老黄接替了会计的工作,就是那个第一个把老黄的谱名写上花名册的老会计。老黄退学,是他一生中第一个精明之处。当时大批“学而优则仕”,教书先生无不成了“臭老九”,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老黄心想,既然如此,这书没得读法了,不如回家抢工分来得实惠。
由于有知识,脑筋活,1979年,老黄荣任生产队长。当会计时,老队长还可以在他跟前托大,习惯性喊他“小黄瓜”,当队长后,大家都尽量把习惯改了过来,不多时,“黄队长”也喊得是自然巴口。如果我没记错,我们的土地是1982年包产到户的,1980年、1981年先搞了两年互助组,我们这一组是我老爹当组长。互助组按自然寨落划分,老黄所在的黄家坝和我们不是一个互助组。以互助组为生产单元,相当于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责任心都明显提高了八竿子,我们组的包谷和稻谷产量在1980年就翻了一番。但老黄们那一组却翻了四五番,令人好生惊奇。他们组有一块大土,叫贵州大土,那是一块火石地,也就是说,它是一块石多泥少的瘦地,大集体时每年只掰不到十背篼包谷棒子,而且尽是些尖镖镖。但1980年有目共睹,贵州大土的包谷苗有草扦那么粗,结的包谷棒子水牛角子那么长,老黄他们收包谷那天,我们特地守在地边数数,一块贵州大土,竟然掰了四十一背篼包谷!
我老爹和老黄有交情,有一天晚上约老黄来家喝酒,老黄不说我们不知道,他一说,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老黄已经悄悄地把他们组的田地分了!那是1979年冬,老黄把他们组所有的户主都召集到家里来,说,依我看啊,种地如找媳妇,现姑娘只有一个,小伙有一大帮,眼见着希望不大,谁肯用力去追,不如我们商量一下,一个姑娘变成一帮姑娘,各人一个,自去用力,好不好?脑筋呆板的人说,一个姑娘怎么变成一帮姑娘?脑筋活络的人说,啊?你要分土?!老黄说,嘘!低了声道,什么分不分呀,你能把它带到外国去么!老黄就把他们组的田地分了,明着大伙儿一块下地,实际上昨天种你家的、今天收我家的,既然是换工,大家都不再敷衍土地,否则你敷衍我,我也敷衍你喽。老黄叫大家都签字画押,分土地的事一点风声也不准透露,要不然,他说,这恐怕是杀头之罪哦。
我老爹说,明明知道这是杀头之罪,你还分?老黄得意一笑,道,那是吓唬他们的,免得守口不牢惹是生非嘛,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我就看出了方向,否则,你借我十个脑壳,我也不敢。这不,土地不是分了吗,一百年不变。包产到户,我老爹一声长叹,有文化有脑筋还是好,所以决计让我读书。现在报纸有没有真正到村,农民群众是不是真正都读报纸,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那时报纸是真正的到生产队的,生产队是要组织社员学习传达的,广大农民群众听没听进去谁也不晓得,但老黄是逐字逐句进行研究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农村要搞改革——只凭这两点,他就敢分田分土。为啥?他想,田地分给大家,没谁会带得出国,犯不着什么阶级斗争,这是其一,其二,哈哈,我这是改革。
正当大家都在称赞黄队长的时候,颇出人意料,老黄却主动辞掉了队长职务。
因老爹是地主,老黄家房屋早就充公变成了学校,老黄和婆娘儿女住的地方牛圈不像牛圈、窝棚不像窝棚,天上有月亮,则屋里见星星,天上下大雨,则屋里水滴滴。老黄吃不过被他拐带的老婆埋怨,决定重新建房。建房建房,那时私人建房容易吗?告诉你吧,我们靠山村谁家要修一个房子,你得趁农闲时节——那时庄稼收完也才有几颗粮食——磨下石把包谷米,备下百十斤烧酒,然后请一帮工程(“工程”在我们黔西北农村特指劳动力),分一些去割茅草,分一些挖土筑墙,一层三间盖草的土墙房,工程尽力一点、手脚麻利一点,也才能赶在落雪下凌之前竣工。如果遇上下雨天气,搁工不说,新墙还可能被雨淋垮,那就可能成为半拉子工程了;尤其筑到山尖(山墙的顶尖),主人家运气差些的话,筑墙的人一个倒栽葱掼了下来,你就捡着医、捡着埋了。所以我们宁愿赖在老祖宗留下的破房子里,也不肯轻易建一个新的,太麻烦,太费力,风险太大。
老黄身为队长,经常开会,公社他去过,区里他去过,甚至还到县城领过一回奖状。他觉得,大地方的砖房真是好!一是牢实,坐百把年不成问题,而且耗子在墙上咬不出洞洞;二是高大,土墙房哪敢筑它那样两层三层!老黄在县城看见一座四层的砖房,当即赞不绝口,说,我妈,要是这厢(栋)房子搬到我们那里,大家一层摞一层地居住,能节约好多土地!从那时老黄就有改造住房的打算,加上他那个婆娘一再埋怨,一再地后悔当年是多么幼稚,所以修房子的事他也就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砖房是说建就建的么?不是。那时只有公家有能力修砖房,我们公社,公校,原来的用房都是从地主手里专政过来的木架子房,直到1970年代才各修了一幢砖房。我们寨这几个有着远大抱负的娃儿,无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目的就为考入八里外的公校去坐几年砖砌的教室,就像今天城里的少男少女拼命地进行嚎春练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到电视上唱两分钟超男超女,可见理想的树立有多重要。但老黄修砖房的理想在当时我们那儿根本就上不巴天下不着地,砖在哪儿,瓦在哪儿,泥水匠又在哪儿。那时的泥水匠,弹得很喽,那是城里的建工队,正规的工人老大哥,不得大型“修建”根本搬不动他。而“修建”两字,在我们听来就是“银子”,搞修建的人是红人,管修建的人是要人。
有志者,事竟成。有一回,老黄非常荣幸地被组织到一个砖瓦厂参观,因他想修砖房,当时就多了一个心眼,别人走马观花,眼在看,心里想的却是参观结束后那一餐久违了的“地主之宜”,他呢,大搞调查研究,真怕忽略了某个细节,直把整个生产过程都默记在方寸之间。我妈!老黄暗道,同样是泥巴做的材料,人家怎么就住砖房哩。
老黄带着婆娘儿女全上阵,但凡有月亮的夜晚,都在竹林边用胶泥打砖,打完一坑胶泥,婆娘儿女自去睡觉,老黄赶着水牛又踩一坑,胶泥被踩得糯的拔不动脚,踩得月亮落坡,这才休息。砖够了,又做瓦,从栽完秧子做到割得谷子。收完庄稼,老黄将砖瓦满满地烧了一大窑,出窑一看,尽管因技术缘故有青有红,但毕竟柔软的泥巴变成了坚实的砖瓦。泥水匠是请不起的了,老黄自己操刀上阵,婆娘儿女给他递砖拌浆,不分白昼黑夜,只要队里没有事务,只要天气允许,一家人都在搞“修建”,竟就赶在雪凌之前,砌出一栋两层共八间居室,捎带一间堂屋的砖瓦房来。我们这边遍地都是杜鹃,春来二三月,花开百十里,说是“花园”那太小了,须用“花海”才能形容。老黄用杜鹃树棒做楼枕,杜鹃木板做楼板,杜鹃木板结实而暗红,即便到了今天,好似新的一般,走在楼板上有一种特别古典的感觉,木气冲鼻,隐约可闻一种原始的芬芳。
去年三月间,“百里杜鹃”的花是我记事以来开得最好的一年。“百里杜鹃”是20世纪80年代才得的名字,报纸电视的报道说,在我们县“发现百里杜鹃”,当时我还年少,对“发现”一说很不理解:明明这些花朵就在我们身边,就在坡上,它们又没躲谁,说什么“发现”?“百里杜鹃”被“发现”以前,我们眼里它无非就是一朵挨着一朵、一丛连着一丛、一坡多过一坡的山花,收工回家,收牛回圈,花儿被我们折得遍地都是,那么多,谁会可惜。被“发现”后,说,这是风景,叫“百里杜鹃”,“国家级森林公园”,全世界最大的天然花园,一朵花也不许折了,折一朵罚五块钱(过去是五毛)——相当于我们十个鸡蛋被狗吃了。每年三四月间,花开的时候,看花的人每天成千上万,那时节正是我们栽包谷的时候,拉着看花的人的客车轿车一串串地从我们地边马路上跑过,他们得闲看花,却害得我们栽包谷也没心思了,定定地站在地里,脑壳像向日葵一样随着那些车队转动。有一天,我们数了一下,单是从我家地边这条路上经过的车子就有518辆。
“百里杜鹃”整个林带呈环状分布,绵延五十公里有余,总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我们这儿是“百里杜鹃”主要景区,尤其黄家坝,其它地方的杜鹃品种单一,要么清一色马缨杜鹃,要么清一色露珠杜鹃,而黄家坝一带,杜鹃品种多达二十多种,比如“马樱”、“团花”、“迷人”、“露珠”,不一而足,世界上的杜鹃有五个亚属,这儿竟占了四个,被称为“黄坪十里杜鹃”,但凡看花的人非来这里不可,只要看了这里,其实也就够了,有句诗叫什么来着,“黄坪归来不看花”。黄坪,这是标在景区导游图上的名字,其实指的就是黄家坝,就像黄克勤其实指的就是“黄瓜”。
杜鹃花节的前一天下午,黄家坝来了一些人,他们一共乘坐三辆小车、一辆面包车。在游人如织的花区,这当然并不特别引起人们注意。三三两两流连于花丛的游人,该留影的留影,该乘凉的乘凉,谁管谁在干啥。
老黄的家,在一大块花荫里。当然,除了姹紫嫣红的杜鹃,屋后的沙桐、房前的竹子也是青翠欲滴。老黄闲来无事,摆一张白杨凳子坐在一株桂花树脚,饶有兴趣地数着在花区沥青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马路与他家只隔着几亩见阔的草地,草地上放着他家一只胖嘟嘟的黄牛。
那时天快黄昏了,遥远的对门山峦,托着一轮又大又圆的夕阳,看过了花的大小车辆,一辆,又一辆,渐次离开花山。
十五……二十……二五……老黄数着离去的车辆。……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噫,这四辆车缓缓靠着草地停了下来。三辆小车,一辆面包车。老黄的牛看了看它们,疑虑着掉转身来。四辆车上下来十多个人,指指点点,顺着弯曲的小路朝老黄家走来。
“……新农村建设……”老黄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
那天晚上,这帮人中有几个在老黄家住了一夜。老黄家屋子宽哪。老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在广州一家跨国公司,一个在北京当翻译,一个在贵阳上大学。广州太热,北京有沙尘暴,他和老伴去住了住,觉得还是没有我们的“森林公园”好,坚决回家来了。
陡然来了这么多人,老黄老两口赶紧招呼,又是敬烟,又是倒茶。茶是开春才从坡上捋来的苦茶叶,喝时苦,回味甜,儿女每年这时节让他们一袋一袋寄过去。老黄家围着竹栅栏的院坝干净整洁,夕阳无限好,空气也清新,一群人舍不得进屋,就在院里坐地。老黄听出来了,明天似乎有什么重要人物要来看花,这一帮子是先来做准备工作的,无外乎一个卫生,一个安全。领头的好像是县里面一个什么领导,喝了一杯茶后,说,活路做完了,你们回去吧,我看老人家这里环境挺好的,我想在这住一晚上,小王,小周,哦,还有吴局长,你们三个留下来,我们凑足四个,晚上也好打打扑克,啊?
老黄留不住,分离的那一群人走过青草地,爬上小轿车,爬上面包车,三辆车别了别脑袋,小声地走了。老黄陪留下的四人院子里坐着,月上东山,老伴搬出张竹编的方桌,就摆在桂花树下,树上原来挂着葫芦样的一盏灯,倏地亮了。老伴端出几样菜肴,一个腊肉蒸干椿,一个土鸡炖天麻,一个干煸土豆丝,一个凉拌鱼腥草,再有炸花生、炒鸡蛋,这都是现如今农村拿得出来的,酸菜是刚从泡坛里捞的,豆腐是昨天就点的,蘸水是辣椒拌豆豉。老伴上菜,老黄就回屋抱来一小坛自酿的水花酒,哗地倒一碗,哗地倒一碗,每人倒了一瓷碗,小王说他是司机,不能喝,那个要给老黄借宿的头儿对他说,今晚不动车了,就喝一碗吧,这是水花酒,须是到农家才有口福的。老黄说,一坛米酒,有啥稀奇。头儿说,哪里,如今到农家吃饭真是太好了,什么都是原生态的绿色食品,就连鸡蛋都是真正从母鸡屁股里屙出来的。就有一样,头儿是有点遗憾的,他想吃包谷饭,老黄家却没有。老黄惊讶地说,你们城里人也吃得下包谷饭?头儿说,二十年前,我也是农民,无非是运气好,考取了一个工作。老黄说,那你应该知道,我们都说包谷饭是“火药面面”——最难吃了,农村娃拼死拼活地读书,就是为了考出去,就是为了吃口大米饭,好怪,你倒又想吃包谷饭。
头儿和老黄聊到月过中天。小王提醒他,扑克已经从车里拿来了,他说,不慌,老人家的故事好听哩。老黄的故事就是他几十年来的经历,如果不喝了点米酒,如果那个头儿一点也不随和,他是不肯就说的,那么,头儿想知道老黄的“转业记”,恐怕只好等到我这篇小说杀青再说。
早上起来一推窗子,近处翠竹轻喧,远处花海茫茫。头儿对老黄家楼板赞不绝口,说这一觉是他有工作以来睡得最香的一觉,而且他做梦到中世纪的欧洲旅游去了。头儿就对老黄说,你应该搞一个家庭旅馆,农家屋,农家饭,农家乐,保证客人把你门都挤破。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老黄这阵子老是盯着那些车子游人琢磨,隐约觉得有点什么文章可做,但就是没想出什么名堂来,或许是老了的缘故吧。头儿说:“靠山吃山,你老这是坐在金山上哪。”头儿的话显出他见多识广,他说,20世纪人们向往城市,连毛主席都要去坐北京城,现在呢,倒过来了,乡村旅游火得要命,那些城里人是最想到农村来的了,恨不得就在农村坐地,只可惜没得农村户口。老黄说,怕不是吧,我们村有人到大城市打工,想住下来,但人家说他没得城市户口,就撵回来了。头儿说,他去的是哪个城市?……啊!污染那么严重,八抬大轿抬我去住,我也不住!
头儿让小周付食宿费给老黄,老黄哪里肯收,说,我们农村人串门串惯了,东家遇到东家吃,西家黑了西家睡,难道说也要收钱不成。头儿说,性质不一样。老黄说,有啥不一样,不都是吃不都是睡。头儿说,我意思是说,我们是干部,干部到群众家吃住,非付钱不可,这是纪律。老黄说,这纪律不好,明显把你们和我们区别开来了。头儿噎了一噎,最后说,我刚建议你搞家庭旅馆嘛,就当你的旅馆已经开张,我们进旅馆消费,该得付钱吧?老黄说,你不提旅馆还罢,既然提醒了我,我就更不会收你钱了,你这么个点子,岂止值这么点钱啊!头儿说,唉,我实在说不赢你喽,那么,只有祝愿你两老的家庭旅馆快些开业,多多找钱喽!
头儿一步三回头地看老黄家砖房,说,好,好,太有乡村味道了。老黄送他们过草地,说,好啥,连瓷砖都没贴一块。头儿说,噢!千万贴不得!一贴就不是原生态的了!你老这房子,比那些贴瓷砖的好!要在外国,贴瓷砖那只有卫生间!
老黄没想到,都到今天了,还有人说他这房子好!
当年他这房子刚一造好,立马在山前山后就引起了轰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卖一季粮食,我也要修这样一厢砖房!”
“黄队长,您烧点砖瓦卖给我们嘛!”
土地下放,农村条件发生了根本转变,谁不想住砖房哩。
老黄几时想到过要办什么砖瓦厂,直到房子造好引起乡亲们惊奇和羡慕,这才猛地在心里说道:
“哈,来菜了!”
遂连队长也不当了,邀约头十个家屋族内,迅即办起来一个砖瓦厂。老黄分析了,土地既然包产给各家各户,再当队长徒有虚名;老黄调查了,十之八九的人家,破落房子都坐了好几代人,半数人家想修新房。他自家修起来的这厢房子,恰像打了一个广告,砖瓦厂正逢其时。
“黄队长”变成了“黄厂长”。
砖瓦供不应求,一时买不到他砖瓦的,就像李逵埋怨卢俊义只吃宋江请客而不吃他的请客时说:“砖儿何厚,瓦儿何薄。”——黄厂长,你为什么卖给他,不卖给我?
老黄的砖瓦厂现在早就停办了。但说实在的,我最怀念他们那个砖瓦厂。如果有谁问我,你对你老家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一定就要给他讲:“在我年少的时候,我家那儿啊,有着那么一个砖瓦厂……”
砖瓦厂离寨子不远,在一个小山坡下,中间一间窑井,四周是几口泥塘、几个场坝。窑井是烧砖瓦用的,泥塘是踩泥巴用的,场坝是堆砖堆瓦用的。踩泥、做瓦、熄窑子,这都用水,水是从一里多外的堰塘引来的,老黄的老爹就死在那个堰塘里。
泥塘里,一个人和一条水牛。那人一只手绾着牛鼻索,一只手挥着一根长长的竹枝,驱使水牛在泥塘里转圈子。泥巴是胶泥,越踩越糯,到后来,人和牛拔脚都相当吃力,拔出一只,“叽”地响一声,拔出一只,“叽”地又响一声,让我们这些蹲在塘沿上的娃们有一种吃糍粑的感觉,仿佛牙齿都要被那一声“叽”给扯落。让我们好笑的是,当水牛一翘尾巴,那人慌不迭地在塘沿抓一把早就准备在那儿的撮箕,飞快地接在水牛尾根,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水牛尾根一鼓,叭叭叭就屙下半撮箕屎来。那人得意地说:“老子!你还没立尾巴,我就晓得你要屙屎!”有时却防范不及,叭叭叭叭全屙在泥塘里,那人一边将屎捧进撮箕,一边倒霉得直皱眉头,大声喝骂水牛:“你这挨刀砍颈根的哟!”
踩好一塘泥,人和牛转到另一个泥塘去踩,五六个打砖的人到这个泥塘来打砖。泥塘一转都是打砖石,打砖石是一块面儿平整的青石,上面放一只砖模,槲栎枋子斗的。打砖的先在模子内框及框下石板扑一把煤灰以免泥巴粘在模子上——煤灰是用细眼竹筛筛过的,细得像是面粉,用一把弓——弓弦是一根钢丝,划一坨踩得糯糯的胶泥,高高举起尽力朝模子里一砸:模子里顿时塞满胶泥,接着弓弦贴着模子的上棱一刮,切掉上面多余的泥巴:剩在模子里的就是一块砖了。有时,模子会有个把角儿没被泥巴胀满,打砖的便用拇指朝那只角一摁:宁愿在砖上留下一个拇指印儿,也让一块砖四角方正。在砖上撒一层灰,这才把砖漏在一块木板上——木板上也撒了灰的,再打一块,也是放在一块木板上,端去摞在前一块砖上,木板摞砖、砖摞木板,一层摞一层,直有五七块砖,这才贴胸的一摞都端去场坝里,一块一块侧棱的摆在一条平埂上,堆到人高,盖上“毛扇”,以防雨淋。“毛扇”状如羽毛,两片竹子夹米草。
场坝里“栽”着转盘,他们把瓦桶站在转盘上,就用一把弓去割胶泥。那弓十分特别,特别在它有两根弦,两根弦的间距就是一块瓦的厚度。割下来一块胶泥,捧哈达一般,把它围在瓦桶上,一边顺时针拨转瓦桶,一边用泥掌迎着瓦桶的旋转将泥面抹得光滑。把瓦桶拎到场坝上,桶把儿上不知什么机关,又不知握着把儿的手怎地一动,那把儿原来竟是两块合成一块的,这时有一块就往内一错,瓦桶一缩,一下提了起来,只留下一只“泥桶”站在地上。等一块场坝都站满了“泥桶”,放眼望去,一坝子圆圈!给人的视觉享受,说不出来的舒服!“泥桶”稍干,有硬度了,马上“挤瓦”。好怪呀,他们的两手合着一“挤”,一只“泥桶”裂成四块瓦片,不成五块,也不成三块,就是四块,而且一块不比一块大,一块不比一块小!一块块也是站在平埂上,好像括号背括号,码的有人高,也盖上毛扇。
太阳当顶的时候,老黄和工人们常拖几张毛扇坐在浓荫里打扑克——看那扑克,旧得四角都没了。又不赌钱,倒认真,看的人你要“报”他的“点”,他一准脸红脖子粗地跟你急了起来,我们是很想看的,却吃他们轰鸡轰鸭般撵过一边,一边还紧紧地掩着手里的牌,好像什么金宝卵似的,不让人看见。
好,我们去泥塘里偷胶泥玩,就在那打砖石上,要么捏小汽车,要么做蛐蛐房。胆大包天的,爬到他们做瓦的转盘上去,盘腿坐地,叫别的娃儿“转”他,一“转”,咔嚓一声,那转盘像打开的伞,有一两根“伞桠巴”就断了,打牌的人听见,慌得举眼来张,娃们早飞飞挞挞的跑翻坡背后去了。更倒霉的是,哪家的牛为了蹭痒,把一堵还没风干的砖瓦蹭翻了,第二天老黄看见,满寨子问:“哪个娃放牛掀倒了我的砖(瓦)!”娃们哪一个会肯承认。转盘给坐断了,砖瓦给掀倒了,老黄见找不着主儿,只默默的,修的修,拣的拣。
所以,至今我特别怀念老黄他们那个砖瓦厂。
但是,老黄他们那个砖瓦厂毕竟是在多年前就已作古了。窑井半塌不塌、缺缺拉拉,内壁铁红,窑底一年到头总有一层面酱一样的泥浆。泥塘的沿儿被挖倒成斜面,里外自然过渡,变成V形凹地,种上了庄稼,只是,胶泥不肥,好多年还没改良过来,上面的庄稼并不好。在地边围栏发现一两片当年夹毛扇的竹片,黑黢黢的,却勾起人对时光的无限怀念。
老黄的砖瓦厂红火了四五年光景。之所以又不搞砖瓦了,因为后来出了一种“水泥砖”。那是一种空心砖,材料是水泥和石砂,机制,有点像我们量包谷量米的筒子,所以我们也叫它“筒子砖”,这种砖块头大成本低,砌房的造价远低于土砖,老黄眼瞅着竞争不过,且那时,周围砖瓦的市场需求基本饱和,遂果断把砖瓦厂停了,转业种烤烟去。
记得那好像是20世纪90年代了,种烤烟最红火。大方的土壤和气候出产优质烤烟,制成烟卷后,香气质好量足,味道醇和舒适,烟灰白色。据说,一盒“中华”牌香烟中,有一支的烟草就是我们大方的。
“黄厂长,放着企业家不干,怎么又当起农民来了?”
“啥,人总是要回到泥巴里头来的嘛。我是农民。农民不种地,还叫农民?”
老黄的烤烟一种又是五六年。说起来老黄真是肯钻研,几年书没白读,每晚上抱着书本凑在煤油灯下啃。做一行,习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后来推行的打顶啊、抹芽啊,那些个种烟技术,老黄早就悄悄实践出来了。他每一年种烟的收入是四五万,别的人家想上万元,只差奔出屁来。老黄年年是烤烟种植大户,每年的烤烟大会,假如老黄不来参加,会议的组织者真不知找谁来介绍经验。老黄的会开到省里面,不光讲了一通话,还抱回来一个沉甸甸的奖品,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嘛,幸好那年我们这儿通电了,不然老黄只好拿它当一张小方桌给孙子做作业用。也就那一年,老黄变成了“老黄”。此前是有名的“黄烤烟”。“黄烤烟”名副其实,第一,老黄是烤烟大户,第二,烤烟不黄不管钱,有“软黄金”之称嘛,而老黄的烤烟,哪一片叶儿不黄?“黄烤烟”的成名,是在老黄参加的第二次烤烟表彰大会上,我们县长想问一声老黄来了没有,却一时没记起老黄的名字,就问:“黄烤烟来了没有?”从此叫开,就像从前人们叫他“黄瓜”,也不记得他名字了,只晓得是叫“黄烤烟”。
“黄烤烟”怎么变成“老黄”?
1996还是1997年,反正就那年把儿,我们县办了一个科技扶贫化工厂,专门生产烘烤烟用的远红外涂料。生产出来后,不是要先让烟农试验一下效果么,可一听说试验,好多人不敢用,害怕把烟搞坏了,坏了一房烟那可是好几百元,开不得玩笑:谁爱试验谁试验去,失败,我躲过一劫,成功,我再拣便宜。老黄呢,一听说研究出了这种东西,跌跟挞斗地问进门来乞讨。他背了一挎包关于涂料的资料回去,关起门来研究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才打了个哈欠走出屋来,拌涂料去烟房涂火管。那年老黄尽管拨了点土地学种西瓜,但九月份烤烟售完,竟然比上一年多收入六千六百块。
老黄被请到各处去指导烤烟生产。于是,开始老黄、老黄地叫他。
那年,农民黄克勤的“事业”达到了他平生最高的地方:一架飞机把它抬到了万米高空,他端着一杯随机赠送的冰牛奶,为下飞机后即将展开的“教学”苦练普通话。人家不喊他黄瓜,也不喊他黄厂长,也不喊黄烤烟,连老黄都不喊,喊的是:黄专家,一口一个“黄专家”。老黄高高坐在主席台上,下面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们不仅带着两只耳朵来,还带了一只笔、一个本子,他教他们如何栽烤烟,如何使用远红外涂料。大方话虽说属北方语系,但我们说普通话是很不标准的,夹杂了太多我们的习惯发音和特别老土的方言,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普通话是“大方普通话”,简称“大普话”,一时时国语,一时时土语,此一语,彼一语,就像包谷耖大米。所以难免下面的人有时就不太听得懂老黄的演讲——尽管他连坐飞机都已经努力练习过普通话了,他们歪头睁眼地望着老黄的嘴,企图从他的嘴形来辨认吐字,但瞎子点灯白费蜡。幸好对方和我方早就料到这一点,在老黄的身边安排了一名“翻译”,实在太费解的话,就给大家翻译成标准普通话,或是意译。
老黄去“讲学”的回数挺多的,有一回,一连讲了40多个县,每天一回到宾馆,第一件事先把舌头理抻,因为说大方话从来不卷舌头,而他一天都在说普通话,从前操练太少的舌头就卷得都抽筋。
这世界上吸烟的人越来越少。原先,大方36个乡镇个个都种烤烟,而现在早已砍掉了半数多乡镇的种烟计划。自然而然,精明的老黄不会再种烤烟。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卖烟时你得求爹爹告奶奶,叔叔伯伯,我这一捆烟明明是二级,你咋说是三级?是哪一年来着,我爹妈烘出一房好烟,金光闪闪,一个烟贩出两千块钱要直接买走,他两人不肯,还以为,烟贩都肯出两千了,背到收购点至少可卖二千五,谁知,后来一卖,什么二千五,连一千块钱都还差二百五,两人悔得肠子搓索子:晓得这样么,就卖给烟贩子算喽!
老黄种菜啦。
收完庄稼,老黄带上学费到贵阳学艺。都说技多不养家,但老黄才不管它,这一回是学种菜。连种菜也要学?老黄对老伴说,要学。寨里一个在农业局工作的,回家休假时种出有他拳头大一个的西红柿,惊得老黄眼睛鼓得比核桃大,听说贵阳有专门的种菜师父,马上赶班车跑贵阳。
坐了一天班车,回到大方县城时天已天黑,老黄没住旅社,连夜赶回寨里。次日,老黄雄心勃勃拎了锄头到园子里,先挖一个半间屋大、半人深的坑,然后铺一道草粪、布一道草木灰,把师父送的番茄种一撒,盖上一层细泥面,便踌躇满志地等着秧苗出土了。果真是意料之中,秧苗很快便出土了,探头探脑煞是招人喜爱。老黄正在欢喜,不防祸从天降,一场雪凌,番茄苗悉数冻死。
老黄没想到事情如此糟糕。但办法总比困难多。那时我们用的电是用堰塘的水发的,电灯没得油灯亮,师父教的“电热保温”敢情是用不上。但老黄狡猾,很快想出煤火保温这一招。他一边悔恨自己的简单求快,一边老老实实地砍竹子盖了一个塑料大棚。棚地里居中挖一槽子,用砖拱成小火道,这边火口,那边烟囱。播下菜种,升起煤火,老黄觉得大功告成,呵着冷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得意洋洋地走亲戚去了。又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太阳忽然就跳出来了。等连滚带爬地赶回大棚,老黄瞠目结舌:一大棚菜秧“煮”成菜稀饭了。悔断肠子,又奈其何。老黄总算再一次认识到,科学的东西,少一样环节、少一样东西都不行,这才又老老实实地买了一只温度计。
后来,老黄的反季节蔬菜三月份便可上市。大方县城蔬菜批发市场的鲜菜,数老黄的又多又好。老黄用大棚种菜的经济效益是种粮食的几十倍,一个两分地的大棚,老黄可以收入五六千元,这个数字也是种烤烟所不可企及的。乡亲们见老黄种菜又发财了,谁不想种啊。当年栽烤烟开始使用远红外涂料时,老黄那是有一点愤懑的。当时,乡亲们既想吃螃蟹,又怕螃蟹咬,不肯参与试验,老黄就遮了一手,明明自己通过反复研究资料已经知道使用涂料绝对增收,但就是不告诉乡亲们,后来老黄那个悔,只因隐藏了一个信息,当年乡亲们一家至少少收入一两千元。现在,乡亲们想种菜,老黄就不再把技术藏藏躲躲了,他也发现,乡亲们对自己越来越信任,不凭什么,就凭这种信任,也是知遇之恩哪,也是看得起人哪,也就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发明的“小火道温床育秧法”尽心传授给他们。老黄还订了一本《长江蔬菜》杂志,自己研究透了再教乡亲们怎样做。靠山村的菜农越来越多,从老黄1户增加到400多户,因为人均收入达到2600元,靠山村被命名小康村,又被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我们村能够发展成一个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村,老黄真是功不可没:从单一的瓜菜到10大类100多个品种,从发明小火道温床育秧法到牵头成立蔬菜协会,从一挑一背进城叫卖到互联网上接单批发,老黄帮乡亲们做了多少事哟。
你看你看,老黄的菜种得好好的,一大清早跑到村长蒋银八家来,说什么,又要开旅馆了。老黄早就被乡亲们称为“发明家”了,蒋银八说:“尊敬的黄发明同志,我请问一下,好不?”
老黄说:“客气个啥。”
蒋银八说:“说来您老别生气,当年您老的父亲明是地主,但吃的包谷饭穿的麻布衣,哪里有您现在的一天好日子过,这么多年您做的哪样不找钱,如果我估得不错,您老的家底不得十万也有八万。娃儿又有出息,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一年少说二三十万薪水对吧,还有一个读大学,取的又是重点,书学费人家全包根本不要你拿一分钱。那么,我就斗胆请问了:您老七老八十的年龄,还开什么旅馆,难道说还不知足,难道说还短那么点钱用?”
老黄说:“如今的政策,只要勤快,谁缺钱用。”
“那……”
“银八你听我说——”
你提到我爸,让我想起伤心的往事。是的,他是地主。但他是怎样的一个地主啊?你说得对,穿的是麻布衣裳,吃的是“火药面面”,你不知道,想焖一碗大米,却生怕被人知道,知道了就要砍脑壳。政策就是那样。政策决定了的。记得大集体时,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没哪天没做满八个小时,但究竟多少人家吃过饱饭?你看,土地一包,情况立马转变。政策是越来越好,只要脑筋开窍,人又勤劳,找钱的门路那是千条万条。托政策洪福,我黄克勤确实找了些钱,现在家里又没啥负担,真该享享清福了,但是——
钱是不能嫌多的。只要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只要是一手一脚地找来的,再多也不能嫌。我爱看报纸,报纸上说的什么?说……哎,你看我这记性,老了,不好使了……嗨,对了,报纸上说了嘛,要富而思进!
人啊,不能贪钱,但要爱钱。有钱不找,那要得罪财神。现在遍地都是钱啊!找都找不尽啊!找了还有、找了还有,如果不及时地找,它就会像坡上的菌子,烂了!有钱你不去找,气死了财神菩萨,等你想找的那个时候,叫你找不到了!
百里杜鹃不是一个例子?如果几百年前我们就晓得它的好处,就晓得拿它来卖门票,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多找几百年的钱?年年都可以找。那,我们还会砍花树做楼枕?怕不自砸饭碗。你看,银八,是不是:百里杜鹃有找不完的钱,但如果我们不找,把花树全都砍了,岂不是想找都找不到!
花快谢了的时候,县里有个领导,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他对我说,可惜了,可惜了。我问他,什么叫做可惜了?人家说,放着一大坡钱,你们为哪样不找?
蒋银八一惊,光着脚就站在老黄面前:“啥,一大坡钱?在哪里?”
老黄道:“他说,我们坡上那些花,全都是钱。”
蒋银八一听泄了气,一屁股坐回去,叫婆娘:“拿我昨天买的毛皮鞋来!”老黄啊,蒋银八说,他说的那些钱,都是他们的,难道我们可以提着根竹竿拦到路口去卖门票!
老黄摇了摇头,叹道:“毕竟领导不是一般人都能当的!人家眼光和我们就是不一样!当时我也是你这一通话,但人家说,哪里,坡上这些钱,有一大半是你们的,我们只有一小点。”
“唔?”蒋银八又吃一惊,抬起头来盯着老黄,一只臭着皮革气的毛皮鞋像抱孩子那样抱在怀里。
老黄说:“他说了,一张门票才几十块钱,如果我们开农家旅店、卖农家酒食,再经营一下我们少数民族服饰,一张门票附加给我们的,岂止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怕都不止。”
蒋银八一听,不禁仔细思量。“对啊……”
老黄道:“我倒不在乎再找什么钱,但靠山村那么多人家,恐怕是盯着我的,我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也才肯做什么,要是我不带头,这条门路就发展不起来,对么银八?”
蒋银八说:“对,对,对对对……那么老黄,你果真觉得这是一条门路喽?”
老黄点头。
“你真的觉得这一条门路特别可靠?”
“是啊,过去我们向往北京,现在他们向往农村嘛。”
“嗨!”蒋银八跳起身来,紧紧握住老黄的双手,说:“老菩萨我求您个事!”
老黄吓了一跳。“啥事?”
“您看……您看这样好不好哈,反正老菩萨您已经说过您目的不是找钱,主要是想带动大家,那么,您先带动我一下,行不?”
“啥意思?”
“您老人家帮我规划一下,让我先开一家农家旅馆嘛——我一早上都在想门路哩——该不会抢您生意吧?”
老黄大笑,“巴不得大家都来抢啊!好,银八,你先搞一个。你是一村之长,正该带头帮群众踩路子哦,要吃亏,村长也该先吃亏嘛。”
“啊?这么说还是不保险?”
“蒋村长!你以为钱真的是堆在坡上的呀?不试一试,谁知能挣多少钱?就说当年的远红外涂料……”
“黄老——您别说了……我干!妈嘞,吃屎都要头脬!”蒋村长睁大双眼看着老黄,充满无限敬意地喊了一声。
老黄愣了半天,他也睁大双眼愣愣地看着蒋村长,仿佛蒋村长不是称呼他似的。蒋村长揉了揉眼睛,仿佛站在他面前的不是老黄,也不是黄老,而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太阳。
责任编辑子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