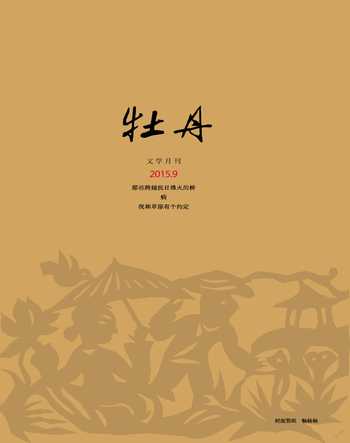花自飘零
何正坤,笔名何尤之,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2007年开始创作,先后在《雨花》《绿洲》《创作与评论》《读者》《芳草小说月刊》《滇池》《厦门文学》《牡丹》等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二百余万字,并有小说及小小说获奖。
走出九龙大厦,她的双眼才沁出泪珠。刚才在楼上,她撑着一贯的莞笑,先在公司的同事群里告别,再和办公室同事道别。然后,理了理及肩长发,拎着蓝色小包,走出了办公室,把高跟鞋踩得“哒哒”响。淡定地进了电梯,不露一些伤痕。
进了电梯仍克制着,脸上已然悲戚。幸好现在不是上下班时间,电梯里空无一人。但说不准会在哪层闯进个人来,万一是同事呢,所以她还得稳稳地端着。
下了楼,走向停车场时,她才松了绑,星点泪花迅速跳进了眼睛里。
阳光很妖,热乎乎地贴在身上,像烟花女子一样煽情。她有些烦,却很无奈。谁能拒绝阳光呢?满街的人都被阳光缠绵,再妖的阳光也烦不得。好在停车场就在前面,三五分钟就走到了。打开车门,坐到车上,她发动了车子。没踩油门,先吹会儿空调。车里太热。她刚才积蓄了满腹情绪,现在可以狠狠发泄了。没有嚎啕,只是倚在靠背上,给泪水找个决口。被现实怠慢了,能找谁发泄呢?那就哭吧。多少泪水都这样,阳光下憋着,阳光后宣泄。
这是她今年找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三个月就丢了。是她自己提出不干的。她并不想离职。面试时经理和她签了劳动合同,试用期三个月,转正后月薪四千。试用期有点长,也没什么,还是签了。但公司竟不按合同办事。三个月后转正了,工资才三千。她不很在乎钱,从不被金钱左右,尽管她需要钱。她在乎的是尊严。没找老板,也没找经理,她直接找了老板娘。她知道这家企业老板娘说了算。老板长得五大三粗,不过是傀儡。公司每一分钱都在老板娘卡上,老板用钱也得找老板娘要。她要找老板娘问个清楚。如果是做得不好,可以解雇,或延长试用期,给个说法才是。老板娘爽快地否定了,说不是。她也认为不是。她做得挺卖力,这三个月还加了不少班呢。既然不是,就是说试用合格,为什么又不按合同办事呢?她问得很直接,连个停顿都没有。老板娘并不讶异她的直接,想必见多了。老板娘说你的工资还是四千,先发三千,另一千是绩效,年底考核后发。老板娘这种忽悠智商还处于初级阶段,纯是强词夺理。别人告诉她,老板娘都是这么忽悠的,等到年底了就说公司亏损,分文没有。她不屑与老板娘理论,更惮于公司前景黯淡,毅然选择了离职。
坐在车上,她终究是落泪了。不为失去这份工作,只为自己一年来的屡战屡败。她是去年春天从深圳回到连云港的。深圳是别人的城市,她没有归宿感。她也不认为深圳好,消费高节奏快不说,她觉得深圳是农民城市,高素质的人太少,一到晚上满大街都是光着背大裤头趿着拖鞋晃悠的。她看不惯。她喜欢连云港,文明礼让,神奇浪漫。连云港是她出生的地方,她想在连云港找份工作,安安心心过日子。但事情并非她想象,连云港不是深圳,就业平台少,她屡屡遭遇挫折。
等情绪宣泄差不多了,她才拾起败落的心情,把车子开出停车场,沿着解放中路茫然前行。太阳像热水泼下来,满街冒热气,柏油路面像东北大炕一样烧得滚烫。即便如此,解放路上依然人来车往,忙忙碌碌。她羡慕忙碌,忙碌的人过得充实,有职业,有收入,有一个可以融入的群体。她现在成了闲人,没有可以融入的群体,没有可以忙碌的生计。她很伤感,开着车不知何往。她可以直接回家的,但她不想回。没工作了,情绪低落沉迷,如同股票的熊市。这时候最好别回家,摆脸色给谁看呢?是自己丢了工作,又没人惹着你。老公不看她脸色,婆婆更不看。那么装高兴点么,又装不出来。装出来就不对了,工作丢了还高兴个啥?指望谁养你呢?婆婆肯定这么冷嘲。婆婆是刀子嘴,什么话从她嘴里滑出来,冷飕飕的像寒风冰刀。结婚这些年,她从来都甘拜下风,不与婆婆争高低。她有她的品位,无谓的争吵她从来不屑。
开车往东,向着家相反的方向。拐上通灌路,经过华联,绕过转盘,上了苍梧路。她开得漫不经心,如同散步。到了苍梧绿园时,她真的想进去散散步。便停了车,进了绿园。苍梧绿园很大,是城市的肺。市民饱受了废气废水污染后,早晚都来这里洗肺,打太极,练剑法,跑步,溜达。现在上午十点了,绿园里没什么人。晨练的都走了,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只有她这个闲人才会来绿园。
绿园里满目碧色,芳草萋萋。她想躺在绿茵上,嗅着青草的清香,闻着泥土的芬芳。但她没那么做,想想而已。她不是小女孩了,没那么矫情和浪漫。结了婚的女人,自然要矜持些。踩着软软的草地,她随意地走着。
绿园的中间是片小丘陵,丘陵上长了许多树。走进树林,树荫下有一排石椅。她在石椅上坐下,看了会微信。朋友圈有人转载了崔永元在周立波婚礼上的即兴演说,她看了,忍不住笑。央视名嘴,一张嘴能平定天下。她佩服崔永元,被他逗笑了。这几年她养成看微信的习惯,特别是在没有可以融入的群体时,微信这个群体接纳了她,陪她打发无聊时光。她的生活里,微信已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替代了许多人,成了她的忠实伴侣。她可以一天不见人,但必须每天看微信。
从微信中抬起头,看到丘陵下面的小溪。小溪是人造的沟渠,水很清,很浅,像在水上蒙了层薄玻璃,能看清河底的鹅卵石。几块巨石嵌入水中,点缀在溪水间。溪水缓缓流动,哗哗的水声轻轻低吟。露出水面的巨石,横亘水中,像一头怪兽虎视着。溪水轻巧地回旋着,绕石而过,涓涓而流。凝视一渠浅水,看溪水打着浅浅的波,悠悠远逝,她竟忽然得了禅悟。与其对峙,不如退避,溪水不与顽石纠缠,照样欢畅而去。生活又何尝不是,既然改变不了现状,何不去适应呢。她觉得求职屡屡失利,与她的倔强不无关联。
但这不是说变就能变的。这是她的行事风格,特立独行,独善其身。她没想过要改变自己。
她本来有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上市公司,是北京在连云港的分公司,管理正规,效益显著。工作是忙了点,但收入稳定,日子充实。如果不是老公,她不会离开的。
她不明白,天下男人那么多,她怎么会爱上老公这样的。而事实上,很多个性鲜明的女人,往往都会选择老公这类随遇而安的男人。她应该属于事业型的,尽管没干出事业来,但好学,能干,勤奋。而老公恰恰相反,像个大男孩子,没一点事业心,太多的时间耗在了吃喝玩乐上。老公的确像个大男孩,比她大两岁,很阳光,帅气,一米七六,挺拔的身材,稚气的脸,看上去像是她弟弟。
男人是要有事业的。男人没有事业心,就像女人没有美貌,对异性没有吸引力。结婚后,她渐渐厌倦了老公。厌倦归厌倦,但不离不弃,独自追求自己的事业,经营着不太稳定的家庭。
后来的一件事让家庭起了硝烟,她不得不辞去了工作。那天老公在房间里说,他的信用卡还不上了。她没以为意,问缺多少钱。老公支吾着,说六万。对于他们这样的家庭,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她问他干什么用了,他竟说不上来,就说吃喝了。她不信。她怀疑他凭借这张脸在外泡女人,他不承认。两人爆发了激烈争吵。以前也有争吵,都控制在房间内。这次惊动了婆婆,婆婆住在隔壁。老公是独生子,婆婆毫无疑义地站在了儿子那边,指责她不该对老公这个态度。她问应当什么态度,要好言相慰么。婆婆说他花多少,有我做后盾,没有我,你们吃什么住什么?
这是婆婆压制她的惯用伎俩,是婆婆战无不胜的武器。结婚五六年,她还没足够能力挣套房子,连首付都困难。老公又是花花公子,挣钱不够自己花销的。他们只能和婆婆住在一起。每次婆婆说到这个,她便哑了口。能说什么呢?初恋时她觉得老公阳光可爱,所以没房没车就嫁了。车子也是自己后来买的。现在想来,初恋是多么幼稚。
每次婆婆指责她时,老公都沉默不语,不向着母亲,也不向着她。老公听了母亲三十多年的唠叨与奴役,早失去了反抗的本能。婆婆五十七了,还没到服老的年龄,动不动就耍点余威,镇着一家人,尤其镇着她这个儿媳。她并没被镇住,却又不得不让步。毕竟住着婆婆的房子,底气不足。而她的谦让进一步成就了婆婆的霸道。她说你儿子欠了六万,超过一年工资了。婆婆说挣钱不就是花的么?花就花了,心疼就不用还啊。婆婆明显是袒护她儿子。她无法容忍婆婆的偏袒,婆婆却不依不饶,指着儿子说,我儿子就这样,从小花钱就大手大脚的。你们能过就过,不过拉倒。
这是下逐客令了,太拿她不当回事了。婆婆的傲慢和狂妄深深刺伤了她。憋屈了一个月后,她决定离婚。她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这事她不用和老公商量,直接和婆婆挑明。婆婆什么意见,老公就什么意见,是也是,不是也是。这个家就这家规。她和婆婆说了,婆婆嗑着瓜子,吐着瓜子皮,轻声说,好。
她真的就离了婚。
离婚后她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住哪。她在市区没房子。要是有房,她早和婆婆分开住了。她的父母原来住通灌南路,在她出嫁后的第三年,父母去了天津。她弟弟在天津混得不错,房子就两三套,车子更不必说。父母想把房子给她,她没要。那时她和老公关系尚好,恩恩爱爱。她弟弟就把房子卖了,带父母去了天津。
父母把房子卖了,她感觉自己在连云港被连根拔起,像无根的浮萍。天真的金色童年,清纯的少女时代,都在刹那间灰飞烟灭。本来以为嫁了男人,就是落地生根,父母的家不再那么重要了。若不是遇到婆婆这种人,她的想法或许是对的。可是现在,她在连云港一无所有,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就像是一个外来人口。
离婚后的那段日子,心情灰蒙蒙的。晚上像个孤魂,在街上游荡。直到身心疲惫,才找个宾馆住下。上班了无精打采,揣了满腹心事。她没和同事说这些,说了有什么用呢。如今的人都这样,只管自己门前无雪,哪管他人瓦上落霜。那些不知就里的同事,仍和她说着笑着。她赔着笑,更多是在想自己的事。她喜欢网上说心思,不是改个性签名,就是在朋友圈里发段心情文字。真的有人读懂了她的文字,是她之前的男同事,现在深圳做总监。总监四十岁,有思想,有魄力,做管理很有一套。他说既然离了,你在连云港便了无牵挂,何不来深圳试试。说他需要个助手,希望她来深圳助他一臂之力。
她不太喜欢深圳,觉得深圳除了不缺钱,别的什么都缺。但她还是去了。如总监所说,她在连云港了无牵挂,在哪没什么分别,到哪哪是家。她不舍得辞去上市公司的工作,可又能奈何,心都没处放了,工作再好有什么用?她遂辞职去了深圳。
深圳并非天堂,除了给她高薪,她实在找不到喜欢的理由。天热得透不过气来,空气混浊得无法呼吸,绵绵小雨像蜘蛛网蒙着。生硬粗俗的粤语,拥挤不堪的车辆,不修边幅的着装,让她对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越来越没好感。最让她没有好感的是总监。她是冲着总监来的,在人生地陌的深圳,她多少得依赖他。但她有原则,工作上服从总监,工作外不服从。工作外是私人空间,总监几番想闯进这块领地。这也是总监邀她来深圳的目的,被她坚决地拒绝了。
她是美女,是那种让男人垂涎的女人。她的脸蛋虽然不很突出,但很标志。瓜子脸,高鼻梁,色靓肤净,唇红齿白。最突出的是她的气质。她的气质不亚于明星,时尚新潮,举止文雅,职业女性的范儿。她的外形更具气质,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长长的秀发如泻如瀑,举止投足间,像个训练有素的空姐。
她三十二了,正是风韵成熟时。而且,她离婚了。
总监没有离婚,老婆丢在连云港呢。总监在深圳是个自由人。她也是自由人。两个自由人同在异乡,何不相互取暖呢?总监不理解她。在深圳,这是很自然的事。
总监显然不懂她。她是女人,自然有情感和生理需求,这点毋庸置疑。但她绝不随意。她讨厌苟且之事,不喜欢玩弄感情,更不追逐男欢女爱。她来深圳,是想做点事业,未必惊天动地,小有成就即可。她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总监遭遇了抵抗,渐渐冷淡起来。总监冷淡了,她在深圳就不想呆了。他是她在深圳的依赖。
来深圳一年半后,她又动了回家的念头。虽说连云港没她一片云彩,但那是自己的根。她想回去了。
人生来就是奔波的。
恰在她踌躇未定的时候,老公来电话了。该叫前任老公吧。前任老公说,六万还清了,他母亲出的钱。你要是念着旧情,就回来吧,我们复婚。她竟莫名地激动,像失散的队员找到了组织。在深圳流离失所,风雨漂泊,过得太难。那么就复婚吧。尽管那个家不很温暖,那也是个家,能给她容身之处啊。
她从深圳又回到了连云港。
她是去年春天回来的,但她并没迎来自己的春天。首先是老公没给她一个春天。如婆婆所说,她儿子从小花钱就大手大脚的,改不了了。信用卡的钱还了,老公又玩疯,天天和朋友吃喝,喝完之后嘴一抹,卡一刷,千二八百就没了。她犹豫着,先寄居一室,复婚再等等吧。她是个执着的人,不想拿复婚当儿戏。
连云港也没给她一个春天,她迟迟没找到工作,这比复婚更糟糕。
连云港的人才网和人才市场,她几乎天天光顾。开着车四处奔波,纵横百里。她尝试了好多岗位。行政经理,销售经理,总办主任,人事经理,都试了,都没干得久。一年投了多少简历,记不清了。进了十来家公司,都辞了,原因种种。发不上工资,违法经营,人脉复杂,没完地加班。这些令她无法接受。
但她的事业心从没泯灭,一边求职,一边报了中级职称考试。她相信考了职称后,找工作会容易些,或许还能迎来事业的春天。
她去九龙大厦面试,是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对面试她的经理印象很好。经理姓时,后来两人成了好友。她本以为从此可以安心工作,不再奔波求职了。岂料试用期满又被老板娘捉弄,时经理也无奈。她只好辞了职,再次踏上漂泊路。
接下来的漂泊又是遥遥无期。想做的职业受到冷遇,不想做的职业频摇橄榄枝。一家酒店招客房经理,看上她高雅的气质。一家广告公司招公关经理,允以高薪。一家商贸公司招市场部经理,提成丰厚。还有两个老板,欲招她为老板秘书,醉翁之意不在酒。
她知道自己长得不错,一般男人见了都心有所思。与生俱来的气质,让她喜欢让她忧。女人都爱美,男人更爱女人的美。美丽已成了绊脚石,困扰着她的求职。而她宁可清贫,也不拿身体做交易。
她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以青春作浮具的职业,她断然不会选择。想吃青春饭太容易了,小姐二奶小三遍地都是。深圳那个总监年薪七八十万,足够她享用。连云港也有老板频频约见,她概不露面。青春是一碗鲜汤,汤冷了,味道就不鲜了。青春总有逝去的时候,彼时青春不复,她将焉附?想在职场的海洋里搏击,就要学会游泳的技能,而不能借助任何浮具。青春也好,美貌也好,都不是永久的依靠,学到东西才是货真价实。
她也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独特的追求。她欣赏有才华的男人,像时经理那样的,她愿意交往。时经理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从不见色起意,遇上美女就动歪心眼。她和时经理交往数月,时经理从无失态之举,连句过分的话都没有。
又跑了七个月,仍没找到工作。进过三四家企业,皆不尽人意。她不去抱怨老板,民营老板就是这样练成的。只怪自己性格刚直,没有水样的温柔,不会见风使舵遇事避让。
而她已面临经济危机,车子快没钱加油了。但她不找老公借,她和他已不是夫妻。她不好意思地向时经理借了,时经理马上打了三千给她。还有一次没钱还信用卡,她找朋友莉莉借了五千。莉莉是她多年的闺蜜。在连云港拥有时经理和莉莉这两个朋友,虽然他们能力有限,她也知足。
到了年底,她又进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总部在北京,连云港设分公司。她对这类公司感兴趣。她一直眷恋之前那家北京上市公司,管理正规,人员素质高,很后悔当初的离职。
但这家公司并非如她所愿,管理完全没有章法,北京的指令像大棒,随意发号。她没有跳槽,她学着水样的温柔,留了下来。先做段时间,等考了职称再说。天下老板一个样,哪家公司会阳光明媚呢。
一个月后,她去了趟医院。她早就想检查了,她的乳房隐隐地痛了半年。苦于收入不稳定,怕承担不起药费,所以一拖再拖。医生给她做了B超,告诉她右边乳房长了个很小的结节。医生给她开了些药。晚上洗澡时,她握着圆润挺立的乳房,无声地哭了。漂泊,奔波,清贫,困惑,她一直在路上行走。生命的器官也跟着她随波逐流,风雨交加。她忽然觉得对不起它们。她几乎忽略了它们。除了脸和头发,其他的生命器官从没得到她的照顾。尤其乳房,为她撑着门面,却一直承受着病痛。
她不想告诉老公。除了身体会断断续续地接触外,其他皆各自为政。老公有老公的风花雪月,她有她的风霜雨雪。互不过问,互不干涉,就像一双筷子,需要时配成一对,不需要时各自成单。
后来,她觉得乳房更痛了点。她明知道是心理作用,就是放心不下。她得找老公借钱看病。本想找莉莉借,但不好意思开口,前面借的钱还没还上呢。时经理可以借,只是乳房生病和一个男人如何开口。想来想去,找老公吧。老公没少享受她的乳房,每次做爱都是乳房先行,她的乳房像工艺品令他陶醉。现在乳房病了,他应当匹夫有责。
然而老公再次让她失望了。老公说他没钱。他真的没钱。他那点工资不够他花销的。她信他,他花销的确大。他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子,三千块工资不够他喝酒的。他还经常像个大男孩,和婆婆耍娇,讨千二八百零花钱。她乳房有恙,他表示无能为力。他也没有太多关注,说很多女人都有这情况。
她什么也没说,一个人坐在车里哭了个够。
她以为老公太拿她身体不当回事了,不想老公其实是关心她的。那天晚上睡觉前,老公忽然问起她的工作。她和老公除了身体没别的交流,包括工作。而身体交流也日渐减少,近两个月几乎归零。两人都提不起兴趣来,钻在各自被窝里呼呼睡去。
老公问她收入如何工作满意么,她没搭理。她觉得他们之间不该有这样的话题,顶多是日常琐事,或新闻趣事。
老公却饶有兴致,坐起来说,帮你找份工作如何?她冷笑,不相信他有这能力。他一心向玩,哪能帮她找工作。尽管她需要份好工作。
她把身体背过去。
老公这回却是认真的,在她身后说,我认识个女老板,把你的情况说了。她愿意接受你,月薪不少于五千。
五千月薪是个不错的待遇。她心动了,转过身来。老公说你不是生病了嘛,我想让你多赚点钱。她问怎么认识女老板的。老公不说。她再问,老公反问,这还用问吗?
她坐起来,看着这个阳光大男孩,突然觉得他很猥琐,没一点阳光,忍不住一阵干呕。呕了之后,她说谢谢。
去吗?老公问。
她反问,这还用问吗?
责任编辑 杨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