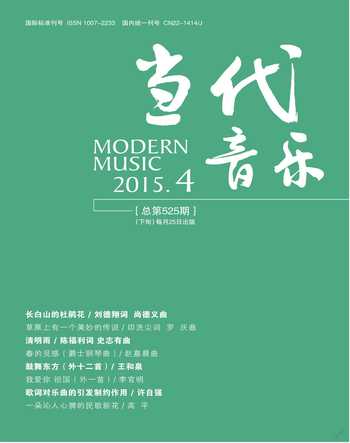歌词对乐曲的引发制约作用
编者按: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歌词创作美学》一书,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许自强先生历时四年、三易其稿的我国第一部关于歌词创作美学论述的力作。该书以34万余字的篇幅,主要从音乐和文学两方面,就歌词的情态美、意象美、意境美、理趣美、语言美及风格美等进行了卓有见地的阐述。对广大歌词作者和我国方兴未艾的歌词创作活动,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与指导意义。本刊征得了许先生的同意,陆续选载书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无可否认,对一首歌曲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作曲。一首歌,能否为多数人喜欢,能否经久不衰地流传下去,首先取决于曲调的成败。苏珊·朗格说:“当歌唱中一同出现了词与曲的时候,曲吞并了词,它不仅吞掉词和字面意义上的句子,而且吞掉文学的字词结构,即诗歌。虽然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了不起的诗,但是,歌曲绝非诗与音乐的折中物,歌曲就是音乐。”这番话自然有点偏激、片面,曲调可以一时掩盖词义,但不可能完全“吞掉”词义。然而,它提醒我们,词和曲的作用并不相等,二者质量常常不平衡。大量优秀歌词因无好曲相配而遭冷落;反之,许多流行甚广的歌曲,歌词却很糟糕。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词在歌曲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词是歌曲的基础,乐曲的内容,也是歌曲的灵魂。黑格尔说:“只有用恰当的方式把精神内容表现于声音及其复杂组合这种感性因素时,音乐才能把自己提升为真正的艺术,不管这种精神内容是否已由乐词提供详明的表现”,即指歌曲如缺乏“精神内容”,没有深刻感人的歌词,就难以成为“真正的艺术”。王玉民所说“歌词是歌曲的脊梁,有了坚实的脊梁才能撑起飞翔的翅膀”,已成为词曲界的共识。中外歌曲史证明:艺术青春长驻的正是那些词曲俱佳、双美兼备的名歌,它们往往是一流的作曲家同一流诗人珠联璧合的结晶。像格里格为易卜生词谱写的《索尔维格之歌》,像贝多芬为歌德诗谱写的《跳蚤之歌》,像门德尔松为海涅谱写的《乘着歌声的翅膀》等。正因此,优秀的作曲家对词作的挑选往往十分严格,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歌曲几乎全部取自于普希金、莱蒙托夫、阿·托尔斯泰、费特等名篇,歌王舒伯特最最钟爱歌德的诗,在他毕生谱写的660首歌曲中,歌德的诗就占366首。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词的好坏要看是否出自于名诗人的手笔,因为词自有本身的审美标准,名诗未必都能入词,这里主要为强调歌词质量对于歌曲生命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提高我国当前歌坛创作质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歌词对乐曲的巨大影响,首先是通过对作曲家的引发和制约作用来实现的,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歌词是点燃作曲家灵感的艺术火花
灵感是人类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长期生活实践和艰苦探索的产物,因偶然机遇的触发而产生的一种认识上的突破和飞跃。灵感具有突发性、亢奋性和独创性。
灵感的到来,大多不期而至,来去倏忽。正如古人云,“恍惚而來,不思而至”,“其来如风,其止如雨”。它不择时空环境,也不由人选择,或因一物一事触发而生,或夜梦诱导而发,或来自冥思苦想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它的形成是非自觉的、偶然的,不为人意志所左右的,因而它又有短暂性。犹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若不及时捕捉,就会从此消失。
灵感出现后艺术家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它忘却了身外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之中,情绪高昂紧张,想象敏捷广阔,甚至如醉如痴,仿佛进入一种“迷狂”状态,西方诗人称之为“可爱的疯癫”。这时,艺术家的各种知识、记忆,思想片断被集中而构成有机联系,创作经验、技巧和能力被充分调动起来,构思中阻塞长久的难题,会瞬间顿悟,迎刃而解。
灵感往往打破常规思维的格局,具有一种特殊的发现功能和表现功能,使艺术家在创作上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许多奇妙不凡的构思,出神入化的描写,隽永闪光的语言,“宛若神助”,最终结晶为新颖独创的艺术作品。可以说,灵感是文艺创作独创性的催化剂。
总之,灵感是一种超常的特异思维,情绪的紧张度、精力的专注度、思维的敏捷度、思想的自由度等,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通常的心理定势和传统格局被冲破,这正是文艺创作最佳的心理条件,也是产生优秀作品必不可少的契机。
音乐家的灵感主要来自于生活,人生经厉、情感积累,蓄之于内,外界景物媒介触发于外,两相碰撞,灵感火花即出。大部分器乐曲的创作源自于此。例如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都是作曲家在优美的田野森林中倘佯,受到大自然蓬勃生机的感染所产生的乐思。
歌曲创作的灵感同乐曲创作稍有不同,对于歌曲创作来说,不一定非要直接的外界景物媒介。歌词,是一种间接的灵感触发剂,有时可以替代直接的刺激。因为歌词是词作家缘于直接生活的感触而酿就的精神结晶,是词作家对于生活本质的敏锐洞察,对于人类情感的深刻把握,往往说出了 “人人心中皆有,人人口上皆无”的心声,也正道出了作曲家想说而尚未恰当总结出来的体验。一旦词作家凝结于歌词中的生活感触深深地打动了作曲家,或唤起他对往昔生活的回忆,激发起作曲家心灵的共鸣,这种间接的媒介(歌词)就能如同电光一般迅速传递,成为点燃作曲家灵感的火花,使作曲家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 苏珊·朗格说:“衡量一首好歌词的尺度,就是它转化为音乐的能力。”她举例道,门德尔松在为歌德的《巫女节》谱曲的时候,谈到歌词给他的灵感启示:“当德鲁依德牺牲,一切都变得如此神圣和难以形容的伟大时,人们确实无需再为它谱写什么音乐,因为音乐已是如此的明确。这里充满了声音,我不假思索(思索如何为它们谱曲)就自吟自唱起这些诗句来。我唯一希望的,是人们能够在我的音乐中,听出我是怎样地被那些美妙的词句激动着。”《黄河大合唱》的产生也是如此,据说当冼星海听到光未然朗读完歌词的最后一句后,立即把歌词抱在手中,一口气跑回窑洞,反复吟诵、激情难已,只用了六个日夜就谱完了这部气势磅礴的不朽作品。佟文西说:“必须用自己火热的‘词情,去点燃曲作者的‘曲情,让音乐始于词尽的时候。”这是完全符合歌曲创作规律的。
歌词之所以能充当作曲家灵感的间接媒介,主要原因在于词作家同曲作家灵感的性质有所不同。生活给予词作家的是文学灵感。一般来说,音乐灵感的产物(曲调)比较空灵、飘忽,而文学灵感的成品(歌词)就比较稳定、具体。倘若词曲作家处于同样的生活氛围之中,酝酿着相似的情感指向时,那么,歌词无疑能使作曲家的构思范围收缩,焦点集中,主题明朗,情感更加具体。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歌词之所以能激发作曲家的灵感,仍然要凭借于作曲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亲身感受。作曲家生茂在谈到为《班长,你留下的枪我来扛》(刘薇词)谱曲的感受时曾激动地说:“写这个曲子时,音符自己往外蹦”。因为歌词的内容正是他在生活中曾深深被感动过的。作曲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亲身感受是第一性的,是直接的,而歌词则是第二性的、是间接的。无论对词作家还是作曲家,生活水远是最终的艺术源泉,所以最理想的歌曲创作环境,是词曲作家同处一起,共同体验,这样他们最易互相启迪,取得默契。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就把它作为一种惯例。石祥介绍:“我们创作组规定,每年要深入基层生活3 ~ 5个月,每次下去,词曲作者搭配,一同前往。很多歌曲是在一起深入生活时创作的。如《野营训练好》、《解放军野营到山村》、《老房东查铺》等歌曲,就是洪源、刘薇和我,同作曲家唐诃、生茂一起参加野营训练生活的产物。这种结合方式,词曲同步,感情融洽,协调一致,容易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除了相似的生活经历外,词曲作家情感的沟通、心灵的默契,也很重要,这大大有助于词对曲的灵感激发力。王健与谷建芬二人合作了许多受人喜爱的歌曲,就因她们之间所建立的深厚的友谊,密切的共同感知、感受、感悟的基础上,词、曲作者相互理解,情感的接近和默契,是最可贵的。格林卡为普希金的名诗《致凯恩》谱曲的经过也是歌坛史上一段心灵默契的佳话。普希金有一首被譽为“爱情诗卓绝的典范”——《致凯恩》,它完全是诗人真实经历的写照,是他高尚心灵的回声: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在绝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喧闹的虚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温柔的声音,/我还在睡梦中见到你可爱的面影……
1824年普希金受到政治迫害,被押回原籍,过着极度孤寂的幽居生活,突然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女友凯恩,得到意外的双重惊喜,诗人枯涩的心灵得到了苏醒,写下了这首名诗。有趣的是作曲家格林卡不但也结识凯恩,而且爱上了凯恩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几乎亲身体验了诗人对凯恩的爱慕赞美之情,正是这种相仿的体验使格林卡把这首名诗谱出了一支精妙绝伦的歌曲。
当然,情感体验的沟通不一定都需要词曲作家的直接交往,或共同经历,常见的方式倒是通过歌词,歌词恰好说出了作曲家的心里话,同作曲家内心深处隐藏的潜意识相契合,成为这种潜意识能量爆发的突破口。歌王舒伯特短暂的一生,饱尝忧患穷困,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其潜意识郁结着一股渴望温暖、幸福的暗流,故而对于像《流浪者之歌》这类天涯游子追寻故国的凄凉心理最易引起共鸣,这首歌曲简直成了他自传式的人生写照。也正因此,在《圣母颂》里,人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在人生坎坷中对幸福的祈求。这类歌曲在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作曲家门德尔松那里,我们是绝难听到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诗品见人格”。其实,对于作曲家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往往能在他的作品中听出他品性人格,情趣爱好,他对于哪类歌词感兴趣,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心灵素质。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之所以为易卜生的《天鹅》谱曲,就因为天鹅那“无言默想”、洁身自好的品格,同作曲家高尚人格有许多相似之处。
歌词不仅是点燃作曲家灵感的火花,又是激发作曲家创作欲望的催化剂,这是歌词中理性意识的胜利。倘若面对一个理性话题,比如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社会政治话题,或者饱含人生哲理的道德伦理话题,词作家照样可以挥笔成篇,而作曲家就会面呈难色。因为音乐形象面对观念、哲理,是软弱无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歌词就成为完成创作意图的铺路石。聂耳目睹日寇嚣张气焰而义愤填膺,民族危亡使他充满创作欲望,但单用乐曲终难表达,一旦得到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中华民族几万万同胞的强烈怒吼,也喊出了作曲家郁积已久的心声,从而一首振铄千古的名曲,一夜之间,迅速诞生。大量歌曲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优秀的歌词正是以它的精警深邃的理性意识,开启了作曲家心中寻觅已久的构思闸门,使音乐创作得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歌词的思想性、哲理性(当然,这种理性是形象化的、音乐化的)呈现出无比巨大的威力,成为作曲家最需要的创作契机。这一点对当代歌曲创作,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纯音乐本不擅说理,然而,对于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歌曲而言,回避说理,就会大大限制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正如我们在歌词的“理趣美”中所论述的,现代审美大众需要理性,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理性,音乐的普及、音乐功能的拓展也需要理性,这正是文学同音乐相结合、取长补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歌词是制约歌曲情调的主要依据
歌曲创作要兼顾两种形象,即文学形象(词)与音乐形象(曲),求得二者的完美统一。从欣赏角度看,恰恰相反,文学形象制约着音乐形象,音乐形象必须为文学形象服务,即曲调要适合词情。歌词仿佛一直在告诫、提醒作曲家:你的每一个音符,不但要符合音乐创作的规律,还应当切合文字符号的内涵,音符要同字符保持基调的和谐。
黑格尔认为,作曲家“要完全渗透到已有歌词说出的意义、情境和动作等等里去,然后从这种内在的灵感出发,去寻求一种意味深长的表现,用音乐的方式把它刻画出来”。可以说,词的情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曲的基调。
词情对曲调的制约性,首先表现在词的内容和风格基本决定了曲的体式和风格。激昂慷慨、气势磅礴的歌词,就需选择进行曲式的战歌体,深沉雄浑、富于崇高色彩的歌词,就要考虑谱成庄严、宽广的颂歌体;而一首柔宛绻缱的情诗,就适合于配以夜曲一类的抒情体。
此外,歌词的语言风格和结构形式对音乐曲调也有重大影响,朴素、简洁的民歌体语言就需配以清新、活泼的民歌风曲调;华丽、精致的文采派语言,就需配以繁复、花饰的艺术体曲调;典雅、庄重的古典式语言,就需配以肃穆古朴的古曲风味。有些戏曲式的歌词,则需配以相应的戏曲曲调。词风中最为敏感的是民族风格和地域风格,因为这类歌曲的民族地域色彩相当浓郁,早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审美习惯,稍一走样就会变味失真。例如,描绘西藏的歌词《青藏高原》(张千一词曲)必须配以高亢、苍凉的曲调,充分吸取藏族民歌的传统风味,才能取得人们的认可;描写老北京生活的歌词,如《前门情思大碗茶》(阎肃词,姚明曲),就要求曲调有一定的京味,故作曲家基本采用了北京琴书的旋律,听起来极为亲切。
词情对曲调的制约性,最主要是词的情调奠定了曲的基调。情调是一首词笼罩全篇的情感基调,包括情感的类型(喜怒哀乐)等,它们都对曲调有巨大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人类的情感形式同音乐的曲调结构存在着异质同构的原理。苏珊·朗格说:“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曲调的分寸把握,主要依据是词的情调,词的情调欢快热烈;词的情感表现直接明朗,曲调须畅达贯通;词的情调曲折含蓄,曲也必须随之起伏变化。两千多年前公孙尼子的《乐记》中就谈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生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生情必须随着词情(心情)而调整。
对于作曲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渗透在词中的一种情感的“内核”,它是情感基调中的“基调”,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情感聚焦点,也是最能启迪作曲家乐思的敏感点。苏珊·朗格说:“歌词必须传达一个可以谱写的思想,提供某种感情基调和联系线索,以此来激发音乐家的想象力。”这对于作曲家相当重要。金波曾说:“当作曲者为一首歌词谱曲时,他不一定十分拘泥于诗词的严谨、纯粹、精微以及段式结构;重要的是他必须感受到抒情主人公的‘心灵状态,获得表现某种情感的‘内核,音调也就随之流出。”的确,一旦曲作者把握住了歌词的核心情调,曲调也就会水到渠成。作曲家刘诗召在谈到创作《军港之夜》的体会时说:“这首词主要是突出一个‘静字和一个‘轻字,‘风儿轻轻吹、海浪轻轻摇,‘军港之夜静悄悄,反复读词,渐渐进入了那种又轻又静的境界,于是,南海边一种带有摇篮曲风格的旋律就流进了我的心底……”
表现情感内核的中心句,在歌词中常常以题目形式直接出现。如《我的未来不是梦》(陈家丽词)、《你把你的手伸给我》(李昌明词)等。作曲家牢牢抓住这些中心句,就如提纲挈领,可以较容易地驾驭全篇,即使中心句同其他词句情调稍有出入,也不致影响曲调的主导走向。黑格尔说: “在歌里也应有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音调,尽管这个音调只适合于歌中某一情感的统一基调,所以主要也只打动某一种情调。”
当然,歌词对音乐语言的制约性是相对的、有限的,词与曲各自都有一定的独立性,正像好词不谱曲,可以当诗读;好曲离了词,也可以当乐曲听。音乐评论家玛采尔曾说:“一个声乐旋律,如果不带歌词地表演它(或用听众所不熟悉的语言演唱),虽然在同一的、综合的音乐和诗歌形象上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但作为一个乐曲的旋律形象,它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意义的逻辑上的完整性。”《长江之歌》未填词前已广泛流传,许多优秀歌曲,当成无词的器乐曲演奏时,并不有损于它的审美价值。
再者,词同曲结合时,曲并不是被动地阐释歌词,更不是机械地相配,要求每一句词同曲都一一对应。苏珊·朗格坚决反对“对诗歌形式和文学概念像影子一样追赶”。她认为,“音乐只能从它自己的‘指令形式中产生” 。作曲家的任务是把文学语言的精髓,融解到音乐形象中去,化为独立自主的音乐形象,音乐形象与其说是语言形象的乐化,不如说是音乐家对于语言形象的一种诗的感受。在理解词意方面,作曲家应有很大的自主性,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想象力和创作个性予以充分地发挥。词只是为作曲家提供一块再创造的跳板,一个起飞的基点,因此,优秀的歌词应当精警、含蓄,留有空白点,点到为止,给作曲家留有充分发挥创造的余地。对此,黑格尔的告诫是有益的:“这种诗必然只对作曲家提供一般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创造和对一切题旨的尽量发掘,来建成他的大廈,而且可以向许多方面自由活动。乐调既然应吻合歌词,歌词就不应尽量描绘出内容的个别细节,否则就会使音乐的宣讲流于琐碎零乱,弄出许多节外生枝,这样就会破坏统一和削弱整体效果。”
三、歌词是规范音乐语言的基本模式
歌词用的是文学语言(语言文字),乐曲用的是音乐语言(旋律、节奏、和声),这两种艺术语言有本质不同,但二者存在着彼此沟通、转化的可能。张俊指出:“歌词是靠口说出声来叫人听的语流。歌曲的曲调,也是靠人声唱出的音流传给人听的。音流和语流同时通过人的发声器官发出声流,又同时作用于人的听觉,使歌词与音乐的结合成为可能。以音流、语流合成的声流曲表现人的情流,通过听觉流进人们的心田,激起情感大潮,这就是音乐与歌词结合的基本原理。”文学语言的“语流”同音乐语言的“音流”,怎样沟通汇合成歌曲的“声流”呢?这主要依靠情感作为媒介,因为无论文学语言或是音乐语言,都须服从共同的抒情需要。在原始音乐中,“音流”和“语流”的合一,正是依靠情感的操纵体现在有声无义、有情无词的语气词构成的“声流”中。闻一多在《歌与诗》里曾指出: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如“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介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
文学语言的语势、语气、语调和节奏,同音乐语言的音区、音色、力度、旋律、节奏,有巨大的共通性。比如,那些深沉、安详的情感,对文学语言来说,须用缓慢的语气、低沉的声调,对音乐语言来说,就适于用徐缓的低音来表现。其实,在生活中有些旋律就是由文学语言的音调演化而成,比如打夯歌、拉纤歌、船夫号子一类民歌,其曲调同说话的声调十分接近。苏珊·朗格认为“歌唱很可能就是由说话的语调发展来的”。有的作曲家说“熟读歌词之后,曲调就自然流出来了”,大约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读读乔羽的《说聊斋》:
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齐都到心头来/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倒比君子更可愛……这几句词倘用山东方言腔调去有声有色地朗读,就会显出一定的音乐性,它同现在的曲调颇为相近。据说作曲家王立平在电话里听乔羽用山东腔一读,曲调就基本产生了。金波说:“音乐家正是由于怀着文学趣味之外的音乐感受力去欣赏歌词,因此才能以音乐的‘色彩曲描绘那歌词的‘素描。”这种声调的转化,对于一些写声音形象的歌词就更为便捷常见。试看《泉水叮咚响》开头:(马金星词、吕远曲)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啊泉水你到哪里你到哪里去/唱着歌儿/弹着琴弦/流向远方……
这词本身就有鲜明的音乐性,谱曲时,曲同词的韵律处置、节奏安排,间歇长短,问答语气几乎完全协调一致,连泉水落地时叮咚之声,都清晰可闻,因而,使这支歌曲充满活泼生气。
需要指出,节奏在由语言形象转化为音乐形象中相当重要。歌词语言节奏快慢疏密,往往决定了乐句节奏的速率、强弱。例如张藜的《不白活一回》:
不白活一回/凤飞彩云追/不白活一回/雁叫鸟相随/不白活一回/金翅鲤鱼敢玩山水/不白活一回/大鹏腾空往高飞/噢 啊/活就活他个船撵浪/活就活他个龙摆尾/活就活他个云升霞/活就活他个地增辉/啊 噢/活他个拼命三郎才有滋味
排比式语言,主题句的反复重现,加上由短渐长的句式,层层加快、加密的节奏感,使这段词呈现出一浪赶一浪、层层递进的气势,唱出最后一句,一锤定音式的主题,才让人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词不要说音乐家,就是普通读者读起来,也仿佛会有节拍、旋律涌出。
节奏是情感的律动,判别节奏性质的标准主要不在于外部词句或乐句的结构划分,而在于内在情感的类型。有时,外部形态十分相似的组合结构,节奏类型可能完全相异。比如: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李叔同《送别曲》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光未然《保卫黄河》
这两段词句从字数、句式看,节奏似乎完全相同,但它们蕴涵的情调迥然不同,从而决定了它们的节奏感的巨大差异,前者舒缓悠长,细声慢吟,后者急骤短促,大声疾呼。
歌词语言对音乐语言的制约性,提示词作家在创作歌词时一定要注意它的可唱性。词作家写词时最好是“唱着写”,而不是“读着写”。朱自清认为“唱歌是‘吟味节奏的工作做的好”。钱建隆谈到《摇啊,小小的吊床》时,把歌词的节奏感同音乐的节奏感统一的意图说得十分清楚:
星儿晃,月儿晃/摇啊摇啊小小的吊床/微风有意轻轻地推/古树有情悠悠地荡/轻轻地推,悠悠地荡/睡着了,勘测队的姑娘/星儿晃,月儿晃/姑娘啊,梦中还在寻宝藏……
他说:“其中‘星儿晃,月儿晃、‘摇啊摇啊、‘轻轻地推、‘悠悠地荡以及再现的推、荡、晃,都在节奏上自始至终产生着摇晃感。后来,曲作者为它谱了曲,用的是3/4拍……词在摇,曲也在摇,摇篮曲就这样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