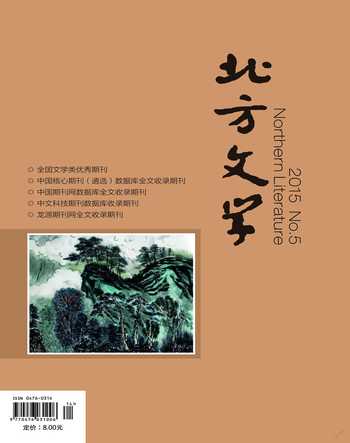质本洁来还洁去——林黛玉与佛
摘 要:“生于繁华,终于没落”是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用独特魅力的艺术眼光和诗画结合的创作手法成就了《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他的大观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真实人物,林黛玉可以说是最印象深刻的人物之一,人们对她的初始印象便是“病弱西子胜三分”的娇柔和犀利讽刺的语言,熟不知她的形象还有另一层的内涵,便是她身上所折射出的朦胧的佛家影子,揭开她的面纱,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林黛玉,分别从她的原型、诗句语言、所居环境及其人生的轨迹来探究她与佛的联系。她对现代女性的形象影响是无可厚非的,深层剖析后的林黛玉对现代女性是有着时代意义的
关键词:林黛玉;佛;语言;人生;意义
会有那么一段传奇在时代洗礼中演绎它的浪漫悲剧,让我们拼尽力气去描绘它的独特韵味;会有那么一部奇书在灯火光影中倾诉它的故事细腻,让我们身临其境地去感受它的神秘魅力;会有那么一个人物在悲欢离合中勾勒她的喜惊悲叹,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去打捞她的才气飘逸。《红楼梦》的林黛玉便是这样的一个洁净脱俗的姑娘,她的容貌、她的才气、她的思想莫不是大观园里一朵奇葩,在潇湘馆中遗世独立。
脱去凡俗的束缚,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存与死亡意义及存在价值,以达到身心的安逸,是佛家思想最本质的表现。《红楼梦》的贯穿中便有这种思想的存在,而曹雪芹最后的留白也已经预示着人生的幻灭,生命的消逝是自然的反映,也是人世间的污浊所致。《红楼梦》正是把幻灭感与徒劳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切都归结于“空”。
一、黛玉的原型和“玉”的佛缘
从曹雪芹的原著来看,林黛玉这个人物,意象层面蕴含十分丰富,有历史画化人物所构成诗画意象,如湘妃、红拂、绿珠、明妃等等;有自然意象,如斑竹、桃花、柳絮、秋菊等等。而对于她的神话原型意象,人们普遍接受得便是绛珠仙子。“绛珠草”来源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西灵河岸上”代指的发源地是古印度,即古代所说的天竺国。而“三生石畔”在杭州飞来峰的天竺寺下,是一处佛教名山。这就奠定了黛玉与佛剪不清的“情缘”。
宝玉、黛玉之“玉”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象征。玉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产生着重要影响。“玉的美对文学的意义, 更为深刻的一面并不在于作品里对它的实际描写, 也不在于它流溢于文学作品中的灵气。而在于它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而这又较为集中的表现在对意境及其特点的形成上。”黛玉的诗性便带有一种通灵的韵味,这和她的“玉”有着直接关系。玉是大自然之灵物,取“玉”使得林黛玉的性格有佛之脱俗,不染尘间之埃。反之薛宝钗的“钗”是世俗之物,注定她的性格圆滑、维护封建社会礼制。
二、“竹”的深层含义
文人与竹有了不解之缘,文人们的笔端便常可见竹子那孤高傲世的清影以及竹子所幻化而成的超凡脱俗的人物,譬如清代文学巨匠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中的潇湘馆。林黛玉是潇湘馆的主人,也是曹雪芹笔下最为清丽脱俗、率性聪慧的女性。
而竹子是潇湘馆的标志,也是林黛玉品格的象征,潇湘馆里,洞庭君山,“斑竹一株千滴泪”,可见,竹子是黛玉的象征,潇湘院的“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竟能惹得老学究贾政也生“出尘”的念头,“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贾政尚且如此,潇湘馆的黛玉更是深受其影响,用竹子隔离了外界的尘嚣,阻挡了封建礼制的污浊之气,保持了自己的洁净之身,这与佛家“出尘”,不受外界的叨扰之本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传说中,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宝玉最初将潇湘馆命名“有凤来仪”。缘于此典,作者以竹暗喻林黛玉高洁的品性。同时,潇湘馆里的竹也象征着林黛玉反封建的精神和高尚的节操。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也就象这质朴而不媚俗的孤高耿直的竹子一样。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鄙薄功名富贵,不愿与恶俗的世态同流合污,水依竹而生,荡涤人的性灵,这便是刚直不阿、率直高洁、不染尘埃的水,一如黛玉。
三、从黛玉诗中谈“洁”
在林黛玉的生活里, 诗是她孤寂灵魂的最大安慰。读诗, 写诗已成为她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态度。古典诗词以其深沉、凄冷的韵味熔铸其风神秀骨, 使她超凡脱俗的叛逆之性和对人生自问的哀婉之态始终荡漾着一种清冷雅丽的神秘韵味。
“肠断乌驻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黔彭甘受他年酸,饮剑何如楚帐中。” 是歌颂项羽侍妾虞姬的。项羽被刘邦的汉军围困在该下, 四面楚歌, 吹散三千子弟兵。虞姬也为项羽舞剑自刎,生死相随。黛玉赞其死得其所,保持了自身的洁净,没有向世俗低头,这首诗正是黛玉明志的隐喻。
那首《葬花吟》是穿透古今污浊的一条豹尾,敲打着社会的黑暗,也彰显了黛玉“洁”的形象。“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之绝唱,细细品味,黛玉其实十分重视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面,她拥有洁身所好的可贵姓。特别她对质本洁来的执着追求,希望两肋生翼,随花飞到天边去追寻这种宝贵的“洁”的净土,是一种极其美好的崇高的道德追求。这种自觉而强烈的洁身思想正是佛中所讲的“干净而来,洁净归土”的清和净,离开尘世的烦扰,回归到那个干净的世界,显示出佛心中有净土的内在。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难解诉秋心?”,黛玉的诗才是是从她幽美绝俗的意境生活中所升化而来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严酷现实,具有叛逆思想的同时,也是写出黛玉思想的纯净,不与俗物相生,
四、言语行为中的佛本思想
由于性格气质的原因,善于接近自然,体验自然。宝玉怕落花被人践踏,把他们时期来豆乳池子里去。黛玉却认为这样顺水漂流出去难保不污浊,不如把它葬入一捧净土的花冢中去,使其随其化了,来的平净。这便和佛家中回归自然,以净白之身莫如尘土的佛本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干净得来到世上,便要在离开尘世洗净周身污浊埋入土壤長眠于宁静之中,去迎接下一个洁净之身的到来。
对于宝钗的引咎自责,她也坦白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极好,然我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可见,她有一颗宽容的心,与机警规避、工于心计的宝钗相比,骨子透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纯净。
五、黛玉人生轨迹之佛家解读
王国维说:“《红楼梦》者, 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价值即存乎此。”《红楼梦》的悲美价值即在于全篇自始至终笼罩一种虚空和宿命的感伤氛围。曹雪芹之所以呕心沥血写这部奇书, 亦是为了表达“ 一种无可奈何的人生空门的悲叹, 一种不可救药的末世衰颓的感伤, 一种犹如梦幻般缥渺难寻的愁思, 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苦痛, 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探索”。
曹雪芹更是呕心沥血地创造了林黛玉这一典型的形象,当然在其人生之轨迹当中必然有人生幻灭与虚无。她生命之热的欲求在寒冷的空间被凝成霜粒,不可知的宿命将人引向虚无的所在:“试看春残渐落便是红颜老死,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知”即为“虚无”。花开花谢非人之能力所能决限,万事万物皆有其运行规律,人生人灭即使如此,这是佛的另类解读,林黛玉的这一形象将这一抽象概念概括地淋漓尽致。天地间一切都已设置,谁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前定。于是林黛玉顺应前定香消玉殒了,她的一生是徒劳的,没有结果的爱情,注定她这一世要还宝玉一世的泪。
黛玉之于宝玉就如伯牙之于子期,是难求的知音,于是乎与宝玉精神共鸣的黛玉必然会有宝玉身上所具有的“佛性”,显然她又有超脱佛性的一面,有着真情实感,与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的依托。黛玉是一个身在“佛界”却有超越佛法的女子,她的生命虽终于葬花,却鲜艳了所有女性的思想,平静了我们的暴风骤雨,使我们归于宁谈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邓辉.论林黛玉的神话原型及其审美意象[J].明清小说研究. 2007(2)
[2]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
[3]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作者简介:李佩玉(1990–),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