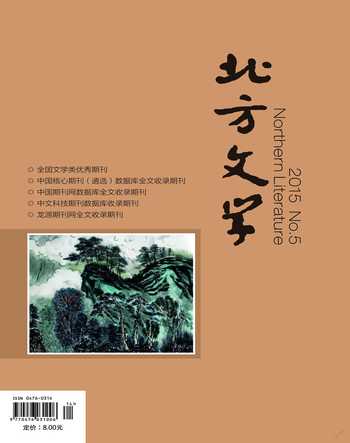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功能论
摘 要: 文章提出了张爱玲小说人物服饰具有身份符号、人物刻画、情节发展、社会变迁等四个方面的主要功能。这些功能加深我们对张爱玲小说内涵的理解。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功能
服饰是张爱玲小说人物特征的重要标识,也是张爱玲用以叙述故事、结构情结的载体之一。在张爱玲系列小说中,人物服饰文化涵义丰富,功能众多。这些功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爱玲小说的理解,同时也加深对张爱玲本人的理解。
一、身份符号功能
服饰往往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表征,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就是通过精心设计人物的服饰,展示人物的职业、国别、地位等。
首先是以服饰表明职业身份。在张爱玲小说中,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服饰打扮。如《封锁》中的男角吕宗桢是一位银行会计师,张爱玲形容他是“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这里,笔直挺立、简洁大方的时尚西服为当时上班族们共同认可的服饰,玳瑁边眼镜和公事皮包表现出了作为会计师的温文尔雅。在同一篇小说中,对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的描写也颇与其职业相吻合,“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蓝与白都是素净的色彩,显得纯洁和朴素,书生气十浓。同样是老师,《茉莉香片》中的国文教师言子夜穿著又不一样,宽大的灰色绸袍与松垂的衣褶烙印着中国式长袍的古色古香,展示出饱读国学的读书人的儒雅气质,也突出了其秀拔的身材。而学生的着装又不同于老师,有自己的特点。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第一次出现时的身份是学生,她在玻璃门里留下影子是:“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 无论是蓝爱国布的布料,还是稳重大方的校服样式,与其女学生的身份都是吻合的。因此,在张爱玲小说中,不同职业的人,在着装上特点鲜明,有明显的差异性。
其次,以服饰彰显人物的身份地位或社会阶层。人物身份地位差异在服饰上最明显的就是体现在服饰的材质上。一般而言,有钱人和位高权重的人服饰华美,样式时髦,布料往往是动物皮毛和丝绸。如《琉璃瓦》中静静穿的是“青狐大衣”、“泥金缎短袖旗袍”,因为她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是“富太太”;《金锁记》中的七巧因为是姜公馆的二奶奶,所以能穿上色彩明艳的银红衫子,质地上乘的雪青洋绉手帕,流行的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袴或青灰团龙宫织缎袍;还有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葛薇龙后来的“磁青薄绸旗袍”,霓喜平金、织金相互变化的满洲式的高底缎鞋,梁太太夜蓝绉纱包头和钻石坠子等,都显示了富贵人物多样的、高贵的服饰。相比而言,农民、小商贩等社会底层则用棉布等作为服装材料。如《封锁》中的董培芝,穿的是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与他吃苦耐劳、守身如玉阶层地位符合;古玩摊上的伙计穿着“紧身对襟柳条布棉袄”;《花凋》中的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第一炉香》中薇龙家里的佣人陈妈,常身穿无论在视觉还是触觉上都十分僵硬的蓝竹布罩褂;《连环套》中的广东穷人总是穿着抑郁的黑土布等。总之,在张爱玲小说中,穷人以蓝、灰、黑为主的竹布衫、黑土布衣服,与富人的绫罗绸缎、动物皮料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服饰的国别特点也比较突出,外籍人物所穿的服饰明显不同于中国式的服装。如《第二炉香》中的一个印度女人,“玫瑰紫的披风”、“莲蓬式裤脚管”十分具有印度服饰的样式;《倾城之恋》萨黑荑妮公主的着装,“玄色轻纱底下穿着金鱼黄的紧身长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她换上了印度装,兜着鹅黄披肩,长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镶滚,指甲上涂着银色蔻丹。”把印度女子对玄色、金鱼黄、鹅黄、银色等炫丽色彩的偏好表现得十分突出。当然,由于生活在中国,难免中外混装,如《连环套》中印度人雅赫雅,身上穿的是挺括的西装,而头上却缠着白纱包头,差异性十分明显。
二、人物刻画功能
张爱玲是个通过服饰刻画人物性格的高手,她善于通过不同方式的服饰描写来表现不同女性的性格或命运。
张爱玲在许多小说中运用了人物对比的方法,通过不同的服饰式样、色彩展现了人物的内在品性。其中,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与孟烟鹂最为典型。
张爱玲笔下的王娇蕊是个热情似火的女子,其服饰自然时尚开放,色彩大胆张扬。她首先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与一般女子不同的热情魅力。佟振保首次到王娇蕊家,就见她:宽松的浴衣修饰出她娇好的身材,头发上堆满的肥皂沫就仿佛一种隐藏的暗号,配合着浴衣,不经意间就能让人嗅到与众不同的味道。而且是不曾系带的浴衣,还一边洗头一边见客,神情自若,与其他女子穿戴整齐、以礼相待完全不同。甚至在吃饭时,也没换装,还是穿着洗头时的浴衣,头发也不曾打理,只是用毛巾随便裹着,以至于头发上的水珠时不时地往下滴,缺乏对客人最基本的尊重,而她自己却一点儿也不觉得失礼。再次见到王娇蕊,佟振保又惊讶其服饰的式样和色彩。她里面穿着深粉红的衬裙,外穿一件“最鲜辣”、“潮湿”的曳地长袍,将人们所回避的红和绿搭配一起,显露出了王娇蕊着衣的艳丽和热情、开放和大胆追求的个性。再一次见面,王娇蕊穿着印花朦胧、色彩叠加的睡衣出现在佟振保面前,毫不回避。究王娇蕊这样服饰着装的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其热情、大胆、叛逆的性格,让人觉得其穿着违背常理,出人意料。她无论第一次与客人见面还是共进晚餐,都以浴袍、睡衣示人。当在家应穿以自由、轻松的服饰时,她又穿着大红大绿的曳地长袍,不按常理着装,随心所欲。二是爱情使然。王娇蕊之所以多次在佟振保面前衣冠不整,是因为她对佟振保充满好感,并逐渐产生爱情。浴衣、睡袍和衣服艳丽的色彩上既让读者感受到她内心的热情和冲动,也都深知这是一种在爱的人面前的服饰诱惑。事实上,王娇蕊也通过其服饰,诱惑到了佟振保,让他终日心神不宁,也因此舍不得将王娇蕊洗头发时不小心溅在他皮肤上的肥皂沫擦掉,还把肥皂沫风干的过程当成一种享受,似乎肥皂沫是连接他两肌肤之亲的中介;还把王娇蕊洗头时掉在地上的那些头发悄悄搜集起来,放在裤袋里,表达出他对她的爱慕。可以说,王娇蕊的性格及在服饰中体现出来的诱惑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与热情的王娇蕊大相径庭的是孟烟鹂的沉默,体现在着装上就是中规中矩,低调含蓄,色彩淡浅。孟烟鹂长得白净秀丽,性格娴静温良,张爱玲将“白”紧紧与她联系在一起,首先体现在服饰上,佟振保无意在浴室见她,“提着裤子,弯着腰,正要站起来,头发从脸上直披下来,已经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短衫楼的高高的,一半压在颌下,睡裤臃肿的堆在脚面上,中间露出长长一截白蚕似得身躯。”这种“白”成了孟烟鹂的写照。正统素雅的少女服装使其缺少年轻女子身上应有的青春活力,举止得当的“白”变成了妇女的呆板、坚硬与无味,在白中,包含了她的软弱、乏味、缺乏趣味的性格,也是其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体现。她的守旧与本分,让她赢得了婚姻与家庭,但因为没有爱情,所以至始至终都是一个空壳的家庭和死亡的婚姻,使她总是努力去扮演一个好妻子的角色,却苍白地独守寂寞,尽管也有石破天惊的私通裁缝行为。而王娇蕊热情似火,是热情的红玫瑰,敢追求真爱、面对挫折坚强。虽然衣衫不整、大胆叛逆让佟振保不敢、也无法给予她婚姻的承诺,可以说是输了婚姻,却赢了爱情。白玫瑰的孟烟鹂和红玫瑰的王娇蕊,其命运在其服饰上已有了定论,但都是当时社会的悲剧。
张爱玲小说中还有不少是直接通过服饰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如《第一炉香》 中的贵夫人梁太太,“一身黑, 黑草帽檐下垂下绿色的面网, 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闪闪烁烁”的蜘蛛网将其为满足情欲,用丫头侄女做诱饵,到处交际求爱的阴险狠毒一面表现的淋漓尽致。《第二炉香》中蜜的秋儿太太,“一向穿惯了黑, 她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般守礼谨严的寡妇们的黑沉沉的气氛, 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总似乎是一身黑”,很好的体现了其作为一个寡妇禁欲主义的品性。《等》中的童太太,“显得脓包, 全仗脑后的‘一点红红宝簪子, 两耳绿豆大的翡翠耳坠, 与嘴里的两颗金牙, 把她的一个人四面支柱起来, 有了着落。”这一“脓包”的服饰饱含了其三十年为家庭操劳的艰辛,也是其俗不可耐的性格体现。
三、情节发展功能
不同的人物,服饰不尽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命运下,服饰也不断变化着。反过来说,服饰的变化推动了人物命运的变化,进而推动小说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第一炉香》的主人公葛薇龙和《金锁记》中的七巧就是其中的典型。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它讲述了女主人公葛薇龙从大陆到香港求学,为完成学业,不得不向姑妈家求助。而其姑妈梁太太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情欲,将薇龙拉入香港上流社会,不断出入各个交际圈,并讓其嫁给乔琪乔,成为这些上流阶层榨取利益的工具。在葛薇龙由正统人家的朴素女子走向沦落得过程中,服饰起了重要作用,它既是葛薇龙堕落过程的重要欲望物,也见证了她走向堕落的过程,由此推断故事的发展。
葛薇龙刚到香港到姑妈家时,一身学生装扮,穿着款式已过时的长款女学生校服,在衫子外面加了一件绒线背心,本想增加点时尚却显得更缺乏美感。这时的薇龙内心纯净,打扮十分朴素,也缺乏装着打扮的审美心理,直到姑妈让她试穿鸽灰短袴的网球服时,服饰美才开始在她心里萌芽。当她在陈妈的陪伴下搬进姑妈家时,陈妈穿的质地僵硬的竹布衣服与姑妈穿的柔软的绫罗绸缎形成鲜明对比,甚至陈妈的辫子都不如姑妈家佣人的辫子,从这时,薇龙就彻底否认了陈妈,和陈妈这一阶层的人划开了界限,心里已和姑妈站在了一起,告别了过去朴实的生活,服饰的诱惑在她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也开始了走向奢华堕落的迷途。
薇龙的心理变化姑妈自然看在眼里,正迎合她自身的利益,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姑妈利用服饰等,为薇龙设计的一个又一个温柔的陷阱,并使她在陷进中沉沦,忘记了完成学业的梦想。梁太太替孙女薇龙精心准备了一个让少女们着迷的衣橱:“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沙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这衣柜让薇龙整夜无眠,反复想象着自己穿上每件衣服的样子。衣柜成了薇龙全新生活的转折点,成了故事情节发展和薇龙命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薇龙内心中质欲被源源不断地激发出来,她开始学会在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服饰出现,或“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陪姑妈请客;或“穿着白袴子,赤铜色的衬衫,洒着锈绿圆点子,一色的包头,被风吹得褪到了脑后,露出长长的微卷的前刘海来”。参加姑妈的山顶野宴。精美的服饰就这样改变了薇龙的思想,不断腐蚀着她的内心,一步步走向深渊。
《金锁记》在张爱玲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成功塑造了曹七巧的性格变态和扭曲的女性形象。张爱玲通过主人公三个不同时期服饰的变化,刻画了其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七巧是一位出身寒微的麻油店的女儿,她十八九岁时,“高高挽起大镶大滚的夏蓝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大镶大滚的服装款式、简洁的色调、朴质的面料,使整个服而大方整洁,洋溢着花季少女的青春气息与活力,高高挽起的衣袖下的白手腕使曹七巧显得特有风韵。然而,由于兄嫂贪图钱财,七巧被卖入了姜公馆,嫁入豪门,同患有骨痨的姜家二少爷成亲,七巧也告别了普通少女的清纯,开始了贵妇的生活。首先体现在服饰上:“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 身上穿着银红衫子, 葱白线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 ”。无论是款式、质料,还是色彩,曹七巧的服饰都有原来的简朴大方变得繁华绚丽。“银红衫子, 葱白线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意味着其服饰的花团锦簇、鲜艳耀眼,告别了往日的单纯,试图掩盖自己内心的苍白和空洞及对软骨丈夫的不满,寄希望引起姜家花花公子季泽的注意。“窄窄的袖口”、“小脚裤子”暗示了曹七巧受束缚的天性和被压抑的命运,不用说婆婆的威严,连丫头仆妇都蔑视她。服饰展示的鲜活的色彩与阴暗荒凉的心理的对比也就揭示出了七巧的命运的逆转。因此,当她失去丈夫独自寡居时,“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 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布漆布地衣,一级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爱与青春的离去,却使她心理变态,她把自己变态的情欲发泄到了儿女的身上,亲手扼杀了儿女的幸福,这时的七巧已变得老态龙钟, 如鬼魅般的黑影让人毛骨悚然。透过其外在的服饰的变化,读者不难看出曹七巧人性和希望的全部沉沦与沦丧。
参考文献:
[1]张爱玲.金锁记[M].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余斌.张爱玲传[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王艳,任茹文.张爱玲传[M].团结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张玉华(1971–),女,湖南怀化人,广西师范学院美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艺术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服装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