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关系共同体何以建构?
谢超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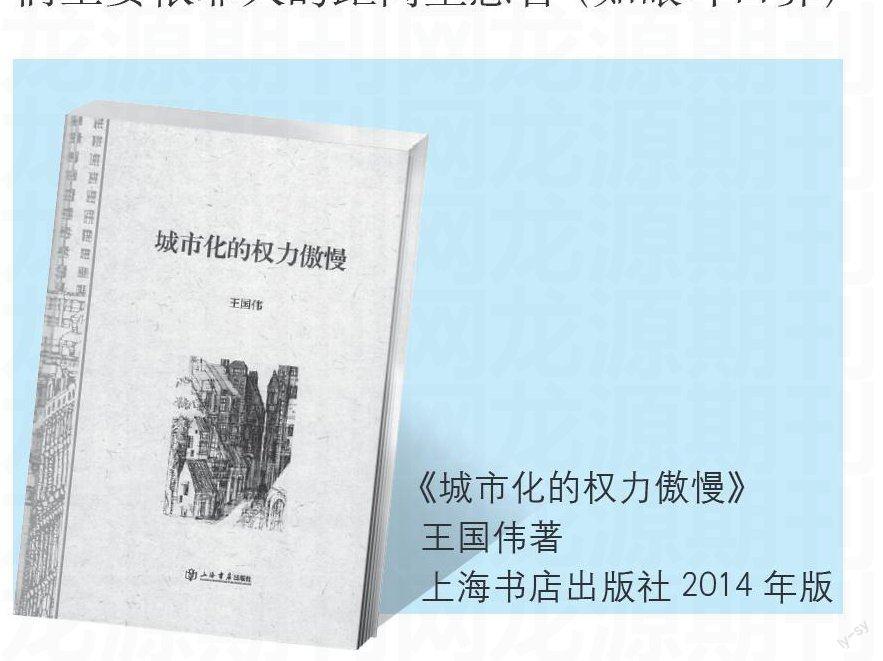
“城,以盛民也”,作为最复杂和庞大的人造物之一,城市因人而生、为人而生。然而,城市却并不是一个“死物”,它有着诞生、成长、发展乃至死亡的自身规律性。作为其创造者的人本身,也成为了这个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对于它的关注和讨论从未停止。
王国伟先生的著作《城市化的权力傲慢》,正是通过对城市以及艺术、文化、权力之间微妙关系的解读,透过遮蔽我们双眼的种种空间假象,揭开与我们纠缠在一起的城市化问题。当我们面对城市各类触目惊心的现实困境时,显然需要这种敏锐的思想和感同身受的叙述,并从中催生我们对体验的进一步理性感知。
丰满的城市体验依赖于关系的产生和持续,而这需要大量的细节作为基础,它们主要依靠人的距离型感官(如眼耳口鼻)来发觉。因此,空间对于人的知觉而言尤为重要,而一座城市的空间营造,则直接影响着其市民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对于城市环境而言,空间建构首先所要处理的,就是自然、人和建筑之间的关系。当这三重元素能够彼此融合,一个理想的城市关系共同体就有形成的可能。
正如本书作者在《自序》中所言,城市环境构成的核心元素,“是城市街道两侧的日常性人际交流”。一个城市的主体建筑单元,基本是沿着街道展开布局的,建筑、人和街道,形成三位一体的城市基本内容。因此,街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构成城市的交通路网。在街道中,人们与同伴并肩,与偶遇的熟人寒暄,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人们在行走中观察着这个城市的细节,“闲逛者”充分运用感官,在感觉中时而融入、时而独立于沿街的建筑群。在观赏街景的过程中,人本身就成为街景的重要内容出镜,并成为链接城市各种元素的活性中介。
然而,我们现实面对的却是低级城市化所带来的“千城一面”的平庸街景:难称宽敞的机动车道,狭窄的人行道,被汽车尾气和烟尘笼罩的绿化带,以及一排排沿街伫立的综合性建筑。当街景只剩下单调和枯燥,道路之于人的意义就只在于快速通行,道路也就变成空心化的物质形式。事实上,原本是为了追随速度而不断拓宽的车行道,并没有给人带来速度的快感,反而,人们对街道敬而远之,失去了日常生活固定场所的实际功能。
所谓“城以盛民”,城市生活经验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在于人群的集合和活动。融入和参与的积极性是自我生产和强化,因此城市人总是倾向于聚集。真正舒适的空间,是既邀请更多的人停留并加入,又能鼓励人延长身在其中的时间。犹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witchell Hall)曾提出的“边界效应”:当人背靠建筑物立面或绿化设施时,既可以减少暴露在空间中带来的不安全感,又可以清楚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并及时作出反应。这样的边界效应,可以给人带来安全的心理暗示,人才会驻足并放心地逗留。空间边界细节的安全性建构和能享受到的空间的开阔性视野,才能满足人对城市街道空间的复合性需求。
反观我们的城市,伫立在街道两旁的大多数是商业性建筑或者“下铺上宅”的公寓式住宅。同道路一样,沿街建筑也只为快速通过的功能意义服务,它们并不能提供鼓励自由行走和停留的边界区域。当行人难以舒服自在地“停下来”,当机动交通的鸣响盖过了人声,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简单集中都无法达成,倾听、交谈和进一步的共同活动又如何可能。本书中《何时能找回那份行走的殊荣》一文,便通过对欧洲传统的“林阴大道风格”和美国式的“汽车大道模式”的比较反思,表达了作者对城市化过程中严重忽视人行走的权利的城市规划的否定和批判。
实际上,林阴大道与汽车大道之争,可被视为两种现代主要城市模式之别的缩影。在“步行城市”中,慢速度将时间体验延长,小尺寸则将空间距离缩短,因此城市和建筑中的细节处理非常重要,人们的面容和姿态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观赏。这些丰富的细节建立起了“碰面”的意义,从而才有人的感受、交流,进而是参与、活动,整个城市也因此显得生动;而在“汽车城市”中,情况却恰恰相反,快速交通模式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时空形态。为了满足高速行进中的车内人的视觉要求,建筑类型趋同、标示牌和广告牌不得不被建成尺寸夸张的庞然大物,而那些一闪而过的景象注定还是面貌模糊的。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人无法获得适宜的视听体验,直接交流的尺度也就随之萎缩。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大都市建设基本都委身于“汽车城市”的行列,在对速度和效益的追求下,现代工业化精神催生出了具有可复制性、可置换性的街道建设模式,仅仅用为街道命名的方式难以避免人们对不同街道的混淆。同时,大多数街道的名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街名也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时常变动。街道原本清晰的地方意义表达已经弱化,人们对于街道的记忆总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具有可识别性的城市意象,整个城市的面貌也难免模糊不清,城市空间的精神向度更是无从谈起。正如本书中“文化决定城市的高度”标题所揭示的:城市的总体形象,不仅仅是由物质空间营造,更由精神图景所呈现。在城市空间对意义进行生产的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赋予建筑和城市以独特的精神向度和基本性格。在此方面,中国古代的空间营造称得上是一种典范。无论是房屋、道路、城墙还是桥梁,无论是艺术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中国古代的土木营造都以“和”的理念为共享的思想资源,讲究自然和人伦和谐关系的勾兑。对宇宙整体面貌的追求,以及调和折中的中庸态度,早已刻入中国文化的传统脉络中。这使得中国古代的空间构型尤其重视对“关系”的处理,它既包括“天人关系”,也包括了“人际关系”。
简而言之,“天人关系”意在协调自然万物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国传统文化素来在意“自然”所带来的诗意美,人造物一定要能被自然吸收,与万物完美融合。因此,与西方思想对功能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执著不同,中国人追求的是“宇内大同”的空间理想。“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经·系辞》)就是我们对于生存空间最素朴的期待。可以说,建筑是一种满足实际需要的形式,它作为一种事件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因此呈现出丰盛的日常性。因此,建筑的存在会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调整。而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制式是木结构,相较于西方古典建筑所采用的石材,木材更易损毁,但也意味着更易修复和调整,甚至原址推倒重建。而由建筑作为骨骼的城市本身,也遵循着相同的生命原则。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往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统一布局建成,其发展紧紧跟随着整个王朝兴衰的鼓点,朝代更迭往往导致政治、军事甚至经济重心的转移,这也足以导致一个繁华大城市成为弃子而逐渐萎缩。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建筑和城市的性格中蕴含着“便于生”的古老智慧。只有兼具灵活性和通用性的空间设计,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合乎使用。而当空间不再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时,即是可以进行调整甚至完全抛弃的。正是在中和的思想下,城市空间在中国人心中承载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
作为中国传统和典型的建筑—四合院,最能体现中国空间图式对“人际关系”的关照。由四个正方位的建筑组合围住中央的一个露天庭院,四围的房屋既满足了居住层面私人化的要求,又以中央的开敞区域保证了公共活动和人际交往。户内私密空间和户外公共空间,被纳入同一个四合单元中。再通过大大小小的单元组合和嵌套,空间的开放性和私密性也可以转换或者叠加。这种四合空间的意义,是一种鼓励交往的空间,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在这样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空间中,每家每户的日常活动的展开具有极大的重叠性和交互性。步行、逗留、玩耍,这些都为人们相互搭话和交谈提供了机会和便利;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的交往环境,则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续和稳固。这就像一个微型的城市空间。尤其要重视的是,无论是中国传统建筑,还是当代意义上的城市,人文尺度的建立,需要合适的距离设定,如果距离失当,城市就失去了交流的基础。
因此,自汉至唐,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采用的也是一种四合式的“城坊制”:城内有由墙合围的坊,坊中设内街。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古代的市集也充分体现了四合式空间的优势。整个坊市四周合围的屋舍是固定商铺,中间的开放区域则用于开市后摆放摊位,进行商业买卖,正所谓“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以说,四合式的空间单元,已成为中国古代土木营造的基本单位。大到整个城市,小到单体建筑,中国古代的空间设计和构建都紧紧抓住这种带有宇宙图景的意义精髓:四方和合。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带有浓厚中国式“人情味”的四合式空间形式,如今为何从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中消失了?这还得继续从“坊市”说起。自坊市出现后,其区域就是被严格圈定的,在没有商业活动进行的地方是不允许出现商铺的。从《周礼》中的《冬官考工记》中可以得知,早期的商业区域被设置在行政中心的后面,以便官员管理。而在坊市外围相对的两角处,更有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吏相向而立。然而,到了宋代,为了满足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商铺也不得不由向内变为向外,最大程度地吸引和方便顾客。坊墙被冲破,城坊制解体。掌权者不得不作出让步和调整,着力制定规范市场行为的准则和制度。商业区域也从行政地区中解放出来,多被放置在市民居住区的中心位置。随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活跃,商铺逐渐摆脱区域限制而在所有的街巷中蔓延开来,形成了我们如今非常熟悉的城市街景的雏形。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古代商业的发展使得四合院式的空间单位被打破,但这并没有动摇中国人空间蓝图的基点。自上古时代开始,无论是伏羲八卦、文王八卦还是河图、洛书,呈现的都是一种平面的空间图式。这种水平向布局最后逐渐形成了最为典型的中国空间格局:北向为尊,南北轴线,平面五方。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最直接依赖于视听经验,而人最自然的运动就是水平方向的行走,因此人类知觉也是与此运动相适应的。“脚踏实地”的在地感,成为人际感情的生根发芽的沃土;平视的目光易于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亲近感由此而生;以自身为中心点的环视,则为人提供置身和融入环境的体验。在这种水平图式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精髓,以及空间体验之于“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当狭小封闭的电梯和逼仄的楼梯间取代了开合有度的庭院和通路,这意味着狭窄的竖向视域开始主导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人往往只能作为底点向上仰视,无限延长的视线将带来敬畏感和疏离意识。城市人情感的形状似乎也在不断地被拉长和窄化,最终纤细到无法承受亲密关系的重量。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垂直空间指向,早已在巴别塔、哥特教堂那直指苍穹的姿态中得到诠释。只是那时的“神人”之别,已经延展为现代的“人人”之别。
差别、个性、独特……这些正是现代化最引以为豪的遗产。西方启蒙之剑披荆斩棘,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狂奔突进,要将“人文主义”的旗帜插满高地。作为西方古典建筑的最高尺度,“神”的形象已经在人的权力欲望面前迅速矮化,宗教的神圣光环被大机器之手打碎。横扫一切的现代建筑,信奉的是“物”的神话。现代空间可被视为一整套“物体系”的产物:同质物构成“模式”,以适应工业时代对标准化操作和量化生产的要求,通过机械复制性达到投入最优化和产出最大化;异质物则形成“系列”,排列和组合成为市场上的制胜法宝,通过营销策略保证产业链的形成和扩充。因此,“世界名画”作为流行装饰物出现在各家各户的客厅,自具情态的水乡成为面目标准的“江南古镇”……商品化正以其不可逆的力量,牢牢钳住城市空间建设的喉头。在资本急速前进的潮头,是欲望之舟索求无度的风帆。一切都是“被展示的文化”,惯例和特例之间的界限早已模糊:正是对于“不同”的追求,使得我们在本质上“相同”。
这就是现代性所编织的进步神话的悖论,它带来的只能是虚伪的“丰盛”。尽管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样、越来越精致的物品塞满,我们所体验到的却不是满足和充实,而是过度和拥挤。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生存和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冰冷的钢筋水泥只能构造亲密的假象,根本无法完成带有体温的拥抱。精神的焦虑、紧张和压抑,已经成为城市人的生活常态。我们已经无法从现代都市“人造的安全感”中获得庇护,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度被粗暴地稀释,彼此守望的传统邻里关系在高楼公寓的缝隙中苟延残喘。内向型的熟人社会,已经被外向型的陌生人社会取代。然而,即使是陌生人之间,也总是需要一个搭话的机会来展开交谈,这种机会往往产生于他们进行相同的活动时,比如因为同一件事情并排站着或者坐着时。在具有街头音乐传统的西方都市,陌生的人们还能以驻足欣赏音乐为契机,开始一番愉快的谈话。然而在中国的城市中,能让陌生人群共同停驻的典型时刻,恐怕就是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时。
这是一个让人“无话可谈”的城市,其空间建构仅余“形”和“饰”,不再产生关系,不再演绎文化,也就无法构建出一个理想的关系共同体。现代城市人容易对自己身处的城市缺乏认同和归属感,一种流离失所的彷徨困扰着现代“异乡人”。因此,面对一大批公共性大型地标建筑的落成,市民们缺乏热情的回应也就不难理解了。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在城市空间建设和转型的这幕大戏中,缺席的不仅仅是观众,还有演员。如今,中国市场已然成为西方设计师逐鹿的场所,国际名声意味着占得先机,名利双收又催动了西式话语权的建立和稳固。市场价值的偏移不仅生产出无数建筑垃圾,更带来了“城市审美沦陷的文化灾难”。中国自身的艺术感觉仿佛已经麻木,对市场被占领、机会被掠夺的暴力,本土设计师也毫无还手之力。面对决策者与出资人的二元结构,文化和资本的合力,以及政治、经济和技术权力的博弈,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建筑多也缺乏文化个性,粗暴的模仿乃至复制已经成为基本业态。难怪王国伟先生在书中慨叹:“在这个高水平游戏的场域中,我们缺席了整整一个时代,不但遗憾而且悲哀。”
中国的城市,如何能在全球化浪潮对现代城市的均质碾压中成功转型?中国的当代设计师,又如何能在西方理念和风潮的围堵中,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尽管现代空间的暴力不断蚕食着都市人的共同体蓝图,我们依旧不能丢失对城市进行再想象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