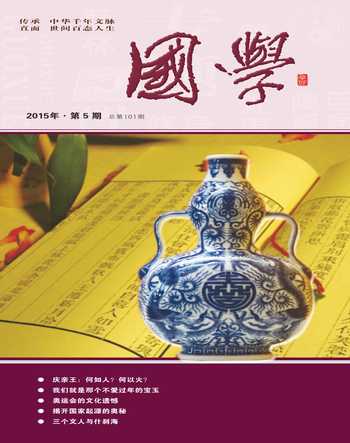浪漫孔子
郭小琲
孔子正视人的正当欲求,努力要使人成为“人”。
孔子是浪漫的,只要你用心读《论语》,《论语》中就会走出一个浪漫的孔子。当然,这浪漫不是少男少女手中的玫瑰,而是超越现实满怀热情的理想追求。
有一句话很能够表达孔子的浪漫:“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色”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敏感词。说这个人好色,那肯定是批评;说那个人有几分姿色,又有点儿暧昧,如今更是难置可否。然千百年来我们抱定一个观念:君子喜好德行要胜过喜好美色。可任谁都知道这是个不易达到的目标。因为实在是好色易而好德难。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话也绝不是泛泛而言。虽然孔子说话时的语境我们无法知晓。推想或许与南子有关。孔子拜访卫国,有着纳贤美名的卫灵公却与南子同车,招摇过市,将孔子冷落在后面的车上;或许另有它因,比如齐人针对孔子而去的弱鲁计划——赠送给鲁国的女乐就让鲁国君侯疏远了孔子。由此孔子生出失落、失望、遗憾也很有可能。所以,当孔子发出那句著名的感慨前先脱口而出:“已矣乎!”那一定是对他亲历的现实、现象很不满了。否则,“朝闻道,夕死可矣”有着异乎寻常的笃定和坚持的孔子怎会说出“算了吧”这样泄劲的话,一定是卫灵公们“色”得过分了。其实过分的何止卫灵公们。史上不知上演过多少荒淫误国的悲剧丑剧,世间也确有无数的龌龊荒唐,其间都有好色的根源。所以,孔子一句“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感慨实在是发聩古今。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把“封建”名号加于孔子,打之倒之,批之斥之。然孔子并不是人所误解的保守老朽。他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正视人的正当欲求,只是力主以“礼”节之。然开放的现代人一定要算男女分途、授受不亲的老账。不过这账算得也是糊涂。糊涂一是说账不分明细,全算在孔子头上,二是这账算得全然不计后果。于是账算过了便迷失了,于是现代人的眼光中透出对于“狼”的崇拜和对于“猪”的羡慕,孔子的浪漫也就自然难懂。倒是明人李贽算得精细,以浪漫之心解浪漫之人:“原不望人不好色,只望人‘好德如‘好色耳。”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努力要使人成为“人”。他忽略道德追求与大脑神经生物反应的根本不同,不在意形而上、形而下的境界迥异,硬是把二者同说并论,并做成一把衡量君子的标尺。这把尺子的刻度一面是“德”,另一面是“色”,阴阳两面此消彼长,高下自见分晓。这也太富有创意了。
我们知道那个行走在湘水畔的诗人歌啸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在表达着一个时代的浪漫情怀,然这浪漫并非突兀而至,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已是滥觞。这浪漫在于开启好德的自醒和觉悟,引领好色的调和与节制,在于使人自别于禽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浪漫的,却毕竟很现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理想的,却是孔子描绘出的浪漫。
现实永远是残酷的,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在浪漫的人眼里,并不是看不到现实的残酷。只是不刻意而已。孔子所见的礼崩乐坏岂止残酷,残缺、甚至是残败都是有的,只是孔子不放弃,一味地想通过改造君子而改造社会。有一次孔子就对子路叹道:“由!知德者鲜矣。”仿佛有阵阵隐痛直抵他的心胸,也让如今的我们感知尚德的艰难。也正因为如此,“好德如好色”的期盼才显弥足珍贵。孔子是感性的,在他的时代见恶恶之,见丑丑之,但依然梦想着,追求着,坚持着。这正是他精神的伟大,也是他浪漫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