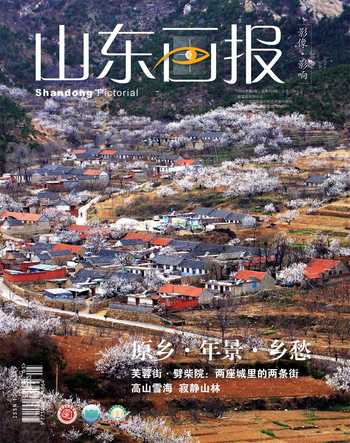两根幽怨 一把悲怅
雷虎



很多人对于二胡的印象,来源于街头卖艺的『阿炳』们。二胡特有的悲凉嗓音对鼓膜的蹂躏,再配上『阿炳』们的视觉冲击,能让身在春天里的你如履寒冰。但是人往往都有那么点受虐癖。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整理旧物件时,偶然翻开高中时听过的老磁带,居然在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旁边看到一盘《二泉映月》。听过之后觉得虐心,就再也抑制不住了。一路高铁直奔苏州吴门桥,去寻找那专门制造这揪心二胡的琴师。
二胡的『罪魁祸首』刘天华已经不可寻,但是却可以找到给其制二胡的琴师王瑞泉之子王国兴『问罪』:整这专发天地悲音的二胡出来,你得有多么悲天悯人的心啊。
蟒皮惊魂
大师的工作室在巷子最深处。我一拐再拐,终于拐到大师藏身的小巷尽头。巷尾出现两栋布满爬山虎的苏俄式二层红砖房。虽然已是阳春三月,大地回暖,但爬山虎却还未回春,认为开枝散叶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懒散伸出枯萎的蔓枝缠绕着老朽的红砖。红砖房的二楼,便是二胡大师王国兴的工作室。
按照以往寻访名家的惯例,寻斫琴家,甫进巷口就能听到太古雅音;探铸剑师,还未进门就可感到肃杀剑气。这次探的二胡制作师,乃二胡界“南王北李”的“南王”王国兴,楼下应该也出点祥瑞之兆才对。但是很遗憾,眼前万籁俱静。
于是我踮起脚伸长脖子往二楼的窗户里边瞟,没瞟到二胡一弦半弓,却引出了一楼面带警戒的小青年。在得知我要找“二胡大师王国兴”后回复我:“大师?我怎么没见过。”欲转身进楼,一秒之后又转过身:“你说要找做二胡的?楼上还真有一位,您从这边请!”说完嘴角挂笑进楼,我还没来得及分析那丝笑容的含义,摄影师已经沿着青年指的“这边”上楼了。
“这边”是挂在右边那栋红砖房上的木楼梯。木楼梯上到二楼后,分出一架木质天桥连着左边的红楼。我屏气凝神还试图寻找那丝“大师之气”。摄影师却不再矜持,被眼前的景致感染后,脚上一级楼梯手按一下快门。当她的脚步声停止时,我没捕捉到与之匹配的快门声,却听到一声惊呼,然后是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蛇!天桥上躺着一条蛇,不是蛇,是蟒!”我听到摄影师的话后,条件反射一般蹦离楼梯三尺远。惊魂初定后问摄影师:“你确定看到蛇了?今天阴历还未到三月三,蛇应该还在冬眠才对!”
“我没看到蛇,我看到的是蟒!”摄影师边说边让我看相机显示屏。当看到一水桶粗电线杆长的阴影浮现在显示屏上时,我拉着摄影师来了个三级跳,逃到离楼梯三丈远的地方。
“我现在明白那小青年为什么对我笑了,那蟒蛇也对我笑!”摄影师哭笑不得。
“我现在明白什么叫大师气场了。这么大条蟒蛇看场子!”我怒从心底起。
我们的动静太大了,惊得二楼探出了一个脑袋。问清我们来意后他指了一下那木楼梯又来了一句:“这边请!”看着我们迟迟未动,他才回过神来。脑袋缩了回去,几秒钟后天桥上多了一个人影。那人身着皮夹克、脚蹬亮皮鞋、梳着大背头,着装可亲可近却让人不敢近。因为他手上抓着那条在我们心中留下阴影的阴影—一条水桶粗电线杆长的蟒蛇。他抓住了蟒蛇七寸,但蟒蛇尾巴却垂到地面上。我和摄影师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异口不同声蹦出了两个词:“驯龙高手!”“天神下凡!”
眼前这位天神和高手合体的大叔就是王国兴。而那吓得我们魂飞魄散的蟒其实不是蟒,而是蟒皮——蟒皮是制作二胡琴膜的材料。王国兴前几天新收了一条蟒皮,放在天桥上晾干准备制琴膜,却不巧被叶公好龙的我们撞见。
“一直以为收天籁之音制琴的琴师是天底下最浪漫的工种,没想到却是一项与蟒谋皮的要命活!”摄影师看了一眼躺在天桥上乘凉的蟒皮,发完感叹后问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问题:“这蟒蜕下的皮在这,那蜕过皮的蟒躲哪去了?”
子承父业
王国兴的工作室所在地前身是一家纽扣厂。1995年,这家厂因为不景气而倒闭了,而王国兴正好从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就和几个朋友一合计,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
“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首先,自己的名字,好记;其次,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最后,还有振兴国乐的念想。只可惜这个念想到现在都看不到踪影。”王国兴边说边拿出了两个红本本。这两个本本分别是颁发自1985年的苏州民族乐器厂“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
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但他对这两个厂颁的奖项情有独钟,是因为那时的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泉同台献技的时期。
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李,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泉则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那是什么概念!”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
1979年,自从父亲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后,父亲就成为了王国兴追赶的对象:“就像是一位纽扣匠,做纽扣其实是枯燥无味的,但是一旦你锁定了厂里最好的纽扣匠为追赶目标,每天的工作就神清气爽了。”王国兴工作时,受到“劳动光荣”的思想熏陶,认为若把二胡比纽扣,起早摸黑两相宜。他从来没把做二胡的自己当成一回事:“父亲制的二胡,获得过国家乐器评定委员会授予的‘国家银质奖,我都制二胡三十多年了,还没人给我颁这个奖,那就说明我的二胡还没做到位,那就继续努力!”王国兴说起来轻描淡写,但是却让人无语至极——那可是二胡界至今为止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最高奖项。做琴齐上阵,拿奖也要父子兵么?
蒙皮绝活
王国兴在二胡界称王,琴筒制作上“制膛”和“蒙皮”手艺是其压箱底的手艺。为保证每把出品的二胡都精益求精。王国兴决定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它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是最关键的“制膛”和“蒙皮”却由自己亲自操刀。亲自操刀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灵感来了,虽然客自远方来但也得靠边站,在工作室里,制二胡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他推开一个小房间,大小不一的木头呈现在眼前:“这是珍藏了十几年的花梨木,这是新进的印度小叶紫檀,这些都是做二胡琴壳的原料。”说完他又推开了另一个房间,四壁居然是一块块木块堆起的木墙。
“二胡琴筒就是由六块这样的板组合起来。每块板长131毫米,前口外边,宽度为51.9毫米,前口内边宽41.6毫米,后口外边宽46.2毫米,后口内边宽35.8毫米,厚度均为9毫米。六块,才能成为正六方形,每块板两边所刨成的角度均为60度。”
在秀完“制膛”绝技后,他又开始展示家传的蒙皮绝活。所谓蒙皮就是把蟒皮蒙在琴筒上的过程。对于二胡制作来说,蒙皮是最为重要的工艺。二胡是靠蟒皮的震动来传导声音,因而蟒皮的厚薄、松紧对二胡的音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蒙皮没有具体量化的指标,完全得依靠蒙皮人的听觉和手感。再者,不同蟒皮和不同琴筒接触都会产生不同的声音。选哪张蟒皮和哪个琴筒配对都有讲究。这个‘红娘做得好,二胡就成了一半;如果强用‘拉郎配,那回头二胡拉出的声音会让你听了想哭!”
王国兴站在一架打孔机前,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往打孔机前送,就如同缝纫工往缝纫机里送布料。当打孔针在蟒皮上打下一个孔后提起的瞬间,他的手麻利地转动蟒皮。“二胡琴筒是正六边形的,蟒皮蒙在琴筒之上,全由蟒皮上打的六个小孔来固定。因而每次打孔时,转动蟒皮都必须是60度才行。”
待所有蟒皮都打完孔后,王国兴下意识地闻了闻双手:“蟒蛇皮上有股血腥味,和蟒蛇皮接触多了难免沾上了。这不,这血腥味太重,房子里老鼠都不敢来。要不是身上有这股子腥味,我还一直以为我是在这钮扣厂里的纽扣匠呢!”
他把蟒皮每个孔里穿好棉线后缠上小木棍,然后把蟒皮顶在琴筒。待蟒皮在琴筒上固定后,在琴筒内壁塞进一个小木桩,然后把蟒皮上的小木棍在木桩上缠绕拴紧,这样蟒皮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琴筒上了。
蒙一张蟒皮,王国兴足足用了十分钟时间。我看到工作室里摆满的琴筒,对王国兴生出无限的怜悯——每一只等待蒙皮的琴筒就像一只雏鸟,要把这些嗷嗷待哺的雏鸟喂饱,一喂就是三十多年,这得要多大毅力啊!看来每一位二胡制作师,都要有一颗做超级奶爸的心才行。
不谙弹奏
“通常我制二胡时,为了节约时间,同一时间只做一道工序。看,这边案板上都是我昨天做好的琴筒;那边木桶里插的,都是我昨天做的琴头;那边墙上挂的,是我上周制的琴弓……”
王国兴在工作室里指点江山。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在案板上,我看到了一排整洁的蜂巢;在木桶里,是一朵朵盛开的硕大蒲公英;在墙壁上,是弓箭手的兵器库……
当我沉醉在这些精美的图案中时,王国兴的身影开始在这些场景中不断游走:取了一块蜂巢、抽走蒲公英中的一朵、摘下墙壁上的一支弓箭……经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变身后,这些零散的配件组合成了一支精美的二胡。
当王国兴把组合好的二胡抱在怀里时,在我眼中,他不再是驯龙高手而是阿炳转世:“与君弹一曲,请君为我亲耳听!”
我已经把情绪调到《二泉映月》的悲凉基调,但是眼前的“阿炳”却迟迟不肯演奏。“抱歉,我不会拉二胡!”王国兴说出了一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话。
“卖茶叶蛋的就应该下蛋吗?”看到我的表情,王国兴来了个更让我惊愕的反问。“对于琴师来说,用最多的心血把最好的材料制成二胡,工作就完成了。至于要让二胡奏出什么样的旋律,那就不是琴师考虑的了!”
——以科左中旗为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