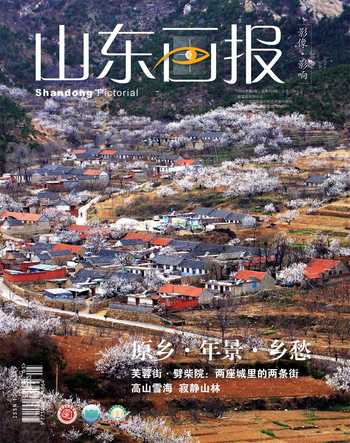一个人的春秋
魏新


最早,一年只分两季,春去了就是秋,秋去了春就来。后来才增加了夏和冬,四季交替,历史也有了更多分明的层次,但春秋无可取代。
因为春秋本身就是历史,是时间,亦是人生。
历史有循环,时间有交集,人生有悲欢。然而,不管历史如何反复,时间如何飞逝,人生如何起伏,春还是春,秋依然是秋。春天的花开得多鲜艳,秋天的叶便落得多凄凉。无限衍伸的春秋,被一代代人见证。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竟有一个时期被称为春秋,实在是太贴切又太富有诗情。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历史时期,那时的人们单纯、质朴、执著、勇敢。那时圣人比庸人自扰,王侯比书生谦恭。那时战争不断,但还不怎么去耍诈,两国交锋参照RPG游戏的回合制,你给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打仗都讲究礼尚往来。那时霸主纷争,可势力再大,也不敢把天子取而代之,连想都不敢想,逢年过节还得过去送礼进贡,夹着尾巴回来,再昂首挺胸。
那时天下兴亡,用不到匹夫去负责,有贵族们扛着,天塌了贵族个儿高,必须先顶。率土之滨,王臣们也不都是奴才,脊梁骨挺得像根葱,剁碎了拌豆腐也一清二白。
读这么一段历史,不感触也难。只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不管是角度还是内容,无法也不用统一。全民写史的年代,从夏商周到明清甚至民国几乎都有一套“那些事儿”,历史成了事儿妈,但是,真正能把历史写精彩的不多,有见识和见地的更是稀有,我深信连根兄是稀有中的一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稀有之人。
要说和连根兄的交情,还要从十年前说起,当时我刚到一家报社工作,在那个单位,他是有名的文人。当时那里聚集了不少这座城市的文人,后来,很多人相继离开,连根兄是其中的一位,我也勉强算一位,因此,回忆起和连根兄的相识,总会产生一些物是人非的喟叹。
第一次和连根兄打交道,是他刚出了一本关于济南本土历史文化的书,我厚着脸皮给他打电话讨要,他很爽快,让我上楼,到他办公室来拿,还在扉页上欣然题词。当时他其实并没有多少样书,也和我毫无交情,如此的欣然应允,令我事后颇为感动。
再后来,由于种种机缘,我们在一起吃过几次饭。没记错的话,不会超过三次。据说连根曾经很能喝酒,但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戒酒了,能喝酒的人一旦戒酒,在酒桌上总显得有点别扭,大家喝完酒之后的酒话,都跟梦话一样,清醒的人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所以后来,连根兄很少参加这样的场合,大家在这样的场合,也很难想起连根兄。
但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旦有人提到连根兄的时候,大家所做的,就是集体点赞。这些赞里,有一部分来自连根的才华;还有一部分,来自连根兄的性情。
连根兄是一个特别纯粹的人,不掺杂质,不趋炎附势,不同流,更不会合污。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媒体原本像个大染缸,在染缸之中浸泡了多年,连根毫不变色,直到连根拔出之后,依然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精神头,即使众人只是装醉,连根依然懒得去装成一副要死的样子。
所以我挺敬重他,将他视为兄弟。在这个年代,不喝酒就能让我说这样的胡话实在具备相当的难度。的确,他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俗人,对人间烟火也没有过多迷恋,就是读书、写作,偶尔给神学院上课。是的,神学院,他曾说为神学院上课怎么还能计较酬劳,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里闪着神性的光芒,让我感到深入骨髓的惭愧。
因此,我觉得连根兄写春秋这段历史,就算不占天时地利,也是彻底的人和。更何况,天时地利都比不了人和。是的,连根兄这个人,一直生活在春秋中。
春秋大业,在连根兄的笔下变成了具体的生动。春秋大义,在连根兄的身上闪烁着点点光芒。连根兄写的,是一个人的春秋,也是所有人的春秋。
春秋或不在,春秋亦永存。谨以此文与连根兄共勉。
(作者系著名学者、作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