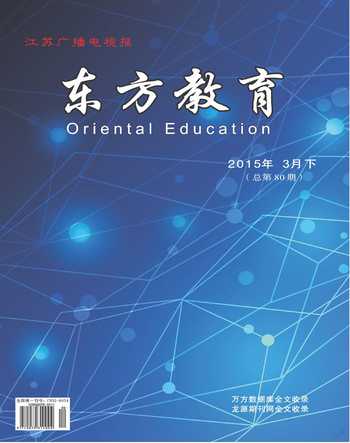《兄弟》读后感
朱海涛
昨晚两点多终于把《兄弟》看完了,这是看余华四部长篇中的最后一部。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到《在细雨中呼喊》再到《兄弟》,有一种感觉,就是余华的小说总给人一种震撼,一种悲愤。可能是“文革”时期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太深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从这四部长篇来看余华仍然是把主要的场景选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而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数是以一种“赤裸裸”的形式展示出来,甚至有些夸张,余华以冷酷和冷幽默的笔调把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爱与恨抒写得格外分明。多次查过余华的简介,出生于1960年的江南小镇,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更致力于剖开文革时期的中国广大人民的内心。他一冷酷的笔调揭示人性丑陋的角落,罪恶、暴力、死亡在这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均有描写,甚至占据了主流。但同时,他也把人性的美好,淳朴、诚挚、真情抒写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汪曾祺先生说过:故乡和童年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一切文学发展到极致都是儿童文学。余华对此应是赞同,死部小说中都着重描绘了主人公童年的悲欢离合。余华的童年在“文革”时期,或许是“文革”给了他太深的记忆。“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那时发生的往事并不如烟。”从这点看,余华是在为生活,为内心写作,没有违背对自己对读者的承诺。
第一次接触余华的作品是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第一次读就觉得文字朴实但情节却太悬乎,多读两次,试着将自己作品的场景中,才发觉别有洞天。余华有时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以经常看到他发微博“抱怨”这“抱怨”那,总以一种极其讽刺的文字发泄或许也是警醒。
后来,再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在地摊上看到厚厚的一本余华作品集,花了20块钱将这本盗版买回来。首先读的是《活着》,读了十多页才发现跟自己喜欢的一部电视剧《福贵》的情节很相似,再一看,主人公名字都一样,百度一下才发觉《福贵》是根据《活着》改编。考虑到对观众的影响,还是删改了许多,毕竟,“文革”那段历史没人敢去“深究”。甚至,主写“文革”的电视剧也屈指可数。后来,《活着》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前些天,看到新闻说又在北京被拍成了话剧。余华后来在微博里说一些作品被改的不满,他带讽刺的引用了拍话剧那个导演的一句话“话剧《活着》以一种天马行空的方式忠于原著”,但他肯定了袁泉饰演家珍的真诚。
回到《兄弟》上来,看完了上部,可以说是非常感人。李兰丈夫死了,宋凡平妻子死了,各带一个儿子,两个命运如此相似的人,带着各自的“拖油瓶”,在世俗的鄙视下,走到了一起,李光头和宋钢两个性格如此不相容的人也竟然情同手足。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借一句话来说就是:李光头这样的传奇(后来的巨富之路)在中国比比皆是,而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绝无仅有。所以很少写爱情的余华自认为在《兄弟》中,他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每个人的爱情,都必定与时代相连。余华说:“文革”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妇父母之间的背叛和出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家庭是空前团结的,就像我的小说里一样,有一男一女,他们互相需要,相依为命,缺了对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的爱情非常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能永远,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年代,谁缺了谁都没啥大不了,是不可能产生美好永久的爱情的。”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爱情最深刻,一种是相濡以沫,一种是相忘江湖。无疑,余华笔下的爱情属于前者。 然而,在一切都看似完美的时候,“文革”袭来,一切都变了,宋凡平被当成地主被批斗,为了去上海接李兰出院,宋凡平“逃跑”了,然而在车站,却被六个带着红袖章的人活活打死,摆在路上。李兰回来,得知宋凡平死了,六年没洗头,因为在刘镇,丈夫死了应该一个月不洗头,没有人知道李兰对宋凡平的爱有多深。七年后,李兰也死去了。李光头和宋钢成了两个孤儿,宋钢答应过李兰,他会好好照顾李光头,剩最后一碗饭了让李光头吃,剩最后一件衣服让李光头穿。。。。。。李光头也对宋钢说过,“即使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你也还是我兄弟”。他们是兄弟,仍然是,一直是。后来,宋钢和林红结婚了,那个李光头日思夜想的女人,李光头和宋钢从此恩断义绝,可是两个人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永远把对方当兄弟。一想起儿时的悲惨,以及后来一家人的欢乐,依然想着对方,记忆还在,感情就还在。小说中有个情节就是李光头在县政府大门口“静坐示威”,穷困潦倒,被认为是收破烂的,宋钢看到了他,将林红给他的他舍不得花的钱和粮票给李光头,李光头竟然理所当然地接过钱。读到这里,我没觉得李光头有多无赖,而是深深地被他和宋钢之间的这种感情打动,他们的默契已经不需要拘束,不需要客气,理所当然才是他们兄弟情谊的体现。我也为自己生活中有这样的兄弟感到幸福。
下部的情节有着哈姆雷特式的悲惨,这也是余华《兄弟》下部被许多人批评的原因。李光头爆发了,宋钢去上海寻找出路,李光头却和自己的嫂子林红苟且了。宋钢得知了,为了成全李光头和林红,他躺在了冰冷的铁轨上,李光头和林红从此视对方为仇人。最后李光头说想要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进行太空旅游,带上宋钢的骨灰。。。。。。有人说,余华是在玩弄读者,余华是受商业潜规则了,还有人说余华这是末日之欢,甚至有人还说《兄弟》中的变态情节正是余华自己的变态人生的写照。我觉得余华是以另一种形式想读者表达些什么,小说中的淫乱,奸邪,贪婪,丑陋,欲望等等,这些或许都是这个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揭示现在这个世界的阴暗一面。余华只不过是用了一招“乾坤大挪移”把时空轮转了一下罢了。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李光头满怀信心来到上海,却发现几年没来,世界已经变了。小说中的原句就是:“五年前,我去上海为福利厂拉生意,只要把福利厂残疾人的全家福照片拿出来,再加上我的真诚热情,就会打动一个个公司的一个个业务员,拉来一笔笔生意。五年后,我拿着世界地图为我们自己去上海拉生意,比五年前更真诚,更热情,也更成熟了,可是、、、”李光头伸开的手指卷了起来变成了数钞票的动作,“现在时代不同啦,社会变啦,要靠塞钞票行贿才能拉来生意、、、、、、”是啊,社会变了,动乱后三十年了,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四百年才能经历的天翻地覆,我们中国四十年就经历了。” 至于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完全能在现实中找到原版。所以余华有所想,也有所做,写下了这部令人争议的《兄弟》,希望余华先生能继续创作,像他自己所说:努力更加接近真实。
——读余华小说《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