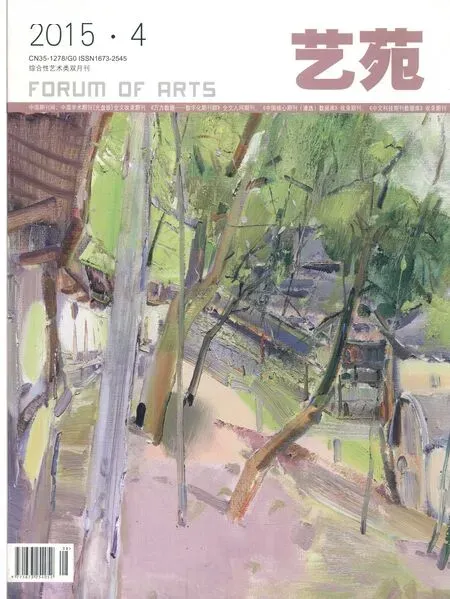镜像时代的生命沉思——再论《一一》的主题与电影语言风格
文‖刘金平
镜像时代的生命沉思
——再论《一一》的主题与电影语言风格
文‖刘金平
“ 昏迷/死亡”事件刺穿了世纪末华丽的富足神话,使《一一》反转进入一个“由死及生”、追问生命意义的叙事进程。而在镜头语言上,杨德昌一方面运用丰富的都会建筑元素展开对人性异化境况的暴露;更重要的是其创造性地对镜像时代的高度自觉与批判性思考,正是借由对镜像的反身指涉,他不仅实现了对电影本身的解码,同时完成了对新千年虚实边界模糊的科技时代的重新编码。
《 一一》;由死及生;镜像时代
在一次采访中,吴念真曾用“看山依然是山”来形容《一一》(2000)时期的杨德昌,在经历了《恐怖分子》(1986)、《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的悲观和《独立时代》(1994)、《麻将》(1996)的愤怒之后,杨德昌在自己知天命的年纪迎来了对生命的宽柔理解,时隔四年再次出手给世界留下了一份“平淡而山高水深”的感动。
一、由死及生
大概是要表达的东西实在太过丰富,从《恐怖分子》开始,杨德昌便醉心于人物群像的错落式叙事。《一一》也是如此,不过不同于之前影片中都市各阶层人物因种种偶然性的交遇而旋生悲喜歌哭,这一次杨德昌将视点落在了“家庭”,他要拍的是生命的各个阶段,是生老病死,而家庭中“所有的年龄都有一个代表,所有的人又都是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经验可以投射都彼此身上”[1]。
影片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父亲NJ(简南俊)是一家电脑公司的合伙人,母亲敏敏是职场女强人,他们跟8岁的儿子洋洋、念高中的女儿婷婷以及孩子们的外婆住在一起。故事开始于小舅子阿弟的婚礼,阳光明媚、草木葳蕤,高调光、优美舒缓的背景音乐以及全家福的全景镜头都展现着家庭生活的和谐和意趣盎然。然而,经典叙事的原则是问题的产生与解决,唯此情节才能得以不断推进。风波似乎首先来自于阿弟的情人云云突然出现在婚礼上的搅场,不过影片在此着墨并不太多,因此真正的冲突来自于搅场后心绪难平的婆婆提前回到家中,而后却因替婷婷倒垃圾而晕倒在路旁,此后她始终昏迷不醒——于此,“昏迷∕死亡”成为一个象征性因素贯穿、笼罩着影片始终(最终以婆婆的葬礼结束),它的骤然登临,让所有人的困境都朝向镜头敞开,也让影片的叙事成为一个由死及生的过程。一贯雷厉风行的敏敏冲着NJ的哭诉可谓是这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段落。家里人轮流向昏迷的婆婆说话,但敏敏很快发现自己每天跟母亲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生活的贫瘠和僵硬令其震惊,她说:“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在这里,“昏迷∕死亡”完成了一个反转动作,刀锋般刺穿了世纪末华丽的富足神话——泪流满面之后,现身的是对“意义”的追问。
然而NJ也无法给出答案,事实上影片中每个人仿佛都有着一种宿命般的失败经验:重视友情、深具远见的NJ在金元原则至上的浅薄商业环境中屡屡受到朋友们摆布,却只能独自愤懑;婷婷因对婆婆的愧疚而日夜失眠,在友情受伤的情况下以为遇见爱情却最终遭到胖子的背叛;瘦小却敏感而早熟的洋洋则在对世界和性的朦胧初觉时便饱受挫折……甚至从这个家庭延伸出去的种种社会关系中的诸多人物,如阿弟、小燕、莉莉、胖子、阿瑞、大大等无一不处于生命的焦灼、沮丧状态。影片中多次出现婷婷手中的那盆绿色植物,无法不让人觉得这是导演有意设下的象征——它总也长不开,一如这个布满挫折的世界中人们无法绽放的生命。

图1 电影《一一》剧照
如前所述杨德昌试图讲述的是生老病死的生命各阶段,家庭成员的经验彼此投射。为了实现这一意图,他充分运用了电影的魅力,以一段精彩纷呈的交叉剪辑将时间性引入共时的空间之中。这个段落将NJ与初恋情人阿瑞的东京之旅、婷婷的初恋以及洋洋对一个女生的暗恋共置在一起;导演选择了相同的时间(连时差都被考虑)、相似的环境,而NJ对初恋的描述(小学时的暗生情愫和中学的第一次约会)也完美无间地完成了对婷婷、洋洋彼时状态的描述……以上种种,构成一个精致的关于“生命∕爱”的循环叙事!然而,故事依然还是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悲观——阿瑞不辞而别、胖子落跑、洋洋一生湿淋淋地回来。后来,NJ抽着烟对敏敏叹气说:“本来以为再活一次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有那个必要,真的没有那个必要。”而刚从山上灵修回来的敏敏也说,“其实真的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那个位子好像换了一下……”——讽刺的是,这是整部影片中这对夫妻最彼此同情的一次交谈,风沙满袖、悲不可遏。一个经典的杨氏前文本幽然现身:“变化是轮回的循环”——《恐怖分子》中的女作家如是说。
但或许是彼时的杨德昌渐渐告别了激愤与悲观,影片给出的结尾却格外温暖。这个逆转由洋洋完成。阳光明媚、草木葳蕤、高调光都一一呼应开头;穿着西装的洋洋以童稚而严肃、一字一顿的声音向去世的婆婆念着告别辞:
“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
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去了哪里,那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叫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
在这个过程中,镜头分别拍摄分坐灵堂两侧的敏敏与NJ、婷婷,他们的目光集中于洋洋,若有所思……镜头的缓缓摇动足以在观众头脑中构成又一副家庭全景(度过劫波之后生命重归平静)。这样一个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段落无疑是另一个杨氏经典,这个喜欢拿着相机拍摄别人后脑勺、告诉他们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小男孩平衡了整部影片的悲观色彩,向所有人揭示了生命的意义。无怪乎吴念真后来回忆这部电影时感慨着说“何其温暖”。然而,从整部影片的情节来看,这种温暖却似乎来之太易、显得勉强——更大的可能或许是洋洋长大后依然会循着NJ的前辄,某一天也感叹“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毕竟影片中NJ曾对昏迷中的婆婆说洋洋“跟自己很像,真的很像”。不过,也可能这个温暖的结尾是杨德昌要给我们的一千根琴弦,史铁生意义上的一千根琴弦?
二、电影语言的现代性更新
与“素人艺术家”般的侯孝贤不同,始终坚持以电影探讨台北都市现代性主题的杨德昌发展出了一套精巧、繁复的现代主义电影语言。这套语言在《一一》时已臻纯熟,工巧精微而浑然天成,颇有“老去诗篇浑漫与”的味道。或许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彼时的杨德昌还生发出了对“镜像”本身的高度自觉。
(一)都会建筑元素与人性的互动
除去错落的群像叙事,《一一》电影语言的现代主义风格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对现代都市建筑元素(不管是整体的建筑物,还是其灯光和内部的线条、景框、物品等等)的惊人运用。杨德昌曾说“建筑是人性与科技平衡的最佳体现”[1],而工科出身的他也确实在影像中广泛涉及建筑与人性的互动——说到底,这根源于建筑森林本就是都市人最显著的生存景观,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异化境况也最外观地暴露于建筑对人性的压迫与宰制中。婆婆昏迷送进医院后,NJ在医院走廊遇见匆匆赶来的小舅子阿弟和美国等人的一个全景镜头(图1),且不说摄影机仅仅拍摄人物在玻璃窗上的影像从而形成双重镜像的大胆构思不说,其构图也极具匠心。画面前景被三纵一横的窗框分割,中景是NJ和阿弟,远景则是美国等三人;NJ虽然位于画面的中轴,但其相对瘦小的身躯却被两条纵向的窗框分别与阿弟、美国等人隔开,而且其空间逼仄、促狭,仅占整体空间的五分之一不到。画面的情境则是婆婆昏迷,赶来的阿弟却吵嚷着“运气”、“还钱”,远景中的美国则正在撒酒疯,如此我们便可理解其构图的意义所在——窗框的分隔表明了NJ的不被理解,以及坚守;而空间的逼仄则明白无误地传达出其无奈。此外,深夜里医院走廊的低调光用来形容NJ的黯淡心情也恰到好处。
不过,影片中对建筑物灯光最令人惊叹的一次运用出现在敏敏哭诉第二天后在其办公室里的一个长镜头(图2):灯光全熄,办公室里一片黑暗;然而台北夜景里远近建筑和道路上往来奔驰的汽车的灯光全部通过玻璃窗的反光而被窗外的摄影机拍下;最诡异的是,不远处一栋高层建筑的最顶端的红色闪烁灯化为一个红点竟停留在敏敏的心脏不远处跳动;大约三十秒之后,沉思良久的敏敏转身走向南茜,南茜迎上来,依然形成一个人物占据中景的全景镜头,而透过玻璃摄下的画面竟像是两人临空于台北夜景之上。“我没有地方去。”敏敏说——“这城市的所有人都无处可去”,杨德昌的意图昭然若揭。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是杨德昌电影中对于城市地志及都会意象最具有象征力量的镜头”[2]196。类似的镜头在《一一》中出现多次,可以说杨德昌对此是自觉且视为得意之笔的。
(二)科技时代的“镜像”自觉
《一一》中精细而浑融的现代主义语言特色固然令人惊喜,但笔者以为,整部影片最让人感受到杨德昌巨大艺术创造力的语言艺术在于其对镜像时代的高度自觉和批判性思考。玻璃、镜子、照相机、监控摄像头、电玩游戏乃至电影本身,杨德昌将这些现代都市中常见的纷繁的镜像制造者有条不紊地纳入影片,与影片形成一个个双重镜像的“镜中镜”结构。借由这种反身指涉,他不仅实现了对电影本身的解码,同时完成了对新千年虚实边界模糊的科技时代的重新编码。
正是于此,胖子和洋洋的意义得到了全新的诠释。
影片中胖子(及其未现身的舅舅)是个地道的影迷,他认为“电影使人类的生命经验延长了至少三倍”——这或许是我们听过的对电影最美丽的一次告白;然而,急转直下的是他最终残忍地杀害了那个英语老师;更关键的是,血腥的砍杀场面被一段拳打脚踢的电玩游戏替代。在这里,真实与虚幻急遽地彼此互相指称:虚拟的电影经验被指认为真实,而真实的杀人经验又被替代为虚拟。不幸的是,电影中体验而来的杀人经验无法为其消除仇恨,而其杀人也绝非一场电脑游戏。于是悲剧终至于诞生。

图2 电影《一一》剧照
如果说胖子的悲剧构成了对虚实之间边际混淆的镜像时代的讽刺与批判,那洋洋则无疑处于价值链的另外一端。事实上他是影片中唯一的天使般的角色。这个8岁但身体发育远远落后于同龄人的小男孩却对世界怀着纯真或许略显执拗的热情与视野。这种热情和视野来自于一个令其百般困惑的问题:“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么?”因此他拿着照相机拍摄了大量人物的后脑勺,只是想要让别人看到自己看不到的东西。某种程度上说,他同样受到镜像时代的戕害,比如被学校里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的监控。这当然涂抹出“以外在的或直接的力量使个体屈服于社会操纵”[3]xxiii的当代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的某一面相。然而,不同于福柯笔下“全景敞式监狱”式的当代社会悲观隐喻,杨德昌并没有彻底将抵抗驱逐出场:洋洋初心不改,依然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整部影片最具力量的时刻即来自于此。
笔者认为无论是对电影有着动人告白的胖子还是举着照相机寻找更广阔的真实并视之为生命意义的洋洋,无疑都是杨德昌的夫子自道。本片拍摄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正在到来的镜像时代成为杨德昌新生的问题域;而作为当代华语影坛兼具理性思维和人文关怀的导演,他对镜像时代的批判性思考也达成了迄今仍罕有其匹的高度与深度。通过胖子的生命悲剧和都市中无处不在(公寓楼、学校等)的监控摄像头以及电脑游戏,他对镜像时代的虚实不清深怀忧虑;而通过那个感动过无数人的小男孩洋洋,他又传达了镜像的积极力量,或许也可以视为他对自己电影生命给予的一个温柔的总结。
无论如何,十三年后我们回头再看,不得不惊叹于杨德昌的深刻预见:在那个台湾还流行着小田抄大田的年代,他便以镜像本身的方式完成了对镜像时代的解构与重构。而如今这个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正越来越将所有人放置于一座镜城之中,无人可以逃脱。
然而是陷落还是重生?结局是开放的,而《一一》本身就构成一个召唤,正像它的英文名字——“a one and a two”——唯一“镜像”,两般命运。
[1]木卫二,利小刀,左敦.空前绝后,独一无二:杨德昌的价值与遗产·杨德昌说杨德昌[EB/OL].http://news.mtime.com/2011/10/28/1473958-9.html.
[2]黄建业,等.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M].台北:跃升文化,2007.
[3]Meenakshi Durham,Douglas Kellner.Media and Culture Studies:Keywords[M].Oxford: Blackwell,2006.
J90
A
刘金平,厦门大学中文系2013级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