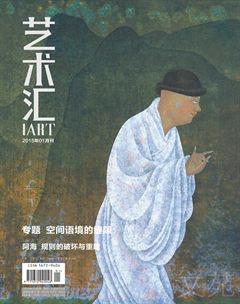张晖 寻找第三领域的美
张晖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在2000年前往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学习多媒体艺术。2006年回国后,他没有继续多媒体的创作,而是回归与自己性格更加相符的绘画进行探索。与同时代艺术家对宏大主题的偏好不同,张晖在绘画中更关心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表现一些具体的事物与情感。各个时节的树枝、柿子、喜鹊、彩虹等等都是入画的对象,他会反复探求这些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以细微的光线、色彩、构图变化来挖掘它们的丰富性。如朋友伍劲所说,张晖像个“爵士音乐家”一样把细腻的情感融入画面。
张晖的绘画风格也随着个人的经历发生着变化,归国以后他的作品更加简化纯净,颜色也更加明亮。与此同时他对于绘画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在《组合》等系列作品中张晖通过颜色、形态等方面的“平面性”实践,试图消弭具体的情节,引领观众进入深层次的思考与冥想当中。而他自己也以这样的创作方式来接近心中的艺术理想:寻找第三领域的美,用艺术作品表现哲学思想,让哲学思想重新构建美。
I ART:你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中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
张晖:上学期间记忆最深刻的是图书馆。在图书馆除了当时在外面看不到的许多原版画册以外,我还读到了很多文学书,比如,茨威格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那时美院图书馆的阅览室很小,五六张桌子,冬天的时候,斜斜的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很温暖。
I ART: 2000年在美国求学期间研究的是多媒体艺术,为什么2006年回国后选择回归绘画创作?
张晖:在美国上学时学习了一段多媒体,也做了几件作品。但画画一直没有完全间断。后来还是感到面对画布比对着电脑一秒一帧的写程序,更亲切更熟悉,更适合自己的性格和兴趣。
I ART: 多媒体艺术的学习和国外的艺术教育对你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晖:多媒体,绘画都是艺术创作的手段。手段和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作品表达什么。重内在本质而非外在形式,这也是中国绘画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表达的尽善尽美,是有一种精神上的铺垫,即完美的艺术被看作是对上帝的爱。当艺术家创作出完美高尚的形象时,意味着他们的艺术参与到神性的世界中。吕克·图伊曼斯在对绘画产生置疑后,拍了几年电影又回归绘画。绘画成为表达他思考的工具,他通常在一天内就完成一幅作品,他从电影里获得的是关乎图像的在场与疏远。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让我对艺术哲学和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多元化的思考。 对我绘画最直接的影响,表面上看就是画面的色彩明亮了。
I ART:你的创作是否有较为明确的阶段性划分呢?还是以贯之的研究某一个艺术问题?
张晖:从画面的表象看,我的作品有着比较明确的阶段性划分,上世纪90年代作品的基调比较灰暗,2000年我离开北京到美国生活。然后是2006年回国,我又重新画了一系列以北京生活环境为素材的作品,颜色和情绪跟之前很不一样了。2009年后作品开始更加简化纯净。我所关注的艺术问题其实很多,一直以来比较关注个人感受。通过绘画给心灵找到一份寄托,一块净土,一个理想家园。 另外,比如丹托在他的书中写到美的三个层次,自然美(模仿);艺术美(形式);第三领域的美。我好像一直试图在寻找那第三领域的美。
I ART:你画了各个时节树的作品,为什么选择这一主题进行表现?
张晖:树枝在我的画里一直有,以前更多的是在风景里面,现在树枝本身占据了画面的主体。我喜欢画树枝。树枝的形态具有单一而又繁复的特性,树枝让我很着迷。画树枝让我进入一个平静到愉悦的过程,像是行禅。找到单一形态的多样性;发现繁复形态的延续性。我希望那些枝桠将成为引领者,引领观者在其间游走,迷失并发现,找到自己的一份平静和寄托。
I ART: 柿子、喜鹊等等都是北京很常见的,你是否喜欢在生活中取材进行创作?是否经常写生?
张晖:我喜欢在生活中取材创作。但我画的都是理想风景,而不是特定实景。所以我并不经常写生,但我喜欢在外面看,然后拍照片纪录下来。最终画出来的是我心中的风景。
I ART:“组合”系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是在探索怎样的艺术问题?
张晖:“组合”系列大约是在2011年开始创作的。在那之前,我的画基本都是描绘了比较具体的一个情节,比如“有彩虹的风景”系列,“光芒四射的太阳”系列。“组合”系列,一方面是对绘画的平面性,颜料,笔触和形状的一个回应和实践。另一方面是在对话中国传统哲学,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组合”系列是我对宗教和哲学的思考,相信人的内心既有神性。
I ART:能否介绍下 “小飞人”系列作品?
张晖: “小飞人”系列作品,相对是比较私人的一个系列作品。我喜欢一个朋友对“小飞人”的评价——色而不淫。对于我,“小飞人”系列有几个层次的意义在里面。其一,是表达我对女性的一个喜欢和敬意;第二,“小飞人”具有东方美,像《簪花仕女图》传达着东方的美学理念;第三,她们在画面中大方平和,无拘无束。在这个层意上她们不仅是女性,代表了广义的人。我给这些“人”置于了一个超于现实的理想境界,无忧无虑,幸福愉悦。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I ART: 为什么在作品中采用比较像装饰画风格的颜色和平涂方式?
张晖:近来我喜欢尽量简化我的画面,平涂手法和有选择性的色彩,是我主动处理画面的手段。我的色彩和平涂方式不是“装饰风格”,是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念的传承。在结构上遵循艺术美的原则,去除传统意义上的光影和体量,把时间,空间和地点模糊化,引领观众进入平静画面的表象下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冥想。
I ART:在你看来,什么是所谓的“绘画性”?相较于装置、影像等等艺术形式,绘画不可替代的魅力在哪里?
张晖:从康定斯基到波洛克,绘画逐渐摆脱了三维与透视。绘画的物理性,形状,颜料,平面的画面成为了绘画。在我看来,所谓“绘画性”在今天,绘画的平面性,颜料,笔触和形状正是绘画不可替代的魅力。
I ART: 有艺术家认为现在的中国当代艺术界存在着许多假抽象,在你看来怎样的作品才能算作抽象作品?
张晖:这里我要提一下马克·罗斯科,他是大家公认的抽象画家。在罗斯科生前,他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总是强调他是在画“人”。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影响了罗斯科一生的创作。他说,“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悲极而泣的事实表明,我的确传达出了人类的基本感情,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就会有和我在作画时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你就没有抓住我艺术的核心。” 罗斯科的目标是走出绘画,全身心地投入灵魂深处。所以,在我看来,如何界定“抽象”并不重要。
I ART:平时的生活、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张晖:全身心的生活,全身心的画画,全身心的玩。
I ART: 最近在创作什么作品?是否有展览计划呢?
张晖: 最近“组合”、“树枝”等几个系列作品都在同时进行。明年三月我在星空间将有一个近几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个展览,很期待。(采访/撰文:郭毛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