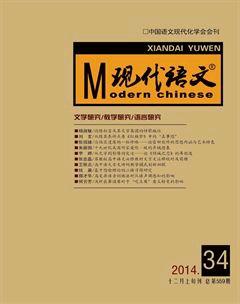《马氏文通》“字无定类”说及其合理性因素探析
摘 要:《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专著,然马氏语法体系自创建以来,其“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词类理论一直为人所诟病。诚然,就其根本,马氏是认为“字无定类”的。但这一结论的得出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
关键词:马氏文通 字无定类 静字
著名语言学家廖序东先生曾说:“汉语之有语法,则自马建忠著之《马氏文通》起。《马氏文通》第一次建立了汉语语法系统,博大精深,是划时代的著作,是古往今来特创之书。”[1]然而,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往往都伴随着争议而存在,《马氏文通》(以下皆称《文通》)也是如此。《文通》的语法体系自创建以来,其“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词类理论一直为人所诟病。本文将以《文通》的“静字”章为主要材料依据,在对马氏“字无定类”思想进行基本认定之后,从“字无定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两方面入手,来分析马氏“字无定类”说的合理性内核。
一、“字有定类”和“字无定类”
《文通·正名卷之一》有这样两句看似矛盾的话:第一,“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亥矣”。第二,“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历来学者们都对此耿耿于怀、聚讼不休。有人认为,马氏单纯从词语在上下文中之义来判定词类,把词类与句子成分机械地一一对应起来,是汉语“字无定类”的始作俑者;又有人认为,“马氏主张的是字有定类的,正是立足于字有定类,他才提出了字类假借说,果无定类,还有什么假借可言呢!”[2]更有人认为,“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就是字有定类吗?既说字无定类,又按有定类来讲,这就是自相矛盾了。”[3]以上各观点看似都有各自的合理之处,但对诸学者的看法进行推敲后,就可发现,造成对马氏“字无定类”不同认识的原因,只不过在于他们对以上两句话的侧重不同。第一种观点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第二种观点只见前者而忽略了后者,第三种观点倒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了,但似乎又对后者的理解不足。
马氏确实是先把一切字进行了归类,“字分九类”;而当经常用作甲句法成分的甲类字用作乙类句法成分时,便说是“用如”乙字、“惟作文者有以驱遣耳”。那么,马氏究竟是认为“字无定类”还是“字有定类”呢?我们认为,马氏“字分九类”的前提并不能否认其“字无定类”的结论。在此,我们首先对马氏的“字无定类”做一个回顾与梳理。
《文通》所谓“字无定类”是指字无不变之类,应根据其在上下文中之义来判定其类别。马氏在《文通》中所述的“字无定类”大致包含三种情况。
第一,一字数词。如:
《论·学而》:“求之与?抑与之与?”第二“与”字为动字,上下两“与”,皆虚字也。又:“夫子之求之也。”上“之”虚子也,下“之”,代字也。
这是指汉语上的同形词,它们虽有相同字形,但意义上毫无关联,分属两个词。对于这种情况,马氏不因字形相同而将其归为一类,而是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进行具体字类划分,是非常符合汉语实际的,并且在现代汉语中也同样适用。
第二,一词数类。如:
《公·宣六》:“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前“门”字,名也,后“门”字,解守也,动字也。“闺”字同。
与第一类不同,这里的“门”“闺”是同一个词,只不过在不同上下文中词义发生临时转变,因而有了不同的词义和句法功能。其实在马氏的叙述中,是将这种情况与“一字数词”视为一种情况来对待的,所谓“凡字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在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但经过分析,我们看到这与前者所指并不相同,有一词与多词的区别,故应区别对待。
第三,字类假借。如:
以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如“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矣。又“齐桓”“晋文”“尧服”“舜言”之属,“齐”“晋”“尧”“舜”皆本名,今则用如静字。
马氏认识到名字多用作起词和止词,而静字多用作定语[2]、表词,故当名字在句中作定语时,处理为“用如”静字。这也就是马氏的“字类假借”。这与前面提到的两种情况共同组成了《文通》的“字无定类”说。可见,马氏在处理词类时,虽先根据一般情况将词语“字分九类”,但对于某些特殊情况,特别是后两种情况时,确实是认为对“门焉”“王臣”“王道”等居于前位之字的词类判定应先知“上下之文意何如”,故其“字分九类”的前提并不足以否认其“字无定类”的结论。同样,“字分九类”与“字无定类”也是不矛盾的,马氏的“字无定类”,并不是说汉语本无词类,马氏“字分九类”成立;而是说对于汉语中有数义之词的词类划分应根据词语在上下文中的具体使用而定,“字无定类”同样成立。可见,二者并不矛盾。但就其根本,马氏还是认为“字无定类”的。这一结论历来为学者们所诟病,但我们认为,“字无定类”结论的得出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
二、“字无定类”的必然性
自《文通》始,词类问题就一直是语言学界争论的焦点。词类的划分、词类的多功能现象至今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静字章,马氏将静字统分两类:象静和滋静。
象静者,以言事物之如何也,滋静者,以言事物之几何也。曰如何,曰几何,皆形之显著者也。
象静滋静,皆静字也,故用法大同。惟滋静一字一数,无对待,无司词,无比品,盖质言也。
马氏因“大同”合象静、滋静二者而成一类,它们所描述的是“形之显著者”,都是“事物之形”。但又因“小异”分二者各为静字之次类,滋静只表示数量的多少,没有反正对待之义,不能带司词,没有比较的形式。
类典型范畴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物体是否归入某范畴,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同特征,而是看它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观察马氏静字划类的处理方式,可以窥测到其整个词类的划分依据之一:大同则合为一类,小异则别为次类。这与类典型范畴思想不谋而合。endprint
以上是马氏词类划分的一般情况,即“常”。我们知道按照马氏的描述,游移在静字、名字等词类周围的还有诸多“名字用如静字”“静字用如名字”的案例。马氏意识到名字经常充当起词、止词,当它位于名词前充当修饰成分时,就说是名字用如静字。而静字是用来充当定语的,“先乎名字常也”,或是充当表词,“以决事物之静境”,但当静字单用位于起、止词的位置时,便是“用如名字”。此其一:字类假借;更有我们说的第二种情况:一词数类。可以说,马氏对待这些情况,采取了“非常”的方法,表现出词类划分的矛盾性,最终得出了汉语“字无定类”的词类理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世界万物是具有连续性的统一体,而被划分的词类则一定具有离散性,这无疑与事物的连续性形成了矛盾。并且,在一个词类家族里,成员之间并不是“质地均匀”的组合,有的与典型成员的相似性多,有的则与典型成员的相似性少,因此,词类与词类交叉领域就成了词类划分的难题。如此看来,事物间的连续性与反映事物的词类系统的不均衡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词类交叉过渡问题解决的游移性。马氏对此采取了“非常”的方法,据上下文定其类别,或处理为某字“用如”某类,进而得出“字无定类”的结论,就有了其现实上的必然性。如仝国斌先生所言:“他已经认识到了词类并不是一个匀质的集合,其内部成员因大同而聚类,又小别而分次。类与类间的次与次往往具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从而把类与类构成一个大的连续体。”[4]这正是《文通》“字无定类”的根本原因。
三、“字无定类”的可能性
这要从《文通》的字类系统谈起。在《文通》中,马氏将语言中所有的实词“凡五类(名、代、动、静、状)”作了“事物”和“事物之属性”的划分。其中,代字是用来代指名字的,所谓“不变之名也,用与名同”。所以,名代二字可归为一大类,以指“事物”。马氏又说,动静二字向对待而生,“古人遣词造句,视同一律,并无偏重”,而状字乃“肖动静之容者”,“与静字无别”,就是说动静状三字也可视为同一大类,以指“事物之属性”。
马氏的词类观反应了“指称”(名代)与“言说”(动静)的对立统一。而当他清楚地意识到“言说”与“指称”间的转换时,其“字无定类”结论的得出也就充满了可能性。
在静字章中,马氏有著名的“静字假借”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名字作表词和他类字作静字。《文通》中,静字用为语词时马氏另立术语称作“表词”,但是,马氏发现“又或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以表起词之为何耳”。如:
《史·魏其列传》:“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天下者”,起词,“高祖天下”,偏正两名也,其表词也。犹云“所谓”天下者乃高祖之天下”也,此所谓用如静字也。
也就是说,马氏认为“高祖天下”这一由偏正两名字而构成的名词短语在这里发生了词性的变化,用以表示对起词“天下者”属性的描述,具有了静字的语法功能,因而当用如静字。今天,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马氏的这种观点,但是从指称理论来看,本来用以命名的指称词“高祖天下”,在这个语境中确实已不再用来指称事物,而是用来表“起词之为何”了,即用以言说了。如金岳霖先生对“孔丘是人”这一命题的解说一样,“主词的对象确实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孔丘”,而“这一命题所肯定的,是这一客观事物有‘人那样的客观属性”。[5]这是指称词的无指用法。
马氏对他类字用如静字的描述,前文已做过介绍,这里简单叙述。马氏认为诸如“王道”“臣德”“吾家”“其言”中的“王”“臣”“吾”“其”等名代诸字皆用在名字之前,用来限定、修饰后面的名字,词性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分析,同样钦佩马氏语言直觉的准确性。刘永耕先生认为,“王道”严格说来已经不等于“王之道”,“王”已不指称现实世界“王”这种对象,其意义略等于“足以王天下的”。“王道”和“道”两个名字在这里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种概念,后者是属概念,前者是对后者进行概念限制而推演出来,所增加的内涵正是“王”所表达的属性。可见,王已由抽象、静态的指称词转为了具体、动态的言说词了。[6]马氏将其称作用如静字不无道理,只可惜当时的语言理论还不足以用精当的术语来表达他的语言观点,以致长期为后人所指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通》“字无定类”的结论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作为开汉语语法理论之先河的伟大著作,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文通》的开创之功,而不是对其过分苛求,因为没有任何理论是完美无瑕的。
注释:
[1]本文所涉《马氏文通》的所有引言及页码皆以中华书局2008年版本为准。廖序东:《评蒋文野同志对马建忠和<马氏文通>的研究》,镇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2]《文通》中并无“定语”这一术语。何九盈:《中国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3]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4]仝国斌:《<马氏文通>的类典型范畴思想——从动字与静字等的关系论述谈开去》,殷都学刊,2007年,第3期。
[5]金岳霖:《罗素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6]刘永耕:《<马氏文通>的指称理论》,中国语文,1998年,第6期。
(闫翠科 四川大学 61006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