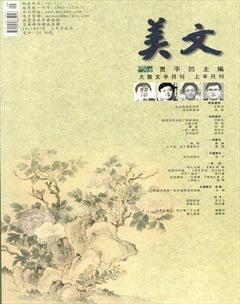上学路上(上)
熊莺




躺在这漆黑老屋的床上时,已近晚上十点。
电灯开关的细弱胶线,别在床头的一只蚊帐钩上。灯关了,但我仍能判断出这间屋里,每一个方位的每一件物品。
地不平,一如田陌山径里,风一过处会扬尘的那种泥土地。床前一米开外的地方,直至墙角,一坡已吐了不少艾绿色粒粒幼芽的土豆。往右,五袋白底蓝字包装的化肥。房门左侧,我床脚的床头外,一只椭圆大木桶里,屯满玉米。
为了让我安放行李,孟申凯老师的妻子取来一顶大号的簸箕,担在半尺高的一只木脚盆上,算是“桌子”了。
屋与屋之间隔墙的上方,是相通的。屋外,山泉水冲刷着一沟巨石。如大雨滂沱,又幻似有猪,哒哒哒通夜吸食。
屋里,隔壁,那夜,六十四岁的这位山村代课老师孟申凯,可能也醒着。
四川东部的达州境内,万源市曹家乡田坝村,從他的这个家,到他受聘代课的另一个村庄,水鼓坝村的村小,约莫四五十里地,老先生是在担心我的脚力。这些年来,几乎每一个有课的周一的清晨,他五点起床,然后,步行四五个小时,九点前赶到村小,为他的学生们上课,每个周五的下午,孩子们放学之后,他又沿路返回。而那个下午,老人在距他家最近的公路旁来接我,要涉一条河,河床几十米宽,河上的桥——一把接一把的梯子,架在乱石上,那“桥”,我是半蹲着身子移步过去的。
黄昏时,孟申凯的领导,曹家乡中心校的校长也来了。孟老师给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租车,经万源的白沙镇,走重庆的“城口”绕道进村;二是以摩托车代步,走他走了十几年的那条路。校长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我。
明白他们的心思,我婉言谢绝了。一个老人,于每一个清寂无人的清晨,风雨无阻,寒来暑往,这一条路,他一走十一个春秋,而我,又岂有理由娇纵。我要随老先生一同步行去那个村庄,如他很寻常的一次去上班,去执教,去见那里等待着他的五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和七名学前班的村童。
一 老先生
四川万源枕于秦巴山脉(秦岭和大巴山)之上。海拔最高处2400多米。万源以东,大巴山的腹心地带,有一山,名花萼山。花萼山约三分之二土地上,栖息散落着一个乡,曹家乡。特殊的地理环境给花萼山,也给这个仿佛在天一隅的山乡带来了特殊的冠冕:高寒贫困乡、“物种避难所”、具有代表性的北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等。当然,也带来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和先生膝下的十二名学童。
最终,由校长定下一个得当方案:雇一辆摩托车运送我的行李;再雇一辆面包车,送我和孟老师一程。面包车可抵达曹家乡的老乡政府前,也就是说,我和孟申凯老师可节省约一半脚程。
有了汽车,孟老师决定晚走一点。
五点,我的闹铃响起来。
头一晚为我和客人们而备的一大桌菜,老先生的妻子一碗碗地在厨房加热,然后端到堂屋,神龛前的那张低矮的小餐桌上。
快六点时,驮运行李的摩托车师傅和送我们的面包车司机来了。孟老师的妻子往丈夫的双肩包里装东西,豆腐、鸡蛋、土豆等,那是学生娃一周“营养午餐”的食材。每人每日,国家给每位小学生补贴四元,学前班的学童,每人自付两元。午餐由老师代做。
已是三月出头,山里的清晨,仍冷得让人手足无措。从头到脚,我武装起来。
我们是差不多七点十分,和面包车作别的。
站在山道上的垭口,面包车一颠一踬地艰难调头,一旁的孟老师把沉甸甸的背包往身后一挎,像个沧桑的背包客。他的右边,山路下,沟壑嶙峋。前面,一车宽一点的泥土公路的远方,那些坚硬的顽石与峰峦,以及四下里的整个大山,还未完全醒来。
有些偏瘦的孟老师从前无福走这样的路。他用手横着指给我看,从前他走对面的峻岭里,走那如今已看不见的一条条小道。
同一个方向,去水鼓坝村,也去孟申凯老师第一次去执教的那座村庄,郭家坪村。
1971年,二十岁的孟申凯第一次走对面那大山,只十几里地,一个单边,年轻他,走了近两个小时。
那时这位民办教师要去的地方,没有学校,当然村子里也没有读书识字的人。村里的一位耄耋老人邓育清,腾出一间堂屋,郭家坪村小,就这样开学了。
村子里,一二十个人,同读一年级。一师一校。学生中,最小的七岁,最大的十一岁。
那时那座村庄通往外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食盐、布匹、煤油等一应生活用品,都靠马驮。
村庄通往外界有两条路,一条奇险;另一条,摔死过人。三十岁的复员军人周怀元,那年从“陡梯子”处过,一失足,这个年轻人,再没能站起来。
朗朗书声,仿佛给这个美丽山村赋予了某种祥和。许多山里人都觉着,村庄里,一夜间仿佛多了妩媚。
一经被山里人称作“老师”,这个“成人高中”毕业生,也再无心回头。
三年后,他被派到另一个村庄去创建另一所村小。大沙坪村村小。
民办教师那时的工资收入分两个部分,乡中心校每月发13元,队里发10元。队里的这10元,只能用于在队里购买全年的口粮,约200公斤。
每学年开学前,孟老师会去乡中心校给学生们“赊”书本。一个学生娃每学期约10元钱的书本费,书本,他先领回来,一应的费用,由中心校逐月从他的工资中扣除。
他全年薪水为156元(队里发的10元只换口粮),也就是说,20几个学生,如果收不齐书本费,一年下来,他得倒赔乡中心校。
还好,山村人仿佛早就明白这理,孩子是全家的希望。那时的老师也是不易的,期末考试,这位民办老师,得带领孩子们跋山涉水去“考试点”会考。
那一年,他至今记得,自己带着二十几个娃去赶考,他们要涉河去对面的沙罐河小学考试。娃们在岸上,他一个一个背他们过河,才背过一半,洪水猛然涨起来。他站在水中央,洪水肆无忌惮地往上漫,他背上的娃开始嘤嘤泣。
……
山路迢迢,小河涨水,最难的都不是这些,有时是自己“不争气”。
在田家湾村小那阵,他小便带血,一拖三年。有一天他实在腰痛得不行了,三十几岁的人了,在宿舍里抽咽。还好,那所村小非“一师一校”,有六名教师。老师们七手八脚,绑起一架滑竿,抬他上船,过河,再换乘拖拉机。在山下的一家部队医院里,他被摘除了一只肾,这才捡回了一命。
只有一只肾的老先生在我前面飞快地走。
山路上,我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有时上气不接下气。
有一阵,我们坐在泥石流滚落在路旁的大石上歇脚。我坐悬崖边的这一块,他坐岩石下的那一方。
一辆摩托车远远地迎面开过来。这是清晨我们看到的唯一一辆车,也是唯一一位乡亲。
路面显然已被清理过,泥石流给山路留下了一堆又一堆的黄色新泥。摩托车手是位年轻后生,车座上驮着两袋化肥。无法看清头盔里那后生的面目。车在几道深深的泥槽中,拐来拐去地蠕动找路。
这条路是2007年贯通的。“村村通”,初衷是为了能让这山山岭岭通上汽车,结果山里泥石流多,雨水多。这路,一年通不了几回。必经这路的人们,后来不再抱有幻想。
不远处终于出现了田陌、人家。
豁然开朗的一大片公路边的地里,几个人在忙碌。见着孟老师,他们直起腰,仿佛天长日久,熟稔得早已无话。他们露出齿,有深意地笑。
山外的油菜花在我来时,已染黄了天空,而这坡上坡下,裸露在阳光下的清寒土地里,油菜仅尺高。他们在种土豆,用牛粪打着底。
这又是一个村庄了。孟老师说。
近两个小时脚程中,我们已路经了三个村庄。
经验中的村庄,应该有许多孩子,许多老人,一株大树,几缕炊烟,有鸡鸣,有牛哞。而在花萼山里,眼前的这座村庄,小坪溪村,只是路旁公路边,那坎子上的几处错落村舍。
是不是,一个孩子发现了有人,一眨眼间,一群六七岁一般高矮的小孩,哄地一下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前,那高高的坎子上。他们站在那里,睁着一双双清澈透明的大眼,一动不动地望向路边。
从前,那坎子上就是一所村小。孟老师回头。那时候,那山上面,那梁上,都住着人家。2005年,小坪溪村小还有140多个学生,光老师都五六个。可现在村里的人都远去了,下山了,听说上半年学校只剩下3个学生了,村小就这样给撤了。
已是清晨八点过光景了,几个孩子为何还在他们的家里呢?按孟老师的说法,如今他们要去上的小学,应该在我们身后,在我和身边这位老先生乘坐了一段汽车,又走了近两个小时山路的那遥远的来路,曹家乡上。
这路,若不临崖,不突遇洪水、泥石流,不遇暴风骤雨、雷霆闪电,不望危岩,不瞰深壑,几米宽的泥土路上,除了累,力不从心之外,你可能一时是看不出它的险的。因为,绵延大山,总横亘在你眼前。
还有多远呢?
这里的地形部分呈喀斯特地貌,我举目望着陡壁四起的山峦。
二 复式课
孩子们站在高处,因为在山弯处,好似一群歇在天岸边的金鹧鸪。
见着老师,学生们从煤屑样黑色碎石的山路上冲下来,将孟申凯老师团团围住。抱的抱,扯的扯。一时无法分个亲疏。孟老师于是一手牵着一个。其余学童,自觉地顺着两边,小手一只只拉起来。山路上,他们走着,像一只大鹏,羽翼正迎风展开。
教室里前后各一张黑板。纵然是复式班,但孟老师只用其中的一张。
五个小学二年级学生,靠左窗坐。两列,共三排。第二列最后一位,学前班的一个学童填补上。
右边两列,各三排,坐着学前班的六位学童。
整整齐齐的四列,前后共三排学生。
孟老师站上讲台。
没有上课铃声,也没有一柄铁器敲击一只三角铸铁的声音,老师示意了一下,轻声说,上课了,然后值日生站起身来领礼:老师好!
同学好!孟老师回礼。
孩子们坐下。
上午9点30分。第一堂课,语文课。
小二的同学翻开《语文》课本(二年级下册、由课程教材研究所和小学语文教程教材开发中心编著),老师让同学们一齐诵读上周学习过的课文。
第二课,古诗二首。《草》《宿新市徐公店》。
老师与同学一道声情并茂地诵读。诵读完毕,老师准备抽一拉同学上来默写课文。刚才领礼的值日生喻朝笔在座位上,跃跃欲试。老师点了她。
体型壮硕的朝笔摔着一头长长的马尾走上讲台,她在黑板一角,在两张A4纸大小的位置上,密密麻麻地写: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她写对了吗?” 孟老师问。
“对!”学前班的学童也在跟着顺口答。
应声如戳,印戳一枚一枚绽满村子与山地林间。
孟老师第一次来这里执教时,这里有一百四十多名学生,老师五名。学童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所完小。他教二十多个学生,二年级和五年级两个班。那时的教室,六间。在室外,在一群鸡子正格斗打闹的坝子下方的那排泥屋里。那时他也上复式班,但那时的学生本分。
复试课堂上,不知为何,那日,学前班的一个小女孩,总是脚前脚后地跟着孟老师。“坐到你位置上去!”讲台上的他小声斥。小女孩也不诧。头顶两撮羊角似小鬏,她就那样仰着面,一脸认真地看着正给二年级同学讲课的老师。
小女孩是昨日入学的,父母都在新疆打工,小女孩也在新疆长大。父亲挖煤,母亲帮店,那边没有合适的学校,年前她被送了回来。由爷爷奶奶照看。被一同送回的,还有小她一岁的她的堂弟。
小女孩是班里年龄最小的。没有办法,孟老师把小女孩送到她的座位。第三列,第二排。老先生刚一松手,小女孩又折返身,去翻看最后一排一位同学课桌上的文具。
小孩子还没有上学的概念,只当是乡间乡亲的小伙伴们相聚在一起了。几本新发的学前班课本,《教学练习册》《拼音练习册》《美术》,她胡乱扔在桌上。书包压在新書上。一双眼,茫然四顾。而眼前她所有的一切,又仿佛不是她所在意的。
布置好功课,二年级的同学开始做作业。
孟老师转身,教学前班的同学们识拼音,同时,识拼音下面的这五个字:
个、八、人、大、天。
是不是后面的小同学不让别人动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小女孩觉得自己,没有得到所期待的重视与回应。每个人有与生俱来的自我存在感。她从自己的座位起身,然后,走到教室后面我的跟前。
几岁了?我悄声问。
三岁。她开始对我的大书包感兴趣。
叫什么名字呢?
胡——轩——
小胡轩站了一会,又回到她自己的座位去了。须臾,抬起自己的小凳子,从教室后门往外走。一转眼,一张童花小脸,后来,穿着细格棉袄的这个小女孩,大半个身子,如一张大窗花,紧紧贴在了教室外的玻璃窗上。
此前,小学班和学前班,分班教学。大小学生,互不干扰。一堂课,上半时老师在这一边,下半时在那一边。后来管不住了,老师在这边时,那边有学生出教室了;老师在那边,这边学前班又有同学哭起来。于是合班。
今天一共六节课,除了课前的“阅读”外,课程表上写着:语文、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班会。因为一早在村长家耽误了一儿,今天的阅读课没有上。
课间休息时,我找孟老师要来了同学们的一份花名册。
小二班:
覃伦彩,9岁(父贵阳打工、筑路。上学路途:1个多小时)
喻朝笔,9岁(父贵阳打工、筑路。上学路途:约5分钟)
甘小艺,9岁(家有双目失明老人。上学路途:约半小时)
甘小巧,9岁(家有双目失明老人。上学路途:约半小时)
卢正兴,9岁(父矿工、打工归来。上学路途:约2小时)
学前班:
赖德铭,6岁(父母新疆打工、装修工、待出发。上学路途:约2分钟)
赖德瑞,4岁(父母新疆打工、装修工、待出发。上学路途:约2分钟)
覃伦璧,6岁(父母浙江打工、玩具厂。上學路途:约1小时半)
田仁丹,5岁(父母在外打工,建筑工、明天出门。上学路途:约10分钟)
胡轩,3岁(父母新疆打工、矿工。上学路途:约10分钟)
杨超,6岁(母亡,父这两年没出门打工。上学路途:约半小时)
覃仁东,6岁(父残疾。上学路途:约20分钟)
括号里的内容,是我一边咨询老师和同学,一边注明的。我是想知道,这个村庄,900多在册户籍人口中,如今,半数以上的人都远走了,他们与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年轻壮年的他们离开了故土,他们带走了他们的老人和孩子,在异乡,他们接受着“城市化”带给他们的欢欣与迷茫,那么,是怎样家庭背景的孩子,如今仍然选择留在这里?而这些孩子,他们又在怎样生活与学习。
三 小鱼儿
第二天清晨,我答应陪距离村小最远的卢正兴同学一同去上学。
清晨六点半,小正兴的爸爸开着摩托车来接我。我宿村小不远处村长家。
细雨,天阴寒。这个村庄所在位置海拔只1000多米,但深谷里,山风凛冽,皮肤割人般疼。我穿戴上所带的全部衣物,村长的妻子又找来一顶带着猫耳朵的毛线帽给我戴上。
车灯亮着,车在濛濛暗雾中穿行,山无棱,天地混沌。我与驾车的正兴爸爸喊山似说着话。
“我得付钱!”我说。我不成想,村长帮叫的车,正是小正兴爸爸的。
“你也是为娃们才来的。今儿我说了算!”
“平时跑这一趟,得多少钱呢?”
“主要是自家用。正兴有个姐姐,在乡上念四年级。十岁的女娃,每周离家回家,一去一来,两头的天,都是黢黑的。娃一个单边,要走四五个小时山路,落雪下雨天,我得去接送。”
正兴妈妈是陕西人,正兴妈妈的父亲,是当年正兴爸爸在陕西洛南,挖矿时的工友。一来二去,成就了这门姻缘。婚后,洛南女子来到了这深山里。这个家,一个主内,照料老小;一个主外,打工养家。
去过广东,也去过山西等地,正兴爸爸最后一次出门打工,是在两年前。
那时他在陕西潼关一金矿采矿,四人一个组,矿床子宽时,一天能采矿石三到四吨,每吨折成工钱,一百多元。若遇矿床子窄,一天不出活的时候也有。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家四个人的田地。后来,他想家了。
小正兴站在门口,无声地笑。有些脏的蓝色动物图案书包,他背在背上。
小正兴很内向,你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哪怕是笑。爸爸让他叫老师,他低头看自己的脚,由内而外的阒静。噤若寒蝉。
小正兴的家在公路旁。屋里的老人还没起床,三开间老屋右侧的厨房内,火龙坑里的火正旺,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着。每天七时,小正兴从这个火舌喜人的温暖老屋出发,九点前到达学校。
还差几分才七点,知道路上的冷,我跟正兴说,再烤一会吧,来得及。
他把一双小手架在火上,小脸红彤彤的。门外,一群鸡,坎上坎下地啄食,一条大黄狗,竖起尾巴,警惕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山上山下,谷里谷外,周遭空空无人。
这个家里,两位老人,一对年轻的父母,三个小孩(正兴10岁的姐姐、还有一个3岁的弟弟),除此之外,家庭“成员”里,还有,两头猪,三头牛,一群鸡,和一条土黄狗。每天清晨,天不亮,第一个起床的是正兴的妈妈,然后是土黄狗,和一群鸡子。然后就是小正兴。
吃过早饭,小正兴上学去了,一家人陆续起床,深山里的这户平常人家的一天,就这样没有变化地开始。
周末或者暑期,不上学的时候,小正兴会帮衬家里放牛,或者打猪草。上学的日子里,他放学后一路玩着回到家,余下的时间,往往只够看会电视,然后做作业。
眼前的路,是2006年全线通车的。这条几米宽的没有硬化的泥土路,一头通村委会,通孩子要去念书的那所村小;另一头,仅十分钟的车程,是重庆的城口。入城口,全是硬化过的柏油路。
这条路,是这座村庄唯一通汽车的公路。是整座村庄的生命线。打工出门的年轻人,生病下山去就诊的留守老人,往返白沙镇去念书的中学生,都得乘车走此路。
面包车,一个单边,约一个半小时车程。车,几乎由山下镇上一名跑了多年山路老司机王师傅私人揽下。电话预订,每人每乘50元。
小正兴很聪明,这条泥路,深一道浅一道有两道车辙,他始终走最靠左边临河谷的那一道。太靠河谷边,可能会掉河谷里;靠右走,走山岩下,担心会遇上泥石流。
是妈妈教你的吗?我问。
他跳跃了一下笑,深深点头。
天已渐亮,路上,辨不清物种的那些树木,叶脉蕾动,总缠绕我。
这是什么?
栗子树。
那个呢?
山核桃。
不对,我立在原地,两株树树形差不多,树皮上的肌理与色泽相差无几。我满腹狐疑地端详。小正兴这下可高兴了,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大人的无知?他指着远方,对面山上的一处白屋旁的一树枯枝,“那是桃花树。”他说。
走了半个多小时山路后,小正兴终于肯主动说话了。他从手心里变出一个小粉粒,只指甲般大。“你看。”他得意地把小手一下子松开。
一只塑料小魚儿。
“谁送你的?好可爱!”
“姐姐从曹家乡带回来的。”
我们于是开始在上学路上的山路旁找水源。他说,这鱼若在水里,水一流,它会游。
找到路边一汪积水,他把小鱼放进去。冰凉的水里,一只小手在水里划圈助力,小鱼儿果然立起身子游起来了。
后来他把鱼儿抛在空中,掷在我们前方的路上,让它像小麻雀一样跑。
无水的陆地上,干酥的山路上,我看见,那尾可爱的小鱼儿,欢喜地蹦着,“存活”着。
路过一片鳞次栉比依山而建的老屋,一位大婶在门前洗衣,一位老奶奶在一株老树下吃饭。大婶远远地招呼我,问我从哪里来,这是要去哪里。
走了一个多小时,从朦胧走到天亮,三两半塌旧厝,几间闭户老房,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户有人居住的农家。望着大婶身后,那一大片没有炊烟,鱼鳞般绵延起伏的瓦房,我问大嫂,那些人呢?老奶奶和洗衣的大婶几乎同时回我,都下山了,进城了。
不远处,路旁一处白色砖房,是小二班女生,覃伦彩的家。每晨路过这里,小正兴会叫上这位同学一道走。今天覃伦彩没有等他。不知为何。
他领着我继续往前走,山路下面是河谷,涧水绕石的河谷对面,山与山之间形成一道天然豁口,小正兴对着那静静的山谷,弯着腰奶声奶气地喊:
覃——伦——彩!覃——伦——彩!
与小正兴同龄的九岁小女孩覃伦彩,每天清晨,她会背着书包,和妈妈一起将家里的几头牛赶上山,然后再赶去学校上学。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找牛回栏,也是这个小女孩和她妈妈的事。小女孩的爸爸在贵阳打工,筑路。
豁口处不远的一排木结构的青瓦山居,是花名册上,二年级同学甘小艺和甘小巧的家。这对双胞胎姐妹花,每日放学回家后,也会去找牛。某一次,牛丢了,姐妹俩找不着,似昔年电影里的“龙梅和玉荣”。后来全家人都出动了。满山遍野地寻,天黑了,他们回到家,结果牛早自己回来了。
那日晨,覃伦彩七点半就到校了。清晨,她的妈妈给她做的早餐是,白米饭,加点油,加点盐,再加少许的只这山里才能一见的那种火锅底料。
那时学校里空无一人,她一个人就坐在教室里,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等同学一个一个地来。
她趴在清冷教室里,那张自己的课桌上,偏着头,看室外的天色一跳一跳地亮起来。
那时教室里有点暗,教室里没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