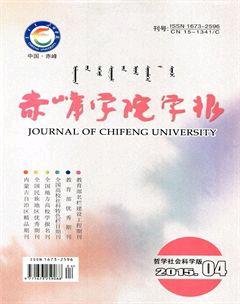《圣武亲征录》的作者、译者考疑
鲍音
摘 要:《圣武亲征录》撰成于忽必烈在位时期,该史籍的译者及原作者是谁,史无定论。本文经过考疑,根据赵璧及孛罗丞相的生平事迹以及相关资料,认为孛罗丞相是该史籍原蒙古文本的作者,赵璧是该史籍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孛罗丞相是忽必烈在位时期的著名史学家,他参预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的撰写,《圣武亲征录》的内容尽含于《史集》中。
关键词:赵璧;孛罗丞相;《史集》;考疑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11-05
《圣武亲征录》(以下简称《录》)的作者、译者究竟是谁,史无定论。本文提出其作者是孛罗丞相,汉译文本的译者是赵璧。此定论有何依据,余作如下考疑,供学界参考批评。
大多数学者认为《圣武亲征录》的汉译文本的译者是王鹗,其蒙文原本的作者,史书中不曾提及,只有胡和温都尔先生在其出版的蒙译(即还原本)《录》前言中提出和礼霍孙是原蒙古文本的作者,而耶律铸是《圣武亲征录》汉译文本的译者。还有学者认为《录》曾被译成蒙古文本,名曰《金册》,译者是谁也无考知。《录》的原蒙古文本已佚,《金册》也已遗失不存。要想考知《录》的原蒙古文作者及汉译文本译者,确实是个比较困难。余所提出的看法也只是一种比较大胆的设想和估测。本题所论“考疑”,意在排除笔者所持观点以外的诸种说法。
一、《圣武亲征录》的撰写年代
关于该史书的撰写年代是考释作者译者的重要的基本依据,从撰写年代寻找作者、译者,当是唯一途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三《史部·杂史类存目》载:“《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首载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纪甲子,迄于辛丑,凡四十年。史载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参知政事监修国史王鹗延访太祖事迹乞付史馆,此卷疑即当时人所撰上者。其书序述无法,词颇蹇拙,又译语讹异,往往失真,遂有不可尽解者。”这里说“疑”是因无旁证来说明是谁人撰出而付史馆的,但肯定“延访”太祖事迹的时间是中统四年,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余以为原蒙古文本撰成付于史馆后,才有了汉译文本问世。
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录》条中说:“《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纪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书载烈祖神元皇帝,太祖圣武皇帝谥。考《元史》烈祖、太祖谥,皆在至元三年(1266年),则至元以后人所撰,故于睿宗有太上之称。然纪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称于其弟,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者矣。”钱大昕的观点是正确的。“烈祖神元”、“太祖圣武”谥号是忽必烈建“八室”神位时确定的。这样可以认定此《录》原蒙古文撰成及汉译本问世时间不早于1266年。
有学者认为,《录》即是《圣武开天记》,此论不准确。《元史·察罕传》载,“仁宗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记》,其书今不传。”因此多有学者认为《圣武开天记》即是《录》。王国维就此问题有过论述。他在其《圣武亲征录校注》的序言中提出《录》不是《圣武开天记》,并说:“据今本《圣武亲征录》癸亥年王孤部条下原注:‘今爱不花驸马丞相白达达是也。考阎复《高唐忠献王碑》及《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爱不花当中统之初已总军事,又其子阔里吉思成宗即位封高唐王,则爱不花之卒必在世祖时,而此《录》撰成时爱不花尚存,则非察罕所译之《开天记》明矣。”如果《开天记》是依据《脱必赤颜》译出,脱必赤颜指《蒙古秘史》,那么写《秘史》时绝不会记爱不花总军事之事迹。因此可以确认此《录》当撰于世祖在位之时。对爱不花在世的时间,我们认为大致是1270年至1280年即至元七年至至元十七年间。再早也不过1260年(中统元年)至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可以确认此《录》非仁宗朝察罕所译之《开天记》。
伯希和也有论述,《伯希和译注本<圣武亲征录>导论》中说:“《圣武亲征录》中写了西夏王国的一个城名‘亦即纳,该城名有数次见于《元史》,特别有两次见于《本纪》,至元四年(1267年)有同样的转写法,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转写作‘亦集乃。看来第一种转写法,1285年后未应用过,可以设想,《圣武亲征录》的编者所用的转写法一定与蒙古王宫办公室所用的转写体系一致,可以认为,哈拉和托城名的第二种转写法‘亦集乃,只运用于1285年后,因之可以说本书原文编写于这一日期以前。”①结合王国维有关爱不花的那段论述,可肯定这部著作据原文译出的时间是在中统初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间,而从王鹗延访太祖事迹的起始年算起,肯定是在世祖年代原蒙古文本撰成付于史馆而后有汉译本成书是无疑的了。
二、《圣武亲征录》汉译文本之译者考疑
《录》的原蒙古文本撰者佚名,对汉译文本的撰者《四库全书部目提要》所涉卷帙中亦提到“不著撰人名氏”。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看法,如胡和温都尔先生在其新译《录》的还原本前言中提出此《录》的撰者是和礼霍孙,由耶律铸译成汉文本。他认为其撰成及译成的时间是1266年至1273年间,依据是这期间和礼霍孙和耶律铸是翰林国史院的监修、修史者,并认为和礼霍孙对其祖乞失里黑的事迹比其他相关史籍论述得更详细。②贾敬颜在《元史》词条里说:“中统三年(1262年)世祖曾下令王鹗等商榷史事,王鹗等延访了成吉思汗事迹,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某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书可能是王鹗等人撰修的。”③王鹗是不是《录》汉文本的译者?贾敬颜只说是“可能”,而不是定论。胡和温都尔先生还在其“前言”中曾提出,当时翰林国史院有位蒙汉兼通的资料员安藏,《录》的汉译文本是否出自安藏之手呢,胡和温都尔先生也未作定论。④
现针对以上所观点略作考疑。先说王鹗。《元史》和《蒙兀儿史记》里都有《王鹗传》。他是亡金遗老,蔡州失守,金主自杀,王鹗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⑤1244年冬,忽必烈在金莲川藩邸,访求遗逸之士,遣使聘鹗。当时忽必烈派赵璧往聘,王鹗来到到忽必烈藩邸:“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务之变,每夜分,乃罢。”⑥但不久,他乞求返还,忽必烈赐给他马匹,还让近待阔阔、柴桢等人随从他去学习经典。后来忽必烈让他徙居大都,还赐给他一所住宅。可知忽必烈对他是相当重视的。1260年世祖即位建元中统,首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让他制诰典章。至元元年加封为资善大夫。他是翰林学士承旨,但他不懂蒙古文,当时的蒙古文是畏兀体蒙古文,他不曾接触蒙古文化。他对金主特别敬重,而金国是败于蒙古而亡的,因而对蒙古文不感兴趣。因此《录》的汉译文本不可能出自他手。至元十年(1273年)王鹗84岁病故。如胡和温都尔先生所说,假定1266年与1273年间《录》汉译文本问世,这时王鹗已是年迈体衰,且不通畏兀体蒙古文,不可能由他译撰成书。⑦胡和温都尔先生说的颇有道理,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史料,而不是亲撰,只能是将搜集来的史料存于史馆以待备用。1266年王鹗任翰林国史院翰林承旨时,已经78岁的老人了。王鹗著有《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诗文》四十卷名曰《应物集》。他没有关于蒙古方面的史著。可以认定《录》汉译文本的译撰者不是王鹗。
胡和温都尔先生提出耶律铸是《录》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对此说,作如下考疑。耶律铸是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的畏兀体蒙古文水平如何,不得而知,其父楚材的写作主要用汉文。据《元史·耶律铸传》记载,他出生于1222年,卒于1285年。至元十三年(1276)进入翰林国史院,诏敕其监修国史,他承担了《辽史》、《金史》的修撰,他确实是位有才华的修史者。如果说《录》的汉译文本撰成于王鹗在世时的话,1276年他进入国史院的时王鹗病故已三年了,他不可能撰成《录》的汉译文本,况且他的主要任务是修撰卷帙浩繁的辽、金史,恐怕无力涉撰《圣武亲征录》。1283年耶律铸“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⑧遂被罢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他成为国史院监修的时间较晚,从时间上推断,他不可能是《录》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况且他是契丹族人,如果他对治史有兴趣的话,也是契丹人的历史。
胡和温都尔先生提出忽必烈在位时期的安藏是国史院的资料员,安藏是否是此《录》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呢?他未下定论。余查安藏确实曾任翰林国史院的翰林承旨。忽必烈曾下旨让徐世隆将尧、舜、禹、汤为君之道、帝王之事撰成书面材料呈上来。等呈上来之后,忽必烈对安藏说:“汝为朕直进解读,我将听之。”⑨此系中统四年(1263年)之事。忽必烈当时命安藏将徐世隆摘撰《书》之所成文字,译成蒙文,安藏完成了译写任务,呈于忽必烈。这说明安藏是位擅长于“汉译蒙”的修史人才,而《录》是“蒙译汉”文本。译家均知汉译蒙、蒙译汉是两种有区别的翻译,能汉译蒙的人,未必能够蒙译汉。余以为安藏是位以蒙文为主,不能承担蒙译汉工作。《录》的译者一定是位粗通蒙文而古汉语水平相当高的一位学者,且一定是位汉族人。安藏是畏兀儿人,世居别失八里,幼习浮屠法兼通儒学。忽必烈即汗位,进《宝藏论·元演集》十卷。如果他译《亲征录》必参佛语。他曾任翰学士知制诰,进而任翰林学士承旨。其所书制诰,亦需译者译撰成汉文。他曾以畏兀文译《资治通鉴》、《难经》、《本草》,曾管理道教事务,元三十年(1293年)卒。安藏译撰《录》汉译文本的可能性尚不可能,而且因为他是宗教人士,如果他译撰此《录》的话,写成吉思汗身世时,不可能将“奉天命而生”的这句蒙古传统写法删去。
余以为《录》的汉译文本的撰成者是赵璧。《元史·赵璧传》载:“(世祖)敕璧习国语(即畏兀体蒙文),译《大学衍义》,时从马上听璧陈说,辞旨明贯,世祖嘉之。”⑩赵璧生于1219年,年幼时,他的家乡山西北部大同怀仁地方,就已是大蒙古国的辖地,那里有许多蒙古族人,对蒙古习俗、人情,他已有所了解,并熟悉蒙古语。1244年他正当青年时就已来到忽必烈身边,他穿的衣服是察必可敦亲制的,视其试服不合适再给改制,破损了,就加以修补。他与忽必烈亲如兄弟,察必把他当作至亲,宠遇无比,关怀无微不至。蒙哥可汗时期他已参预政事。忽必烈命其驰驿四方,访求名儒,王鹗、姚枢等就是由他往聘来到忽必烈身边的。他在师塾中教授蒙古少年,讲授四书五经。他以蒙古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11}如前所述他习学国语(畏兀体蒙文)是忽必烈旨令的,他译《大学衍义》,与忽必烈一起出游,忽必烈常常在马上“听璧陈说”,说明他蒙古语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他在师塾中教学,当是在和林时期,他特别重视生员“知圣贤修已治人之方”。{12}蒙哥汗即位之后,召璧问天下如何治理,他对答说:“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汗听后不太高兴。事后忽必烈说:“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13}赵璧参预的政事往往都最关键的事。蒙哥汗即位是蒙古汗权从窝阔台系转为拖雷系,当时的反对派势力强大,乃马真皇后重用的奸恶不善者还在蒙哥汗身边,还担任着近待,赵璧提醒蒙哥汗是非常正确的。其后蒙哥汗采取果断措施镇压了反对派势力,处死多个反对派人物。赵璧的建议对巩固拖雷派系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南征时期他领军队占据了许多重要城池,立下汗马功劳。他不仅是立笔成文的秀才,蒙汉兼通的名儒,而且也可称得上政治谋略家和杰出军事人才。余以为他是《录》的汉译者的最为重要的依据是,他在太宗逝后不久,就来到和林,耳闻目染,访察太祖、太宗史事有充分的时空条件,对蒙古国兴起、发展有了全面了解,而且他是忽必烈的家臣,汉译《录》,他具备各方面的条件。
王国维在《圣武亲征录校注》序言里说:“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以其‘序述无法,词颇蹇涩,译语互异,未著于录,仅存其目于《史部·杂史类》中。”还说:“作者于蒙古文字未能深造,证以《秘史》踳驳不一而足。”看来译者对畏兀体蒙古文不是精通,而只是粗通而已。赵璧虽然能够译《大学衍义》及《四书》,他的翻译只能说大意不错,仔细推敲肯定有讹误。因为他是汉族儒士,不可能对畏兀体蒙古文认知达到精准水平。但反过来说,如果是蒙古族儒士,他虽然能够译出汉文译本,但古汉语水平且达不到赵璧的水平,这是可想而知的。《道园学古录》卷十二《中书平章政事赵璧谥议》载录了赵璧释解《四书》的事迹,他的释解也只能说释其大意,解其关键的重要内容,以不离原意为旨,不可能释解得非常准确。因为他是以讲通意思为目的的。赵璧把《录》译成汉文本,当然会出现一些舛误,不会那么精辟贴切。王国维说译者“踳驳”,这“踳驳”就是“乖舛”,讹误的意思,作为汉族儒士粗通畏兀体蒙古文,出现一些舛误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必挑剔的。
沙·比拉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译者曾对蒙古原本做过某些改动。”这是指谥号而言的。{14}余以为《录》的汉译文本中的谥号是否是后加的,不能作为定论,因为原蒙古文本也是在忽必烈时期撰成的。可以肯定的是这谥号是与赵璧有相关联系的。此谥号的初定者是赵璧。《元史·世祖纪三》载,至元三年(1266年)冬十月,“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命平章政事赵璧集群臣议,定为八室”。祭祀八室,规范各种规程,议定谥号,庙号名目前是赵璧召集群臣议定的。1266年冬十月始有烈祖神元、圣武太祖、太上皇睿宗谥号,这也是《录》汉文译本撰成时间定为1266年之后的依据。故余以为《录》汉译文本是出自赵璧之手的。这时赵璧47岁,正是精力充沛时期,撰成《录》的汉译文本是不成问题的。原蒙古文本的撰成时间与汉译文本形成时间相差无几,原文作者完全可以使用谥号,谥号不是后加的。
三、考释《圣武亲征录》原畏兀体蒙古文本的作者
胡和温都尔先生提出和礼霍孙是《亲征录》原蒙古文本的撰写者。和礼霍孙,札剌亦儿氏。王鹗逝后,他是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任右丞相,卒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考察其任翰林学士承旨时期,多有政务活动。其政务活动要比孛罗丞相繁多。《元史·世祖纪三》记载和礼霍孙任该职最早应是至元五年(1269年)。当时中书省臣上奏说朝廷必有起居注,世祖即以和礼霍孙、独胡剌充任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同时他还管领国学推行事宜,至元九年(1273年)他向朝廷奏闻,朝廷设国子学。这里国字指八思巴文字。朝廷便令百官子弟入学学国字,此后诏令并以蒙古字行。王鹗逝后命其任国史院翰林学士承旨,兼领会同馆事,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这是繁杂的事务。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主管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他当时仍在作起居注,这是为撰《实录》而作的最基础的工作。至元十五年(1278年)世祖诏谕和礼霍孙,晋用宰执(任命官吏)及主兵重臣。至元十七年(1280年),他曾与高和尚将兵同赴北边,这是他唯一一次行军事任务,当时北边不安定。至元十八年(1281年),他任司徒。司徒是掌管国家土地和人民、官府籍田、负责征发徒役的官人,司徒也称为“丞相”。至元十九年(1282年)被任命为右丞相。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和礼霍孙卒。胡和温都尔先生在其还原本《录》(蒙文)前言中说,和礼霍孙是《圣武亲征录》原蒙古文本的作者,依据之一是和礼霍孙对其祖乞失里黑的事迹比其他相关史籍论述得更为详细。胡和温都尔先生搞错了,乞失里黑是哈剌哈孙之祖,不是和礼霍孙之祖。《元史·哈剌哈孙传》中乞失里黑被记为启失礼,《太祖纪》中记作乞力失。哈剌哈孙是斡剌纳儿氏,乞失里黑是其曾祖,哈剌哈孙之父是囊加台。和礼霍孙是札剌亦儿氏,其父名也不是囊加台,其曾祖不是乞失里黑。这是把哈剌哈孙和和礼霍孙两人弄混了。
纵观和礼霍孙政务颇为繁多而杂,他不曾以史学活动为主任,他的政务活动是在王鹗逝后,虽说是监修国史并作起居注,但在《元史》中不曾有这方面的记载,看来主要是做政务管理工作。他以蒙古文为写作工具,但《世祖纪十一》记载,撒里蛮奏请把以汉文修纂的累朝实录以畏兀字翻译出来,忽必烈阅后准其奏请。如果和礼霍孙以畏兀体蒙文撰写的话,就不必翻译了。大概他忙于政务,这方面的工作说不定可能进展有限,而由独胡剌去完成了。这样可以确认《录》原蒙古文本不是他撰写的。
考释《录》的原畏兀体蒙古文的作者是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因为原本已经遗失不存,所以学界一直不曾定论。首先从叙述手法和风格以及语言和历史观来看,它是一种“独特的汉蒙方言”。{15}因为《阿勤坛·迭卜帖儿》(《金册》)与《录》的内容基本相符,学界就有人认为,《金册》是《录》的原始资料,也有人认为《金册》是《录》的蒙译文本的。已故亦邻真教授就认为《录》的原蒙古文本是蒙文《金册》编撰的基础,《金册》是《史集》中《成吉思汗纪》的基础。{16}他们认为先有《录》,后有《金册》,而后又有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录》也包括了《蒙古秘史》的基本资料。它虽然和《秘史》的资料基本相同,但它的风格与元代蒙古人的史学活动是相联系的。同时它和《史集》的相关部分也相似。因此沙·比拉说:“《圣武亲征录》、拉施特的《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材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时甚至完全相符。”{17}这样我们联想到忽必烈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孛罗丞相,他在王鹗搜集蒙古先世史料时,在忽必烈身边任丞相之职,忽必烈应伊利汗国要求派出诸多科技、文史人才时,孛罗被派往伊利汗国协助拉施特撰写《史集》蒙古史部分。余以为考察孛罗丞相的史学活动,便可肯定《录》原蒙古文的作者就是他。
可以确知世祖即位于1260年时,孛罗已与世祖之幕僚汉族儒士集团共事。至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时,孛罗与刘秉忠、许衡及太常卿徐世隆一起起草朝仪,世祖在开平行宫观览后,大悦,举酒赐诸卿。{18}可知孛罗与汉族儒臣毫无嫌隙,共谋朝廷大事,还经常谈论先祖创业事迹。世祖即位后,孛罗先后任御史大夫、大司农、御史中丞兼大司农卿、宣徽院使、枢密副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在世祖即位初年还很年轻,只是1270年之前的情况由于史书没有记载不太清楚。至元七年十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19}当时安童提出孛罗以台臣兼领,前无此例。忽必烈下旨说:“司农非细事,朕深谕此,其令孛罗总之。”{20}可知忽必烈特别看重其才干,对他十分崇信。孛罗不负所望,言:“高唐州达鲁花赤忽都纳、州尹张廷瑞、同知陈思济劝课有效,河南府陕县王仔怠于劝课,宜加黜陟,以示劝惩。”{21}世祖从之。这是任大司农卿后的第二年之事,孛罗勤政务实{21}之一斑。至元十二年(1275年)朝廷“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22}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23}从其所任职务可知他对忽必烈在位时期的朝廷大事了如指掌。《史集》中的元初史事记载当然与孛罗相关联。《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记有关于他审问文天祥之事。丞相孛罗召见文天祥于枢密院。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愿求早死。孛罗丞相当即反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几帝几王一一为我言之。”{24}这句话说明孛罗深谙史事,自盘古至今帝王名称他都能详细背诵,其历史知识的功底非同一般,也说明孛罗是以著名的史学家的身份在审问文天祥。因此伊利汗国求征包括科技、文史、医学、建筑人才,而派使臣来见忽必烈时,忽必烈答应派孛罗这位史学家去伊利汗国,这也说明忽必烈是知道他曾撰写过《录》的原畏兀体蒙古文本的。去伊利汗国后孛罗与拉施特合作编写《史集》,这也就是孛罗是位精通蒙古史学者的最好注脚。《史集》中的《成吉思汗纪》与《录》“惊人的相似”,正说明《录》的原本作者是孛罗丞相。很多学者都曾说过,孛罗丞相被派往伊利汗国后,便参与了《史集》的撰写。彼特鲁舍夫斯基说:“拉施特利用了孛罗丞相这位来自中国,无比通晓蒙古古代风俗和传说的将官暂留于伊朗的这个机会。孛罗丞相为拉施特补充了文字材料。据苫思丁·卡沙尼说,他们二人有如师生,日复一日,连绵相处一起,‘祥蔼的王公讲述,好学的丞相将他的话记录下来。”{25}孛罗于1283年去了伊利汗国,《录》汉文本译撰成书于1266年之后,在此之前孛罗已将《录》的原蒙文本撰成交付于史馆,在时间上没有任何矛盾。他给拉施特的文字材料中,含有《录》原本的内容,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