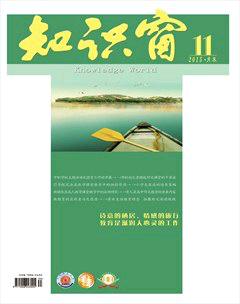朴实无华的青蒿
刘志坚
在我的家乡,漫山遍野生长着青蒿这种其貌不扬的植物。在我的记忆里,最起码有三种统称为青蒿的草。一种叫臭蒿;一种叫艾蒿也叫香蒿;另一种山里人懒得细分,干脆就叫它蒿子。春风刮过,漫山遍野都能看到它们一丛丛、一簇簇肆意生长的身影。它们或身形高大,或体态纤细,或挺拔,或匍匐,肆意地冒出葱翠欲滴的绿意。
这三种青蒿中,长得最渺小的当属蒿子,山里人给它取了一个形象的外号“抓地皮”。它们谨小慎微地、一簇簇地匍匐着生长,似乎紧紧抓着地皮。稍有轻风刮过,就禁不住颤抖般你挤我拥,仿佛只有抱成团,才不至于被刮走。
长着纤细身材的是艾蒿,远远地嗅,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如果用手去捋,保管你的手上沾满浓烈的香,所以它博得了香蒿的美名。它们一丛丛地长在路旁或荒野间,似乎是在比试谁的腰身更窈窕。
长得最高大、最健壮的是臭蒿。它们生长速度极快,几场透雨过后,哪怕是再瘠薄的土地,它们也可以窜到1米甚至更高,植株的根部粗达0.6~1厘米。因为它们浑身散发着难闻的臭味,所以人很少去“骚扰”它们,就是牛羊对它们也是不屑一顾,所以它们很容易就长成了青蒿里的“壮汉”。
人们很早就知道利用这些散漫生长的青蒿,在不同的时令给它们派上不同的用场。
艾蒿被人们看重的就是端午时分,几乎家家户户都要采来艾叶煮鸡蛋。它们浓浓的绿意随着沸水渗进蛋壳或煮碎溢出的蛋白蛋黄上,然后被吞下去。被冠以“辟邪”的神圣使命,是艾蒿最“得意”的事情。至于近年来时兴起的艾灸,使得艾蒿身价高涨百倍,它们被制成艾条、艾柱,熏烤人们的穴位,具有祛病健身的功效。因此,山里人再也舍不得赶着牛羊去啃食它们,而是小心翼翼地采集加工,艾蒿也就显得愈发高贵。
抓地皮的蒿子被人们看重是在穷苦年代的夏季,因为它们点燃之后冒出的烟雾有很好的驱蚊效果。那个年月,蚊帐是奢侈品,更不用说化学气雾剂了。于是,在夏季到来之前,人们就会去野地里割来蒿子,揉搓成条状物,阴干待用。夏夜,在灶坑边点燃蒿子制成的“天然蚊香”,在升腾的淡淡烟雾里,人们便能安然地睡去。
就是那臭蒿,在特定的时候也深受山里女人的青睐。别看它们臭烘烘的,却是制作一种调味品不可或缺的材料。山里人有自制大酱的传统,到了初秋,婶子、大娘们便开始一年一次的大酱制作,她们先是煮熟小麦和大豆,然后把它们晾晒至半干,装到坛子里,接着砍来臭蒿,摘取其顶端较嫩的枝叶,密密实实地放在坛子顶端,最后封口,静待大酱发酵。几天后,美味的调味品就做好了。
至于屠呦呦和研究团队耗费几十年光阴提炼出来的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神药,那是青蒿家族奉献给人类的更高价值。
青蒿,散漫肆意地生长着,用它们朴实无华的生命点缀着山野的四季。而今昌明的时代,看似卑微的青蒿,迎来了更美好的春天,但它们依旧朴实无华地摇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