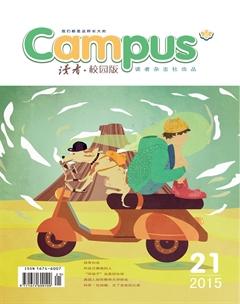纸飞机飞扬过的春天
卷耳喵
紧张的肃杀
有关高考的记忆可以拉得很长。
高二结束前的那个期末班会,班主任站在讲台上一脸严肃地做着高考动员,我们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不论自己的成绩是什么名次,都觉得那张签字纸上的成绩很刺眼;再到秋天的第一次月考,因为努力程度又或者是心理压力,班里的成绩排名陡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还有那年暖融融的冬天,因为我们是高三生,备受优待,暖气和空调竞相开放,窗外下着大雪,我们埋头认真地做着习题;最后是那个夏天,我们满怀着对未来的期许、对过去的责任,赶赴考场。
可所有的记忆都汇成一个点,就是那年的春天。
北方的春天不同于南方的梅雨季——阴雨连绵,它干裂、暴躁,温度忽高忽低,天气忽晴忽雨,仿佛一个新生的孩子,任性而不懂事。
我们所有的高三学生在这个春天里,都迈进了瓶颈期。郁闷焦躁,看着毫无起色的成绩,背着已经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的语句,第一次模拟考试就在眼前,可我们丝毫提不起兴致。
背后的黑板上,倒计时的数字已快要变成两位数,班里的气氛剑拔弩张却又死气沉沉,我们就像被强行推上战场的士兵,仓促应战。
暴躁的我们
小猪和远在加拿大的笔友从过去每天的短信联系变成了邮件往来,一周一封。我监督她,不能因为这样而影响成绩。周一的中午过去,剩下的时间对于她来说全是期盼,期盼每周一中午的邮件。
而我则在课堂上一边听老师讲解着易错题,一边撕扯着嘴唇上的死皮。干燥的北风吹得我整个人都要干裂开来,即便不断地喝水,却还是觉得无法滋润自己。
我和小猪两个人开始进入情绪的不稳定期。
她放弃了异地友情,我放弃了写字,我们两个虔诚地认真学习,可每一次的考试成绩都让我们惊恐万分。这种惊恐不仅来自那鲜红的分数,还有那时候我们眼中那个无比灰暗的未来——我们若考不上大学,未来就会找不到工作,更没有办法实现人生价值,或许一辈子就要蜗居在这座小城里。
这种认知让小猪一度崩溃,她在历史课上因为背不下来大事年表,把自己的头埋在书后,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一边递着纸巾,一边拍打她的后背。她抽泣着,不停地说:“我这辈子完了。”
你看,那时候,我们脆弱得仿佛什么东西都可以轻易击垮我们的未来。
飞扬的梦想
第一次模拟考试前的最后一天,班主任难得微笑地走进教室,她手里拿了厚厚一沓彩色的纸,让我们每个人选一张,然后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梦想,叠成纸飞机。
后排的男生嘟囔着:“这种哄小孩的玩意儿还让我们玩。”
可我回过头去,还是看到他一笔一画,无比认真地书写着,一脸的严肃。
女生们叠的飞机都一样,尖尖的头,张开的两翼;而男生们叠的飞机则五花八门,各有不同,尖头的、圆头的,还有各种长的、短的机身。
我们高三学生独霸了学校的整个南校区,硕大的一片土地上,无数蓝白相间的校服嬉闹着往操场上跑去。
操场后面有一片麦田,绿油油的,生机勃勃。我始终记得刚迈入高三的那个秋天,麦田里是黄灿灿的一片,美得就像画里的景象。老师说:“你们就像这麦子一样,这一季的收割完毕,就要准备播种下一季的了。”
校长憨态可掬地站在台上,握着话筒,什么套话都没有说,只是喊出:“高考加油!”
1800个声音在操场上空回荡,我们把纸飞机抛上了天空。
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飞机,承载着我们的希望,全都飞上了天空。
小猪开始哭,拉着我的袖子不停地说:“我们一定可以的。”
嗯,我们一定可以的。
那一刻我坚信,我们真的会成功。因为我看着我的梦想飞上了天空,它虽然不是最高、最远的,却是我能够抛出的最远的距离。
最后的拼搏
扔过了纸飞机,我们的日子再次恢复了平淡。第一次模拟考试在紧张中到来,我跟小猪在考前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许愿,如果愿望实现了,一定会去这家饭店还愿。那个时候,孤独无依的我们,随便一样东西就可以寄托心念。
那是我高中三年成绩最好的一次,我一举杀入了班级前5名,成为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而小猪也第一次迈入了年级前100名,她高兴地搂着我又抱又跳。
“我们要去还愿。”她叫嚷着。于是,我们又一起去了那家饭店。然后我们来到空空荡荡的操场上,那些曾经的纸飞机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固执地认为,它们真的飞上了天空。
小猪闭着眼睛,虔诚而又真挚。
我以班级前5名的成绩满怀着对名校的期许,迈入了我的高考冲刺阶段。
黑板上倒计时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两位数,数字一天天地减少,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我把晚上睡觉的时间从12点挪到了1点,早上又早起半个小时背英语单词,数学错题本上的题已经被我做了不下10遍,错题本被我摩挲得连页脚都烂了。我不再假借寻找素材的名义翻看高三唯一能看的杂志,而是把这些仅有的时间压榨浓缩。我恨不得拥有一片哆啦A梦的记忆面包,哪怕让我一夜间发胖10斤我也愿意。
这个春天夹杂在寒冬和酷暑间,让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换上了夏季校服,我却还是会想起那架被我抛起的蓝色纸飞机,上面没有什么明确的梦想,只有9个字:愿我的努力不负青春。
我怀着最纯真的信念,度过了高三,也度过了纸飞机飞过的那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