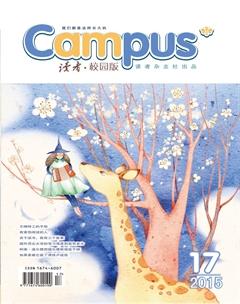我在第三棵树下等你
陈柏清
1
那天和男友逛街,路过一所小学,正赶上放学,孩子们潮水般从学校里涌出来,一个穿蓝裙子的小姑娘在人群中快速穿梭,扑进一个站在校门口小树下的男人怀里,男人牵着她的手,两个人边走边热烈地聊着什么。我不自觉地转换着角度给他们行注目礼,直到他们的背影被人群淹没。
我读初三的时候,中考前学校要求上晚自习,爸爸每天晚上9点就会到学校门口来接我,回到家他会给我做点消夜,无外乎煮一碗瘦肉粥、炒个鸡蛋。那天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要吃手擀面,他说“好吧”。我去洗漱的当儿,他就已经把一碗面条摆在我面前,然后又去厨房端汤。我接过汤碗的时候,没想到碗那么烫,手一抖,汤碗掉在了地上,他瞪眼看着我,有点生气地说:“你这孩子!”我的手正痛得难受,气恼地喊:“我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理了!”爸爸一边擦着地板上的汤,一边说道。我最受不了爸爸妈妈的责备,他也不看看我的手都烫红了,我一气之下把筷子拍在桌上,站起来气呼呼地说:“我不吃行了吧!”然后转身回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听见爸爸在门外说:“你就知道关门,面条不用你吃了……”然后我一边掉眼泪,一边听见爸爸很大声地在客厅里吃面条。我想我又要好几天不跟他说话了。
第二天我下晚自习后,看见他在校门口等着,我趁着夜色,混在同学中走了过去,虽然走进胡同时,黑暗和恐惧使我的心“怦怦”乱跳,可我还是想,就要让爸爸害怕,就要让爸爸着急,要让他知道我多么重要。我知道要是我生气,他就会难过。果然,我到家没多久,爸爸急匆匆地跑回来,我隔着房门听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妈妈:“孩子回来没有?”妈妈说:“回来一会儿了。”爸爸如释重负,但也带着一点愧疚地说:“孩子太多了,没看清。”我心想:“明天看你怎么办!”
2
第二天我一开房门,顺着门缝飘进一张字条:“爸爸今晚在第三棵树下等你。”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倒像是个约会,我把纸条扔在桌子上。放学后,我躲在人群中,看见爸爸果然站在校门口的第三棵小杨树旁边,正死死地盯着校门口看,我一低头一哈腰,又走了过去。快到路口的时候,我回头望望,他还在那儿探着身子,我想他一定是在努力找寻自己的女儿。
人流在减少,他依然一动不动地往前看,我似乎看到了他脸上的焦急,我有些内疚,停下了脚步。终于学生都走完了,只剩几位老师稀稀落落地走出来,父亲跑上前去,跟他们说着什么,然后又迅速地往我这边跑来。他在昏暗的路灯下看见了我,喘着粗气,虽然隔着夜色,我也能感觉到他眼中冒出的火焰,他举起手说:“我真想扇你一巴掌……”
我一转身,刚才的眼泪又收回去了。他跟在我身后,一边走一边说:“你一个女孩子,自己走夜路,出了事儿可咋办?”我自顾自地走,心想:“爱咋办咋办!”大多数人的成长,都是在与这个世界正反对错的碰撞中感受蜕变的痛苦,可是我是在与爸爸的不断摩擦中感受碰撞的痛苦。每一次我都满腹委屈,每一次他都手足无措、一声叹息。而那夜色中的第三棵树,无数次见证了我与父亲无声的对抗。再大一点,我的所谓懂事就是学会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和谐的距离,看人家父女拉着手走在路上,其乐融融,无话不谈,我与爸爸却从没有这样过。
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我上高中,从文理分科到报考专业,我和爸爸都拧着:我要学文科,爸爸要我学理科;我要报文秘,他要我报财经……我们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相互关心,小心翼翼,又疙疙瘩瘩。我们仿佛是天生的南北极,从来不能想到一起。
3
毕业后,果然如爸爸所言,在人才市场上,我的专业遇冷。万分郁闷之时,妈妈打电话让我回家,说爸爸给我联系好了工作。回到家,爸爸不作声,只是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喝着茶水,我突然很想发脾气,可是冲谁发呢?冲一辈子不肯求人,但为了我的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拿了土特产去求老战友的老爸吗,还是冲我自己?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抬眼之间,瞥见了爸爸皱着的眉,我的心一痛……
我不想成为一个不断向父母索取的孩子,不想成为一个“啃老族”,爸爸的爱伤害了我的自尊,可我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因此,他挑落我内心的遮羞布时,我不得不面对也许每个人都携带的渺小懦弱与自私。我们隔着一堵高高的玻璃墙,我那么自卑地蜷缩在角落里,忧伤地感受他高大的父爱。
好在他有妈妈陪伴,我可以堂而皇之继续躲藏。可是有一天,妈妈给我打电话:“你爸一天都没回来……”我急忙开车到他常去的地方找,给亲戚打电话,从我哆嗦的语音、颤抖的双腿,我终于明白我多么害怕失去他。
一夜未睡,第二天准备报警时,他回来了,我们问他去了哪里,妈妈更是声嘶力竭地责备他,他有些蒙,想了想,说自己是要去二舅家,却迷路了,在公共汽车站待了一晚。我和妈妈面面相觑,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悄悄告诉我们,这是帕金森综合征的早期反应。
爸爸变得有时明白有时糊涂,有时还朝我身上扔东西,突然明白过来时,他就像犯错的孩子,不知所措。我跟父亲在一起有时依然很难过,但不是那种难过,而是后悔。面对爸爸的病,我觉得自己的倔强和自尊一文不值,我对自己说,其实我和爸爸之间既没有隔着一堵墙,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一缕风,在彼此的爱中无足轻重的风。我难过但也感到幸运,相对那些失去后痛哭流涕的人,毕竟我还有机会挽回,就像一幅画,从那第三棵树我要涂回去,涂上更缤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