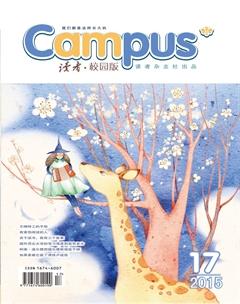好惨的中文课
刘轩
我现在对自己的中文读写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了中文!恨死了老爸和老妈。
我们兄妹二人在阿拉斯加的观光火车上也要学中文。被老爸逼得好可怜!每一次看见老爸拉着4岁的妹妹跳舞,我都会想:“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情调了?”
记忆中,他从来没跟我跳过舞,甚至没怎么和我玩过,如果说玩,那就是比赛、上课。
我到现在都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卧室门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纸,我常在前面被罚站。
纸上的图画已记不清了,据老妈回忆,那是注音符号,每个符号都画成一个人、一棵树、一把椅子或一朵花的样子,使我比较容易记住。
老妈说,老爸年轻的时候,最没人情味了。他出国采访将近一个月,一进家门,不是把我抱起来亲亲,而是喊:“儿子,过来!考考你,老子交代的字背熟了没有?”
大概就在这种所谓的强势教育下,我很小就会背几十首唐诗,能认好几百个汉字,报纸上还登过我的新闻呢!不过,老爸一点也不得意,他说:“小时候背的不算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然,老爸出国没多久,我背的唐诗全还给他了。倒是认的中国字,到现在都还管用。
从象形文字开始,老爸教我中国字,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大概因为他是学画的,所以总用图画的方式教我。譬如:画一棵大树,除了中间的主干,上面左右伸出两根枝子,下面长出两条根,是“木”字。
画一条横线,上面加一小竖,一小横,是“上”;下面加一小竖、一小点,是“下”。
“上”和“下”合在一起,是“卡”。
又画一横线,上面加个太阳,是“旦”。
太阳上面加草,太阳落在草里,是“莫”。
后来,“莫”的下面又加一个日,成了现在的“暮”字。
同样的方法——他画一只手,伸在“木”上,是“采”。然后在“采”的左边加一只手,说是后来的人找麻烦,又加一只手,成了“探”。其实“采”就是“探”。文字应该愈来愈简化,除非为了精确,何必愈变愈麻烦?或许正因如此,在台湾充满文化禁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教我认简体字了。
才离开台湾,他就开始教我读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
奶奶为了这个跟他吵,说他不爱台湾。
他坚持说:“十几亿人在使用的工具,你不能不会用。”
老爸对了!我们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全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课程都忙不完,老爸却要我隔天交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让老爸摇头晃脑、爱得要死的古文课。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课。
当窗子外面邻居家小孩跑来跑去玩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的!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写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字的人,一定是左撇子!”我说。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写汉字省多少力气!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英语是我们的语言,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语言。谢老师出招比老爸狠毒,老爸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而是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敦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有名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很慢,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得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就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
从“五四运动”到老子、庄子。
从苏东坡的《定风波》,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译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文化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
“韩国的华侨子弟,都会中文;东南亚的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还是有不错的中文教育。至于日本华侨的下一代就很难说。美国更甭提了!”老爸常说,“父母一心想变成蓝眼睛、金头发,就算嘴巴上不崇洋,小孩也能感觉到。这种家庭,中文怎么可能保存得好?所以中文教育的成败,跟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关系。”
感谢上帝!自从谢老师接手,老爸就很少再管我的中文学习了。
只是在跑步到树林和湖边的时候,他常要我用中文形容风景。
什么粼粼、涟漪、潋滟,都是这么学的。
有一次坐在车上,他大发高论,提到一群人“瞎扯淡”,突然灵机一动,说:“‘chedan这两个字,我打赌你一定不会写,要是你能写出来,我输给你100块!”
他输了!从此,每次他要赌,出了题目之后,会先盯着我的脸。看我不会的样子,可能叫价50块;看我面有喜色,就只出5块。
我更诈,愈有把握,愈抓耳挠腮,装作不知道,等着他叫高价钱。
我终于开始尝到学中文的好处——赢钱!老爸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提高我的中文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