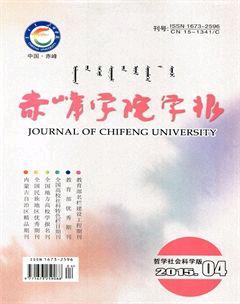《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
曹文刚
摘 要:《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先是比较零碎的片段翻译,远远落后于西方其他国家,也晚于中国其他几部名著。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与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是《红楼梦》在法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这部译著大大推动了这部名著在法国的接受与研究。《红楼梦》在法国的研究,促进了法国读者对《红楼梦》的接受,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的“红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法国;译介;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73-02
《红楼梦》这部中国文学的经典,被许多国家译介,传播广泛,受到广大海外读者的喜爱。各国研究者也从各自视角,对《红楼梦》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鲜、独特的见解,大大丰富、推动了红学的发展。法国是文化大国,中法文化交流频繁,《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与研究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一、《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
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欧洲乃至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译介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德国、俄国、英国、美国,也晚于《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等名著。“汉、法语言上的巨大差异,《红楼梦》隐喻与象征的纷繁复杂与艰深给《红楼梦》的翻译造成了极大障碍”[1]。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只限于一些零散的片段翻译,普通的法国读者难以一睹这部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全貌。
1981年,由法国华裔翻译家李治华及其法籍夫人雅克琳?阿雷扎艺思翻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在巴黎出版,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化事件,从此结束了法国广大读者只能阅读《红楼梦》节译本的历史。“这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全法译本,从此,法国读者终于可以了解到《红楼梦》的全貌”[2]。
这部译著是李治华夫妇与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经过长达27年的艰苦合作才完成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在法国引起了轰动,大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间盛况空前,《红楼梦》在法兰西的接受达到了高潮,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红楼梦》在法国传播的空白。《红楼梦》的翻译出版,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部法文全译本对法国读者来说,就是一幅中国社会文化风俗画卷,他们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他们认识到曹雪芹完全可以归入世界一流文学大师之列。“有些海外论者,将《红楼梦》法文全译本的出版,比之为‘无异以祖国河山,在西方辟出一个新天地”[3]。
“翻译难,尤其是翻译《红楼梦》这样的名著更难。这不仅是因为《红楼梦》本身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要求译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力,更由于牵涉到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4]。李治华夫妇为翻译《红楼梦》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他们用一颗“爱心”和“诚心”来翻译,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始终严守“信”的原则,即使一个普通的词语也要反复推敲、掂量。比如第31回,晴雯跟宝玉发生口角,袭人过来劝解道:
“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得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
“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这里的“姑娘”指的是什么呢?泼辣的晴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宝玉和袭人虽然关系密切,甚至还“云雨”过,可仍是一个普通丫环,与晴雯的地位一样,还没有升到“姑娘”的身份,是不配和宝玉在一起称“我们”的。这里的姑娘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姑娘,而是指比丫环身份高一些的丫环,因此,这里就不能按照一般字面上的理解翻译成Fille(姑娘),而应翻译成Demoiselle(小姐)。可是Demoiselle这个词在现代的法国指的是未婚女子,不是这里的与丫环身份相对的“小姐”。为了使法国读者准确理解译文中Demoiselle这个词,译者特地加了一条注释,指明这是一个地位在丫环之上的临时称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严谨认真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李治华在翻译策略上总体上倾向于直译,而对熟语的翻译,则采用了多种方法。《红楼梦》中运用的熟语不可胜数,富含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译者不只限于直译熟语的字面意义,而且尝试不同的翻译策略,如在译入语中寻找相对应说法,以及在译文中另加词语阐释等非常值得后者学习”[5]。
二、《红楼梦》在法国的研究
1950年代,法国《七星大百科全书》中出现了有关《红楼梦》的词条,编者卡尔唐马克十分注重小说在明、清的重要地位,重点介绍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很好地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但他所说的“想象力”局限于小说的爱情主线:宝玉与多愁善感的表妹黛玉相爱,但宝玉有时对黛玉不忠,黛玉嫉妒心很重,有时会耍小性儿。说宝玉对黛玉不忠,这个判断不太准确,因为宝玉在灵魂深处从来没有背叛过黛玉。
法国批评家透过作品中的神秘的佛教思想外衣,看到了《红楼梦》是中国18世纪社会的一面镜子,是不满现状的,对那个社会是讽刺的,描绘了一个显赫家族以至整个特权社会的衰落。他们认为作者是从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对封建社会的黑暗进行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对弱势群体表达了同情和热爱。有些批评家对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从文化视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宝、黛的文化观的一致使他们在心灵上达到默契,而他们的文化观为他们周围的环境所不容,从而导致他们的爱情悲剧。有的评论家对《红楼梦》的书题“红”与“梦”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西方视角下进行了阐释:“红楼”的表层意思是象征富贵和幸福的住宅,深层意思却是佛教中尘世的诱惑,比如“红尘”,“梦”既是回忆已逝的岁月的欢乐,也是对如过眼云烟的人生的留念与惆怅。小说以神话开篇,构筑了真与幻这一对矛盾,并使其始终伴随着贾、甄两家的命运沉浮,作品具有一种玄学深度。
法国汉学家赖尼埃·朗塞尔在他的《石头与玉——关于语言的中国神话》一文中,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红楼梦》作了分析,将《红楼梦》的研究置于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视域下,视角独特,令人耳目一新。朗塞尔认为曹雪芹在当时用白话文写小说,使《红楼梦》的创作具有语言学的意义,因为古代中国作家一般用文言文创作,用白话文会失去面子和身份,曹雪芹用白话文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贾宝玉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代表,他代表了文人们意识上和语言上的分裂。朗塞尔对《红楼梦》中石头和玉的隐喻结构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石头和玉构成了小说的核心隐喻,石头和玉在中国具有灵性和矛盾性,它上面刻有字,所以它会说话,但它毕竟是石头,所以又不会说话。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是女娲补天之石下到凡间的化身,玉隐喻“欲望”,成为小说的核心主题。小说开头的神话故事统领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石头可被浓缩成玉,它从天上来到人间,投身为新生的婴儿,嘴里还含了一块“通灵宝玉”。这种在隐喻中从能指向所指的转化,符合拉康关于潜意识理论。“假语村言”中的“假语”,也验证了拉康的理论:隐喻充当了指称之间的中介。《红楼梦》故事的开头即预示了结尾,这是一种终点回到原点的结构,小说情节的发展在开篇就已安排好。宝黛第一次见面后,宝玉知道黛玉没有玉,即隐喻了他们之间爱情的不可能,即她不可能有宝玉,也不能表达自己的欲望。“灵”的概念开始使其化身宝玉朝“顽石”转化,宝玉把无意识言语经历展现出来。最后,石头还是变回了开篇中的石头,能指最终到达了其所指。小说的结尾,和尚让宝玉“颖悟”了,回归了玉,其隐喻是欲,与开篇相呼应,把人又带回到了原点。朗塞尔教授用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解读《红楼梦》,其接受视角独特,对中国学者多维度地研究《红楼梦》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鲁尔曼将《红楼梦》的基本情节概括为贵族家族的由盛而衰以及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对其中的优美诗词及精辟的诗评大加赞赏,把它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相比较,将大观园看作“一千零一夜”式的花园。在《红楼梦》中可以找到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和杜甫的《兵车行》的影子,小说中真与幻的矛盾让人想到庄周梦蝶,也因其政治性让人想到爱国诗人屈原。鲁尔曼很喜欢宝玉这个人物,他英俊浪漫、真诚细腻,为爱所困,在情海中沉浮,最后幡然醒悟。鲁尔曼认为曹雪芹的创作观察准确,刻画细腻,文风简洁而优雅,具有杰出的诗才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还提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比如,小说中的儒家、道家思想是如何通过隐喻的手法表现出来的?曹雪芹为何安排一些虚幻的情节?作品有何象征意义?这有利于启发法国读者的深入思考。
三、结语
当前,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受到普遍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已成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文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其在国外的译介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考察《红楼梦》在法国这个西方文化大国的译介与研究情况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是其传播、接受的前提与基础,法国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又大大促进了这部中国文学名著的传播与接受,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本土研究的西方视角。《红楼梦》已经走向世界,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郭玉梅.《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与研究[J].红楼梦学刊,2012,(1):261.
〔2〕陈寒.《红楼梦》在法国的译介[J].红楼梦学刊,2012,(5):197.
〔3〕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160.
〔4〕赵建忠.《红楼梦》在国外传播的跨文化翻译问题[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3):27.
〔5〕黎诗薇.《红楼梦》法译本翻译策略初探[J].红楼梦学刊,2013,(3):295.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