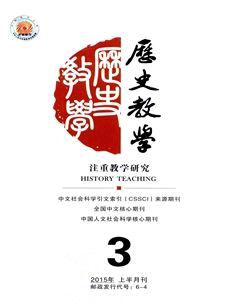儒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线索
【关键词】演儒家思想,基本线索,礼,仁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5)05-0062-05
在高三二轮复习调研中,老师们普遍反映,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单元的基本线索把握不住,于是只好炒冷饭,把知识点过一遍,师生的复习积极性都不高。为此,笔者决定就此课题上研讨课,在备课中,任世江老师的观点使我深受启发。
任先生认为,人教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实际上是指政治思想,具体来说主要是指儒家思想。①江苏省2014年历史学业水平测试说明中,对这一部分内容也明确表述为“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并非只此一端,而是要丰富、复杂得多,但笔者赞同任先生的意见,传统思想博大精深,高中教材篇幅有限,抓住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这个牛鼻子,不失为纲举目张的好办法。循着这一思路,我先后在我区一所四星级高中上了两节研讨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有了新的疑问。课后我又读了一些相关书籍,进行了深入探讨。
笔者以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孔子、孟子的思想是本源性思想。孔孟的思想虽然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但在关键性的原则问题上其实是有差异的,而后世儒家思想是分别循着两人的主体思想演进的。由此,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条基本线索。以下不揣浅陋,分别予以解析,以期抛砖引玉。
《论语》中,“仁”字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每次讲解并不完全一致。②大都是在一定的对话情境中阐述的。这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中,“仁”还未系统化,理论化,更多地体现为实践理性。所谓“仁者爱人”绝对不是平等地爱所有人,而是要讲孝悌,通过血缘构建等级制度。因此,孔子讲“仁”其实是为了释“礼”,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与维护周礼是直接相关的。《论语》中有很多地方都记载了孔子对“礼”的论述和身体力行,以及对违“礼”的愤怒。例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命召,不俟驾而行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如有循。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对“礼”的重视对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董仲舒和朱熹的思想应该说主要是循着这条脉络演进的。而在孔子和董仲舒之间的理论桥梁是荀子。
荀子主张行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承继了孔孟之道。但是,他在立论依据上抛弃了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的解决之道是以礼乐规范人,以后天教育使人向善,可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却以人性恶为依据,利用自私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弱点,以法术势控驭臣民,强化王权专制。法家思想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未被抛弃,只是进行了包装,所谓外儒内法是也。董仲舒是首席包装策划师。
董仲舒重拾曾盛行于上古至周季而中衰的天命神权观,吸收与儒学灵犀相通的阳阳家言,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这里的“人”并非泛指,而是指君主。①他的天人关系理论其实是天君关系理论。此论有让君主畏惧天谴而勤勉施政,以免失去天下人心的限君意图,但从武帝开始的后世君主买椟还珠,只取受命于天的利己之言。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宣称“天地之气,阴阳相伴”,“阳尊阴卑”,由此提出三纲五常的主张,把“礼”的思想绝对化,开启了君臣关系不平等的恶例,开始形成君主只有权力没有义务,而臣子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专制主义传统。
董仲舒借助的天命神权观、阴阳学说以及后来在其神学体系上演化出的谶纬神学到宋代已经千疮百孔,无法撑持了。
而天竺教义适于此时(魏晋时期)大量输入。其本身既具精微之学说,其出世之宗教信仰有解除乱世人生苦闷惶惑之魔力,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及平民明唱舍己从人之主张,取全部民族文化而否定之。此诚中国思想史上空前之巨变。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
经历了魏晋以来佛学在理论和信仰上的剧烈冲击,以及民族大迁徙后鲜卑等“夷狄”风对纲常观念的剧烈破坏,以董子的粗糙天命观来要求和约束人民遵从三纲五常已经无异于痴人说梦了。
程朱理学应运而生,吸收佛家、道家思想,以宇宙论来包装论证儒学伦理观,使得儒学哲学化。概而言之,程朱理学的主张是:“天理”是世界本原,先有理后有物,即“理在气先”。“天理”就是儒家道德规范三纲五常,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要懂得天理,就要有格物致知的功夫。
朱熹为了论证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提出了所谓道心(天理)、人心(人欲)的理论,但受到陆九渊的质疑:
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人心为人欲,道心为天理,此说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
——《象山集》
陆九渊反对朱熹的人心、道心说,其理由有二:一是把道心看成是天理,人心看成是人欲,这就会使天人分离,与董仲舒以来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相悖。二是指出了这一主张的内在矛盾,就是道心为天理,人心为人欲,两个心分离,岂不是人有二心了?可是人心只有一个呀,那么道心安顿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鹅湖之会朱陆论争。在朱熹的理论形成过程中,陆九渊的辩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陆九渊的驳论使得朱熹只好承认,道心、人心都在心中,并没有分离。
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为什么朱熹竟然说“人欲中自有天理”(或者说人心中有道心)呢?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伦理思想,而伦理离不开人,离不开人欲。如果真的“存天理,灭人欲”,就会使儒家伦常自我毁灭。试想:没有情欲,哪来的夫妻,那也就不会有父子,这些都没有了,哪里来的君臣?如此,则三纲五常都不存在了。道心、人心都在心中和“人欲中自有天理”好像把朱熹理论的内在矛盾解决了,但这又埋下了“隐患”。
《论语》中孔子多次慨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孟子说“食、色,性也”,这是不可违背的人性。比起三纲五常这些束缚人性的所谓天理(道心)来说,人的各种欲望(人欲)要强大得多,朱熹要求道心管辖人心,可是道心、人心同处一心,既然儒家讲天人合一,那么各种欲望是人性最自然地流露,是顺乎自然的,包括情欲都是如此(这一点朱熹又不敢否认),道心哪里能管得住人心?加之朱熹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人欲中自有天理”,因此,朱熹就曾经非常担心地说:“专言知觉者,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也就是说会把人欲就当做天理。五百年后,朱熹的话果然在李贽身上应验了。
最早提出“仁”的虽不是孟子,但他解决了“仁”的理论基础的问题,这就是“四端”的思想。这在教材中是涉及了,但易被忽视。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
孟子是“仁”这一思想的真正奠基人,这些言论为后世思想家如陆九渊、王阳明、李贽等发扬“仁”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陆九渊自认是孟子思想的直接传人。他本孟子的“四端”说而把“心”规定为伦理性的实体,谓:“四端者,人之本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认为:“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时即恻隐、当羞恶时即羞恶、当辞让时即辞让,是非至前,自然辨之。”因此,王阳明称:“陆氏之学,孟氏之学也。”陆九渊反对格物致知,由孟子学说引申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这是一种直觉认识论:既然一切认识、一切格物都是为了达到“豁然贯通”,了悟伦理本体,那何不直接求之于本心,又何必费神劳思,一件件去格物呢?只要去掉心中的各种弊病,伦理的光辉便会自然显露。朱熹曾说过:“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三纲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陆九渊由此指出:塞天地唯一理,而吾人心即理也,故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王阳明的学说与孟子的学说也密不可分:
阳明论政,大略以孟子《礼运》为蓝本。虽足针砭专制,究非真出新创。……至其论学,直欲与西汉以来之儒家正统思想挑战。……末学弊极,浸至是非以孔子为权衡。纲常致个人于桎梏。迁延至明,殆已趋于僵化……阳明继起,乃揭思想解放之赤帜,发为学贵自得之论。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自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出自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盖人心之本体即是明德,私欲障碍则本体丧失。圣贤庸愚,同具此心。苟能致知,皆能明德。
——王阳明《传习录》
阳明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冲击理学对人们的思想桎梏,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其学贵自得的主张实际上是认为人人都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人类于精神生活完全平等,不容有高下尊卑之别。这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中的人文主义是息息相通的,必然导致人的个性解放。因此,西方学者称王阳明是东方的马丁·路德。
针对理学的格物致知、先知后行的学说,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主张:
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的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
——《传习录(上)》
知即是行,行不离知,阳明的“知”不同于格物致知的客观认识,完全成为道德意识的客观自觉,即“致良知”。自觉的行就是知,“我行故我在”。
王阳明的学说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他的再传弟子李贽更进一步发挥阳明心学,成为“异端”:
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本身,而对于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王守仁开其风,李贽极其流。李氏弃官削发,不啻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四伦也。认男女平等,许妇人讲学,提倡婚姻自主,是打破男女之防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然后其心乃见,无私心则无心矣。……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必不能安其身于鲁也决矣。然则为无私之说皆画饼之谈。
——李贽《藏书》
李贽削发为僧,弃纲常伦理如敝屣。他抓住朱熹理论的漏洞,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考察人欲的合理性,大胆肯定人的正当私欲,否定“存天理,灭人欲”。勇于打破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束缚,追求个人自由。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这部分是许多老师感到困惑的,因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似乎都是在反对理学,抨击纲常伦理,怎么却说还是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呢?其实,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孟子、荀子思想甚至某些理学思想的延伸,是以儒家的“仁”、民本、唯物思想为武器反对“礼”、三纲五常。那么“活跃”作何理解呢?这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天才设想已经不自觉地向西方人文主义、民主思想靠拢了。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君臣、君民两个基本关系。在这两方面,孟子均提出了与孔子截然不同的观点。
君臣关系: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孔子看来,君臣等级关系必须厘清,不可僭越。臣必须尽心事君,如果遇到昏君也只能“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不这样看,他把君臣关系看成是平等的关系,君还必须对臣言听计从,做到三有礼,否则臣对君的死亡也可以置之不理,不去服丧。如果君对臣不逊,臣也可以对君不客气,贱视他甚至仇视他。这与后世的“愚忠”真有天渊之别!
君民关系: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孔子“礼”的思想主张等级服从。孟子则不同,他对无道昏君毫不客气,骂他们是率兽食人的禽兽,诅咒他们断子绝孙。更令人惊诧的是,孟子认为人民对残贼他们的昏君有革命权。这与卢梭的思想何其形似!只是卢梭立论的基础是社会契约论,而孟子立论的基础是仁义道德。最为可贵的是,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举起了民本主义的大纛。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虽没有与西方学者有直接接触,但承继孟子仁政、民本思想并进行发挥,与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符合时代动向的真正的新声音”。
黄宗羲“缘阳明以上接孟子”,“申民本之义以攻击君主专制”。主张“置相”,认为夏商周三代卿相与君主职务相同,君臣共治,所以兴盛。秦以后君主专制,尊君抑臣,至明太祖甚至废除相职,官制的败坏臻于极致。因为君主世袭,不可能代代贤明,但只要丞相可以传贤,就足以补救君主政体的缺失。他所说的丞相实际已经接近近代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了;他痛斥君主专制,指君主为天下大害,认为立君所以为民,君臣都应是人民公仆。君主定的典章制度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法”,主张建立真正的法,也就是新的政治制度;还主张改革“学校”,除育有用的人才外,尤须监督批评政府,形成健全的舆论,使得天子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国家地方大事在京师郡县之学校中公议,这其实已经接近于近代的议会了。①
顾炎武看到了中央过度集权之弊,他的解决之道是“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使地方官员“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这种地方分权的主张接近近代的地方自治思想。他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经世致用的思想则直指宋明以来道学家们的空谈误国: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宗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日知录(卷7·夫子言性与天道)》
王夫之继承了荀子以来的唯物思想,批判了王学、改造了程朱,发展了张载的“气”唯物论,并尊之为正宗。他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对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从“势”(即客观历史规律)的角度来认识世界,达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对于主张“理在气先”唯心论的理学,这无疑会有釜底抽薪之效。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2500多年的传承过程中,分成了两条基本线索:经孔子——荀子——董仲舒——朱熹沿袭“礼”的思想,形成第一条线索,即专制主义的逐渐深化;经孔子——孟子——陆王——李贽——黄、顾、王传承“仁”的主张,形成第二条线索,即从民本主义趋向民主主义。后世对儒家思想的褒贬实际上针对的分别是“仁”与“礼”。前者是合乎历史趋势的,值得肯定。后者更多的是糟粕,应当抛弃。笔者在研讨课中的体会是,循两条线索可将教材中的主要史实串联起来,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但囿于课堂容量和学生的接受能力,讲清其中的基本联系即可,不宜做过多的延伸。
【作者简介】王得众,男,1970年生,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市吴中区历史教研员,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