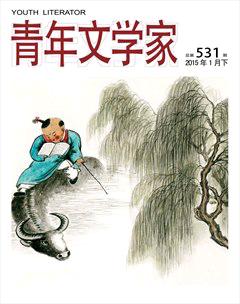浅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空间叙述
摘 要:《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认为是美国迷惘一代的代表作,本文要追问的是作者如何以七万字容纳了整个二十年代的时代精神,这一解决之道可以从小说中独特的空间叙述方式中窥得一二。
关键词:空间叙述;象征性;现代性体验
作者简介:姜丽娟(1989-),女,汉族,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3-0-0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过剩的资本主义生产,美国迅速进入了狂欢的时代,被称为“喧嚣时代”(Roaring Time),而 F·S·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1940)的创作极具代表性。一方面,战争的影响和大规模的都市现代化进程,使得包括菲茨杰拉德在内的年轻一代作家在价值认同上陷入了迷惘;另一方面,欧洲现代主义思潮对菲茨杰拉德有着重要影响,比如意识流写作。然而,当笔者在审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最具影响的小说时,却发现作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形式。他通过音乐、诗歌的互文效果,叙述视角的选择,以及独特的空间叙述等技巧,在保持结构紧凑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现代都市体验蕴含其中。本文拟从小说中具体的空间叙述文字入手,分析小说在上述两方面所达到的效果。
一、上层社会的精神表征:汤姆·布坎农住宅
小说中以尼克为叙述视角,由于他与汤姆和黛西之间的亲戚关系,他得以拜访了后者的住宅。菲茨杰拉德在叙述这一空间时,选择“草坪”作為运动主体——它带着尼克的视线一路奔向目的地。“草坪”的“爽性”进一步感染了“常春藤”,导致它也沿着墙往上爬,接着,这一视觉场景让位于夕阳之下落地长窗的平静。最后,汤姆·布坎农的身姿“突然”映入了尼克的视野。早有研究者将这一段叙述看做是作者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借此加强了戏剧化,似乎汤姆刚刚骑马跨过。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也理解作者对这一空间叙述的安排意义。我们从小说上文中知道汤姆非常有钱,例如汤姆搬家时,“从森林湖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尼克对此惊讶不已,因此尼克眼中的草坪变成了如汤姆一样“奔跑”起来,并且带动了整个空间的急速运动,而在这个空间的动态最终又汇聚于汤姆身上。
这一滑稽的叙述效果还在继续:由于“草坪”过快的奔跑速度使得尼克来不及细细欣赏汤姆的全部财产,只看到“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然而这片空间的拥有者不愿就此罢休,在接下来的交谈过程中,汤姆以一只“巨大的手掌”向尼克相当“随便”地介绍了自己的财富,读者才知道这片空间不止是草坪的空间,那个“火红的花园”其实是一大片玫瑰花园,还有停留在海湾上的游艇。读者看到的是随着生活方式更加奢侈,汤姆的样子也发生了“典型”变化,这种空间的真实性描述以及人与空间的类同化感受,被菲茨杰拉德精确地捕捉到了,这样的空间叙述已经不同于巴尔扎克小说中对于空间的符号化的描写了。
与汤姆·布坎农的强壮和粗俗相对的是黛西的居住空间,尼克在客厅中见到了黛西。在这一空间叙述中,菲茨杰拉德通过不同寻常的词语搭配暗示出个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房子的“轻逸”氛围:“房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沙发的沉重被置换为轻飘的气球,白色的一群加强了这种飘逸感,同时尼克听到了窗帘发出的“劈啪声”,这只不过是尼克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准是”一词也暗示了尼克听觉上的虚幻可能性。由此,飘逸和宁静就共同营造了这里的梦幻化效果。其次,当汤姆进入她们的空间,粗暴地关上窗户后,“地毯”和窗帘、两位少妇一起落回地面。如果说窗帘可以在关窗之后不再随风拂动,那么本来就在地上的地毯更不可能脱离地面,而作者选择将“地毯”、“窗帘”这两个意象与人物并列,便是有意为之,是为了暗示这一居住空间与人物精神上的同一性。很快,我们就能在描写黛西的文字中找到这种对应关系,而黛西与乔丹·贝克的道德感伤的相似性也在后文中得到了暗示,比如乔丹撞到人时将责任推到行人身上与黛西撞死人后的反应。最后,则是这个空间的虚空性,因为尼克只注意到了房间内庞大的长沙发椅,而没有叙述更多的其他陈设。由此,我们也可以察觉到作者在处理这一空间叙述时的技巧,他并不是要“现实地”描绘这类富人的住宅,而是“象征性”勾画某些最具精神内涵的空间特征,黛西在这样的空间里打发时间,汤姆也任由她的幻想。
二、无法穿透的“城市废墟”:灰烬谷
在小说的第二章,菲茨杰拉德通过尼克描述了一个迥异于长岛和纽约的生存空间。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它们不仅构成了这一空间,也构成了人的形体和生活:这些灰蒙蒙的人形存在的同时也走向了毁灭。这里的人物没有差异,也毫无活力,他们更像是一群废墟上的幽灵,随着货车一声“鬼叫”,便开始日复一日的活动。这一生活空间处在纽约两个繁华之地的交界处,路过的纽约人却不愿意正视它,依然沉浸在狂欢之中,但是尼克却无法忽略这一空间带给他的冲击和困惑。当尼克和盖茨比一同经过这一地带时,他甚至看到了一幅颠倒的景象:白人为黑人开车,以及一辆灵车经过。正如对于汤姆·布坎农的住宅空间叙述一样,有关灰烬谷的叙述明显也具有了象征性和幻想意味。菲茨杰拉德之所以描述纽约城这个灰暗地带,是有意要造成一种不协调感,它表征了“大都市精神”的黑暗面——一个被不断压缩的生存空间,一台被现代化生产废弃了的机器,或者一群被社会生活异化了的灵魂,等等。尼克看到灰烬谷中人一直处在隐秘的运动之中,这是一种对全局的历史性感知,当他们“一窝蜂”涌上货车时,便“扬起了一片灰尘,让你看不清他们究竟在做什么”。
菲茨杰拉德在《我所遗失的城市》中,对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个人记忆进行了梳理。曾经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没有边界的,但是当城市被金钱包裹的外表剥落,在刚刚建起的帝国大厦高处,菲茨杰拉德看到了真相:“城市的边界消逝在四面的乡野,融入一片蓝绿之间,唯有后者才真的是无远弗届。这番可怕的顿悟让人进而明白,纽约终究只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整个宇宙,于是他在想象中精心搭建的那一整套熠熠闪光的观念体系轰然落地。” 这篇文章发表于经济大萧条前期,但他的这番感受在20年代出版的作品中已经初露端倪,灰烬谷正是菲茨杰拉德突然意识到的大都市生活的边界,是不同于“蓝绿色”的永久的幽暗,盖茨比死后的那片空间也并入其中,而这片废墟般的空间上却遗留下来埃克尔堡医生的眼睛,他的那双历眼睛正是菲茨杰莱德对整个时代的直觉,尼克、生活中的菲茨杰拉德都无法超脱于这一城市空间,因而“看不清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也如盖茨比一样不知道美国梦会将自己引向何方。于是茉特尔瞒过丈夫与富人汤姆频频约会,威尔逊从寻找到最终杀害盖茨比,这些都是在隐秘中进行的,却被高悬于灰烬谷的那一双“过时了的”埃克尔堡医生的“眼睛”冷漠地注视着。
三、不合时宜的梦想“子宫”:盖茨比公馆
尼克对盖茨比的公馆的第一印象被一笔带过,只突出了它的“庞大”。但当他陪黛西和盖茨比一起进入公馆的内部时,尼克对于这个空间的感受才达到了高潮。在进入这个庞大的“子宫”之时,菲茨杰拉德已经用几个怪异又极具物質性的修饰词传达出了尼克的感受,例如“长寿花闪烁的香味,山楂花和梅花泡沫般的香味,还有吻别花淡金色的香味”,浪漫气息与反讽意味并存。当黛西进入这一“子宫”时,尼克看到的是黛西异样的兴奋和盖茨比的紧张的反差,更加诡异的是,尼克仿佛看到了那些陌生客人的幽灵在满屋子地晃荡:“到了里面,我们漫步穿过玛丽·安托万内特式的音乐厅和王政复辟时期式样的小客厅,我觉得每张沙发、每张桌子后面都藏着客人,奉命屏息不动直到我们走过为止。当盖茨比关上‘莫顿学院图书馆的门时,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了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突然发出了鬼似的笑声。”这些在寥寥数语中就完成了的叙述,却高度浓缩了现代居住空间所可能包含的情感体验,它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人所拥有的某一居住空间,更是这一外部空间与其内心空间的格格不入感,而后一点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天才之处。因此,在随后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奢华的爵士宴会空间里,盖茨比却连游泳池都没用过,而他长久停留的空间只是那一片“蓝绿色”的草坪,只有这一点沾染了盖茨比的精神质地。
关于这一空间的叙述还有一次,就是黛西真正来参加宴会之时。在这次宴会上,旁观者尼克心中升起一番幻想,最为贴切地表达了他,甚至是作者对这个空间、对盖茨比本人的复杂情感。尼克幻想在这样的宴会上有一位“真正艳丽夺目”的少女,她与盖茨比眼神相遇的一刹那,就可以把盖茨比“五年来坚贞不移的爱情一笔勾销”。无疑,这一场景将会改变整个空间的爵士音调。但是在这个幽暗时刻,这些又都不可能发生,因为盖茨比的幻梦已经超过了现实中的黛西,因此,小说情节的转变实际上已包含在尼克对这一空间的哀伤的想象中了。这个用金钱打造的公馆,并不是盖茨比的生活空间,而仅仅是诞生了盖茨比的梦想的“子宫”,相应地,那些曾经进入过这一空间的人们则以幽灵的形式虚幻地占有它。小说的结尾处延续了尼克对盖茨比的公馆这一空间的思考,并将人与空间统合在一起。尼克认识到,盖茨比对那盏绿灯的新奇态度并不孤立,他的梦想在人们发现这片空间时就已存在,只是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盖茨比的梦想的虚空性:“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当尼克把这个失了根的空间放入历史长河中加以关照时,他也找到了盖茨比的精神归属地,因此用“伟大”一词来缅怀盖茨比。毫无疑问,这也是作者对待那些想要在历史的河流中逆流而上又总是被带回到过去的人们的哀歌。
四、结语
身处时代漩涡中心,菲茨杰拉德在“切近”(海德格尔语)纽约这一大都会空间时,选取了更为凝练的表达方式。他以尼克的意识作为叙述中心,勾画出现代人与现代空间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他们或者完全依附于自己创造的物质空间,犹如用一顶“钟形罩”将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严格隔离开来;或者突然置身无法穿透的迷雾般的空间里,又极力逃避;或者以金钱维持与时代同步的喧嚣声,而自己却滞留在梦想和现实的褶皱里。于是,“我们奋力前行,小舟逆水而上,不断地被浪潮推回到过去。”现代性的时间在小说的结尾处被凸显出来,而“小舟”成为这一体验的参照物。具体到小说里,“小舟”正是他们居住的房子、路过的废墟,以及梦想的“巨大子宫”,因此点缀于小说中的空间叙述最为典型地代表了菲茨杰拉德的现代性体验。
参考文献:
[1]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2]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崩溃[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