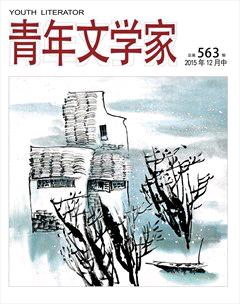汉赋语言的音乐性研究
摘 要:汉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上的一座丰碑。骈散结合的汉赋与音乐渐渐远离,脱离了音乐的束缚,汉赋逐渐兴起与成熟,语言文字的独立性也慢慢凸显。在这个过程中,汉赋的文字语言一方面与歌乐分离,另一方面又受到先秦诗乐舞合一以及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体现出自觉与不自觉的音乐美感,这样的音乐性美感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意在通过对汉赋中句式、语音、音节和表达方式的分析,找出汉赋语言与音乐的联系,以研究其独有的音乐性。
关键词:汉赋;音乐性;节奏;音韵
作者简介:卢荻菲尔(1989-),女,江苏南京人,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饮食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5--04
一、汉赋的音乐性继承
(一)、盛世下的音乐背景
汉代的音乐袭先秦礼乐之风,纳西域异族之乐,有着辉煌而灿烂的成就,这在我国音乐文化史上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儒家思想认为,学习并掌握音乐的技艺,在音乐中得到品性情操的升华,是君子必备的才德之一。比如孔子就曾跟随师襄学习奏琴,其弟子“七十二贤人”也精通音乐。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赋予了音乐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教化意义。在经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文人在音乐上的造诣也不可小视。比如作家司马相如,对音乐有着极高的鉴赏能力,武帝常令他与音乐家李延年合作创作,司马相如赋辞,李延年作曲。司马相如在音乐上的造诣在其作品中也有体现,他的赋中对于音乐的描写总是技艺高超,生动传神。技艺高超的音乐家在汉代也是层出不穷,最闻名于世的就是李延年。李延年的音乐才华让人惊叹,他将创新精神和对音乐饱满的热情注入到作曲当中。作为举世闻名的宫廷乐师和我国被最早记录下名字与作品的音乐大师,李延年常给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的辞赋配曲,还把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编为28首“鼓吹新声”用于乐府仪仗。
西域音乐的引入使汉人更确立了崭新的、多元化的音乐创作理念。在主奏乐器方面,金石乐器退居成辅助旋律的节奏乐器,取而代之的是更具表现力的吹奏乐器。武帝时期,横吹乐器(如箫等)加入到了乐队当中,吹鼓乐中吹奏乐器箫清幽婉转,哀怨缠绵;鼓铿锵激昂,气势庞大。两者的合奏让音乐虚实相伴、动静结合,有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汉赋的音乐性继承
汉赋骈散结合,亦诗亦文。汉代的作家对于先秦古诗有强烈的认同感,认为诗才是赋的源头,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2]《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也提到:“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虽然汉赋中的文体因子趋向多元,但这种诗为源,赋为流的认同感让汉赋作者对着音乐频频回望。纵观《全汉赋》,散体大赋大多都有描述音乐器乐演奏和歌舞升平的内容,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等赋作甚至直接以乐器作为主要描摹对象,骈散结合的多元化文体和“不歌而诵”的形式更是赋予了汉赋以语言文字本身的音乐美感。
司马相如在他的《答盛览问作赋》中提到:“合綦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成质, 一经一纬, 一宫一商, 此作赋之迹也。”[4]讲求赋要追求宫商谐韵、平仄曲直的音乐美,也要追求绚丽多姿的视觉美感。这是对汉赋语言内在音乐性的最早的提及。陆机《文赋》中也有“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之说。虽然学者多把“浏亮”作言辞明朗解释,但实则更指音节在诵读时的明丽。[5]
赋体文学是一种适宜于诵咏的语言形式。在“不歌而诵”的基本要求下,汉赋脱离外在乐曲的声调节奏限制,文辞愈发铺张华丽,对事物的描摹得以横向罗列铺展,繁复铺陈的文辞突破了诗歌体裁和音乐外在的限制,语言以一种独立的音乐化形式成为文学的核心。语言诵读的节奏和韵律代替了音乐演奏的节拍和旋律,加之文字本身的文学含义,使文学语言的感性形式和理性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二、汉赋语言的节奏性
(一)、汉语语言的节奏
节奏是文学语言获得音乐性的重要因素,汉字的语音除了音色之外,音长、音强、音高都和节奏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道:“各种语言由于其节奏上的基本因素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汉语中,音高是节奏的主要基础。”[6]汉语的四声发音不仅包括音高,也包括音长,比如“海”字的发音就明显比“问”字要长,所以当声调不同的汉字被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六朝时就有汉语的四声之论,但到唐以后才把四声归为平仄两类。“从我国有些地区的吟诵实践来看,平声字一般读得低一点、长一点,仄声字一般读得高一点、短一点。如此很有节奏地交替出现,就自然地形成了抑扬顿挫的鲜明节奏。”[7]比如王粲《神女赋》中的“陶阴阳之休液,育夭丽之神人”一句就是“平-平平-平-仄仄,仄-平仄-平-仄仄”,在节奏上是“长-长长-长-短短,短-长短-长-短短”,在音高上就是“低-低低-低-高高,高-低高-低-高高”,这样就形成了张弛结合,波动起伏的线条感。
(二)、对仗的整齐美感
在先秦的“诗乐时代”,“语文合一,声音语与文字语在此时代中犹没有什么分别”,“盖古之人所以不知散与骈者,即因语言文字尚不分散的缘故”,而中国的文学从以《诗经》为标志的“诗乐时代”发展到以楚辞汉赋为代表的辞赋时代,“因改造语言之故,遂造成渐离语言型而从文字型演进的时代,同时也可称是语言文字分离的时代。”[8]在继承上古“诗乐时代”的大背景下,散体文章基于音乐的外在伴随定式,不自觉地偶尔出现骈句,而当文字语言逐渐摆脱音乐的束缚,語言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之后,汉赋的骈化就是作者语言审美的自觉追求了。
对仗兼顾了文字在表意上的暗示功能和读音上的和谐之美。朱光潜先生指出:后世律师的对仗是由赋演变而来的。在赋的演变中,意义的排偶较早兴起,之后才推广到声音的对仗方面。[9]艾略特提出:“一个词的音乐性存在于某个交错点上:它首先产生于这个词同前后紧接着的词的联系,以及同上下文中其他的不确定的联系中;它还产生于另外一种联系中,即这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直接含义同它在其他上下文中的其他含义,以及同它或大或小的关联力的联系中。”[10]比如张衡《归田赋》中一段:“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对仗相当于音乐中两个平行乐句,上下两句字数、句式一样,词性相当,意义互补,平仄相对,表现出整齐的音乐美。
汉赋的对偶句大多以三字句和四字句而构成。这样的对偶和铺陈是之后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发展基础。汉语的节奏可以以音节来划分,一个音节就是一个顿(也可称之为音步,音组等),而一句中最明显的一顿就称为“逗”。中国古诗中一句必须要有一个逗,诗句被这个逗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林庚先生把这一规律称为“半逗律”[11]。在五言中,一句的前三个字之后或者后三个字之前通常处于半逗的位置(“二一‖二”、“二‖一二”和“二‖二一”);在七言中一句中的前四个字之后常常是半逗的位置(“二二‖一二”和“二二‖二一”)。 所以汉代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是建立在诗经四言句的基础上,并和汉赋多用三字、四字句子是密不可分的。当汉赋的文学语言被大声诵读出来的时候,它就和音乐一样,是一种线性绵延的声音过程。在声调的高低交替和韵脚的循环往复中,“顿”就是标志节奏的明显单位。汉语中,一般一个顿中包含两个独立音节,那么四言中就含有两个“顿”。
“粗略地说,四言诗每句含两顿,五言诗每句表面似仅含两顿半而实在是三顿,七言诗每句表面似仅含三顿半而实在有四顿,因为最后一个字都特别拖长,凑成一顿。这样看来,中文诗每顿通常含两字音,奇数字句诗则句末一字音延长成为一顿,所以顿颇与英文诗的‘音步相当。”[12]比如贾谊《鹏鸟赋》中“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远”中的“兮”就被拉长,更突显了这一感叹性语气词的抒情作用。一般来说,被拉长的这个单音节音步与句子前面由轻重音构成的双音节音步形成差别,造成节奏变化,同时,奇数字诗句的句末一字在诵读的时候被拉长元音来补足音步,在节奏变化时兼顾和谐,不会造成头重脚轻之感。
三、 汉赋语言的音韵旋律性
(一)、汉赋的“通”、“独”之术
“通用”、“独用”这两个词作为关键词频繁出现于古代的韵书中,它们是古乐中重要的制乐手段,也是南宋以前儒者皆通的诗韵音乐术语。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名称,从西晋到隋唐,“通用”被称之为“同”,“独用”被称之为“别”。宋元之后,这两个独字之后被加上了“用”,称为“同用”、“别用”。明清之后,人们改“同”字为“通”字,改“别”字为“独”字,称为“通用”、“独用”。尽管有着不同的称为,它们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作为调节汉字发音音高的一把标尺。[13]在音乐上需要使用“独用”之音来达到声和义的统一。所谓“无穷”的假借和转注之音,“转起音注为别字,不转音而借为别用,恰如西晋吕静、六朝夏侯詠、隋朝陆法言等人之制乐手法,音高相近相似之字相互使通,转注假借和之以乐,得之以歌。”[14]如顾炎武先生所言:“有定之四声,以同天下之文,无定之四声,以协天下之律。”[15]
早在先秦时文学语言就有着懵懂的“通”、“独”之感。朱熹注《周南》中“关关雎鸠”的“关关”二字为“不同音高”,余载注《韶舞》中的“平平”和“惟惟”为不同音高,又注“王”字为“必注为同意音高”。这说明,“王”字就是独用字,是不可替代的,而“关关”等字就是通用之术。汉赋中同样有许多通假字,比如张衡的《西京赋》中,“慘则尠于驩”的“尠”字、“柞木翦棘”中的“柞”一字、“奋鬣被般”的“般”字等都是通假字[16]。李善在《文选注》中注:“惨则尠于驩”为“尠,少也,与鲜通也”;注“柞木翦棘”为“柞与槎同,仕雅切”;[17]注“奋鬣被般”为“般, 虎皮也。《上林赋》曰:被班文。般与班古字通。”班固《西都赋》中“桑麻铺棻。”一句,李善注:“王逸《楚辞注》曰:纷,盛貌也。棻与纷古字通。”扬雄《羽猎赋》中“屦般首”中的“般”,李善也注:“般音班。般首,虎之头也。”[18]同时,汉赋中多借用“之、兮、矣、耳”等字调节整体音高,使得语言拥有动人和谐的旋律感。
(二)、押韵的继承与发展
韵的运用是语言获得音乐性中的旋律性的重要手段。古人按发音方式将汉语分为喉、牙、舌、齿、唇五音,与音乐中五音的概念相通。宫音是喉音,商音是齿音、角音是牙音、徵音是舌音、羽音是唇音。汉代刘歆提出宫音厚重、商音敏疾,角音圆长,徵音抑扬递续,羽音低平的说法,不同的韵脚能带来不同的音乐效果和表现不同的情感主题。比如“江洋”等韵发音明朗响亮并且圆润悠长,就犹如音乐中的大调一样,适合表现积极明朗,奋发上进的情感基调,而“一七”等韵低平晦涩,难以大声朗读,就犹如音乐中的小调一般,婉转曲折地表现哀怨凄凉的压抑基调。而句子中最突出的音,或者是押韵压的主韵,就是音乐中确定调性的主和弦音,而其他的变韵就好比其他的调式音符。一般来说,主和弦音表现基本调性,而变化音用以丰富色彩,这样换韵的时候就增加了语言的平仄,体现出旋律美感。
虽说汉赋“不歌”而以“口诵”作为其传播方式,但我们绝无法断言在跨入汉这个时代之后,汉赋与先秦诗乐以及楚辞的押韵规律撇清了关系。换言之,汉赋充分继承了之前《诗经》、《楚辞》文体的押韵规律,大量运用了“转韵”、“杂韵”等方式,并且兼容并包地发展出自己的一派文风。 陈第认为汉赋的押韵与《诗经》《楚辞》有不解之渊源,他在《读诗拙言》中提到:“说者谓自五胡乱华,驱中原之人入于江左,西河淮南北间杂夷言,声音之变,或自此始。然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平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况有文字而后有音读,由大小篆而八分,由八分而隶,凡凡变矣,音能不变乎?……自周至后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19]对于这样的观点,王力先生也较为赞同。纵览《全汉赋》中的文章可发现,汉赋虽然在押韵的方式和体式上有所不同,但押韵常常出现并伴随有规律性。与《诗经》、《楚辞》的押韵方式比较接近的是诗体赋和骚体赋,这两者通常拥有整齐的句式并且通篇都押韵。大多数诗体赋通篇都押在一个韵脚上,比如刘安的《屏风赋》通篇押韵,除此之外,杨胜的《屏风赋》、路乔如的《鹤赋》、苏顺的《叹怀赋》等等也都是通篇押韵。这种押韵规律在汉赋甚至是《诗经》中较为罕见。汉赋中比较普遍的是偶句押韵并且在偶句上转韵。比如贾谊的《鹏鸟赋》,其文章第一节总计十二句共五韵全部押鱼韵,之后开始转韵;第二节仍为十二句共六韵全部押之韵,然后再次转韵;第三节首句即入韵,共六句四韵,押谈韵,之后换韵;第四节以下均为四句一转韵,无其他变化。[20]在汉赋中,更多的用韵令人捉摸不透,似乎无规律可循。有时候是规律的换韵,有时候又像是作者随意而为的押韵,这在汉大赋中较为常见,与诗体赋和骚体赋截然不同。
章沧授在《汉赋美学》中说:“赋家是用诗的格式来写赋,而不是用散文的方式创作”。[21]可见,汉赋在押韵的方面不但继承了《诗经》和《楚辞》的押韵规律,而且融会贯通,将押韵方式与自身文体和句式的发展结合起来,随文而转韵并加强了换韵的整体频率。汉赋的作者在追求句式整齐,气势磅礴,字形华丽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语言的音乐性。
(三)、双声叠韵和句式回环的谐韵之美
汉字的每一个读音都有本身的平仄曲直,加之朗读时分配变通的停顿长短、声音强弱、声调高低等因素,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悦耳的语言旋律。在古代的韵文中,作家通过协调编排文字的声调、韵脚和节奏,使得言辞和谐动听,诵读起来也没有滞阻,唇吻调利,朗朗上口。《文心雕龙·声律》有言:“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22]人的声音自然含有宫商的旋律性,音律的源头就是人的语言声音,那么经过才华横溢的汉赋作者所精心编排雕琢的文学语言就更是具有独特的音乐性。
汉赋中存在大量在语音上有双声叠韵关系的联绵词,这大大增强了汉赋语言的音乐性。“联绵词是用两个音节表示一个整体意义的双音词”[23]。同时,联绵词中的两个字仅仅是一个词素,不能一分为二。凡是一个复音结构连用时的意义与这个复音结构其中的一个字单独使用时的意义毫不相关;或者一个复音结构其中一个字单独使用的意义与这个复音结构联用时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而另一个字不能单独使用;或者一个复音结构的两个字都不能单独使用,单独使用便各自无义,这三种情形的复音词都是联绵词。[24]双声指构成联绵词的两字在上古声母相同或相近而韵不同,比如王集《浮淮赋》:“於是迅风兴,涛波动,长瀬潭偎,滂沛汹溶”中的“滂沛(滂阳/滂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汩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烛坤”中的“璀璨(清微/清文)”。叠韵指两字在上古韵部相同而声母不同,比如张衡《西京赋》:“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中的“婵娟(禅元/影元)”;扬雄《甘泉赋》:“岭巆嶙峋,洞无涯兮”中的“嶙峋(来真/心真)”。用双声叠韵来加强文学作品的音乐性,“它们是由声韵律和音顿律相叠而成,客观上起到与联绵字一样好听、好读的效果。”[25]
司马相如《上林赋》中一段描写山的文字:“于是乎崇山矗矗, 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嵳嵳。九嵏嶻嶭,南山峩峩。岩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閕,阜陵别隝。丘虚崛礨。隐辚郁壘,登降施靡。”多用叠字,双声叠字铺陈而下,有窾坎镗鞳之妙,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逸韵”之美。
句式的回旋同样肩负着强调作者情感与增加文章音乐性的责任。同类的乐音在同一位置重复,或是同一段旋律的回旋,这就构成声音回环的音乐美。比如贾谊《簴赋》:“举其锯牙以左右相指,负大钟而欲飞。”“戴高角之峩峩,负大钟而欲飞。”和“樱攣拳以蟉虬,负大钟而欲飞。”[26]每隔几句就有一句“负大钟而欲飞”,构成整句旋律的回环,且这一句由仄声打头平声结尾,从压抑的基调一下变成昂扬积极的情绪,语音与文字意义相辅相成,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并构成余音绕梁、绵长悠远的音乐美感。
结论:
诗乐舞分离下“不歌而诵”的汉赋脱离外在乐曲的声调节奏束缚,语言得以获得极大的表现和发展空间,以一种独立的音乐化形式成为文学的核心。汉赋作为屹立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文体,继承了先秦文学的内在音乐性,吸收了西域文化的音乐表达方式,并发扬出自身特有的音乐性。汉赋语言中大量的对仗和铺排是其节奏整齐的音乐性表现,奇数字诗句句末一字的蜕化音步而、及骈散结合的多元化句式则是节奏灵动却不单调的突出体现。在音韵方面,汉语语言本身的四声平仄就足以带来特殊的音乐体验,而作者或刻意追求或兴之所至的押韵更丰富了文字自身的音乐感。大量双声疊韵联绵词的运用使得句子悦耳动听,而韵脚的回环往复和平仄相交的读音赋予汉赋文学语言丰满的旋律性。从“依声咏”到“咏依声”,汉赋不仅受到先秦诗乐的影响,还受到来自民间的说唱文学的影响,同时汉赋语言的音乐性也为说唱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文学艺术下移后能够保持充足的活力并得以代代传承。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464页.
[3]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4]西京雜記:六卷/(漢)劉歆撰 (晉)葛洪錄 影印本,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8年(1919).
[5]陈柱《讲陆士衡文赋自纪》释“ 绮靡”云:“ 绮言其文采, 靡言其声音。”( 《学术世界》 1卷 4期)其实不止诗讲究文采和声音, 也当如此, 就声音而言, 诗之“绮靡”在于声韵清丽, 赋之“浏亮”则在于高亢。如, 曹丕《善哉行》:“ 乐极哀情来, 寥亮摧肝心。”按,“寥亮”义同“ 浏亮”。唐李煜《秋莺》:“ 栖迟背世同悲鲁,浏亮如笙碎在缑”.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版,第183页.
[7]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0页.
[8]郭绍虞《语文通论》, 开明书店, 1941年,第 68页.
[9]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 年,第 202-217页.
[10]T·S·艾略特《诗的音乐性》,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181 页.
[1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 第 97页。
[12]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84 年,第 133 页.
[13]宋光生:《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6月,73页.
[14]宋光生:《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6月,76页.
[15]顾炎武:《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6月,42页.
[16]傅剛.俄藏敦煌写本 242号《文选注》发覆 [A].文学版本研究[C].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P276- 294.
[17]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M].巴蜀书社, 2000.
[18]踪凡:《李善<文选注>对汉赋的注释》,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2007年5月.
[19]转引自姜书阁.《汉赋通义》.济南:齐鲁书社,1989:341.
[20]周焕玲:《汉大赋语言艺术研究》,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21]章沧授.汉赋美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15.
[2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7卷《声律第三十三》,5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3]蒋礼鸿、任铭善,《古代汉语通论阅》,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年,P319.
[24]徐振邦,《联绵词概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P15.
[25]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6]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第21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上),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9月.
[3]班固:《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83年
[4]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 [M].巴蜀书社,2000年.
[5]章沧授:《汉赋美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6]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7]T·S·艾略特《诗的音乐性》,载《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8]徐振邦,《联绵词概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9]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语文出版社,2001年.
[10]宋光生:《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年9月.
[11]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5月.
[12]郑明璋:《汉赋文化学》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13]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陈松青:《汉乐、汉赋与汉诗》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4期.
[15]郑明璋:《论汉代音乐文化视野下得汉赋创作》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2007年3月.
[16]马予静:《论文学语言的音乐性在赋体骈律化中的作用》中州学刊1999年5月第3期.
[17]蒋丽霞:《汉乐府音乐性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8]孙丽娟,江燕:《论汉语语音的音乐性》.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6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