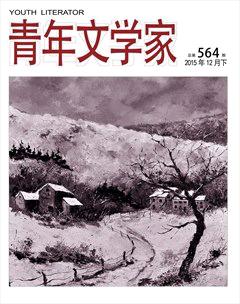从结构主义视角浅析电影《赛德克?巴莱》
摘 要:魏德圣导演的影片《赛德克·巴莱》以历史上真实的“雾社事件”为原型,其中彰显了历史、文化、人性等多方面的深刻内涵。本文拟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其分析,发掘《赛德克·巴莱》中人类学的色彩和魅力。
关键词:结构主义;野蛮;文明
作者简介:彭翀,女,汉族,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大学2013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族群文化。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2
影片《赛德克·巴莱》的名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内涵。“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是真正的意思,赛德克·巴莱即“真正的人”。在赛德克族的信仰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赛德克·巴莱。在他们生命结束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要经过彩虹桥,彩虹桥的尽头是一个猎场,只有真正勇敢的战士才能通过这座桥成为赛德克·巴莱。电影《赛德克·巴莱》即讲述了赛德克族的一段悲壮历史:1930年,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原住居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众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发动了震惊当局的雾社事件。
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二元对立思想深邃而明晰,为人类认识历史、认识自身、认识他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工具。在《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中,充满了二元对立的事物,这些事物充分反映了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和情感。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赏析这部电影,不仅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赛德克族人民的精神内核,也可引起诸多对于现代文明和发展的反思。
一、猎场与学校 :野蛮与文明的碰撞
“没有出草取过敌人首级的男人,是没有资格在脸上纹上图腾的。收桥的祖灵看着他们,干净没有图腾的脸,你们不是真正的赛德克!”从这一方面来看,赛德克族是野蛮的,或者说,他们可以被归为现代文明定义的野蛮体系中。日本人殖民者占领台湾岛后,在当地建立了邮局、商店、学校,并派出了老师对赛德克族的小孩进行日语教学,传授他们生活的礼仪。
电影中,花冈一郎作为一名赛德克族人,已经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并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他对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说:“头目,我们现在不好吗?我们不必再靠猎杀过日子,这样文明的生活不好吗?”莫那·鲁道反问:“什么叫做文明?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他们看见自己有多贫穷了!”莫那·鲁道的这番话,几乎将表象中的野蛮与文明颠倒,引发更深层的思考。随着情节的不断推动,日军在打压赛德克族人的抵抗过程中一直处于劣势,日本军官最终决定使用糜烂性炮弹灭绝赛德克族人时,他对下一级的军官说了这样一段话:“叫你们文明……你们却逼我野蛮!”至此,日本殖民者的行为将其文明的外套卸下,裸露出他们野蛮的目的。当文明的方法无用时,日本人决定用生化武器征服他们,糜烂性炮弹对人身体的伤害是残忍并具有毁灭性。
野蛮与文明是对立的,在这部电影里也是互相转换的。看似野蛮的赛德克族,实则有着自己坚定信仰的文明;看似文明的日本殖民者,实则掩藏着不易暴露的野蛮。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不是进化的两个阶段,二者可以共存甚至可以在同一文化中共生。猎场里有厮杀和血腥,学校里有知识和文化,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载体,它们有各自倾向的一面。但是,猎场里也有文明,赛德克族的文明是对勇敢的追求,是对“血祭祖灵”唯一不变的坚持。学校里则暗藏着统治他者思想的预谋,是包藏着野心的地方。
二、彩虹与太阳:自我与他者的纠缠
每一个赛德克族人都在追寻赛德克·巴莱,真正勇敢的人才能通过彩虹桥,到达另一端的猎场。彩虹在赛德克族人的心里,是世俗通往神圣的桥梁,是寻找祖先的路途。电影中多次出现了彩虹的意象,彩虹即代表者赛德克族对自我的认识,彩虹就是他们的身份标识。彩虹是与自然相连接的,代表着原始和人的自然天性,而作为日本殖民者的代表的太阳,则是征服和文明的代表。原本是界限分明的两种信仰,却在台湾岛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交织,从而引发了信仰的错乱和身份认同的模糊。
作为道泽群屯巴拉社的头目铁木瓦力斯,在小时候受到了莫那·鲁道的威胁:“我不会让你长大的”。这在铁木瓦力斯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一道阴影。后莫那·鲁道联合众部落发动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铁木瓦力斯知道家园的猎场和亲人都被统治着,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他在小岛的友善诱骗下,竟然联合日本殖民者一同对抗镇压莫那·鲁道发起的反抗。小岛一直以朋友的方式和态度与铁木瓦力斯相处,这让铁木·瓦力斯以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胜过同族的关系,而小岛也利用了铁木瓦力斯自小在心里的阴影,使得两个部落互相残杀,而这正是日本殖民者最乐意看到的结局。铁木瓦力斯的内心是纠缠的,他深知自己失去了猎场和家园,也知道应该“血祭祖灵”,但在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在日本殖民者友善的外表下,他选择了将矛头对象曾经生活在同一土地的族人。
然而,在彩虹和太阳两种信仰交织的文化中,铁木瓦力斯的身份认同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本是赛德克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赛德克族人的血液,但是他们却从心里认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他们身份和处境的尴尬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了日本警察的一郎和二郎游离于本族人与日本人之间,身份的暧昧注定被两个圈子所排斥而处境尴尬。一方面本族人嘲弄他们有一身“日本警察的皮毛”,而不把他们视为同类;另一方面,哪怕他们接受了日本文化,与各自妻子的名字、服饰完全日化,仍要面对日本人的质疑:两个番人难道也能生出一个日本孩子?当花冈一郎得知莫那·鲁道要联合各个部落大规模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他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认可日本的文明,认可当下的有秩序的生活状态,但当莫那·鲁道反问他什么是文明时,反问他最终是想进祖灵的猎场还是日本神社时,花冈一郎犹豫了。赛德克族的血液在他身上流淌,“血祭祖灵”的信仰是他从出生就带着的一个根,然而日本的殖民文化却在不断的松动着他原来的根。
自我与他者的纠缠最激烈的一幕在花冈一郎帮族人取得枪支后,并没有参与战斗。他身着赛德克族的衣服,手持番刀,他的妻子也是赛德克人,她身穿和服,与花冈一郎达成一致。花冈一郎番刀一挥,将自己的妻子杀死,然后他又捂死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最后,花冈一郎选择了极具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破腹自杀。就如他的弟弟花冈二郎所说:“切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儿也别去了,当个自在的游魂吧。”在这,彩虹信仰与太阳信仰的交锋达到了顶点,自我与他者的矛盾突出至极。两种文化就如两股势力在花冈一郎的心里交织斗争,身份认可的错乱导致花冈一郎在自我与他者中不断地游离。
身份的认同并不总是非此即彼,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也并非绝对。在花冈一郎的身上,自我与他者即对立又共存,自我有时即是他者,他者有时亦是自我。
整部影片《赛德克·巴莱》无处不显示着二元对立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作为人类学中非常最重要的结构主义,正与此不谋而合。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既有以极端对立的形式出现,也有以温和可容的形式出现。番刀与枪炮、猎场与学校、彩虹与太阳,这些都是二元对立也是二元对立的文化的载体。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纵向发展出现的载体,也可被视为同一时代横向的不同类别。
参考文献:
[1][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张祖建译.结构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1.
[2][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03.
[3]雷攀.太阳与彩虹的信仰之战:《赛德克·巴莱》电影叙事学解读[J].中国电影评论,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