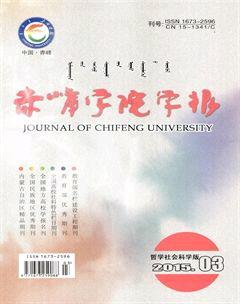庄子审美视野下丑向美转化的逻辑分析
汪静
摘 要:庄子思想理论体系的中心在人的哲学上,即对人的个体价值、个体精神的开拓与探求,因而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庄子的最终目标是将丑转向大美。现象界的丑如何向美转化,大体有这样三种方式:矫揉造作之丑“法天贵真”、外在形体的丑陋以“德”来内充、对于内在心灵的鄙陋则应放弃功名之心。庄子重视人的内在修养即“德”,其主旨在破除外在残缺丑陋的观念,树立注重内在心灵美的大美思想。
关键词:庄子;审美;丑;美;转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3-0042-03
一、矫揉造作之丑“法天贵真”
庄子以自自然然为美,反之则丑,而这种背离自然之丑,唯一的化解之法便是“法天贵真”,“法天”也就是法自然。“法天贵真”既是庄子美学中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庄子化丑为美的根本方法。《渔父》曰:“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天”即自然,而“自然”之不可改易则是因为它存在着“真”性。人之所以要“法天贵真”,就是要师法自然以保持人类的真正自由。“真”是一种合天理、合规律的本来状态,只有真才有个体独立的人格,才有个体的自我价值。而失“真”也就违背了自然,“自由”是庄子追求的人生目标,是“大美”,是“道”。因而,对于个体来说,失“真”也就是不自由、离“道”的表现,从而也就导致丑。
西施皱眉是因心痛而起,是自然本真的行为,痛而皱眉是自然的常态,所以美,且在其“真”, “真”也就是自然的常态,。丑就丑本无可厚非,而东施却忸怩作态,便丧失了自己的本性,结果是丑上加丑,丑到了极点。“丑人”之“丑”不在其本然之丑,而在于失“真”,矫揉造作则丑。每个人都有属于其个性之“真”,丧失这种“真”,也就没有了本性。所谓“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骈母》),长就长好,短就短好,一定要把长的变短,短的变长,不但带来了痛苦,反而弄得更丑,破坏了自然之质,丑态百出。因而,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更应该根据其自然本性,率性而为,如果强其所为,则扭曲了自然之本性,而丧失了自我。只要自然,合乎了“真”,合乎了“大美”,也就合乎了“道”。
《天运》曰:“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切妻子而去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西施颦眉出于自然之真情流露,因而美。而其里之丑女刻意模仿,只能是丑上添丑。在庄子眼中,美的东西真实无伪,以真为本。失真则有违自然之理,也就与美挂不上钩。“天真”是“丑”与“道”联结的先决条件,“天真”之“丑”也即自然的本真状态,只要是作为自然的本真状态呈现,“丑”的事物也可以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内在之美而在“道”那里得以升华。
二、“形”之丑以“德”充
庄子笔下还有一大批怪诞、丑陋形象。如《骈母》曰:“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趾;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只要是合乎自然的“性命之情”,骈母枝指类的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宗师》写子虽“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但他却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可见美与丑都不过是自然的造化,这里主体的心态是自由的,合乎道的。以上这些形体残缺之人可以说均可归为“畸人”之列。
孔子《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孔子的“德”显然不是庄子的“德”,孔子的“德”重“仁”、“礼”,而庄子的“德”则与“仁”、“礼”无关,庄子的“德”,得“道”而生。“对于庄子来说,德当然和仁、礼等无关,它是宅心于虚的,也就是《人间世》中说到的心斋。但虚并不是一无所有,如‘虚实生白所显示的,在虚静的心灵中,可以生发出另外一个光明的世界,这就是不同于形体世界的精神的世界。”[1]庄子对“德”多有论述,尤其明显地体现于《德充符》。在《德充符》篇中,庄子虚构了六个肢体残缺或外形丑怪的“畸人”形象,以他们的完美道德来体现他们内在精神的力量。何谓畸人?庄子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大宗师》)“至于庄子这里所说的‘德,不仅不同于一般的道德法则,而且也不同于所谓‘自律的德性,例如儒家崇尚的‘仁或康德的‘绝对命令。庄子倡导的‘德,实质上是‘得,即‘得道。就是说,‘德充者乃是‘得道之人。因此,庄子倡导的‘德充实质上乃是‘道充。”[2]可见庄子之“德”有别于儒家之“德”。庄子之“德”是“道”在人事上的落实,能够进入体道的人生境界,便达到了自由精神境界。钟泰在其《庄子发微》中对庄子之“德”和《德充符》这一名有详细叙述。曰:“‘德者,得也。得者,有诸己也。‘充,充实。《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曰美,曰光辉,皆形著于外者。”[3]庄子视“德”于“形”之上,还提出“全德”一词,即保持内心之“德”而不摇荡,“德不形于外”。《德充符》载:“‘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
所谓“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是比‘形更要紧的东西。单纯就形体而言,死去的母亲和活着时比较并没有什么缺失,但豚子之所以受惊逃走,是因为‘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形体虽然在,但豚之所以为豚者却消失了,‘使其形者消失了,这使形体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母亲也就消失了。‘使其形者才是使母亲成为母亲的东西。”[4]在《德充符》中,庄子列举了鲁国的兀者王骀受断足之刑,而“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这是因为王骀能够有“游心乎德之和”的自由心态,因而他能“视丧其足为遗土”[5]。庄子视“形骸”不过是人的身体的寄托之所,人的内在精神对“道德”的所归才是人的根本。兀者申徒嘉和郑国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而郑国子产以与之同座而感到羞辱,申徒嘉说:“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骇之外”。子产所见的是“形骸”的残缺,而未能见其精神的全美,这是世俗的见解。《德充符》中还有一人物哀骀它,奇丑无比,“以恶骇天下”,却见爱于众人。“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支离无和鸯大瘿两个形体残丑人而深受卫灵公、齐桓公所喜爱,以至于看常人都是残疾人,显然三人那种内在完美的道德人格精神超越了外在形体的丑陋与残缺。endprint
庄子的审美观重人的精神层次,而且他还更加肯定了丑怪的形式完全可以包含和升华出精神的美,使得丑与美的对立消失,达到审美主体的精神自由。“事实上,他(按:庄子)更喜欢通过形体的残缺来表现德的内充。为此,他塑造了从兀者王胎、申徒嘉、叔山无趾到瓮怏大瘿等一大批形体残疾者的形象,也许他觉得,形体的残缺更能突显出德的完全和充实以及它的意义。庄子笔下的形体残缺者都是魅力非凡的人,这种魅力显然不是来自于形体,而是内在之德,是心灵中孕育的德性的光辉。”[6]卫灵公、齐桓公完全被“丑”的审美力量所征服,以至“视全人,其短肩肩”。在庄子看来,一个人如果人格精神是完美的,那么人们就不会在意他形体的丑陋,反而觉得他比形体健全完美的人更加高大。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这是庄子所谓的美的真正所在。当然。这不意味着庄子否定形体美,例如庄子所理想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之美及西施之美。当形体美与内在的德之美相冲突时,他更重视的是内在精神之美。
三、失“德”之丑弃功弃名
庄子推崇老子的圣人的观念,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提出“至人”、“神人”、“圣人”,这是他对失“德”之丑之内化寄予的目标。失“德”也即失去内在美的精神美德。那些神人、至人们不谋求功名利禄,逍遥于自然之中而不与人相争。“……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那些丑陋的失德之人也只有像至人、神人、圣人那样,做到了无己、无功、无名才将完满。《齐物论》曰:“圣人不从事于务……而游乎尘垢之外。”“众人役役,圣人愚钝……”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名,自命也。”《人间世》云:“德荡乎名,智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智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尽所以尽行也。”《天运》亦曰:“名者,公器也。”可见,在庄子看来,“名”是可以伤身灭命的。且《则阳》云:“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人间世》又云:“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不已。是皆求名实者也。”因而,庄子主张“为善无近名”(《养生主》),名与实应该排除掉,并从根本上去掉那些羁绊性的虚名。正如《庚桑楚》中云:“券内者,行乎无名;……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
《逍遥游》云: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爵火不熄,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可见,就名与实而言,主张用实来定名,人只有抛弃那些贪欲,才能面对所处的世界。失去“德”性是可怕的,“‘人刑或许只是对形体的惩罚,比如断足或者无趾,而‘天刑则是对心灵的桎枯。相比起来,天刑是更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带来的是心灵的残缺,是德的破坏。这是远比形的残缺更要紧的东西。”[7]
《缮性》曰: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己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
可见,庄子认为要摆脱内在的鄙陋得“不肆志”、“不趋俗”。所谓“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庄子这里所说的“无为”,实际就是为了说明“无功”,而做到“无功”,则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了。《缮性》又云:“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列御寇》曰:“夫明者不胜神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徐复观先生也曾这样说道:“人情总是以自己作为衡量万物的标准,因而发生是非好恶之情,给万物以有形无形的干扰。自己也会同时感到处处受到万物的牵挂、滞碍。有自我的封界,才会形成我与物的对立;自我的封界取消了(无己),则我与物冥,自我取消了以我为主的衡量标准,而觉得我以外之物的活动,都是顺其性之自然。”[8]庄子亦然,他认为可以通过回归,把个体从纷繁杂乱的尘世中上升到无挂碍的自由境界。
因而只有摒弃世事的牵累,才能让心境平和,而只有心境的平和方可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免除世事的纷扰,才能使个体的本性得以复归,成为自然之体。只有心灵的桎枯没有了,个体才能真正自由地活着。《逍遥游》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给那些为外在名利所束缚的内在鄙陋之人指出了这样一条明路,也即“弃功”、“弃名”、“无功”、“无名”,这便是庄子笔下这些内残之人应该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4〕〔6〕〔7〕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66,60,60.
〔2〕王树人,李明珠.感悟庄子:“象思维”视野下的《庄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8.
〔3〕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6.
〔5〕曹基础.庄子浅注[M].中华书局,2000.72.
〔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商务印书馆,1977. 394.
(责任编辑 张海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