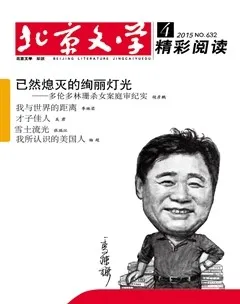记忆驿道
回望
与家人或友人告别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驻足回望。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时候,回望能得到回应。当他们亦如我一般回过头来,淡淡地微笑,轻轻地挥手,那一刻,即便是极平凡的一次小别,也会像一朵清芬的花,盛开在暖融融的心间。
更多的时候只是回望,单纯的回望。望着匆匆离去的背影或是悠悠闲闲的步履,相聚时的一情一景又浅浅淡淡地缓缓掠过。想起纪德曾说:“只有让今天的欢乐退席,明天的欢乐才可能出现。”此情此语,回望中的离别便有了一种特别的韵致。
其实,回望的岂止于离别?
回望更多的是我们生命的历程。生日,便是这样一个回望的驿站。有人说,生日是我们反省自己的节目。不管你的生日如何度过,总会有一个空隙,让你安静地自然而然地回望自己生命年轮中的又一岁,回望生命中的快乐与忧伤、幸福与苦痛。回望是一种必然。我们需要回望,需要在回望中咀嚼生命的细碎与美好。
也不仅仅是生日的回望。或许就在经意与不经意的一瞬,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跳入眼帘,可能牵出的就是长长的一段岁月。
一沓旧札,一则日记,一本旧书上的赠言,一副老式的破旧眼镜,一件洗得泛白的旧布衫,一个过时的背包,一顶染有陈迹的草帽,一个空空如也的香水瓶,一本旧的通讯录,一首老歌,一部老电影,一条似曾相识的石板路……每一个细节都恍若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湿润而新鲜,带给我们一种快乐的宁静。
回望应该是生命的芳草地,它氤氲的绿意里有反省有觉悟,也有温馨的怀念与记忆。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一切经过了的点点滴滴,都会积淀于记忆的驿道上,等待你深情的回望。
在匆匆前行的忙碌里,驻足回望,是缱绻的抚慰,是美好的清凉。生命需要回望,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尘土、沙子和草皮?
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在她的一篇随笔里这样写道:“最富于才华的文章,倘若脱离了它的基本生存要素,也只不过是尘土、沙子和草皮而已。”
我不想让这则刚刚拉开帷幕的文字,上演一场弥漫教条的“正剧”,蒙田说:“我并不教诲,我只是叙述。”借用他们的话,是希望这个内心涌动着不安与繁复的夜晚,能在从容的叙述里得到平静和简单。
曾经在一个课堂上讲过文章的“生存要素”,即学问、才气、见识和情趣,缺一不可,就像一张凳子的四条腿。学问是底气,才气是“魔法”,见识是独到而深入的眼光和见解,情趣是拒绝迟钝、拒绝刻板的“个性”。
此时重温这“四条腿”,一阵阵的脸红禁都禁不住。想起若干年前读过的一篇文章,有外国人始终弄不明白:用筷子怎么喝汤?我曾经侃侃而谈的学、才、识、趣也是这“筷子”吗?这“筷子”能用来喝汤吗?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问题吗?把筷子放在一边,用勺子喝或端起碗来喝,就这么简单。真正渴望“我手写我心”的人会拘泥于这“筷子”吗?完全清楚地懂得“生存要素”的人,是否一定能写出学、才、识、趣兼备的文字?
再回到“四条腿”的理论上来。这个比喻并非我原创,我只是借用而已。在我和黄建华先生合著的《新VS旧——关于文明的二人对话》一书里,有一篇《为何不能张口就是钱?》,我们在讨论“张口就是钱”的困惑与弊端时,他提出“钱”只能是个人或社会的一条“腿”,而任何一张凳子只有一条腿断然是立不住的。
这个比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能唤起诸多联想。一个社会的“四条腿”,除了经济之外,是否还应该有法律、道德和文化?一份情感的“四条腿”,除了缘分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理解、尊重和责任?而一篇文章的学、才、识、趣用“四条腿”来作比,也就水到渠成。
而我此时进一步联想到的,是这“四条腿”的“凳面”。没有“凳面”,单打独斗的“四条腿”可能成为一张完整的凳子吗?当然,你会说,没有“凳面”的“四条腿理论”根本不可能成立,但我还是忍不住在学、才、识、趣这“四条腿”之上加上了一方心灵的“凳面”。我想,若没有心灵的“凝聚”与“熔铸”,学问可能成为“书袋”,才气可能流于油滑,见识可能呈现冷漠,情趣也可能造作而轻浅……
读一本好书,品一篇好文章,应该能听到一个灵魂的脉搏与心律。灵魂不在场的书,至多是舞台上的一个小丑,粉墨登场,让人一笑而过。灵魂不在场的文章,即便穿着浮华的外衣,也很难掩其内里的苍白与空虚。
书如此,文章如此,一份工作、一段情感、一个家庭乃至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借伍尔芙开篇的那句话,是否可以这样说:最富有才华的人,倘若脱离了他的灵魂,脱离了他的真性真情,也只不过是尘土、沙子和草皮而已?
两只杯子
不知是谁将它们置于一个平台上的。台面很乱,堆叠着很多待清理的东西。两只杯子是这凌乱中的“另类”,它们神闲气定,静若处子,你的目光会自然为之所牵引。
一只是深棕色的紫砂杯,一只是青白色的细瓷杯。色调的反差并不影响它们并列的和谐。
“紫砂”的杯盖和杯底均饰有相同的龙纹,一条条蛟龙穿行游动于云水之间,造型质朴而精致,有刀刻的力度和细腻的神韵。它安静地立在那里,似一个忠厚成熟的长者,有岁月的沧桑镌刻在它的朴素与沉稳里;还有一点严肃,甚至有一点气韵苍凉的神圣。而“细瓷”则是一份云淡天清的浅致,是一阕冰清玉洁的小令。它温温婉婉地依在“紫砂”的近旁,恍若一娴雅静敛的女子,纤柔、宁和、恬淡,有几分飘逸的妩媚。它的杯身饰有青蓝色的花纹,若一袭莹润婉约的“旗袍”,把“细瓷”的优雅衬得恰到妙处。
把“紫砂”托在掌心里,有点沉,细细摩挲之间,你仿佛可以感觉到泥土与火焰的呼应与融和,那是一种纯朴的写实的气质与浪漫的融和,是生命的本色与梦想的融和,是生命的沉着与轻盈的融和。而轻抚“细瓷”,是点点浸润的凉凉的光滑与柔嫩,轻叩杯沿,缭缭清音如淙淙泉响,让你不忍惊扰它,仿佛怕惊扰了一个悠远清凉的梦。
有一份默契在它们之间氤氲。一个有秋日的沉郁与成熟,一个是夏日的明快与纯净;一个美在气骨的“重”,一个美在神韵的“轻”;一个刚中有柔,一个柔中寓刚;一个浑厚古朴,一个清新典雅。它们如此迥异,又如此相似。它们以那样简朴单纯的姿态静默着,一缕阳光斜斜地抚照着它们,温情脉脉的音符在我们心中缭绕,让我们仿佛看到的是树林,是田野,是天空,是大海……
莫名地为它们担忧,我仿佛能听到它们美丽的叹息,能感觉它们轻轻摇荡的忧伤。它们是带露的叶,是娇柔的花,也是丰沃的土,潺流的溪。我们能做的,唯有珍惜。
就做一棵树吧
缙云山,一处颇不起眼的山坳里,突然有两棵比肩挺拔的树炫然入目。
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因为离得比较远,我也看不清春天的枝叶是否已抽芽。舒舒朗朗的浅褐色枝丫,自然又自如地伸展。奇特的是,两棵树比肩之内侧,枝丫短促而纤细,恍若有两只手羞涩地牵着;而那外侧的枝丫却是另一番景致:绵长、舒展而对称,像一面扬起的风帆,又像一双高举着的遥相呼应的手,那般和谐而灵动。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它们都相互致意。这两棵树仿佛在向我昭示着幸福。在乍暖还寒的料峭里,我想象着春叶满枝的盎然,想象着夏意葱茏的繁盛,想象着秋气横生的清静,还有此时残存的冬日禅意。除了幸福,我不知道怎样的词语可以替代?
这时候,有朋友提醒我说,那两棵树是生长在一座合葬的坟茔上的。我不由得一震。不是风帆,不是手,是树之碑?树的幸福是根植于沉痛的怀念里的?我眼里的幸福是建立在痛苦的墓石上的?
我不知道那坟茔里安息的是怎样的两个人,但我仿佛能够阅读这两棵树,阅读它们曾有过的春夏秋冬,曾有过的快乐、幸福与悲伤、痛苦,还有彼此的懂得与隔膜、分担与共享……
远远地凝望那奇特而美丽的树,树下的坟茔在我的凝望里也成了一方美丽的石头。有风掠过,树树依依,轻轻摇曳,仿佛在问:人比树幸福,还是树比人幸福?
树们安静自如地生长,它们眼里看透了多少人世间的恩怨风雨?人们懵懵懂懂地成长,要经历多少坎坷跌宕才能到达安静自如之境界?
在微雨微风中与树告别,在微雨微风中回望它们的美丽。就做一棵树吧。即便没有比肩挺拔的幸福,安静自如地生长也是好的。
仅此一本?
出差哈尔滨,在稍显凌乱的新华书店里穿梭,希望能寻到一本心甘情愿不远万里带回去的书。在一大摞灰色书脊的间隙,一本暗黄色的书在我第二遍目光的搜索中定格——《梁漱溟先生讲孔孟》。莫名地有点激动,恍若一个久违的朋友不经意地跳到了眼前。
捧在手上,还没来得及细翻,就急急地问店员:“还有吗?”答:“全在架上。架上没有就没有了。”我把上上下下的书架查找遍了,竟真的仅此一本?还是不甘心,询问收费处,答案依旧。不由得自问:一本不够,难道想扛一大摞回去不成?
我其实并不确定需要多少本,仅此一册的结果让我一半是遗憾一半是庆幸。我曾经在一本文史方面的杂志上读过《梁漱溟先生讲孔孟》的连载,印象深刻。梁先生的见解坦诚、独到而宁静,一个话题仿佛就是一盏灯,曾将当年模糊的心路一点一点地燃亮;关于仁,关于乐,关于讷言敏行,关于不迁怒不贰过……像一只只山鸟曾在我的心湖上跃动,且扑扇出一方“含真抱朴”之清凉天空。
翻看版权页,是2003年6月再版的,印了6000册。这本书是以梁先生上世纪20年代在北大讲授“儒家思想”的课堂笔记为据,在整理者李渊庭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修订完成,并于1993年梁先生百年冥诞之前出版的。李渊庭1994年去世,我想他捧着先生的书离去,定是无憾的。十多年之后,书架上有那么多书无人问津,梁先生的书却仅此一册,更当欣慰才是。
回程中,转机于上海虹桥机场,这是我印象中售书点最多的一个机场。在一排热闹斑斓的杂志书架旁侧,闲散地丢放着几本古香古色的册子,大16开的封面上印着优雅、精致的古代艺术品。是全彩版的《古董拍卖年鉴》。
最喜欢的还是瓷器。远至北齐、西夏的高古陶,近至清代、民国的青花。我并不关心每件器物下面的成交价格,吸引我的是陶瓷的沉静典雅之美。不管是单色、静敛的含蓄,还是五彩、莹润的妩媚,似乎能触摸到每一寸的细腻、匀净和婉约。我想起梁先生在书里提到的“雍容安闲的中国态度”,那是不是瓷器的态度和精神呢?
“正当的人生是安闲的,不是跑的;是恬静的,不是忙乱的……”瓷器的生命是安闲的,是恬静的,它们“没有野心”。梁先生也是这样“模范的人”,他强调生趣与和乐,排斥占有的冲动,看重“顺天理之自然”,为的是“圆满了生活,恰当了生活”。我仔细地翻看着画册里那些精美的瓷器,脑子里却浮现着梁先生瓷器一般隽永的智言慧语。
不由得想,这些瓷器那么美,却又那么易碎。在当下“事事求快”,“只问多少,不管好坏”的世风里,那么美的思想是否也会如此易碎?又想,即便那么易碎的瓷器,在“拍卖年鉴”里的亮相,也如此完整而丰富,有生命力的智慧又怎么可能轻易随世风而逝呢?
巧的是,当我买下瓷器“拍卖年鉴”时,那懒洋洋的售书小姐飘出一句话:“这是最后一套了。”呜呼,此乃天意乎?
别离的笙箫
3月3日,周五,第二节课。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可能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有两个同学那天过生日,大家乐呵呵地为他们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的眼里含着泪,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接着昨天的课,讲完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朗诵了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我还有意无意地提起了上学期末抄给大家的崔瑗的《座右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以这样的方式在与你们道别。
下课铃声响了。平日里下课,我们总是老朋友一般挥挥手,至多我说“今天到这儿”就过去了。今天,我让班长叫了“起立”。我说,希望你们对老师说声再见。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里已有了些许的哽咽,眼里已盈满了泪水。你们是那般敏感,在整齐地道完“老师再见”后竟不离座,你们着急地追问:“老师,怎么啦?”我笑笑说“没事”,然后逃也似的离了教室……
我看到了你们的泪,看到了你们“集体示威”式的不舍,看到了你们真诚而纯洁的心。我想对你们说,不管发生怎样的变故,希望你们相信,我爱你们!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我知道说出来已显得非常无力,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明白,明白老师的心与你们是一样的。
到了晚上,接到了你们打来的电话,你们已从其他老师那里证实了今天的“最后一课”。你们“怪”我不辞而别,你们在电话那头哭着,我在电话这头哭着。我知道我很难面对你们的“不舍”,很难……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我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与你们告别。虽然确实是因为工作需要,可以解释,但一切解释的理由都会被“别离”的事实击得粉碎。我已不可能回头,尽管不舍。我曾对你们说过,人生没有无谓的体验。我和你们在“别离的笙箫”里体验到的美好真纯的情感,或许会成为我们未来生命的养料。
这几天,陆陆续续收到大家写来的信,最让我感动的是你们通达的理解。你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爱一个人,就应该为她着想……”这样的话,真是让人落泪啊!
感谢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彼此真心的交流赢得的欢声与笑语会永远铭刻在我心上。你们纯净的快乐一直感染着我,我在你们的笑脸上感受着青春、热情、真实、纯洁和干净,更感受着你们拔节的生长!每天的《班级日记》就是一首诗,一首明媚而向上的诗;每天的“课前一分钟”就是一首歌,一首清脆而明亮的歌;而每周的《日知录》更是一幅长卷,色彩斑斓,芬芳四溢,让我流连忘返。陪伴你们的日子,我是幸福的,虽然有时候很累很累,但“累”的内里却有独属于我自己的一份充实的快乐!
感谢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清泉般美丽的日子。我在你们干净的笑靥里清洁着自己,我在你们明媚的朝气里年轻着自己,我在你们稚嫩的冲动里成熟着自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我常常对你们也是对自己说的话;“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这是崔瑗的《座右铭》里的诗句。我想让你们知道,生命的花季只有一季,好好珍惜,努力完善自己,别错过了成长的最佳时节!
“啊,真好!”这是我情不自禁的一句口头禅,出自内心,没有丝毫的伪饰,那是我为你们哪怕是点滴的进步而由衷的赞叹。你们用了“深情”这个词作了它的定语。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依然能深情地对你们说:“啊,真好!”我想,那定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时刻……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