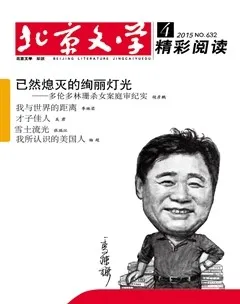消失在书笺里的墨香
一
文坛从来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文人嘛,都是聪明的男人女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曹丕曰: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都不是省油的灯。俗话说,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座次百零八条好汉,没有本事,想混出个名堂,难。不相轻的有否?也有,但不是在一个等级的空间。或者大师与后进,这是奖掖,更是提携,朝上仰视,是景仰是高山仰止;或者是男人与女人,这是欣赏,是迷恋,尤其是对美丽、洒脱,多情而睿智的女性,她更有机会成为明星式的中心人物。
近日,读一本《林徽因的会客厅》,着实地读出了点什么来。都是文人事,可也不就是可有可无的。林徽因的会客厅,是文坛上的靓丽风景,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是迷人的风景。这或者是独一无二的,此前未见,或者有个八道湾的苦雨斋,还是有所不逮。此后呢,有一个二流堂,也颇有声名,可是都没有林徽因的会客厅如此旖旎,诗情画意,仿佛是天上人间的美丽神话。
林徽因的会客厅,令人神往的,不是会客厅,会客厅哪儿没有?也不是那些声名很大的来客,却是这位光采照人的女主人,即林徽因。当时的客人,都是极一时之盛,那么显赫的男人,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李健吾、卞之琳、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等等,还有男主人的梁思成,但在她面前却都弱化成了客厅里的壁灯,成为她的光芒的陪衬。他们是如此情不自禁,又是如此地心甘情愿。
“时间是一个最理想的北平的春天下午,温煦而光明。地点是我们太太的客厅……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这是一篇题目为《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文章的一段。谁能想象,这样的文字,分明带着讽刺味儿的文字,却是出于一向温婉,与人为善的冰心之手。这似乎是意外,其实一点并不。冰心与林徽因,都是才女,是脚底敲地板都会响的人物,性格,还有留学的背景决定了她们的风格不同,可以看出,冰心更趋内敛、蕴藉,而林徽因则是张扬、豪爽的。这是不同性格的碰撞,但骨子里何尝不亦是一种传统的文人的相轻?
据说,林徽因当日没有撰文回应,她只是让人给冰心送去了一小瓮自己从山西带回来的上好老陈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漂亮。不愧为林徽因。而冰心呢,也很漂亮地把老陈醋收下——大家心照不宣。
可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向林徽因发难的冰心,若干年后她却也受到了来自更年轻的同性文人的发难。是否一报还一报?如果不这么宿命地说,却也只好说是无巧不成书了。无论林徽因,还是谢冰心,恐怕谁都不能预料及此。
向冰心发难的是同样才华横溢的张爱玲,有她的文字,白纸黑字为证,也是上世纪40年代初,那风头正健的年月,在《我看苏青》中她说:“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这话还算客气,那么,与张爱玲同时走红的苏青就很不客气了。她说:“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常在作品中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这样的话,已经不只是讽刺了,是直批脸面的挑衅,恐怕谁也咽不下这口气的。
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冰心对此作出了回应的任何文字,她不可能不知道,内心又如何?肯定不会一笑置之的。而不回应,或者是不屑,还是其他的原因呢?我们不能揣测,但应该说,不回应正是最理智的。
她们都是一代风流人物,除了苏青稍逊风骚,不在同一个级别之上外,其他三位都势均力敌,各领风骚,看她们的心理的微妙,或者恰应了一句古语:蛾眉之善妒。她们不仅是文人,还是女人,再怎么聪慧,这“善妒”的天性,也不能幸免的。而且越是聪慧的女性,越是可能相轻的,这却也说不定呢。
她们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据说,冰心后来就从不提起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或者也自悔当时的孟浪。因为这与她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不吻合。不过,写了就写了,悔却不必的。这就是历史,也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看人,其实并不全面,有时囿于成见,有时先入为主,有时更是以偏概全。其实,人是多面的,我们都说自己亲见,可我们的观点,更多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奈何?
二
民国文人中,颇有几则被传为佳话的爱情,沈从文和张兆和可称其中之一。据说,当年在上海教书的沈从文,乍遇张兆和,即惊为天人,不顾一切地展开了这份绝世的“师生恋”。别看沈从文是个“乡下人”,可他执拗,不达目标不罢手,这是他的长处;他不善言辞,可是他有一支生花妙笔。当年写了多少动人灼热的情书,虽没有准确数字,但有人开玩笑说,他的情书写遍了大半个中国。矜持的张家三小姐,因此倒是被感动了,并答应了婚事。
他们的爱恋可也备受波折的,这当中也有过种种美谈。如面对沈从文炽热的情书,书香门第的张家三小姐最初是抗拒的,她觉得这不是一位师长所该有的举止,太不像话了,故把一大沓情书都交到了胡适那儿,多亏了胡适的睿智与妙手促成。后来,沈从文追到苏州张家,设法讨好张家大小,曲线救国,最后,终于真诚所至,金石为开。晚年张家二姐允和撰文回忆:她当时打电报给沈从文说,乡下人喝一杯甜酒吧。
沈从文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创作的丰收。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脍炙人口的经典《边城》《湘行散记》就都得益于爱情的滋润。《边城》写于蜜月期,翠翠就有张兆和美丽、聪慧的影子。这时,沈从文的心里充满了甜蜜的诗情。而《湘行散记》则是由沈从文新婚后不得不忍受分别之苦,回乡省亲期间所写的信整理而成的。在爱情的驱动下,沈从文像写日记似的写下了一封封信,十分生动而优美地记下了途中的心情、风土人情,及风景。
如果没有一段意外的插曲,这爱情该多完满。责任完全在沈从文,在妻子生下第一个小孩时,他有了一段婚外情,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孩。他依然挚爱着他的“三三”(张兆和),但他天真地以为,妻子之外,他也可以同时爱其他的女孩,他以为两者并不冲突。可是,怎么可能?诗与现实总是难以调和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偶尔的“桃色”事件,却使他与他的“三三”纯真的感情,从此蒙上了阴影——神话般的爱情,于是也有了遗憾。
诗人卞之琳写过一首经典的诗《断章》,很短,只有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他爱上了一个不爱他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张家四小姐充和。爱了她一生一世,但可悲复可笑的是已远嫁美国多年,90岁的张充和却说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恋爱过。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怪卞之琳的太羞涩了,他没有沈从文把情书写满大半个中国的勇气,他的情书只敢写在心里,连写进诗里也那么隐隐约约,欲言又止。又如何不失败?他的爱情很美,却也令人倍感凄哀。
而说到爱情,当然还有徐志摩那惊世骇俗的爱情。他追求他的爱,义无反顾,轰轰烈烈。在爱的借口下,他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为他生儿育女、侍奉翁姑的女性;但他却也再三地备尝爱情的煎熬,遭遇爱情的戏弄。他的生命里有四个爱他或被他爱的女子,可是,事实上他一个都得不到。这是怎样悲哀的爱的悲剧!不过,他的伟大,或许在于在那一个还非常传统的时代,他敢于旗帜鲜明地亮出了爱情至上的旗帜,并飞蛾扑火,死而后已。
有两个男子,不不,应该是三个男子明确地表示爱一个女子,这应该是怎么风光旖旎的故事,可以让人产生更多的悬念与遐思。但在这里,一切都那么襟怀坦荡,月白风清,似乎在不可能中成了可能。他们都不是庸常的人,是令人景仰的人。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志同道合的爱情,徐志摩、金岳霖对林徽因柏拉图式的那份精神上的爱恋,其实都是历史的绝唱。
这份情感似乎向世人诠释了爱情的另一种可能,是在豁达心境下爱的牺牲与奉献。爱情或者不仅仅是自私与占有,有时超越了肉体,是精神上的相知和尊重,同样可以拥有天长地久的永恒。
而当我们看到了近90岁的周培源,对着已经80岁了、瘫痪在床的妻子,依然那么诚挚地说“我爱你”时,我们的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滚涌出来。
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文人,心事与爱情,也是如此另类,温情的、动人的。即使越轨,却也是充满了天真的孩子的情怀。
三
故纸堆里也并不都是隔膜的,有时也有惊心动魄的触动,有刺目的鲜活,那么苍凉或者让人内心酸疼,呈现的却是摧心裂肺的血淋淋。
先说一个故纸堆里惊现的故事,是关于陆侃如的,他是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齐名的另一位“五四”时期女作家冯沅君的丈夫。他们夫唱妇随,鹣鲽情深,令人羡慕。可是,这爱情的神话,却也终于经受不了岁月的沧桑,忽然就轰然坍塌。
张耀杰一篇文章为我们揭秘:1951年,陆侃如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与女下属有染,在打成右派后,这事终于被揭露了。同样的出轨,陆侃如与沈从文,好像并不一样,沈始终有孩子似的天真,仿佛更可原谅。而陆侃如,却因为身份与对象的关系,让我们多少有些以权谋私的感觉——是不是如此?好像已没有去澄清的必要了,事实总是事实。不过,相比之下,陆侃如的“桃色事件”,仿佛不可单纯地把它当成“桃色事件”看了,时代毕竟不同了,政治如一把钝刀深深地捅进文人的生活与情感里。请看冯沅君的反应吧,她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大半生与‘老虎’同衾共枕,竟无觉察,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丈夫出轨,妻子不痛心疾首,当然不可能的,只是这话可说得刀子般锐利,不但没有一点温情,却也已带着政治的痕迹了。后来,陆侃如以反动和生活腐化的罪名被关,他也已不像沈从文的只是受到道德的惩罚了。而冯沅君在给他的信中,却也很有些义正词严的味道:你想多做好事,这当然好,不过动力不应放在我身上。动力从哪里来?应该从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赎罪来。以后来信信封上不要写教授字样。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罪恶的标志。——字里行间更是只有政治,只有一种对时代的趋奉与迎合了。她的老同学苏雪林说她,他们兄妹都会扯顺风旗,从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可谓深知者也。冯沅君的兄长,乃文革间“梁效”中的冯友兰是也,据说抗战胜利时,此君也是鼓噪着为蒋介石献“九鼎”的重要角色之一。
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尤其急澜卷涌的政治旋涡里,文人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夫妇如此,师生也不例外。该知道沈从文和萧乾吧,没有沈从文的赏识,也就没有后来的萧乾。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临近解放时,郭沫若的一纸檄文,还把他们扯到一起,接受审判。可是,也是政治的原因,他们不但渐行渐远,最后竟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孰是孰非?其实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但有两个细节却耐人寻味,据说,反右时,沈从文揭露萧乾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后来,从干校归来,沈从文家分两处,生活十分不便,一回在路上相遇,萧乾好心地提出代他向有关方面反映。可是沈从文不领情,冷冷地抛下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政治,又是政治把师生多年的相濡以沫的温情生生切断,他们从此形同陌路。
同是沈从文,他与丁玲,还有丁玲牺牲了的丈夫胡也频,都曾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丁玲被捕时,他奔走营救,又受托千里送孤,友情多么感人。可是,又是政治的原因,他们的友谊破裂了。还有沈从文与范曾,他们后来的冷漠,都是由于政治,当范曾贴出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时,我想,沈从文会是欲哭无泪的。
在20世纪这个跌宕起伏的伟大时代,战乱、饥饿、侵略、革命,这些字眼构成了它的波澜壮阔,构成了它的风云激荡,在生与死中挣扎,肉体的摧残是残酷的,可是,对于不少知识分子而言,最可怕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斫丧。
一个刚强的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嗟来之食,如朱自清;可以站着死,如闻一多。而当义无再辱时,老舍、傅雷可以选择以死抗拒。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却也深感到了无奈与苦涩。
死有时更加容易,只有生才是痛苦的。即如最后不得不死的老舍,他是多么热爱生活,他的小院里种满了菊花,秋天他盛邀文朋诗友到家里赏菊吟诗。可是,这么热爱生活的人,却不断地被迫着在政治上表态,用狠毒的语言去批判昔日的好友。他被政治切成了双面人,在台上他义正词严,是批判者;在台下他却温情地向着被批判者传递他的关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但就是如此,他还是死了。
这些文人,他们爱着、恼着,悲哀和欢欣,都那么真切。生逢这个时代,艰难却也生气蓬勃,他们都有学识与才华,不少人都被后人推许为大师。他们活着,也挣扎着,或从容,或窘迫,总是有七情六欲,有缺点有不足的,可是他们很鲜活地活着,踏歌而行,从来就那么昂扬,却又呻吟于时代的压力下。俱往矣,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故事,却如韵如歌。
责任编辑"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