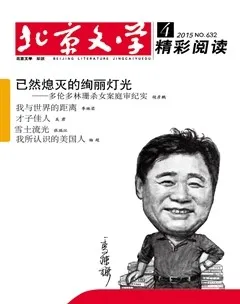守望的姿态
一
盛夏的阳光在灰瓦白墙上踱步,以我不曾察觉的方式;一如眼前这座陈慈黉大宅,惶惶然已经存在了百年,以前美村人几代人不曾察觉的方式。我更愿意相信,眼前所见是一片沉寂的门扉、天台、泥塑,早已没有主人的气息,后人也没有在这里迎过朝霞落阳,被族人尊崇的激情过度点燃,被无可预知的时代变换掏空,被遗忘的忧伤蚕食,永久地还给了天地。大宅的生命,那淋漓充沛的故土情怀,早已经一灯传遍千灯,在潮汕嵌瓷、西方石膏琉璃、泰国楠木、桑浦山的油麻石上凝结,用一个家族四代人的传承接力,换来一个族群在全世界的张扬,对血脉的信仰,留在每一块砖墙上。
沉静而沧桑,温柔而硬朗——建筑原本就该这样。百年之后,我们注定更加懂得潮人对故园的眷恋。
眷恋,在这个南粤一隅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故园:那两棵青绿色的伞状樟树直指天际;沿着湖面生长的柳树枝条在水面上晃晃悠悠度日子;灰色的城市图景,主角是家门前延绵深幽的小巷,前景是一片黄得泛黑的矮墙,顶上是一片蓝而又蓝的狭长的天空,和一团滚滚的硫黄般柠檬黄色的火球……不敢再往下细想,相隔了才11年的故乡,仿佛已经在前世的时空。或许,一个人离开了家乡到本来不相干的地方去了,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土地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了。
建筑像是一个人的记忆,生长在这片土地,允许遗忘,却不会欺瞒。这座房子里不曾有过陈氏家族真正的繁衍生息,却有着切切实实的呕心沥血。我以主人的心思,在各个房间细细查看、揣摩。
像一座迷宫,在这栋古老的大宅里穿来穿去,一个一个房间只有我一人,我被控制在一个凝固的时空,令人敬畏的封存。然而,时间突然流动起来,陈慈黉在我眼前晃了一下,又转身而去,我看到背后走来一个与他眉眼相近、短小精悍的小伙子——他的父亲陈焕荣,黉利家族的奠基人——一个陈家不敢忘记的人。
陈焕荣又名陈宣衣,陈宣衣给人最初的印象不过是一个丢在茫茫人海中不被人注意的潮汕小伙子:个头不高,从小丧父,母亲孀居,生活困顿。像当今从大山里、贫困地区来到城市的打工仔一样,15岁的陈宣衣不甘心在乡里过一辈子,经亲戚介绍到樟林港口打工,随“红头船”南来北往。这一年的6月,英军舰船抵达珠江口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爆发。我无从知晓,陈宣衣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还是历经战火之后离开了汕头,可以肯定的是,从澄海前美村到樟林港十几里路上,他不是孤单一人。
下南洋,是潮汕人迁徙之路的延续。晋唐时期从中原开始南迁的潮汕人,手里没有一张地图,也不用罗盘指引,历经艰辛来到海边的平原沃土上,大海并没有令他们止步。1684年清康熙帝开放海禁后,如潮水般涌来的贸易机会,让沿海的潮汕人看到了机遇,纷纷下南洋讨生活、做贸易。为与其他省份船舶区别,广东的潮汕渔船及商船将船头油刷成朱红色,俗称“红头船”。
陈宣衣出发的樟林港,自明清以来就是“通洋总汇”的粤东第一大港,是万千潮汕人出海的起点。澄海历来有“岭东门户、潮郡襟喉”之称,澄海人去暹罗就像我们今天从江西南下广东一样自然。前美村家家户户都有年轻的小伙子跟着叔伯长辈,前仆后继,接力赛一样,踏上这条熟悉的出海路。
家在背后,世界在前面。离乡背井出海前,每个前美乡人所看到的景象都莫不如此吧。
二
旧日的黑白相片里的沉郁契阔,那种辽远的茫然和体面,要不是对大时代下陈家大宅命运的好奇,可能我很快就忽略了墙上的族谱和照片,毕竟100多年的时空,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太过久远,更何况岭南大地上的一个潮汕家族的故事跟我没有任何干系。可是,为什么站在大宅的庭院,看着墙上陈慈黉的画像、陈家族谱,听着前美村讲解员的讲解,我感到时空在轮转?
1910年,一个朝代摇摇欲坠,辛亥革命即将爆发,一个动荡的时代步入躁动的前夜。是什么样的力量让陈慈黉以打造百年基业的心志,为次子陈立梅建造宅第,并一早就取好了饱蘸荣耀名字的“郎中第”?同样是华侨子弟,闽粤的海外华人子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见多识广的陈慈黉为何安顺守命地相信故土的安稳可以脱离国家命运?家业的兴盛足以令他胸怀壮志,期望凭借一己之力守护故土永固?精明的潮汕生意人怎么会对这个时代如此不敏感?大宅的建造一发不可收拾,一建就是30多年,这恰恰是中国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潮汕人眼里永远只有生意吗?
大时代下的个体总是渺小得如一粒沙,没有表情、面目模糊。任何历史书也不会讲述这样的潮汕故事。从前的气息,像阳光密集而直接地落满了外墙,可惜都是幻境。大宅经年累月处于建设、推翻、重建的过程当中,陈家几乎没有在这座宅子里住上一天。也许,陈慈黉对于生命的延续不止寄望于子孙血脉,还有与这方土地共存的大宅,这可是他的气息与精神长存的隐秘空间。空间的再造,时光的凝固,保持某种姿态屹立,表达着建造者穿透时空的雄心。陈慈黉成功地将他的渴望清晰地留存在天地间。
陈宅的布局最能体现陈慈黉的雄心。除了“三庐书斋”外,“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都采用传统的“四点金”“驷马拖车”,与北京故宫为代表的帝王宫室结构有众多相似之处。
形体最为高大端庄、装饰最为豪华气派的中堂是陈宅的主体和建筑中心,堪比故宫的太和殿。围绕着它按尊卑顺序依次在左右展开的厅堂,以及附带的包屋或从厝,可以被视为故宫的东西宫。四角设“更楼”,便利守护人员来回巡视和保卫,与故宫的角楼何其相似。外面还挖有池塘和环绕的沟渠,俨如故宫的护城河;前面有宽阔的阳埕,不妨想象为微缩版的天安门广场;内花巷为平房,外花巷为二层楼房,内低外高,错落有致,形成方寨格局,俨然是“方者中矩”之姿态;四周由骑楼、连廊相接,有的屋脊还用方砖铺成人行天道,营造了扑朔迷离的深宫景象。若干个小院落由之衍生出来,大院套小院,小屋连大屋,颇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气象……
一个中轴对称、等级森严、向心围合的建筑,其富丽堂皇恐怕与潮汕人这个迁徙民系的文化大有关系。民间历来把建房当作砌皇宫,其精工细作的审美趣味无不让人想起远古贵族的遗风,给人留下这个民系来历的遐想。一座宫廷式的古典建筑在南方大地上出现,既有衣锦还乡的强大心愿,其中也透出了遥远贵族生活的历史信息。能够将这样的心念与趣味坚持千年,几乎成为一种集体基因,潮汕人有一种外人难以理喻的心性。
站在二楼眺望,错综复杂的连廊被碧绿的爬藤植物覆盖,好像焕然一新,时代和时间被抹去,老旧的砖瓦里,透出光亮。陈家好像就在眼前了,可就是看不清楚,只有大宅是真实的,自命不凡又安逸松弛。前者流传在无数潮汕人心中,后者掩映在苍茫岁月里。在潮汕土生土长的同事,竟然也是第一次拜访陈家大宅,虽然她家距离前美村仅十几公里。这座南方私家宫殿,像被遗忘的瓷器一样,甘愿披上岁月的尘土,收起满身的光华,安守在平原的深处。
三
“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这活脱脱就是为陈宣衣写的生平。
保留了当年做舵工的习惯,陈宣衣总是会凝望大海,维港无穷尽的远方是他目光所聚之处,他并不在意眼前的船来船往。他的面庞、表情、身形,对于黉利家族的后人来说都已经模糊不清,更何况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陈宣衣这个名字不如“陈慈黉之父”“黉利家族奠基人”来得具体和重要,后两者是他留于后世的坐标。生命消亡与传承相生相伴,但决不可以为仅凭血脉、族谱或是回忆录就能够令记忆不会模糊甚至错位。只有不甘于向命运妥协、将生命从荒凉走向兴盛的举动,才呈现了某种意义的永恒。
出海后第三年,陈宣衣的长子陈慈黉出生。1865年为清同治四年,打拼15年的陈宣衣回乡开始造屋工程,建了“通奉第”又造“仁寿里”。由此开创了黉利家族这漫长而精致的造屋过程。
一个家族,一百多年建造一座自己的屋子,多么简单的心愿,多么质朴的情怀。何况潮汕人几百年的迁徙路途上,每个日夜都有着安定下来拥有一方属于自己天地的渴望。披星戴月赶着路的男人女人,他们的血脉骨肉在脚掌生茧的磨砺中长大。守住一方土地的渴望,犹如一颗种子,悄无声息地卷入大地,伴着晨风雨露,伺机发芽。
19世纪的最后几年,陈慈黉下决心回到家乡,创建新乡。他将新加坡的企业陈生利行变卖,将卖得的银元装了无数箩筐和麻袋,由蒸汽轮船运回来。这是一个全乡欢庆的大日子,村里十几个精壮劳力敲锣打鼓将招牌和银元抬回村里,拆股分银。银元堆成一个个小山,数不过来,只好用斗量。这是陈慈黉衣锦还乡的开始,他有着更大的人生宏愿,在生长的土地建起梦想中的大宅,荫庇后人流芳千古。
我看到的陈宅,包括了“老向东”(郎中第)、“新向东”(善居室)、“新向南”(寿康里)及“三庐书斋”。506间房间,占地25400平方米,可谓前所未有一组规模宏大的南方民居建筑群落。在造屋的过程中,时间变得重要起来。“郎中第”历时11年,“寿康里”与“三庐”书斋历时9年。最后一座大宅“善居室”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动工,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因战争原因被迫中止。
生命的传承与消亡也在同时进行。似乎是完成了心愿,抑或是看到后继有人,“郎中第”建成后翌年,陈慈黉病逝,次子陈立梅成为家族新的掌门人。这时的黉利家族已经号称潮汕华侨首富。陈立梅在投资房地产、创办黉利货栈汇兑钱庄的同时,又着手营建“寿康里”及“三庐”。与父同命,他同样是在豪宅落成后病故。1930年,陈立梅次子陈守明挑起家族事业重担,开始着手兴建由他祖父、父亲计划,却来不及动工的“善居室”。这是故居中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座,也是历时最长、经历最坎坷的一座。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开进村里,工程被迫停下……陈宣衣的心愿,栖身于家族的营垒,在时空撒播,陈家家业和子孙如我眼前荷塘里的荷叶一样,生气十足地生长于世上。
在这片华宅里,还缱绻着一个女人忠贞的爱情及倔强的守望。李彦芝,饶平县县长的女儿,在二八年华嫁给慈黉爷的幼子陈立桐,也算门当户对。孰料陈立桐20多岁就因病去世,留下年轻的女子独自面对漫漫人生。李彦芝是一个倔强的女子,不肯在夫家表现出一点可怜。“善居室”原本就是慈黉爷为幼子所建,立桐去世后,由李彦芝监工完成。
我在想,与其说“善居室”是李彦芝对先夫的凭念和相思,夫妻之间的忠诚与爱,一诺千金的信守;不如说是一个女人在男尊女卑的大家族中坚守的据点和堡垒,在陈家族群中地位的象征。一边是枪炮轰鸣,王朝崩塌,另一边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安静的精雕细琢,中原的硝烟战火太过飘摇,眼前这块土地上的一寸寸拔地而起的楼宇,是她可以看得见、守得住的指望。
除保留“驷马拖车”式建筑格局,李彦芝又在潮汕式平房上增加了南北书斋楼和亭台阁楼、双后包点缀,并有大量西式阳台、拱门、圆窗。即便是群宅中最为宏大、壮观的一栋,李彦芝仍不满意,多次责令拆除再建,以致延误工期。日军占领汕头,村民闻风逃走,陈家逃到香港,几十年没有再回来,留下未完工的“善居室”——油漆未干的门窗,手工精致的石雕,深深庭院里的那塘月色,满室的贵重家具、名人字画。 李彦芝不是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她聪慧、坚强、果决,却无法预料到自己再也不能够回来。任何人力的坚守都敌不过大时代的动荡。
前美村的人,陈家的人,都在一场战火中飘散了。村里的人陆续回来了,陈家的人,越走越远了。没有谁再关心新乡的房子。没有谁敦促工匠复工,建造和斗技已经结束;院子不用再扫,窗子不再需要晨昏开合,尘土不再飘起,树叶自顾落下。
90多岁,李彦芝在香港去世。传说,她死的时候双眼未合。
四
光阴一晃几十年。再走进深宅,门厅紧挨着门厅,过道连接着过道,房间多得像春天返潮时窗玻璃上漾满的水汽。我一间一间房走进去,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纷繁琐细的瓷砖装饰,从地面到门窗、回廊,华美张扬,各个不同。
陈宅的光彩藏在里面,无处不在的中式和西式的装饰风格,让我错乱了时空,以为错入了殿堂。目力所及,东西方符号交错辉映,神奇地碰撞:廊柱柱式是古希腊多立克柱式与爱奥尼亚柱式的综合体,爱奥尼亚柱式的立柱仿若有卫城胜利女神神庙的精巧、纤细、柔美;门匾上典雅的潮汕木雕与支柱上巴洛克式的花柱头相互交融;圆形和拱形的西式门窗与方形的中国式门窗相得益彰;门廊、窗套上的装饰花纹既有潮式的花鸟图案与寓意,又有西式的几何图形与意念;抬眼看到用泰国楠木精雕细琢的楹梁、门窗,低头望见本地桑浦山油麻石磨制的石阶、石柱、石碑雕刻;密集工整的几何式拼图与传统寿桃、祥云同廊争辉;中式的通廊石柱梁上干脆刻上英文字母“ABC”,直接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接纳。
真正让我恍入幻境的是地面上无处不在的由釉面砖拼成的几何图形,还有门厅墙上细小的马赛克,都有暹罗的影子。马赛克上笔直的阳光条和太阳的装饰,有装饰艺术的现代主义趣味,我看到的是一条从暹罗到潮汕的漫长航线:泰国乃至欧洲的建筑材料如何漂洋过海运到香港,再到潮汕的乡间,进入前美的土地?这需要怎样的一种决心。
为了把建筑材料在数十年时间里源源不断供给,一条人工河流开挖了。从南溪码头到前美乡,陈宣衣曾经走过的平原上,沿着已经有的小溪流,开拓出了一条十几公里长的河道。多少人重复着同一个挖掘的动作,多少人肩挑背扛,挑出淤泥,艰难推进。数十万根暹罗楠木、大量沙土石头、水泥、瓷砖、马赛克,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材料从红头船上卸下,装上小船,一趟一趟靠上前美村的码头。
潮汕百公里内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他们是施工队,也是设计师,对于潮汕建筑的结构和技艺烂熟于心,是最精湛的民间工艺师。不被东家催工期,不用吝惜珍贵的材料,每日围谷笪(潮汕一带流行的由竹篾编织而成的晒谷器具)斗技,如果能够忘却外面改朝换代的动荡,这是一段多么好的日子。工匠在谷笪内精雕细琢,等到工程完成了才掀开围蔽,请主人过目。每次围谷笪斗技其实是陈宅气氛最为紧张又欢快的时候。就像任何美好事物的孕育自有其神秘之美,怎样等待都不过分。长则数月,短则几日,工匠们互不干扰,互不模仿,主人家提供好茶好烟享用。工匠斗的不仅是手艺,还有耐心、眼界和心气;技高一筹者得到的不仅是赏赐,还有荣耀乡里的名誉。
“郎中第”是慈黉爷主持建造的第一座宅子。此时的陈慈黉已经富甲一方,并没有荣耀乡里的急迫心情,他打算用余生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千秋基业。他懂得,此时慢一分,就为子孙的家业夯实一分基础。仅“郎中第”就反复三次推倒重建,经历十年方建成。所以,工匠们往往是师徒、父子几代人为陈宅挥洒汗水,也赚到了丰厚的银元。慈黉爷经常来了解工程进度,如果见到工匠干活太过卖力赶工,他就会找来工头,给工匠发了工钱,让他“理完家事再来做工”;见到挑沙土的农民,为了赶路将沙土撒在路上,他也要上前劝告:“慢慢来,别一次挑太多。”如此多次反复,工匠们很快摸清楚了主人家的脾性,“儒气”切要过“拼性”——做得精细比干得卖力更重要。
大火轮运来的数万根暹罗楠木原木打进了宅基地,沙土石头将地基一层层填高。新乡宅基地原是一片水洼田,陈慈黉嫌地基软、地势低,为了把地基夯实,填进了原木。直到第三次,陈氏族老不得不提醒慈黉爷:自古起厝,都要遵循前低后高的原则,更何况后面是旧村老宅,宗祠所在,如果陈家宅第高于宗祠便是大不敬。慈黉爷这才打住填土,动工建屋。可是,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地基仍然差了分寸。有人动了歪脑筋:反正陈慈黉家不差钱,推倒几次,这些废土不就将地基填高了吗?房屋推倒重来是否与此有关呢?可以想象得到陈慈黉的富有。这是红头船的奇迹,是一个迁徙的民系不停息的脚步带来的红利。
岭南大都是中原移民,他们长途迁徙,于岭南拓荒、垦殖,又闯荡海外。一旦发达了,都不约而同返乡砌屋。安土重迁的观念深入骨髓。在陈慈黉返乡造屋的壮举之后,600公里之外的开平、台山,也成了一个大工地,数千座中西合璧的碉楼在这片侨乡纷纷耸立,富有者像立园的主人谢维立,也曾为建造私家花园而开凿人工河道,他的建筑材料来自遥远的欧洲。开平碉楼,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欧洲中世纪拜占庭、哥特式建筑,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建筑,无所不用,它是一个万国建筑博览会。
陈宣衣和谢维立的人生宏愿如出一辙。慈黉爷更有穿透时空的眼光,陈宅无论从中西建筑的融合,造型的精美、讲究,其规模、内涵、审美趣味,都要比后建的立园更具建筑艺术之美。这与潮汕文化传统不无关系。陈宅从自己本土的建筑出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建筑!可惜,它默默无闻隐藏在澄海一角,百年了也不为世人所知。
兴建陈宅的同时,陈慈黉在汕头商埠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建筑计划在实施。就像中国历朝历代大家族的发迹,与土地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骨子里有着强烈农耕意识的潮汕人,对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从陈宣衣时代开始,陈家从未停止过为家族储备土地。陈家于光绪十八年就在汕头商埠购置房产。从1898~1928年的30年间,黉利家族在汕头购置了大量的土地,为后来广建楼群作了充分的土地储备。
时逢粤系军阀陈济棠主政广东,主张兴办实业,鼓励华侨投资,黉利家族大手笔投资500万银元,在汕头商埠的永兴街、永泰街、永和街、永安街、升平路、商平路、海平路、福合埕和中山公园前一带大兴土木,400多座骑楼式和洋式建筑住宅楼建起来了。
一座陈宅能够在前美村的土地上出现,不仅仅是凭着陈慈黉经世传家的心愿就可以完成的,它依托的是兴建数百座商骑楼的设计、施工人员,还有建设所需的大量进口材料。这些人必定接受了西洋建筑文化的教育,成为建造西洋建筑经验丰富的工匠和建筑师。陈家以一支商业大椽,为自己的家宅描画下了最绚烂的一笔。
资本的力量是惊人的,它可以打破时空、朝代的变迁,至今影响着汕头的城市面目。陈家的举动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宗亲及潮汕的海外华侨,他们纷纷回到家乡建起一座座大宅,一幢连着一幢,鳞次栉比——一个崭新的市镇拔地而起。
五
同事自顾坐下,熟练地泡起了主人家的功夫茶,说着家常。我在陌生的语言中自我猜想,念想着属于我的赣方言,然后等待他们把聊天的内容翻译给我听。
月光下的陈慈黉故居,在银灰色中呈现出原初的样子——树还是那样的高,似乎陈家人离开后就再也没有生长过。四处黑压压的一片静谧,好像一场梦,看见自己生活多年的老街道,泊在月色里。灯火从窗口透出、闪烁,瞬间消失。随着缺憾和远行的一次次累积,这个遥远的印记总是在我不经意间出现。
我的心随之安静,并静静享受着这样的情绪。倾听更加从容。柴米油盐也罢,百年沧桑也好,眼前主人家的好茶和一室融洽,才是这座大宅最真切的时空。
在潮汕的几天,在一家家精致的茶台前,我着迷于主人家一次次纳茶、淋罐、烫杯、洒茶的动作。手起手落,潮汕人雅致的生活情趣和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尽显无遗。
终于要离开了,却有着莫名的眷恋。我来到潮安县与澄海县交界的婆姐岭,寻找慈黉陈公陵墓。当地去年才来过的人,也几次错过了岔路口。南方旺盛的草木让大地一季就面目全非。我不禁感慨南方阳光、雨水和生命的猛烈。
在古埃及人看来,住宅不过是人暂时的居所,而坟墓才是人永恒的宅邸。与新乡连绵的华府相比,这里不被打扰,适合驻足、待立、流连、冥想……墓地失去了时间,反而有了生命永恒的质感。我想象着,一百年来,散落各地的陈氏族人相约到这里拜祭,他们口音不同、语言各异,甚至素未谋面。而在他们的血脉深处有着相通的基因密码,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编纂出一个陈氏族群的世界地图——它凸显出了潮汕民系一个小小根须的脉络。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