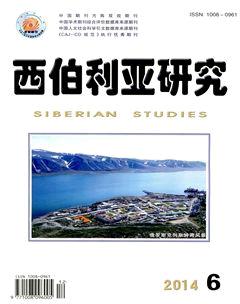中国语境中的索尔仁尼琴形象
赵海霞 许传华
摘要:在中国,索尔仁尼琴的形象经历了由负面到正、负两面并存的重大转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外,更重要的是源于他的意识形态观和文学理念。他的政治言论、创作中的政治意识以及他所倡导的人性价值和道德诉求等对其形象的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索尔仁尼琴;中国;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6-0061-05
索尔仁尼琴(1918-2008)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70年),对俄罗斯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创作的“劳改营文学”,诸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59)、《第一圈》(1955-1958)、《古拉格群岛》(1973)等,突破了文学和思想的禁区,大胆描写其时无人敢涉足的“古拉格”,发掘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内容。不仅如此,其艺术创作手法及技巧也备受推崇,获得诸多学者的认可与赞誉。萨哈罗夫(CaxapoB A.)指出:“索尔仁尼琴无疑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之一。他的作品通过戏剧性的冲突、鲜明的形象、独特的语言表现了一位历经艰辛的作家对重大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立场。”美国学者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也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不是政客,不是将军。他是一个艺术家。索尔仁尼琴的艺术阐明了真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艺术是颠覆性的:颠覆了历史,颠覆了错觉,颠覆了弥天大谎。”
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家,不折不扣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时期,他公开发表《致苏维埃领袖的信》(1974),阐释了俄罗斯发展的困境,表达了对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解体之后,他又发表《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倾塌中的俄罗斯》(1998),对俄罗斯的历史、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一一阐释,显示出对俄联邦的忧虑。在与俄联邦前总统叶利钦对话时,他说:“我不能掩饰自己的痛心,这儿不时发生丑闻、抵制、示威性离职的活剧或是耗费精力的程序上的争论。”
值得一提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从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面世之后,他就备受指责,尤其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及俄罗斯命运的言论,更是受到指责和批判。苏联诗人西帕乔夫(1899-1980)于1974年2月20日在《文学报》上撰文《文学弗拉索夫分子的终结》,将索尔仁尼琴定义为“苏联的诽谤者、叛徒”;以“劳改营”为写作题材的沙拉莫夫(1907-1982)也对其不满,认为“索尔仁尼琴的行为是一种投机的行为,目的是依靠挑衅获得个人成功。”
由此看来,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艺术家的索尔仁尼琴,另一个是作为思想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种形象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构建了一个复杂且矛盾的索尔仁尼琴形象。那么,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他又呈现出何种形象呢?
一、改革开放之前:鲜为人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于1962年在文学杂志《新世界》上发表第一篇“劳改营”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年发表《柯切托夫卡车站的一件小事》、《玛特廖娜的家》以及《为了事业的利益》,之后便蜚声世界,许多国家争相翻译索氏的作品。中国文学界也分别于1963年和1964年翻译出版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斯人译,作家出版社)和《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索尔仁尼津即索尔仁尼琴,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
但是,随着索尔仁尼琴与苏联官方矛盾的加剧,尤其在苏联政府颁布《关于从图书馆和图书销售机构撤销索尔仁尼琴作品》(1974年)的法令之后,《新世界》杂志1962年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年第1期(刊载《玛特廖娜的家》和《柯切托夫卡车站的一件小事》)、1963年第7期(刊载《为了事业的利益》)、1966年第1期(刊载《扎哈尔·卡利塔》)以及索氏作品单行本都遭到封杀和毁灭,而此时他的作品在苏联本土已经禁止出版。为了捍卫自己的出版权益,他将作品运往境外出版:1968年,他的小说《第一圈》(美国《Harper&Row》出版社)出版;同年,《癌病房》在法兰克福(《I-loceB》出版社)和伦敦(《The Bodley Head》出版社)同时出版;1971年,法国巴黎“YMCA-PRESS”出版社出版索氏的作品《1914年8月》,1973-1976年出版索氏的《古拉格群岛》一书,1975年出版《列宁在苏黎世》等。同时,关于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广泛展开,内容涉及其政治思想、历史观点以及作品批评。诚如美国学者艾瑞克森(E.E.Erieson,Jr.)所言:“在1974年索尔仁尼琴遭到苏联政府驱逐出境之后,西方以极大的热忱欢迎他,将他看作英雄。”
与之相反,此段时间在中国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译介、出版和研究一直处于萧条之中,没有相关作品的翻译,亦没有对索氏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说,在西方对索氏及其作品译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文艺学界对索尔仁尼琴的反应是冷谈的,甚或是漠不关心的。
导致索尔仁尼琴译介及研究滞后的原因,除了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文化大革命)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索氏作品本身的特点。第一,其作品主题单一、沉闷,主要描写他所经历的古拉格。诚如陈建华教授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史论》中所总结的那样:“由于索氏作品大多卷帙浩繁,且多为令人压抑的劳改营题材,使不少读者望而却步,这就造成了在中国谈论索氏作品的人不少、真正理解和研究索氏作品的人不多的尴尬局面。”第二,索氏的作品铺陈广泛,人物众多,少有跌宕起伏的文学情节。其史诗性著作《红轮》涉及人物多达几百个,却没有—个典型人物,这种历史性的大篇幅、多声部、多话语的书写造成读者阅读方面的困难。第三,其作品大多书写真实的历史现象,近似于历史式的平铺直叙。例如,《古拉格群岛》副标题为“文艺性调查初探”,作者宣称:“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另外,在叙述手法上,索氏大多采用“小时间、大空间”的布局,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叙述发生的事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将时间限定在一天之内,描写了整个劳改营一天的活动,从起床写到梦乡。在《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仅用四天的时间描述了一群人物的命运,上至高官、下至劳改犯。这种话语时间大大长于故事时间的叙述方式影响了其时对索氏作品的接受。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索尔仁尼琴在中国的形象是负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意识形态观,源于他对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的否定立场。1973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他批评苏联政府的大国主义和世界主义行为,敲击苏维埃政府的专制与专横,他写道:“难以忍受的不是专制主义本身,而是强制的经常散布的意识形态的谎言。不能忍受的不仅是专制主义,而是专横和目无法制。”他还批评苏联政府没有考虑民族利益,只顾破坏世界帝国主义和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活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准确地奉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在被驱逐出境之后,他对苏联政府及社会主义的批评更加肆无忌惮,1975年6月30日,他应美国劳联一产联(AFL-CIO)的邀请在华盛顿发表演讲,谈及苏联和社会主义时,他说:“任何事情都是按照党要求的方式来做的……这是一种没有独立媒体的体制,没有独立司法的体制;这里,人们既不能影响外部政策,也不能影响内部政策;这里,任何不同于国家的思想都受到排挤。”因此,他拒绝使用“苏联”一词,认为“俄罗斯”应当与“苏联”区分开来,1976年3月1日,在应BBC“全景”节目采访时,他特别强调:“在我使用‘俄罗斯时,我通常将它与‘苏联一词区分开来。”在《牛犊顶橡树》中,他重申:“作为一个苏联人是耻辱!这几个字是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得出的全部结论,是我整个50年来的结论。”所以说,对苏联尤其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与攻击是导致索尔仁尼琴在中国形象不佳的重要原因。
但是,直接导致索尔仁尼琴形象在中国低下的原因更在于他的“中国威胁论”一说。他认为,由于中国和苏联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国必将是苏联潜在的敌人,中苏军事争端在所难免。不仅如此,他还批评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对西伯利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阐释说:“10亿人口的中国对至今尚未开发的西伯利亚的强大压力,并不是旧条约中所争论的那一小块地区,而是整个西伯利亚……随着这块土地上的移民人口的增加,这种压力也就更加增大。”对中国的直接批评和错误言说直接导致中国学界的反感与敌视。因此,早期翻译出版的作品都是以内部参考的形式发表的,其目的并不纯是为了获得索尔仁尼琴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而是为了审视或发掘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弊端。这是索尔仁尼琴形象在中国走低的重要原因。
二、改革开放之后:回归本位的索尔4-尼琴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公开出版发行了《癌病房》(1980年)、《古拉格群岛》(1981年)。中国台湾也分别出版了《癌症病房》(即《癌病房》,1981年)和《第一层地狱》(即《第一圈》,1982年)。截至目前,索尔仁尼琴的《牛犊顶橡树》、《古拉格群岛》、《红轮》(第一部、第二部)等代表作都被译成中文。与其同步,对索氏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取得长足进展,国内学者分别就索氏及其作品的道德力量、宗教体悟、审美经验、政治诉求、历史意识、民族观念以及国家认同等问题进行了解读。就研究成果来看,索尔仁尼琴的形象由之前的完全丑化、否定转变为否定与肯定并行。
否定者觉得,索氏由于长年的古拉格生活,使其创作思想和心理扭曲,产生报复行为,无视、捏造事实,“愈来愈把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使得政论的因素大大增加,有的作品完全成为反共的宣传品……毁了自己的艺术才能”。这里,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误解、误读始终是他在中国产生负面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1980年,他为中国台湾出版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一个可怕的、不人道的、神秘的国家。”1982年,在访问台湾时,他又利用两岸“政治意识”的差异,大放厥词,大肆攻击中国大陆。如此种种,使得索氏负面形象有增无减。
然而此时,也出现了一批对索尔仁尼琴创作的肯定者,他们抛弃索氏的负面形象不论,转而关注其文本的艺术价值,客观而中肯地解读了索氏及其写作。他们认为,索氏作品的真实性、典型化,其创作技巧的时空超浓缩性、“非英雄化”处理、复调性,以及其创作思想中呈现出的人性回归、道德诉求、政治隐喻等,都说明“索氏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也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精华,又融汇了现代派文学技巧,形成了自己深沉、凝重、悲怆、冷峻的独特风格”。这种境况的改变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多元化、开放性文化氛围使得学者有可能理性、客观地对索氏进行一番整体架构与画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而真实的形象。研究者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范畴,将索氏的创作看作一种精神存在,是对政治的文学书写,是对人性回归原点的阐释性解读。这种回归文本创作的解读方式对于索尔仁尼琴摆脱政治的局限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建华教授的《新政治小说的新意识与新叙事——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短篇小说创作论》将索氏的90年代短篇小说定义为“新政治小说”,通过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人性形态透视”和“文化形态透视”探讨了作者的新叙事样式。还有诸如刘文飞的《“俄罗斯问题”:索尔仁尼琴“政论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主义》、刘亚丁的《(癌病房):传统与现实的对话》、胡学星的《现场解说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温玉霞的《聚焦:一天、一院、一事——索尔仁尼琴小说赏析》等都是通过文本解读索氏创作思想、创作主题及创作意境的客观解读。
不管是从政治意识、社会历史方面来解读索氏的创作,还是从文学形象、文学功能、审美体验等来阐释索氏的文本,所解析的史料、创作内容都是同样的。分析者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主要缘于索氏创作中的政治意识和文学理念。
索氏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诚如他自己所言:“我的积极性让我不可能心平气和无动于衷地去看待社会的无序、社会的不义和经济的失调现象,去观看一些厚颜无耻,但无人批驳的观点蔓延和有人对当代历史的错误阐释……这一切一种无可遏止的力量促使我去积极地干预政治生活。”其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由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需要而特批刊行,此后其著作大都被禁止在国内出版,这“首先是因为它的政治性,而不是它的艺术性”。为此,他多次将作品偷运到国外公开发表,此事成为他与苏联当局闹僵的导火索,结果是他于1974年被驱逐出境。但即使是在西方,他也始终被政治问题缠绕着,尤其对西方的法律、民主等问题不满,多次撰文批评西方,认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惨重的削弱,远远不是无可争议的苏联坚强的外交政策取得成功所致,而主要是其文化和世界观体系在历史、心理和道德上的危机所致”。对此,P.A.梅德韦杰夫解释说:“西方的政治,西方的媒体,西方的一切文明,西方人,被认为‘忘记上帝,已经二三百年没有走过正确的道路;所有这些都加剧了西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对索尔仁尼琴的失望。”这种左右开弓、两边不满的“异见者”难以与政治摆脱干系,也不可能博得所有人的认可与正面评价。
由此,索氏的大多创作都与政治或政治映射有关。例如,他的《第一圈》等“劳改营”系列文学和政治隐喻小说《癌症楼》等都是关于其时社会历史的政治书写。但在创作理念上,他坚持写真实,用形象再造历史,从人性、道德的视野书写历史,认为“艺术家不能给自己设置政治目标,或改变政治制度的目标,只能将它作为一种副产品,但反对不真实和谎言,反对杜撰,反对于人类有害的意识形态,争取我们的记忆,争取记忆事情的本相——这些是艺术家的任务。……我坐下来写作时,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再创造发生过的一切”。这里,他运用历史意识,廓清纷繁芜杂的世俗世界中的文化价值取向,发掘现实世界的本质,揭示人之生存、人性价值的意义所在。索氏的这种以人性、道德为基点的创作获得了学界的肯定,博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索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形象的两面性大都因为他的政治异见和文学道义之故,是他创作中所不可避免的矛盾所致。正如任光宣教授所言:“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人们对索尔仁尼琴及其创作的各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论述和评价,这是不同思想的表现和反映,也是索尔仁尼琴的矛盾创作个性使然。”
三、索尔仁尼琴卒后:余热未尽
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仙逝。这于俄、于世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2009年,为了研究与发掘索氏的文学思想和艺术价值,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呼吁说:“他的很多有关强国与发展民主自由的思想是现实的,具有永恒的意义,其文学和哲学巨著需要全面深刻的研究。”在此背景下,不仅学界纷纷转向索氏及其作品研究,而且各地也发起各种纪念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俄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资助的索尔仁尼琴专题网站建成、索尔仁尼琴坐像在别尔哥罗德建成、美国佛蒙特州建立索尔仁尼琴博物馆、莫斯科也将建立以索氏命名的索尔仁尼琴中心。
在中国,索氏研究也突飞猛进,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索氏主题研究论文1985-2007年22年间总共有69篇,但自2008年至今5年的时间,索氏主题研究论文计有128篇。近5年间,索氏主题研究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突破,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扩展。前22年间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索氏创作的译介、政治身份的认定等,因而其形象鲜以正面示人;其后的5年内,索氏的身份认同、其创作与特征、作品中蕴含的价值等均得到重视,并开始进行深入解读与发现,索氏的形象改观良多。
索氏研究正在进行中,余热未尽,相信未来的研究成果将更加丰硕。
[责任编辑: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