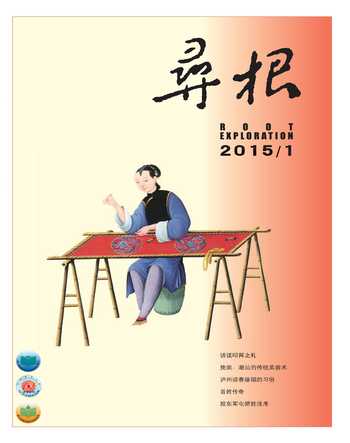太行山文书中“刘二姐现象”
李延军
“刘二姐现象”的提出
2013年11月,邯郸学院入藏了一批主要来源于晋冀豫交界地区太行山区的民间文献,时间上自明代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12大箱10万件左右,是研究这一时期太行山地区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批文献被定名为“太行山文书”。笔者在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发现不少有关“刘二姐拴娃娃”同题材的、不同时期地方小戏或曲艺唱本,代表性版本有光绪十二年兴文阁版弦子腔《刘二姐上庙》、民国初期北京打磨厂学古堂版《刘二姐拴娃娃》及中华印刷局版滑稽大鼓《刘二姐拴娃娃》等。这些唱本的主角均为同一个人物——美丽风流的“刘二姐”,叙述的也均为同一个故事——婚后不育到庙里“拴娃娃”。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相同,但其所反映的历史背景、市井百态,均随时代和地域不同而改变着。如此众多的唱本均同时指向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事件,极具历史文化典型性与研究价值。 单从这几个典型版本的“刘二姐”成书或流行年代看,这一现象从道光到民国至少一百年时间里,一直流行于中国市井坊间。刘红林在《长三角地区曲艺的历史沿革》一文中介绍弹词历史时,提及“明代中叶以后,一般称作弹词,留有传本《雷峰塔》《刘二姐》两种。”由此推断,“刘二姐”这一形象至少在明朝中叶,就已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弹词唱本中。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除上述几个典型唱本外,还发现不少其他艺术类型或传播方式的“刘二姐”,广泛流行于市井坊间或相关文献记载当中。如晚清民初风靡于天津的各种曲艺形式的“刘二姐拴娃娃”,清末杨柳青版画中有“刘二姐拴娃娃”,成书于1922年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了不少各地拴娃娃风俗。如今的河南坠子、曲剧仍有传统保留剧目《拴娃娃》。可见,“刘二姐拴娃娃”这一现象的历史跨度,从明代中叶至今至少已约有五百年之久,具有典型的历史悠久性。
仅从现有资料反映的地域分布看,“刘二姐拴娃娃”现象广泛存在于江浙长三角地区,北京,天津,安徽寿春,河南淮阳、安阳,河北张家口、邢台、邯郸,山东泰安、聊城等地,各地艺术表现形式有弹词、天津时调、京韵大鼓、单弦、北京琴书、山东梆子、河南坠子、河南曲剧、河北梆子、邢台弦子腔、邯郸鸡泽弦子腔等。北京琴书单以表演“刘二姐拴娃娃”而出名的演员就有翟青山、吴长宝、关学曾等。在戏剧界有一副流行很广的对联叫“刘二姐逛庙,杨五郎出家”。
这一现象与秦汉时期把赵地美女习惯称作“赵姬”,汉乐府诗中把美女习惯称作“罗敷”,云南把美女习惯称作“阿诗玛”,广西把美女习惯称作“刘三姐”,藏族地区把美女习惯称作“卓玛”等历史文化现象,有惊人相似之处。尤其是“拴娃娃”这一行为,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世俗信仰、生殖崇拜、风俗人情、市井百态,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底层民众的深刻影响,均具有典型的标本似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各种版本的对比研究,还可以从中洞察底层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不同时代特征及其变迁轨迹,应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笔者首次称之为太行山文书中的“刘二姐现象”。
原始生殖崇拜与“刘二姐现象”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便开始了生殖崇拜。那时候人们仅仅依据孩子是女性所生,便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当作神秘生殖力量的源泉或寓所,顶礼膜拜。在各地考古发现的岩画、出土文物中,均有女性生殖器和怀孕女性形象出现。这种人类对自身的生殖崇拜,有效性极其有限,于是逐渐转向对那些生殖能力强大的自然物的崇拜。
仰韶文化中的“鱼祭”“鱼纹”,颛顼是半人半鱼的鱼妇,鲧是一条“白面长人鱼”等记载,反映的就是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现象。鱼的形状与女性外阴相似,鱼腹又多子,繁殖力强大,于是人们相信鱼身上一定寄寓着某种神秘的生殖力量。后来出现的“鱼轩”“鱼书”“鱼蓝”“鱼灯”“年年有鱼”,都是人类早期对鱼生殖崇拜留下的痕迹与证据。
蛙,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显示出强大的繁殖力;且蛙的肚子浑圆膨大,与怀孕妇女的肚腹相似,因此,蛙也是被赋予了神秘生殖力量的象征,被加以崇拜。临潼姜寨出土的鱼蛙纹陶盆中,就有典型的蛙形图案,蛙身浑圆而膨大,其间斑点密布,寓意蛙腹多子的强大生殖力量。
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就是从蛙的生殖崇拜演绎而来。浑圆无垠的苍穹,被祖先想象成蛙腹;满天密布的繁星,被看作是腹中蛙籽,后来演化成了女娲补天的五彩石子。一位“一日七十化”的蛙女,便被塑造成我们民族最初的母亲神。
后来,我们的祖先又把蛙与月亮联系起来,倍加崇拜。月,盈亏圆缺,恰与孕妇肚腹膨大缩小现象类似;成年女子的信水,每月一次,也与月亮的盈亏圆缺同步,因此称“月经”。这样,月亮又被赋予了生殖意义上的神秘联系,被想象成神蛙,或认为有这样一只神蛙存在于月亮之中,并为这只神蛙取名“蟾蜍”,之后又转音为“嫦娥”,最终演化定型为一位主司婚恋生育的美丽女神。后来又衍生出“月老”或“月下老人”的神话传说。
父系社会后期,图腾生殖崇拜改头换面,逐渐定型为世俗化的祖宗崇拜,继续承担维系神化男权社会功能。如今的祖宗、宗庙、祖籍、祖国等词,均是祖宗崇拜的遗产和反映。
“祖”,甲骨文里作“且”,形如男根。郭沫若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各地出土的各种形如“且”形的男根模型文物就是佐证,既有石祖,也有陶祖。祖即且,就是祖宗崇拜的遗物与象征。“祖”的最初意义,就是祭祀祖先的宗庙或宗庙里的祖先(牌位)。易中天说,最初宗庙祭祀的就是男根——“且”,后来特指对氏族开创有功的某位男性祖先,“且”上刻有祖先的名字或符号。再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文字也出现了,“且”也不再堂皇,石牌和木牌逐渐代替了石祖和陶祖,但仍叫“且”。为了供奉“且”,人们盖起了房子,供奉“且”(神主)的房子和地方,也跟着称为祖(宗庙)。祖庙由此而来。
一个氏族建立,首先建立祖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当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作“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作“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祖国”就是家国一体化的“祖宗之国”,因此,一切为了“祖宗”“祖国”,便成为我们民族生死荣辱的依据和目的,犹如血液一般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肌体中。
这一系列原始生殖崇拜与神话传说,是我们民族的来路与文化基因。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颦一笑。太行山文书中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域的一个个“刘二姐”们,那么热衷于拴娃娃,生儿子,无不受这种生殖崇拜基因潜移默化般驱使,为使“祖宗”后继有人,“祖庙”香火不断,“光宗耀祖”,尤其生育主持宗庙祭祀仪式的男孩,成为我们民族每个人莫大的神圣使命。
宗法礼教文化对“刘二姐现象”的教化绑架
中国古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孕育出高度垄断的宗法礼教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上升为专制教化伦理道德体系,一代代强制洗脑教化,造就了整个社会男尊女卑、生殖至上的泱泱世风。
首先,我们民族文化最早的符号——“阴”( )“阳”( )就与生殖直接相关,郭沫若说是男女生殖器外形抽象而来。由此演变而来的《易经》,不乏男女地位的经典定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从文化源头上就规定了男女关系天造地设,天在上,地在下,天罩着地,地顺着天,男尊女卑,不可反其道而行之。
《易经》中与男女生育有关的卦辞,至少有26处之多。“姤”卦有:“女壮,勿用取女。”意思是说:女大强壮,不要娶她。卜辞中有“贞,有子”,吉利的事,就是有儿子了;“不嘉,有女”,走霉运了,是个女婴!有的卦辞把“妇孕不育”“妇三岁不孕”直接说成是凶兆,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民族崇尚生殖、男尊女卑的文化基因。
《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求偶咏唱。《诗经》中不乏诸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的爱情佳句,更有对少女出嫁时的赞美:“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螽斯》全篇都在反复咏叹“宜尔子孙”的得意之情:振振兮、绳绳兮、蛰蛰兮!号召广大妇女要像蝗虫和蝈蝈那样,多生快生。《麟之趾》更是掩饰不住对子孙满堂的羡慕之情。
但生男生女结果迥然不同,有“璋”“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如果生男孩,要小心地放到床上,穿漂亮衣服,玩玉器,连哭声也视作非同寻常,一定是个穿朱服做官的腕儿,所以,生男孩,捧圭玉,叫弄璋之喜。生了女孩,则直接扔在地上,随便用一个布片包上了事,只给她纺槌瓦片玩,将来会纺织做饭,侍奉丈夫公婆,不给父母添麻烦就够了,只能叫弄瓦之喜。
女性受到生活上的虐待还在其次,更为严重的是伦理教化上的压迫。《礼记·内则》首开闺媛礼女性歧视教化先河,被立为周代妇德标准。一生都在“克己复礼”的孔子,宣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继而孟子又喊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声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汉代赵岐对此又进一步发挥:“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孝的核心直接解读就是生儿子,不生儿子,对家是不孝,对君是不忠。不生的责任,女性势必首当其冲,罪莫大焉!
《孝经》把“孝”视为“天之经、地之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父母生下子女,最大的事业就是繁衍后代。“人之行,莫大干孝”,孝是诸德之本,并将孝亲与忠君、孝道与法律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动用专政工具,来维护孝道秩序。
在这一系列孝道文化重压下,女性社会地位江河日下。《礼记》托孔子之名指出:“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孔子家语》交代:“女子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周礼·天官·内宰》教导女性恪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四德,汉儒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进一步强调:“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此,“三从四德”便成为长期束缚中国女性的专用枷锁。
秦始皇不仅“车同轨”“书同文”,还诏令天下“行同伦”,把“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的命令,刻于泰山巨石之上。到汉代,不仅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更有西汉刘向作《列女传》,东汉班昭作《女诫》,把对女性压迫的宗法教化及闰媛礼事业推向高峰。尤其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班昭,其现身说法之举更具迷惑性:“夫有再娶之义,妇无再嫁之礼。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祗,天则罚之。礼义有衍,夫则薄之。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主同也。”班昭不愧为才女,还是个“二圣人”,话说得精彩也够露骨!西晋文人张华的《女史箴》更被历代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唐代更有女性大佬挺身而出,以其女儿之身为宗法文化献媚祭旗。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著《女则》在先,武则天写《内训》紧跟其后,著名的唐代宋氏五姐妹终身不嫁,为宗法妇道守身殉节,著书立说。大姐宋若莘直接承袭圣人《论语》之名,写出细说女性清规戒律的教材《女论语》,其妹宋若昭不甘落后,为该书续写辅导教本,积极为封建闺媛礼的事业增砖添瓦。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变态得登峰造极。程颢、程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女子守贞,寡妇守节”。程颐先吓唬女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回头又吓唬男人:“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后世的历朝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民间有《女儿经》《闺范》《教女遗规》大行其道,高层有明成祖徐皇后仿则天女皇著《内训》,集“古圣先贤”妇女美德于一书;酸儒王相之母刘氏,位卑未敢忘忧“妇”,更是热衷总结“贞妇烈女”与“贤妻良母”典型案例,写出《女范捷录》。王相又将之同班昭的《女诫》、宋若莘的《女论语》、徐皇后的《内训》,汇编成册并作注,取名《闺阁女四书集注》,被誉为“女四书”流传于世,贻害无穷。康雍年间的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辟有“闺媛典”专辑,堪称妇女清规戒律百科全书。清朝在继《唐律疏义》《元典章》之后,继续将“三不去七去之礼”纳入《清律》。直到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女性方从制度文本上摆脱这些专制文化的枷锁与桎梏。
有学者说,男日儿,女日婴,所谓弃婴,其初意专指抛弃女孩。韩非子曾提及“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可见杀、弃女婴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从字源角度看,“婴”字的构成是两贝加一女,一般认为两贝是女子脖子上的项链串珠,但有学者推测,更可能与俗称女孩“赔钱货”说法有关。
在数千年漫长宗法专制文化的浸淫下,生存在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无一不置身于这种男尊女卑生殖至上的专制文化枷锁之中,在其无处不在的教化捆绑下亦步亦趋。女性的权力和地位极其卑微,生儿子成为其最大的社会功能,连女性自己尤其是女性学者都看不起自己,还有谁想做女人,愿意生女孩?!无论是刘二姐,还是二青头,人人概莫能外!只有生了儿子,才能在社会上谋得一席生存之地。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我们民族有着如此久远的生殖崇拜文化基因、数千年封建宗法制度的刚性约束,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文化的专制教化,孕育了我们民族每个人的历史人文底色——崇尚生殖,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凡有这种历史人文背景的人,就是一个疑似的“刘二姐”;凡有这种历史文化存在的地域,就会有疑似“刘二姐现象”;我们民族的历史有多久,“刘二姐现象”的存在就有多长。拴娃娃的“刘二姐”们,被民间艺术演绎定型成一个典型艺术形象,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也许各种适合的艺术土壤与契机,在明朝以后水到渠成、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们才能从名不见经传的太行山文书中,发现如此众多反映“刘二姐现象”的民间艺术作品,由此成就了“刘二姐现象”的历史悠久性、地域广泛性,及其历史文化上典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