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骨科
许文舟
醒来,已是下午五点多,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在哪。蝉鸣般的喧哗,夹杂着菜市场那种嘈杂,摩肩接踵的人流在忙碌中穿梭。儿子睡在另一张床上,妻子红肿着双眼,在一摞单据面前发呆。再想想,我想起来了,是昨夜敌不过瞌睡,一头将车撞到同样睡着了的水泥墩子上。亲人就在我床边围坐,从她们满脸焦灼中,我知道,我这个努力不让自己打扰世界的人,竟然掠扰了所有的亲友。
我不知道儿子伤到哪了,反正车祸发生时,怎么喊他都没醒,这下可把我吓得六神无主,我简直就是哭着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妻子的,此时是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二十分,根本就没考虑说话的语调是否婉转了,妻子一定吓得不轻,以至我出院后的许多日子,我与她同时会在凌晨三点多惊醒,之后的半个夜晚都了无睡意。也许上天只是想惩罚一下我,皱了皱眉头便派来了救星,让三位夜行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来到面前。报警、叫120急救,然后把儿子抱到路边,把我从被卡的地方弄出来,我才发现左脚不听使唤。
妻子赶到市医院的时候,天已微明,检查刚刚结束。儿子昏迷四十分钟之后醒来,他参与了对我的救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推着车子,对我说,爸爸你得坚持。我知道一时半会不可能离开医院的病房了。我绝对相信自己受到神灵的悲悯与护佑,左一点,车子就要下河,这时的南汀河像匹发情的母狼,汹涌的河水绝对可以吞没一切。右一点,是峭壁悬崖,下去的话人车俱毁。车子恰好撞在水泥礅面上,折断了那么多骨头,至少,作为写作的人,还可以构思,动笔。
针水一组接着一组,护士蒙着嘴,说话含混不清。我全身不能动弹,每隔两个小时翻一次身,是护士下达的任务,而这一翻,就得重新疼痛一次。特级护理是这样的,洗脸漱口擦身翻身等都由护士完成,在那些晃来晃去的护士中,来了一位其实也就看见一个鼻子的女孩。她自我介绍的时候,摘了口罩说,她叫尚明洁,是我的责任护士,接着宣布了住院的注意事项,好像什么违规都与钱扯上关系。
我的名字变成了90号,前来看我的人问我名字,护士也会说:“是90号吧,在靠右边的第一间。”“90号醒来,给你翻身”、 “90号给你打针”、“90号给你量体温”……医院同样给我安排了主治医生,但从进骨科到两个月后出院,我的主治医生除了每天早上不超过一分钟至两分钟的查房,基本都不与我说什么。这个主治医生姓什么,我都记不住了,他最大的动作就是看片子,生怕接触到患者的身体一般,始终与病床隔着一臂长的距离。有几次,我想说这疼那痛,说出口半句,他已经转身出门了。
各种片子综合起来,结论是左髋臼粉碎性骨折,肋骨骨折八根,并且大面积坍塌,右手一二节骨折。除了骨头部份,还产生气胸,胸腔有积液。
这一刻起,我决定了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随之暴发。伤口滴血,喘息细若游丝,程序化的针水扑打着炎症,那些疼,是自己疲劳驾驶的馈赠。就因为瞌睡,将一家人卷入黑暗的谷底,同时也把亲人卷进来了。几块骨头说断就断了,支持和保护身体的功能彻底丧失,小幅度的侧翻身,举手抬头这样的动作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严重的是呼吸与说话困难重重,话只能微弱地说出,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尚明洁护士让妻子去买了两大包气球,同样是规定的动作,让我每天不停地吹,说能将一屋子都挂满吹饱的气球我就可以出院了。刚进医院的那几天,别说吹气球,就是喘一小口气都异常艰辛。一只小小的气球放到嘴边,怎样也无法把它弄饱起来。每天清早,我被痰堵得满脸煞白,只能借助吸痰器,一次又一次将它们生擒。吸痰器对器官伤害大,护士主张我自己努力,靠捶背、叩胸、咳嗽等方式吐出来,可是哪怕再轻的咳嗽,那些呲牙咧嘴的肋骨便开始报复般地生疼。
手上骨折的地方,上了石膏,作为固定,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给我上石膏的是新手,那么多纱布与石膏终不能绑正我骨折部位,一个月后,我的手有点变形了,母指与食指之间无法张开,食指也弯得离谱。左脚坠挂三瓶近九斤的矿泉水,叫做皮牵引。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坠也要坠,不能也要坠,否则出院后脚伸不直与医院无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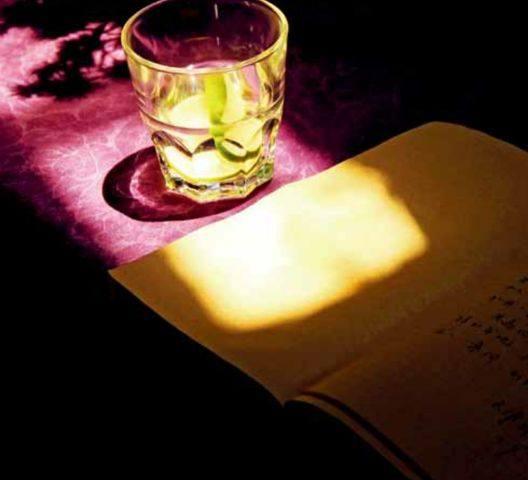
九斤水坠在脚上,那份罪比一刀切下去难受,而且必须连续性,一天歇息加起来不过一个小时,护士说了歇歇停停效果不出来。夜里做梦,都是被人拴着跑不动的情形,加上床本身呈斜坡状态,睡不到半夜,就会被九斤水拖到床脚,只好让妻子给自己松绑。每次医生都为肺部片子上那些白色的斑点皱眉,我也隐约感到自己这个肺将给医生与我带来无尽的麻烦。电话通了,只能说上句,接下来气不知跑哪去了。
90号病床临窗,这个窗口既可以接纳太阳的东升,也可以收尽日头的西斜,是好位置,可以看住院大楼下的老榕树,听老榕树上鸟儿年轻的歌声。可是这是初秋,火辣辣的阳光简直就是泼进来的,太阳才升到一竹竿高,屋内就热得够呛。超薄的窗帘把阳光筛过一遍,中午时分,病房里的人还是喘不过气来。虽然有风进屋,但它已经不能消弭熏天的脚臭与燠热了。尚明洁倒也会宽人心,说正好可以消毒,但她每次进来,高绾在她脑后的盘髻不一会便渗出细密的汗珠来。
擦完药水,给我翻身,用两个枕头垫着,好让风能吹到泡疹的地方,扫扫毒气,爽爽身子。尚明洁的交接班,就像交接这几颗泡疹一样,交接的时候,免不了又一次翻身,非要把我的身子全部暴露出来,点着泡疹的个数,第二天她来接班,夜班的护士又会将这些泡疹点交还给她,又得一次翻身。我的身上布满了童年的各类疤痕,我不想让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目光盯在我那些疤痕上窃笑。也许是为了抚慰,尚明洁说她童年也是个男孩子型的顽童,大寨村的树没有她不会攀爬的,没有哪个鸟巢躲得过她,同样没有哪个柿子秋天过后还敢在树上赖着不走。她也从高高的树上掉下来过,但落到地上得很快起来,不然她妈妈的棍棒就抡到头上了。每年她都要收到一些感谢信,几面锦旗,她的事迹上了报刊,但她还是那个除了工作还想去韩国听音乐会的发烧友。
尚明洁才二十五岁,却工作了六年,从昆明医学院护士专业毕业,本来可以留在昆明,但爹妈死活不让她在那里呆下,就回来了,开始的时候,骨科护士的活太繁太杂太多,她上了一天班,就请假哭了一天,她自己也怀疑是不是干不下去了,后来她坚持了下来,现在已经是骨科的骨干护士吧(这是我想的,用不着护士长同意)。遇上尚明洁,也算是一种缘,那么多骨科护士,偏偏有人就把最好的一个安排给我。疼了,说给她,她没有权利开药给你止痛,但她能与你谈谈与伤无关的事,比如说说她学车的危险经历,说说她想去韩国游玩的情况,说说她现在休息超过两天就觉得浑身不舒服的事情。除了吊针、换药、整理床铺,尚明洁也帮你理理摆满了的床头柜。她会倒掉你隔夜的茶渣,重新把开水给你灌上;她会帮你摆放一下鲜花,并洒点水,延长花香时间。我有能力将一只气球吹得南瓜大的时候,她也吹了一只,透过她稚气的眼神,我想起了云县大寨那个跟着一只气球奔跑的女孩。
车祸发生后,家里的生活全乱了套。妻子一个人承担起一切,在无数细碎而繁琐的事情中,我读到了她不常示人的坚硬与韧性。当灾难与生活发生羁绊与瓜葛时,她理得清谁轻谁重。因此我也觉得,坦然面对就是最好的反思。不把伤痛的情绪传染给别人,躺在病床,即便丛生出再多的感伤与无望,也要像窗外的老榕树面对枯索与凋蔽的到来,在医院留给的空间里,周正地活下去。
出院后,家里又成为我疗伤的地方。我仍然只能躺在床上,妻子在锅盆碗筷、菜刀砧板、油瓶盐钵中穿梭。让我心痒难忍的不是报刊约稿,不是吃喝全包的笔会,而是面对家事一筹莫展的无奈。偏偏总是有许多事情发生,水管漏水,灯泡烧掉,儿子需要重新复查,社保催交,房贷需还。
我能拄着柺杖走到小院,将身体倦缩在阳光下,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情。每天一个鸡蛋,一小时阳光,半斤骨头熬汤,统统被妻子翻了倍,康复倒也称心。三个月后,我能把大部份时间管理归一,一部份交给网络,一部份留在书房,还有一部份用来晒太阳,陪着一壶茶水,向生活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