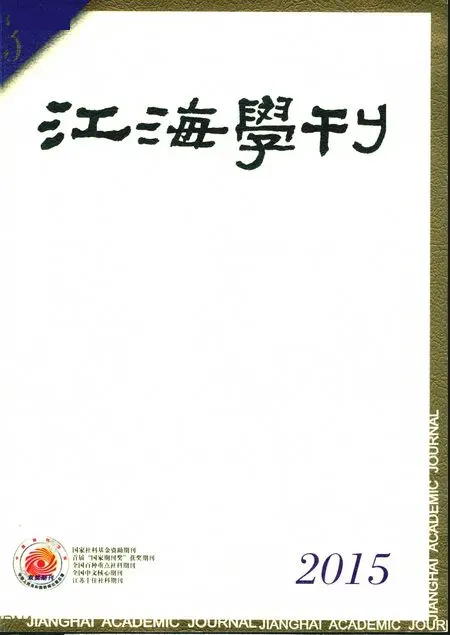“理”、“神”与心灵解释*——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中国心灵哲学的“发现”与“西式解读”
王世鹏
16到18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在“西学东渐”为中国人带来惊诧的同时,同步展开的“东学西渐”也让欧洲人对东方文明感到折服,甚至产生了狂热的迷恋。一时间“到北京去”、“到中国去”的呼声响彻欧洲,由此形成了一次东西比较研究的热潮。东西方的政治、哲学、宗教、教育、艺术等众多领域都被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视域。其中,中国儒家的“理”与西方基督教的“神”是被关注最早、讨论最多、后续影响最大的一对比较范畴。最先真正在哲学意义上对“神”和“理”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他的研究在当时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从事东西方比较哲学研究的第一人,而后莱布尼茨对“神”与“理”比较的继续讨论则将这场研究推向了高潮。其时,西方人在进行地理大发现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大发现,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发现中国也有如灵魂观之类的心灵哲学。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就是这一发现中的“哥伦布”,他们发现了蕴藏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心灵哲学思想,并与西方基督教的相关观念进行比较研究。他们所进行的“理神比较”中包含着丰富的、深刻的心灵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不但对于理解“神”、“理”及其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其中的很多内容即便放在今天也足以引起心灵哲学和东西心灵哲学比较研究的重视。
一
马勒伯朗士的比较哲学著作只有一部,即他在1708年发表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性》。在该著中,马勒伯朗士借中国哲学家和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对中国儒家的“理”和西方基督教的“神”进行了第一次严格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比较。按照马勒伯朗士自己的说法,其比较的最终目的:一是要批驳中国人所形成的错误的“天主”观念;二是要汲取中国人观念中隐含的微乎其微的一点真实成分,以使中国人“皈依改宗”。为了论证这一结论,马勒伯朗士从心灵哲学的角度,对中西心灵观、身心观等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比较研究。
为了向中国人证明“神”这种具有无限性的存在体,马勒伯朗士实际区分了两种意向对象,即实际存在的对象和不存在的对象。前者是指“凡是精神当前地、直接地知觉的东西”①。他在这里特别强调“当前地、直接地”,因为在他看来,是否能够具有这一特点正是实际存在的对象和实际不存在的对象的区别。比如,我面前的书桌能够成为我的心灵的当前的、直接的对象,所以它一定是实际存在的对象,即便这书桌是在我的梦里出现,它也同样是非常实在的。但是那些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心灵面前的对象,则是“不存在的东西”。换言之,是否能够成为心灵和精神当前的、直接的对象,是判断事物在本体论上是否具有存在地位的标准。马勒伯朗士做出这种区别所依据的是一个他反复强调的原则,即“想个什么都没有和什么都没想,知觉个什么都没有和什么都没知觉,是一回事”②。而上帝作为具有无限性的存在体,是可以成为心灵的当前的、直接的对象的,“而我想到无限,我当前地、直接地知觉无限,因此无限是存在的”③。
马勒伯朗士同样借中国人之口对基督教徒给出的这种上帝存在的证明提出了质疑,而这种质疑使其比较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心灵哲学的意味。其争论的焦点体现在以下问题:第一,精神当前的对象究竟是“在我们以外存在”还是仅仅是“精神本身”。第二,所谓精神,究竟是“有机的、净化了的气(物质),还是不同于物质的另一种的东西”。第三,精神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如果精神是有机的,净化了的气(物质),那么它就是有限的,这样一来,有限的东西里面能不能看见无限。
对这些问题,中国人的看法是,精神的对象仍属精神本身,这个对象不过是作为“有机的、净化了的气(物质)”,通过一定的方式呈现给你的,根本不会在你之外存在。因此,无限即使作为你的精神当前的对象,也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无限绝对存在。基督徒认为,中国人的错误在于把精神看成是气(物质),而气(物质)是有限的,有限当中并没有足够的实在性得以见到无限。但是,这与我们自己的经验是相违背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心灵、精神当中见到无限的东西。他认为,我们日常的经验也证明,精神并不是有限的,比如我们可以从有限的空间中得到无限的观念。因此,精神一定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有机的、净化了的气(物质)”。他反问中国人:“物质(气),不管你怎么净化吧,它怎么去表现它所不是的东西呢?特殊的、可以改变的器官怎么能够看到或者表现常住不变的、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真理和永恒的法规呢?”④
对此,中国人同样从经验事实出发,指出有限的东西并非不能表现无限。中国人认为,从经验上看,精神表现外物并不需要具有和外物同样多的实在性。“用不着表现者本身非包含它所表现的全部实在性不可。”⑤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外物是因为有理存在,人在理中看到万物。基督徒对此的解释是,外物本身并非精神的当前对象,真正的对象是关于外物的观念,而物质对象本身,我们是看不到的,也因此不能成为精神的直接对象。换言之,一切知觉来自于观念,我们唯有通过观念来认识对象。他说:“你所看见的物质的宫殿本身并不是看见宫殿的这个精神的当前对象;它的当前对象是宫殿的观念,是触动精神或者现实感染精神的东西。”⑥由此,他推论,理必定是无限完满的存在体即上帝,这才使我们“在理中看到万物”。而人们对于无限所产生的知觉之所以不明显,是因为观念的强度与它所产生的知觉的强度成反比关系。比如,关于房间的广延的观念所产生的知觉就明显强于关于天空的广延所产生的知觉。所以,由关于无限完满的存在的观念所产生的知觉就是最轻微的。
双方争论涉及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是:理和上帝如何存在,它们与万物的关系是什么?在此争论中,双方所用的论证再次涉及大量的心灵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知觉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纯粹的物理过程能否产生思想,即灵魂或精神是不是有机的、精细的气?精神和大脑是不是同一的一个单一的实体?
对于知觉的原因,基督徒认为,只能够是以下这些东西,即或者是外物本身,或者是灵魂,或者是理或者上帝。首先马勒伯朗士认为,外物本身不是知觉的原因,因为即使把人所能够认识的一切物理过程都清楚无误地描述出来,也仍然得不到对知觉的认识,精神的思想是不同于物质的另一种实体的变化。他说:“大脑的各种震荡和动物的精气都是物质的变化,可是它们与精神的思想是完全不相合的,精神的思想当然是另外一种实体的变化。”⑦所以,知觉不是大脑的变化,而只能是唯一能思维的实体即精神的变化。这种看法与中国人对于知觉原因的说明完全相反。在后者看来,知觉、精神完全同一于大脑的物理过程:“大脑纤维的震动,和那些小物件或者那些动物精气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知觉,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推理,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各种思想。”⑧基督徒对中国人所主张的这种朴素的身心同一论提出了责难,认为精神和大脑尽管有关,但决不同一,马勒伯朗士说:“老实说,你清楚地领会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物体的布置和运动是各不相同的思想或者各种不同的感受吗?如果你清楚地领会到了,那么请你告诉我,欢乐或者悲伤,或者你愿意是什么其他感觉吧,是由于大脑的纤维的什么布置?”⑨中国人承认自己无法具体地说明不同的思想或者感觉如何与大脑的神经运动相同一,但仍坚持认为知觉不外是气(物质)的变化,以疼痛为例,感觉到疼就说明“疼是扎,疼是在手指上”。基督徒则反驳说,手指上的疼与手指被扎出现窟窿是两个不同的、可以相互独立而存在的观念,因此疼不是手指的变化。换言之,知觉不是气(物质)的变化。从经验上说,失去手臂没有手指的人也能感觉到手指疼,这就是证明。因此,疼的感觉只能是由“手指的观念”所引起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引起了手指疼的知觉呢?马勒伯朗士进一步借基督徒之口把灵魂排除在知觉的原因之外,并由此来证明上帝是知觉的原因。基督徒从四个方面说明灵魂不是知觉的原因。首先,灵魂不熟悉视神经和眼睛的情况。第二,灵魂没有光学和几何学知识,没法通过眼睛里的投影得到关于物体形状、大小的正确认识。第三,灵魂没有能力在一刹那间进行无限量的计算,完成大量的工作。第四,我们对于物体所产生的知觉并不受我们自己意志的控制。把其他因素一一排除之后,基督徒得出结论认为,灵魂、身体都不能够胜任的工作只能由上帝来完成。因为只有上帝完全知道几何学和光学,掌握一切知识,能进行正确而迅速的推理,所以,只有上帝才能够直接对灵魂发挥作用,使我们产生知觉。“上帝建立了灵魂和肉体相结合的一般法则;我们应根据这些法则并且按照印在大脑里的各种感觉,得知面前的物体,或者在我们的肉体上出现的东西。”⑩
二
继马勒伯朗士之后,莱布尼茨对“理”和“神”进行了更为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中同样涉及了大量有价值的心灵哲学思想。尤其是在“神”和“理”比较中对西方灵魂观与中国魂魄观进行了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而且,与同时期的欧洲学者相比,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研究更具可信度和参考性。汉学家艾田蒲评价说:“在1700年前后关注中国的人之中,莱布尼茨无疑是最了解实情、最公平合理的一个,他的著作也是唯一一部我们今天还可以阅读的著作。”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述非常丰富,除了分别于1667年和1716年出版的《中国近事》和《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之外,还包括近200封尚未整理出版的书信。
莱布尼茨了解“理”、“气”、“魂魄”等儒家思想所用的原始材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马勒伯朗士的著作,二是耶稣会士龙华民和利安当等的著作和口述。但是,在“神”“理”关系、中西灵魂观等问题上,莱布尼茨并没有受到龙华民、利安当等人观点的制约,反而针锋相对地与之展开争论,并指出了后者的错误。例如,在“神”“理”关系上,龙华民和利安当把程朱理学的“理”完全看作是“具有唯物性质的”,认为“理”并非是“至高的神”,而只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原始物质”,中国人没有关于神的观念,由此他们得出中国哲学是一种纯粹唯物论这样的结论。莱布尼茨反对这种观点,批评他们“认理为纯被动性的、生硬而毫无人情的、和物质一样的,是不对的”。莱布尼茨认为,儒家的“理”和基督教的“神”是有关系的,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儒家把理看作是万物的第一推动者(First Mover),这种看法与基督教的至高神观念非常接近。另一方面,儒家的理还可以指代众神祇,即有行动与知识的特别精神体。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儒家的理究竟是纯物质性的,还是纯精神性的存在,抑或二者兼有。换言之,中国人是否承认精神实体的存在?莱布尼茨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就涉及对中国人灵魂观念的研究,涉及中国人是如何认识灵魂的本质的。
在关于中国人的灵魂观问题上,莱布尼茨与龙华民、利安当二人进行了更激烈的争论。龙华民和利安当对中国人的灵魂观基本上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在有关灵魂的问题上说法不一且明显有误。利安当说:“儒家和最有学问的人认为我们的灵魂来源于天,是天的最稀微之气,或者天的天气;灵魂离开肉体时就复归于天。它们以天为归宿,由天而出,又混合于天。”他认为,中国人所谓的灵魂来自于最后又复归于的这个天,是物质性的天,是和气相一致的东西。所以他说:“他们认为灵魂之复归于‘上帝’,不过是灵魂分解在气的物质之中,它和粗笨的躯体一起,失去全部知识。”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把灵魂称作魂魄,中国人的魂魄观念与西方的灵魂观念具有很多一致之处。他根据《书经》和朱熹的说法,认为中国人所说的人死,指的只不过是组成人的各部分分散开来,回归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魂或者灵魂具有天的本质,因而升上天去;魄或者身体具有地的本质,因而归入地中。人的生死只是天地的结合与分离,并无造成普遍本性(即理)的任何改变。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人对于人死之后魂魄运动的这种见解是否代表中国人把灵魂看作纯粹物质性的东西呢?
根据龙华民的观点,既然中国人认为死亡分开了属于天和地的东西,属于天的东西在本性上与气和火有关,并回归于天,那么毫无疑问,灵魂就被认为是“纯物质性的在气中消失的”。莱布尼茨则认为,龙华民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弄清楚“中国人说灵魂与天或上帝重合的意思”。他指出,正确理解中国人的灵魂观必须依据“一切即一”这条“中文公理”。这条公理的意思是“一切”都分享“一”,如果把这个“一”误解为“唯一的物质”,那么“一”与“一切”的关系自然就变成了物质分配的关系。龙华民不理解“一切即一”这条公理,才会错误地把灵魂回归上帝认作是“化成气一般的物质”。莱布尼茨认为,作为普遍本性的理与作为个体性的灵魂是有区别的,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物质分配关系来解释。因为,魂魄有来去升降等运动变化,但作为普遍本性的理却无这样的变化,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种分配再回收的关系,魂魄也可以在人死后继续存在。中国儒家主张灵魂可以与不同形式的身体相结合,这就说明,灵魂“的确继续存在;要不然,他就会回归普遍本性的”。莱布尼茨还通过中国人的地狱观念来证明他对中国人灵魂观的看法。比如,他指出,中国古代学说承认灵魂在身死之后有受到赏罚之事,中国儒家虽然不主张探讨地狱和炼狱,但其中有人相信“山林中乱跑的游魂实是身处一种炼狱”,这同样证明中国人承认灵魂是不朽的。
通过对中国人灵魂观念的重新解读,莱布尼茨就把“理”解释成一种既有物质性又有精神性的存在。这样的理实际上等同于他自己哲学中的“神”。基于这种认识莱布尼茨还把理与他自己建立的单子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理有时指至高神,有时又可泛指众神,即赋有动力和知觉的单子。所以,理和单子是有相同之处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说有别于经院哲学和笛卡尔传统皆重视的身心分别,是对身心关系中流行的二元对立思维方法的一种超越。理与单子的比较也仅在此一点上最具可比性。因为,理与单子归根结底在层次上、性质上是不同的,理是原则,而单子则是原子性的简单实体。所以,莱布尼茨把理比做单子,如说得通的话,只是因为两者皆指向超越身心二分的本体论原则。
三
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在比较研究中对“理”、“气”、“魂魄”、“心”等概念的理解与中国哲学的“原貌”都有一定的差距。在马勒伯朗士的研究中,西方的“灵魂”与中国的“魂魄”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完全没有被注意到,“魂魄”、“灵魂”、“心灵”被混为一谈,并都使用“l’âme”一词来表示。但是,“有机的、净化了的气(物质)”并不等于西方人所讲的心灵,反倒是和马勒伯朗士称作“禽兽心灵”的东西更为接近。按照朱熹的说法,魂和魄都不是心灵,对人而言,心灵应该是人之主宰,是寓于人的形体之中并指导着它的“理”。再者,用“l’âme”表示“气”(物质),就把人的精神意识都实体化了,但是在朱熹那里,物质化的身体与能知觉的心灵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蜡烛的“脂膏”与“光焰”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前者后者也就不能存在。相比之下,莱布尼茨对中国人“魂魄观”的分析更为细致、具体。他不但注意到“魂”和“魄”的不同,而且能够从“理”的角度入手分析“理”和“心灵”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对西方“灵魂观”与中国“魂魄观”的认识,还是对两者之间的差异的分析都被大大简单化了。在西方哲学中,“灵魂”一词也具有多重含义。有时它是指与肉体相对立的、可以轮回转世的精神实体。有时它指的则是呼吸、生命的起源,人的意识活动的承担者或者本质。中国人的“魂魄”概念更为复杂,涉及对“阴阳、形气”的理解,因此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与西方的“灵魂”、“心灵”作比较。
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理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偏重于本体论,而完全忽视,或者没有条件注意到其更为重要的价值性的、伦理的方面。比如,在作为宋明理学重要内容的“理气论”的理解上,马勒伯朗士的认识过于片面,仅仅知道“理只能存在于气(物质)中”。因为他对“理”的理解不够深入、全面,又把中国哲学误判为唯物论、无神论哲学,所以他把重点放在了“气”这一概念之上,从“气论”和唯物论的角度来理解理气关系。其结果是,在他的理解中,理的地位被气拉低,所以他才会认为“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中西方认识论的差异,完全用西方的特别是他们自己哲学的认识论范畴、框架来剪裁理学认识论。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中,“心”不仅指“人心”,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天地之心”,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思维”,后者的主要功能是“生物”,即创造万物。天地之心即是创造万物的“仁心”,心就有了道德的因素。所以,理学的认识论主要是一种“道德认识论”,认识论囿于伦理学。但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此都一无所知,所以前者把中国哲学的认识论说成是“灵魂的认识论”,后者则用“单子”与之进行比较。
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对上帝和理的比较受其各自目的影响,都明显带有分优劣、见高低的意思。为了证明中国人的“理”观念与西方基督教的“神”的观念很接近但“后一个观念更好”,马勒伯朗士对中国哲学采取了过分矮化和打压的态度。其《对话》中的“中国人”也没有被作为一个平等对话的参与者,而是成了一个观点不断被修正的“受教育者”。后来的康德、黑格尔等人对中国哲学持有种种误解,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源头之一就在马勒伯朗士。“从马勒伯朗士以后,西方许多哲学家都在重复他的观点,认为中国哲学不具备哲学特征,没有思辨性。”莱布尼茨在研究中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出于对中国哲学的好感,他在很多方面为中国哲学进行了善意的“补充”。比如,对孔子的“鬼神观”作了过度的解读和阐释,对“理”和“单子”的比较也显牵强,甚至认为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
实质上,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理神比较”在他们自己表面上宣称的目标之后,都隐藏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真实意图。比如,马勒伯朗士所描述的儒家思想实质代表的是某种形式的斯宾诺莎主义,这样基督徒在“对话”中对儒家思想的驳斥就带有向当时流行的斯宾诺莎主义示威的目的。所以“当马勒伯朗士嘴上说‘中国人’三个字时,他心里想的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当他写‘理’一字时,他想的是‘Deussive Natura’(如自然的神)”。莱布尼茨在进行“理神比较”时,虽然对儒家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公允的评价,但他的主要目的仍是从中国儒家思想中为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寻找论据。莱布尼茨毕生寻求一种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哲学”,从而实现一切人的结合,一切国家之间的普遍和谐。他认为,只要对世界各民族思想传统中真实的、有价值的部分加以提炼和保存,就能够总结出一切哲学的基本相容性,就可以奠定东西方哲学协调的基础。所以,莱布尼茨在对中国哲学的材料掌握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为中国哲学“补充”素材的方式,以肯定中国哲学的价值。正如克拉克评价莱布尼茨时所说:“他与后来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都将东方哲学作为有效武器来对纯粹欧洲目标开火,这种策略直至今日我们还能在许多地方看到。”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不足,但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理神比较”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庞景仁先生也认为,“‘理’的观念的不准确性丝毫没有改变《对话》的价值和功绩”。马勒伯朗士在其《对话》中讨论的内容,实质上已经涉及了意向对象、意识本质、意向性的超越性及感受性质等当今心灵哲学争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神”与“理”、“灵魂观”与“魂魄观”等的比较也确实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比较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比较研究证明了中西哲学之间在思想方法上可以具有一致性和相互印证之处。比如,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所用的方法就更具有中国特色。根据莱布尼茨的说法,他的哲学研究所用的方法是逻辑式的推理,通过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将整个体系演绎出来。但是他为自己规定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涉及“单子论”的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所以,后来以莱布尼茨的继承者自居的沃尔夫就因为超越身心二分的单子概念不符合笛卡尔“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而加以拒斥。事实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方法上更类似于朱熹对于理所用的方法,即理只能由悟性来认识,说不出什么逻辑。莱布尼茨与中国思想的一致之处还不止于此,甚至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与中国思想的某些学派都有惊人的一致性。㉔比如,佛教华严宗关于“理”和“事”两个层次的区分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内容和方法上的一致性即是如此。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把心的概念解释为单子,作为单子的心可以自觉地成为现实之镜,但它又不只是一堆影像的总和,而是表达全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镜。巧合的是,中国唐代的法藏同样以镜子为喻来说明心与万物的关系,即万事万物皆为绝对心体的表现,心体是包罗万象的。莱布尼茨以镜为喻最终得出“一即多,多即一”的宇宙和谐思想,而华严宗的结论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马勒伯朗士:《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性》,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⑩马勒伯朗士:《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性》,庞景仁译,《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