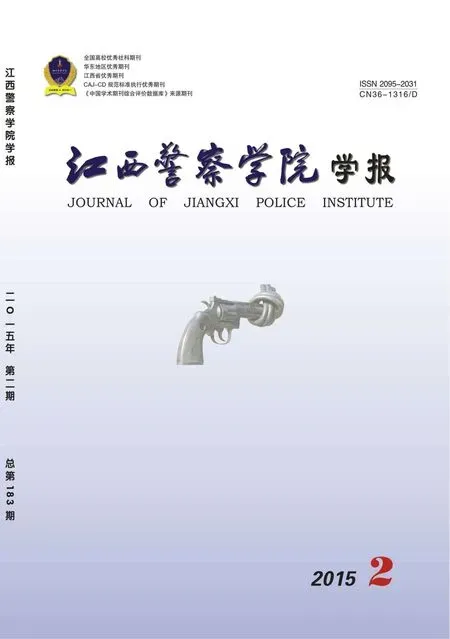“药儿”行为的定性及规制反思
李文军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207)
一、问题的提出
西安市政府于2014年3月13日晚通报,该市枫韵幼儿园和鸿基新城幼儿园违规给幼儿集体服用盐酸吗啉胍片(ABOB),别名“病毒灵”,涉及幼儿1400多名,部分幼儿出现心肌酶偏高、肾积水、心肌炎等症状。两所幼儿园的法人代表孙某及其他4名涉案人员,在明知自己没有取得法定资格的情况下,为提高幼儿的出勤率、增加幼儿园收入,从2008年起即开始购入处方药“病毒灵”违规给幼儿服用。后经公安机关查明,自2008年11月到2013年10月,涉事幼儿园冒用其他机构的名义,先后分10此从4家医药批发零售企业先后分10次购进“病毒灵”5万余片。[1]据悉,相关责任人员以涉嫌非法行医罪被公安机关拘留。毋庸置疑,幼儿园为了提高出勤率,防止向家长退还托管费以保障幼儿园的收入来源,事先未经家长同意和有关部门的审批就给孩子喂食处方药,这样的行为确实给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涉案人员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但相关负责人长期喂食幼儿“病毒灵”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已构成犯罪,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商榷。诚然,公安机关认为涉事幼儿园保健室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相关责任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喂食儿童“病毒灵”的行为已涉嫌非法行医,但“喂食”行为解释为“诊疗”行为有类推适用的嫌疑。假如仅为平息公众情绪,在依法无据的前提下对行为人强制追责、以刑制罪,这与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的宗旨不符,也与保障公民的自由、人权相抵牾。
二、“药儿”行为的定性分析
“药儿”行为虽然在主体上满足非法行医罪要求,但喂食幼儿“病毒灵”的行为是否属于“行医”行为仍然存有疑问。另外,非法行医罪保护的客体是公共卫生秩序,而“药儿”行为表现为对幼儿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如肾积水、心肌炎,其侵害的客体是儿童的身体健康权利,所以“药儿”行为与非法行医罪保护的客体存在差异。换言之,“药儿”行为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公安机关以非法行医罪拘留相关责任人的做法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行为人以牟利为目的,长时间欺骗、强迫幼儿服用“病毒灵”的行为,属于虐待儿童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药儿”行为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
首先,“药儿”行为不属于“行医”行为。行医是指从事医师职业活动,而医师执业活动是将医疗、预防、保健作为一种业务实施的,故行医必然是一种业务行为。只有当行为人将行医作为一种业务活动而实施时,才可能危害公共卫生秩序,所以本罪的性质决定了行医是一种以医疗、预防、保健为业的行为。[3]而行医作为一种业务活动其面对的业务对象是不特定的,即其诊疗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非法行医罪客观上表现为未取得医生职业资格的人从事非法行医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其中非法行医活动即是指非法从事诊断、治疗、医务护理等业务,属于典型的职业范。换言之,非法行医人员也把行医活动作为一种职业,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展开,只不过其行医主体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从本案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涉事幼儿园的保健室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相关责任人均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在主体上符合非法行医罪。但给幼儿喂食处方药病毒灵的行为是否就是行医行为,笔者认为还值得商榷。幼儿园作为一种学前教育机构,主要是对幼儿集中进行保育和教育,并非以开展医疗活动为其主业。虽然幼儿园里设有保健室,但其主要工作是负责园内的卫生保健工作,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看,这些保健室并不对社会公众开放并接受诊断、治疗活动。[2]所以,其喂食幼儿药物的行为不属于“行医”的范畴。
其次,“药儿”行为主观上并非为了“诊疗”。一般来说,医疗行为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医疗行为,是指出于诊疗目的所实施的行为,包括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生育的处置,按摩针灸等符合医疗目的的行为;侠义的医疗行为则是指广义的医疗行为中,只能由医师根据医学知识与技能实施,否则便对人体产生危险的行为。[3]笔者赞同广义的医疗行为,并认为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特点:第一,医疗行为是必须以实施诊疗业务为内容的行为;第二,行为人必须具有持续或反复实施医疗行为的意思,假如行为人缺乏这一主观要件,则不能认定为从事诊疗业务。所谓诊疗,是指医师为了预防疾病、治疗伤病、助产、矫正畸形等,向患者使用医学技能、知识的活动。
诊疗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诊断和治疗:诊断是指就患者的身体、伤病的现状等进行诊察,包括视诊、问诊、触诊、听诊、检查、打诊等,根据现代医学的立场大体上可以判断疾病原因,选择治疗方法的活动;治疗是指以恢复患者的伤病、增进健康为目的且应由医生实施的行为,包括手术、投药、处置、注射等。[3]西安“药儿园”事件中相关负责人并不是为了实施诊疗,相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保证幼儿的出勤率、稳定幼儿园的收入,从而不顾幼儿是否有预防疾病的需要,也不以增进幼儿健康为目的。也即,“药儿”行为就是在掩盖其非法目的的外衣下以预防疾病为幌子喂食儿童处方药,所以相关负责人的行为不能表明其具有“诊疗”的目的。
再次,“药儿”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儿童健康。非法行医罪保护的客体是公共卫生秩序,即行为人故意妨害国家对公共卫生安全的管理活动,破坏公共卫生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包括公共卫生,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国家的规章制度开展活动,以保证社会结构体系、社会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有序性以及连续性。由于人类并不想仅能够生存下去,具有渴望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倾向。但是,社会的有序性是建立在管理基础之上的,而管理活动的有序展开与一定的行为准则密不可分。“行医”的行为对象是社会中的成员,其从事的活动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假如国家不对其进行干预整治,势必会造成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无法得到保障。为改变行医行业乱象丛生的局面,国家颁布了《执业医师法》,要求只有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医师资格,并且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然而,“药儿”行为只是针对特定个人从事的保健、医疗、预防活动,根本不可能危害到公共卫生秩序。笔者认为,“药儿”行为在本质上讲侵害的客体是幼儿的人身权利,即身体健康。如果认为“药儿”行为侵害了公共卫生秩序,则相关责任人侵害的对象就不仅局限于幼儿园内部,其“诊疗”的对象应具备不确定性,严重破坏了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制度。换言之,成立非法行医罪必须侵害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然而针对特定对象的喂药行为并没有危害到公共卫生秩序。两家幼儿园的“药儿”行为,客观上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事实上,通过体检得出的报告显示,只有少数幼儿体检结果的个别项目有异常,并不是所有幼儿都出现了指标异常现象。所以,“药儿”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幼儿的身体健康权利,而不是妨害了公共卫生秩序。
最后,“药儿”行为并未达到本罪情节严重标准。根据司法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非法行医入罪的“情节严重”:第一,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第二,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第三,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第四,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第五,有其他严重情形的。西安两幼儿园喂食儿童“病毒灵”的行为,事后经体检查明,有少数幼儿出现了肾积水、心肌炎,腹腔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等症状,但按照解释的规定,很难将这一结果认定为“情节严重”中造成幼儿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此外,对“药儿”事件的责任认定和规制,应在查清事实基础上,按照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不能仅为平息众怒而不顾刑法的具体规定。根据媒体报道,西安“药儿园”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对两家幼儿园幼儿进行了检查,从体检的报告结果来看,393名幼儿中正常者为328名。[2]体检中虽然发现少数幼儿个别指标异常,但没有发现有共性的异常现象。对于极少数幼儿出现的身体异常情况,临床数据和相关资料都很难表明与被喂食“病毒灵”有关,缺乏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药儿”行为属于虐待儿童健康的行为方式
首先,“药儿”行为已被涵括于虐童行为之中。人们长期以来由于对虐童行为缺乏比较全面的认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儿科医生Kempe等以论文形式将虐童行为呈现后才逐渐引起人们关注。到了20世纪90年代,虐童行为在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成为了一个热门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虐童行为不单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医学问题。自此,诸多专家学者对虐童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其定义作了相应的概括。但是,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在定义上难免会有出入。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解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虐童行为作出科学界定。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年对虐童行为(CA)作了如下界定:[4]虐童行为是指有抚养义务、监护权和支配权的人对儿童发育、健康、生存以及尊严造成伤害的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性虐待、情感虐待、躯体虐待、忽视及经济剥削。国际儿童虐待常任委员会(ISCCA)对虐童行为所作的定义为家庭内对儿童的不正当对待,(包括性的虐待、身体的虐待、心理的虐待、放置不理的虐待),家庭外对儿童的不正当对待以及其他各种对儿童不正当的对待。[5]
日本的《儿童虐待防止法》(全称为《有关防止儿童虐待的法律》)中将虐童行为定义为保护人对其具有监护义务的儿童进行如下行为:长期弃置不管或不给饮食导致儿童正常身心发育受损,或者对保护者以外同居的人对儿童施加暴力等行为的监护不周和懈怠;强迫儿童进行淫秽行为或者对儿童进行猥亵;对儿童身体施加暴力有可能造成伤害或外伤的行为;对儿童使用侮辱言辞激烈辱骂、拒绝;让儿童目睹家庭暴力造成儿童严重心理伤害的行为。其中保护人指对儿童具有监护义务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儿童是指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认为,虐童行为是指成年人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人身、精神、财产、性以及其他权利,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对虐童行为所作的界定太过宽泛,忽视和经济剥削的证明略显困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难以得到普遍认可。国际儿童虐待常任委员会(ISCCA)对虐童行为的界定比较模糊,未明确说明虐童行为的主体以及影响程度。皮艺军教授对虐童行为所下的定义也太过笼统,且未说明虐童行为的主体。总体上讲,日本《儿童虐待防止法》中对虐童行为的定义比较全面,包括有虐童的行为主体,受虐儿童的年龄限制,以及伤害的具体程度,并将虐童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虐童行为的界定需要结合本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如刑法中“儿童”的年龄,世界各国的规定存在着较大差别,有的规定为18周岁,有的规定为16周岁,而有的却规定为14周岁。
透过以上对虐童行为定义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虐童行为一般是指具有保护者或者监护者地位的人,对14周岁以下儿童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造成其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的行为。其中“暴力”、“非暴力”手段即可指行为人缺乏正当意图前提下,长时间喂食儿童药物,造成儿童身心受损的行为。西安两幼儿园为提高幼儿的出勤率、保证幼儿园收入,长时间以“聪明豆”为幌子强迫、欺骗幼儿服用“病毒灵”,最终导致部分幼儿身体健康出现异常。其中“强迫”、“欺诈”即可分别解释为虐童行为定义中的“暴力”、“非暴力”手段。
其次,“药儿”行为的社会危害与虐童行为相符。虐童行为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长期的虐待会致使儿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受损,对其成年后的生活学习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有的甚至走向犯罪道路。在谈到儿童的成长教育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幼儿好比幼苗,培养得宜才能发荣滋长,否则幼年遭到损伤,即使不夭折也很难能成才。儿童虐待可以划分为四个方面,即儿童忽视、儿童生理损伤、儿童性虐待以及儿童情感虐待。从造成伤害的结果来看,身体伤害包含有儿童生理忽视、儿童生理损伤以及儿童性虐待三方面内容;心理伤害包含有儿童情感虐待和儿童情感忽视两方面内容。
身体伤害是指儿童遭受各种形式的体罚或变相体罚后对其造成的器质性损伤和生理功能损伤,一般主要由儿童生理损伤、儿童性虐待以及儿童生理忽视所致。儿童生理损伤(Physical Abuse)是指施加或者允许非意外性的身体伤害发生在18周岁以下儿童身上,从而导致其身体健康损害,身体功能损害和丧失,皮肤损伤,死亡,以及使其处于可能发生上述伤害的险境中。[6]虐童行为对受虐儿童造成躯体上的伤害由轻(擦伤、青肿)到重(昏迷、骨折、内脏出血),同时还伴随器质性和脏器功能性损伤,较严重的虐待可以导致儿童正常生理功能遭到破坏,免疫力下降,继而引发多种问题,而最严重的虐待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或死亡。[7]儿童性虐待(Sexual Abuse)是指不论儿童是否同意,在任何地方任何人对儿童做出的性侵犯和性剥削,其中性侵犯是指侵犯儿童的性器官,以及引诱和猥亵儿童,性剥削是指利用儿童从事色情以及贩卖或散发色情物品等。[8]儿童生理忽视(Physical Neglect)是指有意或无意地,长期忽略了儿童的生理需要,以至危害或损害了儿童的正常健康发展,如未提供足够和适当的衣服、食物、住所以及环境卫生等。
心理伤害一般是指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保护人作出干扰儿童对于客观世界中物、事、人的正确评价和认识,挫伤儿童学习的积极性,导致儿童睡眠和行为异常,情绪紧张,早期社会关系的改变,认知功能的水平降低,甚至出现心理危机和心理障碍等影响儿童健康有意或者无意的,习惯性或者经常性的行为。这种心理伤害主要由情感虐待和儿童情感忽视所致。儿童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是指用羞辱、漠视、孤立、恐吓、羞辱等方式,对受虐儿童基本心理满足如自尊、爱、安全的侵犯,从而伤害和影响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儿童情感忽视(Mental Neglect)是指没有给予儿童关心、关爱,不及时予以心理安慰,忽视儿童的情感等。
在西安“药儿园”事件中,相关涉事者为保障幼儿出勤率,提高幼儿园收益,竟以欺骗、强迫等方式长期让幼儿服食“病毒灵”。后经医院体检查明,少数幼儿出现不同程度的心肌炎、肾积水、心肌酶偏高等症状。笔者认为,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为谋取利益无视幼儿健康的行为属于虐童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幼儿生理严重损伤。另据媒体爆料,有部分孩子在服药后将药片咳出,结果被老师罚站;老师发现有孩子借故去厕所吐掉的,竟然规定以后在服药期间不准上厕所。事实表明,“药儿”事件背后潜藏着对于关心、爱护儿童文化的缺失,涉事者不惜以欺骗、强迫喂食药物的方式达到其攫取利益的目的,造成幼儿身心受损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与虐待儿童带来的后果无异。
三、“药儿”行为的规制路径
诚然,“药儿”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虐童行为方式之一,但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第260条虐待罪还难将涉事者绳之以法,因为该罪的行为主体仅限于家庭成员,未扩大到家庭成员外主体。所以,针对此问题学界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思路,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是修正《刑法》第260条,把犯罪主体扩大到家庭外成员,限制告诉才处理范围;二是引入日本的暴行罪,完善我国的轻伤害犯罪;三是鉴于儿童属于弱势群体,《刑法》有必要给予特殊保护,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保护儿童的立法经验,在《刑法》260条下增设之一虐待儿童罪。
(一)修正《刑法》中虐待罪的基本立场
我国《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的犯罪对象仅限定于“家庭成员”,即虐待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只能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不包括家庭成员之外的其他相关人员。关于“家庭成员”的范围,学界大多数所持的观点认为其必须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即血亲关系、姻亲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并且应该在同一个家庭范围内共同生活,其中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同时也包括自愿承担抚养义务,并一起共同生活的其他亲友等。[9]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认为,传统中国的人际关系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晕,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10]在这种社会模式下,亲疏关系永远很明确,只有离中心最近的家庭成员才可能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照料、扶养、教育义务。[11]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的社会模式被逐渐被解构。人们为了工作、学习、生活,地域之间的流动性渐渐增强,传统的“差序格局”模式随着社会的变迁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离中心较远的“非家庭成员”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生活在一起,并缔结成一定的帮扶义务,如独居老人与家庭保姆之间的关系。
根据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虐待罪被规定于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这固然与当时的国情有关。而在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典》中,分则取消了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代之以将其所辖之罪名全部重新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因此,这就意味着本罪侵害的法益发生了改变,由妨害婚姻、家庭变为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现行《刑法》第261条遗弃罪原本也规定于1979年《刑法典》妨碍婚姻家庭罪一章,但由于可把该法条中规定的“负有扶养义务”进行扩大解释,行为主体可以相应扩大到家庭成员外,如医院的医生,敬老院的职员,家庭保姆,学校教师,以及临时护工。因此,遗弃罪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办法来应对社会的变迁。然而,虐待罪由于自身文字表述的局限性,无法规制家庭成员外有照护关系主体间的虐待行为。
有学者站在提升虐待罪评价力的立场,认为修正现有《刑法典》第260条虐待罪比增设260条之一虐待儿童罪的效果要好,原因在于虐待儿童罪的主体范围有限,不能规制家庭成员外主体间的虐待行为,如敬老院护工虐待其看护的老人,工厂老板虐待其管辖的员工,以及医生虐待其所医治的病人。相反,把虐待罪的主体从家庭成员之间扩大到负有照护义务关系主体,就可以解决家庭成员外主体间的虐待行为。另外,虐待罪“告诉才处理”模式不利于保护受害人,致使受虐者寻求救济较为困难,因此,应限制本罪中“告诉才处理”的范围。
(二)引入日本暴行罪的基本立场①
① 日本《刑法典》第208条暴行罪:“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处二年以下的惩役、三十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或者科料。”科料是一种财产刑,是强制犯罪人负担、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方法,它与罚金没有本质区别,主要不同在于前者数额小,不得缓刑,后者数额较大,可以缓刑。在日本,科料的金额在一千日元但不足一万日元,而且只适用于轻微罪行的刑罚。与罚金一样,当行为人不能缴纳科料时,也能易科自由刑。
“暴行”一语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将其分为四种:[12]一是最广义暴行,它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物理力)的一切情况,其对象不仅可以是物,而且可以是人。据此,暴行分为对人暴行与对物暴行;二是广义暴行,指不法对人行使的有形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身体行使,即使对物行使有形力,但对人的身体具有强烈物理影响时,也可构成暴行(间接暴行);三是狭义暴行,指对人身体行使有形力;四是最狭义暴行,指对人身体行使有形力,并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程度。对于暴行的定义,通说采用的是狭义暴行。
虐童行为一般是指具有保护者或者监护者地位的人,对14周岁以下儿童采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造成其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的行为。然而,虐童行为采用的“暴力”或者“非暴力”手段造成的伤害,按照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通常很难评价为轻伤以上程度,因为我国《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规定达到轻伤以上程度才可构成故意伤害罪。在日本,由于其设置有暴行罪,所以可以对轻伤害行为进行评价,有利于严密其刑事法网,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益。有论者认为我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要求达到故意伤害程度的立法模式过于粗疏,难以起到打击和预防犯罪,保护受害人人身权利的效果。所以,应当在我国增设暴行罪,这样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从“厉而不严”到“严而不厉”的转变。[13]我国刑法目前之所以“厉而不严”,原因就在于犯罪圈划定的范围较窄,许多严重侵害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不被认为是犯罪,但该行为一旦达到入罪标准,由于刑罚较为严厉,犯罪人因此受到的惩罚较重。
在我国,与日本暴行罪相类似的故意伤害他人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致人轻微伤的,一般不构成任何犯罪。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造成轻微伤的情形绳之以行政处罚,最高仅十五日拘留和一千元罚款。在日本,暴行罪是对故意伤害罪的补充,惩处故意伤害罪的未遂形态,以体现对人身权利的严密保护。由于儿童长期遭受身体和心理的折磨对其以后的生长发育较为不利,所以将暴力致使儿童轻微伤的行为入罪显得尤为必要。有学者认为虐童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引进日本的暴行罪,在条文的设置上可表述为以殴打或者其他暴行侵犯他人身体的,处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目的在于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纳入到刑法罪刑体系中来,同时也与《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与刑罚相衔接。[14]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日本对儿童保护制定的法律更多沿袭了英美国家的立法传统,其主要采取单行法规集中立法模式。1947年的 《儿童福利法》与2000年的《儿童虐待防止法》将保护儿童的刑事和行政制裁措施直接规定在一部法律中,而在《刑法典》里面不再单独设置专门针对保护儿童的特殊罪名,代之以暴行罪规制侵害健康法益但并未造成伤害结果的行为。笔者认为,暴行罪并未体现对儿童健康法益的特殊保护,未能践行联合国要求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同时也存在与一般暴力行为难以区分的不足,极其容易导致犯罪的扩大化,不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所以,鉴于日本行、刑结合的集中立法模式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法律体系不符,我国虐童行为入罪的立法路径不能选择日本暴行罪的立法模式。
(三)创设虐待儿童罪的基本立场
主张创设虐待儿童罪学者的基本立场是,认为虐童行为单独入罪符合世界上保护儿童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可践行国际公约保护儿童的特殊要求——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西方发达国家,虐待儿童行为一般会受到严厉惩处,轻则给予一定行政惩处,重则按照《刑法》规定予以追诉。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认为,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典》没有虐待儿童罪,而家庭成员外主体虐待儿童的行为按照现行《刑法》第260条却无法入罪。因为根据《刑法》第3条罪刑法定原则,虐待罪只能适用于家庭成员间,而不能扩大解释到家庭成员外的主体。假如非要对家庭外具有照护关系行为主体的虐待行为绳法,只能勉强适用寻衅滋事罪中“随意殴打他人”这一条款,从法条的原意上讲可能更接近。所以,这一立场的学者主张创设虐待儿童罪,借此可以有效遏制虐待儿童的行为,践行联合国儿童保护公约特殊保护儿童的基本要求。
也有学者认为,在现行《刑法典》中创设虐待儿童罪,可与猥亵儿童罪、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等罪名形成体系,针对特殊主体特殊保护,从而体现出我国对儿童进行特殊保护的价值倾向。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其他家庭外成员间的虐待行为,比如医生虐待自己所医治的病人,敬老院看护虐待自己所照顾的老人,工厂老板虐待自己所管理员工等,可以设置其他与之相对应的罪名。例如香港《侵害人身罪条例》规定了对所看管少年人或者儿童忽视或虐待进行治罪的条文,另外又在《精神健康条例》规定受雇于精神病院的护士、医生、雇员或者其他人,如故意疏忽照顾病人或者虐待病人进行治罪的条文。[15]
美国几乎每个州都有专门针对虐待儿童的专门立法,且虐童行为入罪的门槛相对于其他伤害行为要求较低。为保护受虐待儿童,美国各州在实体和程序法上都做了完备的规定。大多数州还创建了少年法庭,颁布少年法庭法,专门负责处理涉及遗弃儿童和虐待儿童的案件。英国也制定有专门保护儿童的法案,如1889年儿童保护法案专门制定了惩治虐待儿童的相关规定,该法案体现了对受虐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此外,瑞士、日本、意大利等国刑法还制定有暴行罪,对儿童实施虐待但没有造成肉体伤害的恶劣行为最高可以判处徒刑。此外,新西兰①《新西兰刑事法典》第195条规定:“虐待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纵容自己监护、照顾的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受虐待致使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精神失常或精神障碍的,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德国②《德国刑法典》第171条违背监护或教养义务罪规定:“严重违背对未满16岁之人所负监护和教养义务,致使受监护人身心发育受到重大损害,或致使该人进行犯罪或卖淫的,处三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等国家也针对虐待儿童行为设定了特定罪名。所以,应该将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予以落实,创设虐待儿童罪,以此对家庭成员外主体的虐童行为加以约束,才是破解当前虐童事件频发的治本之道。
四、结语
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民族存续发展的希望。笔者赞同在我国《刑法》分则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一章中创设虐待儿童罪,作为260条之一。单列的虐待儿童罪,应当有别于原立法中的虐待罪:在诉讼程序上,改变“不告不理”追诉模式,公诉机关应该主动介入进行侦查,对构成犯罪的涉案人员依法提起公诉;在法定刑配置上,虐待儿童的法定刑应偏重于虐待罪的法定刑,以体现侵害儿童法益的严重性。至于其他家庭成员外主体间负有照护关系的虐待行为,可借鉴《德国刑法典》第225条的规定,扩大我国《刑法》第260条虐待罪的主体,并对“告诉才处理”作出一定限制。
追究“药儿园”事件中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是必要的,但不能在依法无据的前提下对行为人强制追责、以刑制罪。就目前查明的证据显示,“药儿”行为根本不符合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所以,以非法行医罪予以拘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有类推适用的嫌疑。《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威慑作用,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铁则还是必须得到遵循和坚守。此外,“药儿园”事件也暴露出我国儿童保护、药品监管制度的漏洞。为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出现,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这才是化解“药儿”类虐童事件的根本之道。
[1]黄冠.“药儿园”事件中职能部门去哪儿了[N].新华每日电讯,2014-03-17(003).
[2]刘宪权.“药儿园”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N].解放日报,2014-03-28(005).
[3]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92-993.
[4]周佳娴.香港儿童虐待防治的经验与启示[J].少年儿童研究,2006,(6):38.
[5]黄辛隐.日本儿童虐待之现状与研究[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6,(2):11.
[6]李环.建立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干预机制[J].青年研究,2007,(4):1-2.
[7] 刘娟娟.儿童虐待问题研究概述[J].青年研究,2008,(2):37.
[8]黄重.心理健康视野中的陶行知儿童教育思想[J].福建陶研,2007,(3):28.
[9]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50.
[10]费孝通,马克昌.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27.
[11]徐文文,赵秉志.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研讨[J].法治研究,2013,(3):104.
[1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61.
[13]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5-56.
[14]孙运梁.我国刑法中应当设立 “暴行罪”[J].法律科学,2013,(3):80.
[15]何剑.论“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