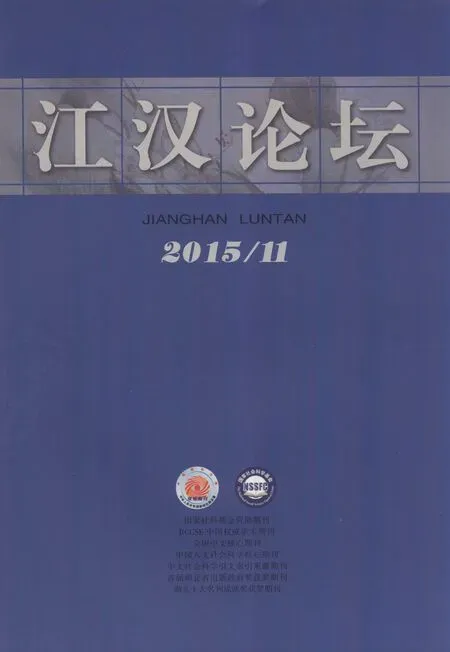道著与情衰:中国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
刘怀堂
忠孝观念与文学书写
道著与情衰:中国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
刘怀堂
中国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有三种基本形态,即传奇形态、演义形态和写实形态。这三种形态的忠孝书写存在着悖论,即小说文本自身书写忠孝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是以人物体现忠孝或者义的主旨时相互抵牾;同时,又尽可能地调和这些悖论,使之尽量统一——或点明小说忠孝主旨,或直接赞扬人物的忠孝或忠义。小说的忠孝书写深深地打上了王朝的烙印,即忠孝道著,扬名显亲;忠孝情衰,廉耻道丧。其彰显的是历时性下的国家意志,最终目的是家国稳固,社会和谐,对于当下弘扬传统文化美德,弘扬正能量,不无积极意义。
古典小说;忠孝;书写
中国古代几乎历代王朝都以法律的形式将忠孝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如《齐律》“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而隋唐则在此基础上损益为“十恶”,后一直延续到明清,并成为王朝意志下社会所接受并认同的伦理内核。作为各个王朝提倡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律化或意志化了的社会伦理,这一内核历来为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所书写,它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小说发展史。古典小说对于忠孝的书写与王朝兴衰紧密相关,共同构成了一幅古典小说忠孝书写的历史长卷。
一、从传奇到写实:忠孝书写的三种形态
鲁迅先生曾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则古典小说有意识地书写忠孝当始于唐朝。换言之,唐人的“有意为小说”,拉开了忠孝作为古典文学一大母题或内容的文学史序幕。自唐朝以来,古典小说对于忠孝的书写先后形成了三种基本书写形态,即传奇形态、演义形态及写实形态。
第一,忠孝书写的传奇形态。这是古典小说关于忠孝书写的最基本形态。明代桃园居士云:“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小说与诗律,称绝代之奇。”唐人的有意为小说,使得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传奇的烙印。这一传奇形态,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明清,尽管有所变化,但传“奇”的色彩始终如一。
唐传奇的忠孝书写形态有二,分别以《高力士外传》和《聂隐娘》两部传奇为代表。
《高力士外传》用对话体形式来书写高力士对唐玄宗的忠孝。小说主要连缀了高力士与唐玄宗几个对话场景,展示了高力士对于唐玄宗的忠心。小说开篇写高力士在太宗陵寝宫见到太宗遗物小梳箱、柞木梳而感叹,说太宗“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孝孙”,并“具以奏闻”唐玄宗,唐玄宗视为夜光之珍,命史官书之典册,开篇即奠定了小说忠孝主题。作为内宫宦官,高力士对于唐玄宗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比较中肯的建议。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对话就是关于皇权权柄下移问题的建议。唐玄宗曾对高力士说:“军国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回答说:“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表达了高力士对唐玄宗大权旁落的担忧。小说中不仅写了高力士对皇帝的忠心,还写了高力士对母亲的孝道。高力士10岁离开母亲,30年后迎母于泷州,“便于养父母家安置”。期间高母验证高力士胸前黑子细节,感人颇深。
小说并未将高力士脱靴、高力士与李白的恩怨等写入小说之中,而是以宫中其他日常生活为素材进行剪接,直接书写高力士对于皇帝与母亲的忠孝。这种对话体展示了皇帝与宦官之间的生活点滴,无疑都是皇宫秘闻。郭湜在小说结尾说:“淫刑以逞,谁无得罪!湜同病者,报以志之。况与高公俱婴谴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可见,这些秘闻都是郭湜从高力士处听来的。不可否认,高力士的自叙多少带有粉饰之意,小说有为尊者讳之意,但郭湜侍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与高力士同时,又与高力士同贬一处,小说所记高力士忠孝之事当不会空穴来风。有学者认为,该部传奇“把高力士为人老练圆滑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①。可聊备一说,但小说主旨应如晚明李贽所云:“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说阉宦无人。”
小说为高力士这位生前权倾朝野、死后褒贬不一的宦官立传,尤其是歌颂其对皇帝的忠与对母亲的孝,无论是高力士本人,还是小说记载的事情,都极具传奇性。
如果说高力士的忠孝是传统之大忠孝,那么,《聂隐娘》展现的则是藩镇割据时期诸侯豢养死士之忠孝。《聂隐娘》是以奇人异事来书写聂隐娘对于地方割据诸侯的忠心。聂隐娘本为凡人,因遇异人而学得超凡的本领——脑袋里可藏兵器,其所骑的驴子是用黑白纸剪成的,其本人可变身为小虫子藏于人肚中,能飞并杀人于无形,这些都是读者闻所未闻的令人惊异的事情,无疑增强了忠孝书写的传奇性。她被节度使刘昌裔收为帐下,依靠这些奇异的本领,几次帮助刘昌裔化解生命危急。类似的小说还有《昆仑奴》等,都是通过匪夷所思的超凡能力表达对主人的忠义。
尽管唐传奇中书写了忠孝内核,但不得不说唐传奇关于忠孝的书写形态尚处于草创期。就主旨而言,忠孝只是作为唐传奇众多的主题之一而被书写,尚未达到文学史母题的高度。据唐传奇史,前期传奇主要沿袭六朝志怪传统,书写神怪、因果报应,涉及忠孝或以忠孝为主题者甚少。中期传奇主旨比较丰富,主要涉及到神怪、爱情、历史和侠义几类。其中,只有历史类与侠义类的少部分作品涉及到忠孝主题。后期传奇虽然丰富,但只是六朝志怪的死灰复燃,少见有书写忠孝者。而中国文学史在阐述唐传奇时,也只将之分为爱情类小说、讽刺类小说、政治类小说、侠义类小说四类,几乎没有涉及忠孝书写的传奇作品。可见,在文学史家眼中,忠孝不是唐传奇书写的主要内容或对象。
因过分注重传奇色彩,在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单一,题材偏向人所未道、人所未知、人所未闻,造成了表现忠孝主题的题材单一性。而且书写方法单一,《高力士外传》纯粹用对话体,《聂隐娘》则让人物直接自叙神异的本领,情节粗糙,未能铺展开来,更缺少变化。这样一来,使忠孝的书写过于直白,缺少张力。作者只关注传奇性,而忽略了小说关于忠孝的书写。
到了宋元时期,忠孝书写形态比较多样。涉及传奇形态的作品,在书写忠孝时尽管依然保留着传奇色彩,但有所削弱,出现了由传奇向演义转变的趋势,以宋代传奇《隋炀帝海山记》为代表。
小说《隋炀帝海山记》以隋炀帝一生几个片段组织起来,穿插着几个人物活动,将忠孝放在较为广阔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展示出来。隋文帝立杨勇为太子,而杨广拉拢权臣杨素欲图谋太子之位。隋文帝可能知道此事,临死前托付杨素立杨勇为帝,并告诫杨素说,如果不按照他的话做,他死后也要杀死杨素。隋文帝死后,杨素并未立即将消息公布出去,而是密谋矫诏立杨广为帝。作为臣子,杨素违抗皇上遗诏,是为不忠;他依仗拥戴隋炀帝的功劳,不把隋炀帝放在眼里。作为惩罚,小说让死去的隋文帝找杨素报仇。小说猛烈地抨击了不忠于皇帝的臣子,从反面传达出小说对忠孝的肯定。与此相反,小说还出现了对小人物忠孝书写的剪影。小说中有一个小宦官王义,深得隋炀帝宠幸,其实天下因隋炀帝的倒行逆施而大乱,隋炀帝责怪王义知道天下大乱而不告诉他,王义明白地告诉隋炀帝:这场大难恐怕难以挽救了。隋炀帝又责怪王义不早点提醒他,王义说:“臣昔不言,诚爱生也。今既具奏,愿以死谢也。天下方乱,陛下自爱。”随后王义自刎。人物虽卑贱,但其忠孝节义凛然,高乎杨素之上。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对于隋炀帝其人结局的处理。小说的结局是:隋炀帝众叛亲离,被叛军司马戡所杀。隋炀帝不得民心,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如此帝王诚如百姓之“寇仇”。在忠孝的书写上,小说不再直接地反映传统的君君臣臣伦理,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具有后世意义上的民主精神。
尽管《隋炀帝海山记》被收入《唐宋传奇总集·南北宋》中,尚带有六朝志怪因素与唐传奇的传奇色彩(为书写忠孝主旨,小说主要选取了如杨广出生异象、与死去的陈后主聊天、洛水射鲤、侍妾梦隋炀帝身处烈火之中等事件),但小说中的杨素跋扈、王义死谏、司马戡弑君等却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演绎而成,带有明显的人物历史演义的成份,体现出从传奇到演义的转变轨迹。
宋元以后,古典小说忠孝书写形态发生了改变,但传“奇”因素仍有保留。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忠心的书写。张飞为保护刘备,断后阻击曹操追兵,一人一骑横矛立马于当阳桥上,战意滔天,吼声如雷,惊死夏侯杰、吓退曹操百万雄兵,将张飞对于大哥刘备的赤胆忠心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三国演义》对于张飞此举更是不吝笔墨大加赞赏:“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一声好似轰雷震,独退曹家百万兵。”此类例证在清代历史演义中比比皆是。清代出现的中国通俗小说史上著名的“三大家将小说”《呼家将》、《薛家将》、《杨家将》,以演义体形式歌颂了家族群体对于皇室的忠烈,其中对于人物的忠孝书写带有传奇色彩。
明清小说忠孝书写的传“奇”性,在明清公案小说、神魔小说中也有体现,这两大类涉及忠孝内容的小说是以演义形态出现的。最典型的莫过于清代名著《三侠五义》之《龙图公案》,小说主要以演义形态塑造包拯这个清官形象,为此,小说选取了不少奇异甚至色情、荒诞不羁的故事情节,而该小说的主旨是通过包拯形象极力宣传并提倡忠君思想。这就使全书于演义中书写忠孝主旨过程中体现出较浓的传“奇”性。
第二,忠孝书写的演义形态。这一形态当始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于明清盛行。有学者认为,宋元乃至明清话本小说,故事中的人物还是以传统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标准来塑造,说话人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传统道德的宣传员,道德说教色彩较浓郁。②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对于忠孝书写有两种形态:一是直接书写忠孝,以《梁公九谏》为代表;一是间接书写忠孝,以《五代史平话》为代表。
《梁公九谏》讲述的是唐代狄仁杰九次劝诫武则天将帝位传给武三思的故事,文字简略,但狄仁杰对唐室的忠心耿耿可谓天日昭昭。元代话本《红白蜘蛛》亦是书写了郑信对于朝廷的忠心。而《五代史平话》主题比较复杂,忠孝只是隐含其中,甚至并未视为一个母题而加以表达。其中的刘知远故事,主要叙述刘知远发迹变泰,期间穿插与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李三娘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忠贞,并未成为小说的主旨,只是依靠读者感悟而出。这类历史演义,只是注重于历史人物事迹的展示,忠孝书写不是作者的关注对象或内容。
明清是忠孝书写演义形态的繁荣时期。几乎各类题材的小说都涉及到忠孝主旨,不妨据此分类阐述之。
历史演义形态。《三国演义》即是很好的例证。这一形态对于忠孝主旨的书写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正统忠孝的书写。《三国演义》全书以蜀汉政权建立前后诸多事件为主线,又以刘备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为核心,将汉末蜀、魏、吴三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来演义,体现出明显的拥刘抑曹倾向。二是家国忠孝的书写。三个国家之内的忠孝书写,是传承传统的家国忠孝。曹操虽然是被谴责或抨击的对象,但其文臣武将莫不对其忠心耿耿。三是强化个人的忠与义。孔明之于刘备、荀彧之于曹操、周瑜之于孙权等之忠诚,均可圈可点。
草莽人物类演义形态。如《水浒传》以人物为中心组织故事情节,用传奇的方式叙述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聚义而归顺大宋,并为大宋建功立业的一系列事迹,书写了以宋江为中心的梁山好汉对朝廷之忠孝以及兄弟之忠义。《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即表达了这一主题。
家将类演义形态。以清代“三大家将小说”为代表。这三部小说以家族政治、军事活动为题材,淋漓尽致地演义了这三大家族悲壮之忠孝。《薛家将》书写薛仁贵家族三代为唐朝浴血奋战,却被奸佞谗害而满门抄斩,结局是薛家后代顾全大局,继续为国效力,最终赢得贞观盛世。《呼家将》以宋仁宗时代呼延家族与国戚庞氏家族之间的抗争为故事主线,书写北宋名将呼延赞后人呼延得模满门抵抗外辱、维护皇权的忠贞。《杨家将》书写杨继业祖孙三代前赴后继保卫大宋的赤胆忠心。
公案类演义形态。这类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以其活动为主线,选取相关故事并串联起来,将小说主旨通过人物展示出来。《三侠五义》是典型代表。
神魔类演义形态。这类小说以神魔为核心,以现实来写神魔世界,从而书写忠孝主旨。在主旨的书写上,一是以神魔为主体来书写忠孝。如《西游记》,借唐僧西天取经故事来书写孙悟空等的忠孝。一是将历史演义与神魔演义结合起来书写忠孝。如《封神榜》将武王伐纣历史神魔化,并加以演义。西周文王、武王原是商王的地方诸侯,因商纣王荒淫无道而起兵讨伐之,这本是以下犯上,乱了君臣大义,但小说却歌颂了周文王、武王,谴责商纣王的无道。在忠孝的书写上,《封神榜》表达了鲜明的民主精神。
可以说,明清时期的这几类小说中,历史演义类、草莽人物类与家将演义小说以忠孝作为小说书写主题与核心,与其他书写忠孝的小说一起形成了忠孝作为小说书写母题的繁荣时期。
第三,忠孝书写的“写实”形态。这里的“写实”之意有二:一是相对于传奇与演义而言的,尽管带有两者的色彩,但不注重之,而是关注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二是指发生在历史当下之时事。
忠孝书写的写实形态,以宋元话本为较早,这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可见一斑。话本写汪信之因与其兄不合而外出谋生,渐渐成为一方富豪。其时,南宋正图恢复中原,汪信之遂投阙报国。当时他的两位友人程彪、程虎寄住他家,因怨恨其子给予他们的馈赠太少,遂诬告汪信之谋反。汪信之被迫逃离,而家人全部被捕。为救家人,汪信之投案自首,全家得救,而他被处斩。有学者认为,汪信之以忠义为本,品质可贵。
这类例子在明代小说中较多。《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借金玉奴之手惩罚了负心薄幸的莫稽;《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控诉了背叛爱情、薄情负义的李甲,歌颂了忠贞于爱情而投水自尽的杜十娘;《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歌颂了扶危济困、不欺暗室而诚信立身的道德楷模赵匡胤。
这类小说忠孝之书写,不同于演义类小说,而是将关于皇权之高大上的忠孝书写转向市井小民之卑小下的忠义表达。民间之忠孝,有夫妇之忠贞、朋友之忠信、父子之孝道等,尽管有虚构,但其所记载的事情均有其生活原型,比较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市井小民对忠孝的理解与阐释。
古典小说对于忠孝的书写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是因题材不同而形态多样,因而主旨的书写也各不相同。只能说传奇、演义与写实只是三种基本形态,还有两种或三种形态同时借鉴甚至融合的形态。在主旨的体现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如前文笔者阐述了历史演义类小说书写忠孝的三种形式,但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如《三国演义》认同刘汉正统忠孝,却又花费大量篇幅书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忠及其集团内部的忠孝。这涉及到忠孝书写的悖论问题,下文将阐述之。
二、忠孝书写的悖论与调和
第一,忠孝书写的悖论。主要表现在忠孝主旨的表达上自相矛盾。《三国演义》表现了正统的拥刘抑曹观念,但在三分归一时,并未将天下重新归到刘氏手中,反而借孔明托梦给钟会,说蜀汉天命已尽,告诫他破川后不可妄杀平民。这就模糊了小说对于刘氏汉家王朝忠孝主题的书写。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对于关羽忠义的书写,矛盾更加明显。在小说中,关羽是作为忠义的化身加以书写的。桃园结义,奠定了其忠义之根;其后,小说更是不吝笔墨一桩一件地写关羽挂印封金、五关斩六将,于战乱之中保护刘备妻室,千里单骑寻找刘备,大书特书了关羽对于刘备的忠义。不仅如此,小说还不惜为关羽之忠义增加砝码——让关羽和张飞在古城相会,张飞误解关羽已降曹操,要杀关羽,关羽不得已杀了追踪而至的曹操大将蔡阳以证清白。可以说,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夸大甚至神化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
事实上,文本所书写关羽的忠义之事存在着矛盾:一是降曹;二是华容道放走曹操。类似的忠孝书写矛盾在《水浒传》、《西游记》中都有体现。《水浒传》中的宋江江湖上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其含义可从元代无名氏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第五折宋江道白可知:“安邦护国称保义,替天行道显忠良。一朝圣主招安去,永保华夷万载昌。”一部《水浒传》正是按照这个中心来展开的,可见,此绰号“呼保义”是写宋江对于朝廷的耿耿忠心;“孝义黑三郎”写宋江对于父亲的孝顺;“及时雨”写宋江“济人贫困,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之江湖、兄弟之“义”。这三个绰号反映了宋江的“忠”、“孝”、“义”,不仅如此,小说最终让宋江归顺了朝廷,为朝廷效力,并在小说的名称上加以体现——《忠义水浒传》。据此,小说是将宋江按照忠孝仁义的人物形象来塑造的,换言之,小说中的宋江是忠孝仁义的化身。
事实上,文本关于宋江的忠孝仁义书写存在着诸多矛盾。按照正常的社会秩序来衡量宋江所做之事,即可明白这些矛盾之所在。晁盖抢劫生辰纲事发,朝廷派人抓捕,身为国家公务员的宋江,不但不协助办差,反而阻挠并通风报信,当是出卖国家机密罪;晁盖上梁山后感谢宋江救命之恩,宋江与之书信金钱往来,当是交通盗匪罪;浔阳楼题反诗,上梁山为盗魁,聚众攻州战府,是为十恶之首“反逆”罪。如此书写,宋江如何“安邦护国”?而江湖上“呼保义”之美誉,也有些名不副实。
宋江杀死阎婆惜,身陷囹圄;身为匪盗,公然对抗朝廷;甚至将父亲与家族一同迁到梁山。西汉贾谊认为,孝有四层意思:仁慈贤惠、爱护亲人是孝;按时祭祀先祖是孝;五世安乐是孝;顺于德而不违是孝。宋江于此这四点无涉,显然,其“孝义黑三郎”之绰号至少是当不得“孝”字的。
再看宋江的“义”。为保命,杀死阎婆惜;为弄权,将体现晁盖领导思想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为断扈三娘后路,攻打祝家庄时允诺不攻击内应扈家庄,结果却将扈家庄杀个鸡犬不留;为忠义,招安于朝廷,希望在战场上挣个封妻荫子,结果108位梁山统领阵亡了81人;为顾全自己忠义之名声,毒死李逵,并暗示吴用、花荣尽忠(两天后,两人在宋江坟前自缢而亡)。
小说将宋江所作所为视为“义”、将宋江本人看做“英雄”与“忠良”,高度赞扬了宋江的忠孝义。这种忠孝评价,明显与宋江行事存在着矛盾。而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矛盾,有人说宋江对宋朝是愚忠,也有人如清代金圣叹斥责宋江虚伪奸诈,无“忠”可言。可见,在忠义上,《水浒传》文本存在着“一个二极悖逆的价值选择”③。
《西游记》中孙悟空闯龙宫、闹地府、乱蟠桃盛会、大闹天宫,都是不忠不孝之事。对其所做的惩罚是让其保佑唐僧西天取经,并答应事成之后让他修成正果。事实果真如此,孙悟空因此最终成为诸天神佛之一。西天取经固然是一件无量功德,但与孙悟空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就渺小得多了。因为西天取经只要如孙悟空之流者皆可胜任,并非孙悟空不可,是谓小忠;但孙悟空此前所为乃谋反,是谓大逆,大不忠。以小忠而掩大逆,可乎?可见,在忠与不忠的书写问题上,小说存在着抵牾。
第二,忠孝书写的调和。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存在的悖论是不可忽视的。它既影响忠孝书写在文本上的表达程度,更影响读者对于忠孝的解读。小说家在加工或创作作品时,力求在文本上尽可能地调和忠孝书写上的冲突。
《三国演义》中,关羽忠孝书写的悖论,可以桃园三结义盟誓词来解释——“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关张结义是以“义”与“恩”为核心价值,这也是维系刘关张三人集团的精神支柱。在此情况下,关羽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以是否符合恩义为标准进行判断。所以,屯土山约三事是缘于忠义,华容道释曹操是缘于恩义。④小说还写了关羽托梦刘备,诉说自己含冤而死,要刘备为其报仇,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再三劝阻,倾全国兵力攻打东吴,兵败而刘备不久去世。此事在很大程度上当基于盟誓之“义”。对于曹操之恩遇,关羽一直念念不忘。小说自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再写到关羽时往往加上“汉寿亭侯”封号——此封号是曹操借汉献帝名誉封给关羽的(其实为曹操所赐封),甚至其帅旗上也大书这一封号。刘备及其集团并未觉得不妥,而是欣然接受了。关羽纵敌而于军法当斩,而刘备出面求情饶恕之,亦是基于不能“背义忘恩”这一核心价值。故,《三国演义》中关羽忠义的自相矛盾才能得以解释。
《水浒传》中,宋江忠孝书写悖论的调和,从《临江仙》词可窥全豹:“起自花村刀笔吏,英灵上应天星,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济弱扶倾心慷慨,高名水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这是宋江出场时作者称赞宋江的一首词。词中,作者高度赞扬宋江其人,说他是济弱扶困、甘雨四方的豪杰,将宋江忠、孝、义都一一展示给读者,为宋江形象的塑造定下了调子。小说中,宋江种种行为常常与“忠”、“义”发生冲突,为调和这一矛盾,小说让宋江“将人生理想的实现圈定在既存的礼制秩序之中,将内心的冲动压缩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并将这一‘自我设限’作为通向理想彼岸的桥梁。这样一来,‘兼济天下’的人生构设,便变做了‘忠义’人格的自我实现,对上讲‘忠’,对下行‘义’。……这,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人生标准:‘我一生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⑤基于此,才有宋江种种悖论的行为。
三、忠孝书写的王朝投影
文本自身忠孝书写产生的悖论并非涉及忠与不忠、孝与不孝这样简单,悖论的调和亦是如此。即使同一题材、同一部小说忠孝书写主旨相同,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其境遇也是不同的,其原因就是小说的忠孝书写有着王朝深刻的投影。
一是王朝兴衰影响着文本忠孝书写。王朝兴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唐传奇产生于盛唐而兴盛于中晚唐,纵览整个唐传奇主旨,诚如学术界所言,文人汲汲于仕途经济,所撰传奇多为驰骋才情,罕见涉及忠孝者。安史之乱前,李林甫当政,藩镇逐渐尾大不掉,唐朝乱象渐显,忠孝节义受到严重冲击,文学史上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目的是重建李唐王朝的道统与文通,惜乎李唐江山已朽,这场运动最终失败。与唐代古文运动相呼应的是《高力士外传》,其虽书写高力士忠孝,但也只是凤毛麟角。《聂隐娘》传奇,尽管在客观上书写了忠义,但不是该小说的真正主旨,且这一忠义不是体现传统王朝所提倡的忠义——只是忠于割据一方的诸侯。这就偏离了古典小说关于传统忠孝的书写。唐朝的强盛及其崇尚功名之风,使得早期唐传奇过于传“奇”而驰骋才情,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如此,忠孝主旨就不是小说书写的对象。唐玄宗后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由盛转衰,朝廷上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地方上藩镇割据而相互攻伐,道德沦丧,君臣大义淡漠,有识之士试图扭转这一局面却回天乏力,《高力士外传》可谓那个时代孤独的天籁之音;而《聂隐娘》体现的忠义则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畸形儿。唐传奇多作于文人之手,他们原本是传统忠孝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国强而营营于功名,社会动荡则忘记了或回避忠孝。宋代建立于战乱,道统需要重建,而文学上出现了重建道统与文统的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了成功。宋代传奇《隋炀帝海山记》极力提倡忠孝与抨击臣子的不忠不孝,话本小说《梁公九谏》书写了文臣对于朝廷的铮铮忠心,民间话本“说三分”中的拥刘抑曹等,都是道统重建的反映。而《五代史平话》之刘知远故事,则是忠孝书写的民间演绎。元代社会黑暗,民族矛盾尖锐,文人仕进无望,但传统的忠义观并未消失,依然为文人所继承。话本《红白蜘蛛》的忠孝书写,是文人在对朝廷忠孝无法实现之时的一种寄托。这种情况在元杂剧《单刀会》、《救风尘》中都有体现。明代立国,政治与统治思想上先严而后松,古典小说对于忠孝的书写亦随之而变化。明洪武立国至嘉靖时期,政治高压,统治思想严酷,要求对皇权绝对的忠诚,文学与艺术必须反映忠孝伦理。这一时期,王朝发布的禁戏令可以与小说忠孝书写相互发明。明代崇祯之前,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不仅体现王朝意志,更为社会所接受,都与其所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二是王朝对于书写忠孝与否的小说之暴力干预。明清两朝不仅严禁有伤风化的淫词小说,而且不少原本被认可为书写忠孝的小说也受到了王朝严禁。遭禁的书写忠孝之小说,如《龙图公案》、《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尤以《水浒传》遭禁为最严。崇祯时期,社会动荡,原本为统治者所欣赏的能体现忠孝的部分古典小说,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王朝的宠儿变成了打击对象。崇祯十五年下旨严禁《水浒传》与山东李青山起义有关。此时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统治者直接忽视了小说本身忠孝书写的正能量,反而视宋江等人的忠义为李青山之流造反所模仿的形式与对象。《水浒传》不但不再是“忠义”之书,而是统治者眼中的诲盗“贼书”、“妖书”。于是,此前深受大明王朝认同的《忠义水浒传》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清朝亦多次严禁《水浒传》,如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同治等朝都严禁《水浒传》。尤其是咸丰以后,满清政权外忧内患不断,大厦将倾,统治者极端仇恨《水浒传》。明清两代的做法,与其说是否定水浒之忠义,倒不如说是防止百姓效仿水浒借忠义之名行造反之事。这样,《水浒传》原本弘扬的“忠义”就成为当朝者眼中倡乱的“悖逆”。他们不再关注水浒的忠义,而是极力否定,认为水浒是“教诱犯法之书”,不仅导致无知小民扰乱地方社会秩序,还会严重威胁当朝统治地位。无怪乎自明崇祯以至清末,《水浒传》一直被统治者视为反面教材而严加禁止。嘉庆帝说:“无知小民,多误以盗劫为英雄,以悖逆为义气,目染耳濡,为害尤甚。”正表明了统治者暴力干涉《忠义水浒传》的真实心态——以国家暴力手段来规范子民按照王朝意志行事,显示出了明清王朝对于忠孝的迫切需要。
应当承认,古典小说的忠孝书写诠释了封建王朝的国家意志,弘扬了小说所处时代的道德需求。忠孝的书写以及王朝的影响与干预,两者都有同一指归:有利于国家稳固,社会和谐。这对于当下小说乃至文艺作品的创作不无借鉴意义。
注释:
①袁闾琨、薛洪责力主编:《唐宋传奇总集·唐五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②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③冯文楼:《“忠义”:一个二极背逆的价值选择》,《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④⑤李冬梅、张雅芳:《论关羽的忠义形象》,《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责任编辑刘保昌)
I206.5
A
1003-854X(2015)11-0094-06
刘怀堂,男,1968年生,河南罗山人,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湖北孝感,4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