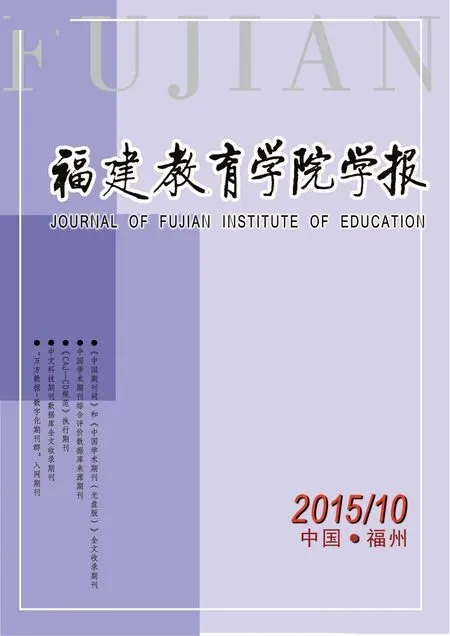主题与地域视域下的中国现代刻字艺术
王毅霖
(福建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福建 福州 350000)
现代刻字是一种以刀代笔,以书法为载体,以木板为材质(也包含竹片等),融设计、摄影等艺术样式于一身的新型艺术门类。尽管我们可以把传统刻字艺术的源头上溯到原始时期古人类的岩字画等历史上,但作为现代刻字艺术却是全新的语言,并且其由来与邻国日本、韩国息息相关。正是其特殊的来源促使了今日刻坛多元的、有趣的,甚至是难堪的境地。当然,造成这种状况主要的原因远非这些。
一、民族麾下的“主题”与“地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刻字艺术由日、韩传入中国。迄今为止,现代刻字艺术在国际地位上,日本始终占据重要的堡垒,这与其常到欧洲展览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对现代刻字艺术的尊敬。而中国这个东方传统文化大国迅速地体会到了这种不平等的尴尬:一方面,新的形式为书法艺术陈旧的面孔带来了新鲜的容颜,许多人为之雀跃;另一方面,现代刻字是由日、韩这两个曾经一度为古代中华文明附属国度传递过来的艺术门类,这使这个一度以先生自居的中华突然之间要变成一个坐在小板凳上聆听教诲的学生,于此,许多艺术家难以接受。现代刻字艺术必须为其源于日韩的出身感到羞愧?许多书法家趋向于这么认为,只有在自身传统文化乳汁的哺育下,中国现代刻字艺术这个新生儿才能得以健康成长。于是寻找属于自身文化风格的焦虑开始漫延。这样时刻,形式无疑是最为简捷的途径,“主题刻字”应运而生,换言之,民众必须为这种进口转国产的艺术支付“主题”的附加税。
何谓“主题”,许多学者已经为我们理清其来源和语义,大致为最初源于德国音乐术语中的主旋律,后经日本传入中国,意为“作品题材”或“中心思想”。[1]216至于把“主题”引入刻字艺术是1998 年的事,在经二届全国现代刻字理论研讨会上,中国刻字艺术委员会致力推出“主题创作”这一概念,并以此为目标。“‘主题创作’将是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必须进行汇纳和总结,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2]14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影响,“我们曾明确提出了发展‘主题刻字’的构想,从理论和创作角度倡导和实践了‘主题刻字’的创作理念,这有力地引导了当时的刻字创作,其后全国刻字展的一些优秀作品大多受到了这一创作理念的影响”。[3]3可以见得在淘到“主题”这个舶来的词语时,中国刻字艺术委员会的诸多领导们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芝麻开门的钥匙,他们的欢呼声犹然在耳。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主题”对于中国现代刻字艺术而言决计不是随风凭浪而至的飘流瓶,它源于八九十年代对母体文化追问的思潮,在寻根文化强大的背景之下,民族主义作为众多签子被有意抽出的唯一一支并奉为神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换言之,八九十年代对母根文化的追问是这出戏剧宏大的背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母根及存在的追问的声音重重交叠杂错并缠绕在几代人的心中。
因此,“主题刻字”无疑是一种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姿态,中国特色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文化维度,即便走入了“学院派”的胡同里同样是一种大义凛然。本能民族性的觉悟和苏醒演变成了一场运动,主角是一些自视甚高的倡导者,轨道上冲刺着的是一些对书法、美术不甚了解的爱好者,铺天盖地的呐喊掩盖了粗糙简单的技法与形式。民族精神异化成为一种运动无形的盾牌,对肇事者的奖赏促使运动的持续与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量的统计使自尊心得到了惬意的满足,“我们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刻字国家”“书法与刻字的母国”这些口号重新使我们引以为豪。重塑大哥的形象是某些领导的夙愿与毕生追求,这足以擦除八九十年代我们效仿日韩刻字的民族情感上留下的痕迹。
风格突围是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之下以“主题刻字”为口号进行的。民族精神的麾下不仅有“主题刻字”还包含了“地域风格”。在“主题刻字”的大背景下,“地域风格”悄然来临,缘于刻字委员会某些领导的大声斥喝使这个孱弱的身姿逐渐岸然。值得玩味的是他与“主题刻字”如影随形,尽管某些大力提倡主题刻字的领导们声色俱厉,“地域风格”依然存在。虽然往往只是以作品的形式默默地存在,但倔强地站立的姿态始终没有改变。主导的意识没有意识到二者其实就是一对孪生儿。时常相互的指责、排斥、相互竞争,刻坛热闹起来,煞是一番风景。
然而,当我们再次把视线投入“地域风格”的来源和出处时发觉的是只有几句语焉不详的说辞,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提及不是对“地域风格”的提倡,而是大声斥责:“在国内,作者个体之间的风格也可完全独立出来,避免目前所谓的‘地域风格’所造成的近亲繁殖,这种近亲繁殖是一种畸形的发展。”[3]4除此之外,来自正面的声音杳然无声息。考据其出处不得不借助非正式出版的采访:“‘地域风格’是2004 年在厦门举办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的评审中提出来的,当时黑龙江、福建等省份体现出了较强烈的整体风格,于是一些评委提出了‘地域现象’和‘地域风格’的说法”。
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和“地域”往往被认为是治理后现代“全球一体化”的一剂良药,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大概理应以此为荣。
对“主题刻字”的反击仅仅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态度的声明,地域风格若意欲在中国刻字占一席之地就必须真正地开辟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空间的架构在于地域性和个体性,并以对中国书法、地域文化、本土哲学等母体文化寻求某种特殊的特质加以强化和培植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魅力所在。
“从20 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怀疑主义的欠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5]107同样,主题刻字的提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这种倡导怀疑的欠缺。怀疑主义的欠缺导致“主题刻字”产生何种后果也许只有在将来我们才会猛然悔悟,若干年后的理论家在盘点代价之时也许才会对其份量有个大概的估算。
培根说:“没有主题的艺术和装饰品并没有根本的区别。”[6]86以理推之,现代刻字若能冠之以艺术的作品,主题是其必不可失的要素。简言之,优秀的刻字艺术作品必定要有主题。那么,“主题刻字”对于主题的提倡是否就是一种画蛇添足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一场骑驴找驴的游戏。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主题的语义能否作为一种形式的代言体。换言之,就是“主题刻字”或“主题风格”称呼本身是否有问题?此外,没有主题的作品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吗?“主题刻字”能否承载现代刻字的所有的表现形式与存在意义,现代刻字艺术语言本身可不可以仅仅作为一种审美的形式,就像是风景画?
二、模式的诅咒
当主题成为一种代言体,“主题刻字”成为中国刻字的主导方向,刀法和线条的表现力无疑成为主题的一种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语言内在的形式美导致了主题的淡化,悍卫“主题”无疑必须在刀法和线条的表现上作出让步和牺牲。这才使学院派的拼贴主义得以借尸还魂。尽管存在主义者和表现主义们的嘲笑是可以至之不理的,在某种程度某个时间的维度上,“主题”的提倡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大而无当的口号。恢复艺术的整体性要求反对一门综合的艺术论为单独的类型和形式。
对某种主义,某种“主题”的倡议和鼓吹无疑是走向多元主义的反面,这时权力往往是多元化的一个最大的阻力。当然,权力往往也要接受多元力比多的冲击,这种冲击力有时也会冲垮权力筑成的堤岸。有趣的是,这种力比多有时也来自倡议者的内部乃至本身。吕如雄《矛盾》与王志安《战车》就是一个胜于雄辨的例子。简单的拼贴主义连倡导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产生风格过时的想法,并且越来越看清这不过是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风格胡同,在这个样板的胡同里,剪刀加浆糊大行其道。
“主题刻字”提供的一种精神范式和形式图式对“个性”形成无形的压抑与扼杀,在注入民族的强心剂之后,支撑起的不过是一个个长相相似、面无表情的作品躯壳。对于入展的崇拜、欲望或渴求使众多投展者变成了盲目服从的群体,艺术家的主体审美在权势的压力之下异化变形,围绕着所谓“主题”的一系列符号被不断重复再现和强化,作品的价值标准也得以悄然地转移。个性被权势所移植,在“主题”的掩盖下,他性的审美被合法化。此外,随着时日的进展,“主题”在概念上的修订和风格上的扩张无疑是一种必然的举措。“主题”的扩张导致了对“地域风格”地盘的裁减和侵占,凭借着理论的话语权把“地域风格”挤兑到“雷同”的字眼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策略。确定一个标耙,攻击它,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与功绩,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更何况这种阴谋被识破的机率不高,从而使“主题”在早期“地域风格”的领地上插满自己的旗帜,旗帜的撤换是在对各种理论文章和写手们收编后的掩饰之下进行的。
地域风格具有的强烈地域色彩和个体特性,被权势话语逼迫得要以雷同性作为自己的最大特征。非彼即此的单纯思维使“主题刻字”的空间得以拓展,对于地域风格语义蕴含空间的暴力压迫使自身阵地得以扩张,把地域除雷同以外的空间巧妙地掠夺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尽管个别理论家把“主题刻字”的橄榄枝垂向福建刻字界,没有理由和迹象表明,刻字界甚至是福建刻字界对这种青睐表示认可和欢迎。勿庸置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个别理论家的眼里,“主题刻字”的命题意义转移了。侍少华的分门别类可以解读为是一种柔性的批判。在其书刻创作的五种取向列举的四个“主题刻字”的作品中,福建籍的陈秀卿、洪顺章的作品赫然在列。[7]96尽管侍氏的视域还是没有超越“主题”的地平线,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分门别类要比把“主题刻字”界定于剪刀加浆糊之下的形式之中来得高明。但这并不说明早期的“主题刻字”是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口号,这个美学形式口号的提出隐含了诸多观念与想法,蕴涵着的是在强势的日本刻字权势笼罩之下“风格突围”的理想。然而,随着时日的发展,即便抛开命名暴力带来的语义不符,中国刻字艺术的发展已然撑裂早期的命题空间。
此外,再次观照地域风格,即使无法从理论上寻求支持的呼声,地域风格依然没有放弃实践上的行动。但当自发的群体审美认同感演变为一种有意的对抗时,行动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地域风格成为一座堡垒后,灰颜色与单调的构图和刀法成了与外隔绝的城墙与护河。的确,“主题刻字”对“地域风格”的指责也并非是空穴来风,风格的整体性也可能导致另一个极端,“雷同”与审美认同感仅仅一墙之隔。地域风格作为“本土”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确是可以提倡和发扬的。但是绝不能以此作为一种风格准则、一种艺术标杆。立足于地域(本土)对从广大的国度、姐妹艺术、甚至以国际的视角去汲取养分才是这门艺术以“现代”为前提的正确走向。因此,合理的发展群体、完善的教学体系,理论后盾的培养等等皆是相当重要的前提。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激情四射的召唤,隆重而热闹的开场,三月半载的狂热,直至最后的撤退甚至是抛弃,没有高度的推进,没有深度的掘入,没有标高,没有方向,这种教育勿宁说是一种西绪福斯式的苦役。在这个狂热的群体下,以艺术为名号只是使之聚集的一个充分的理由,美学追求被名利的欲望逐渐吞噬以至只占边缘角落十分狭小的一个份额,存在主义炽热的灵魂业已遁迹,蒙住个性眼光的是权力异化的形式和名利崇拜编织成的罗网。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合理的发展体系迫在眉睫。
某种程度下,我很欣赏“游牧”这个词,它在一定的意义下象征了彪悍、自由,甚至是侵袭。这是一种新生的姿态,是一种活力的姿态。一门新生的艺术,没有理由与底蕴去固守,就像是守住一座空城堡一样的没意义。倘若我能为此生造出一个词来,那就是“文化游牧”了,鲁迅先生不是说过“拿来”吗?那更适合现代刻字艺术。反之,如果我们固守一种或几种倡导下产生的风格,走入模式的牢笼在所难免,风格取向的价值判断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8]15
三、“现代”的深渊
清理一下中国刻字艺术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全国第三届刻字艺术展后的中国现代刻字走向了语言的自觉,到了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这种语言体系已经臻于成熟,王荣兴作品的设计形式感与书法完美结合成为现代形式与古典元素结合的楷模;刘洪洋作品的黑白分割淋漓尽致地彰显水墨的意境;吴刚作品则是极尽巧妙地展示文字结构、笔画的借用之道;洪顺章作品形式的雕塑感与文字内容深邃的语义和文性糅合在一起;蔡劲松作品体现一种雕塑立体的体积美与文本内容的高度契合;郑建松作品以其圆刀去抒写如诗的夕阳之景,起伏有致的圆刀有如田园虫鸣之声此起彼伏,诗性的韵律与节奏是艺术家心性在刀笔交织的篇章上的投影。
然而,古老的格言就如梦魇般地缠附于现代刻字艺术,“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其划定的一个圈。2004 年的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之后,中国现代刻字艺术从形式到语言等诸多层面没有得到多少的拓展,究其原因乃自身内部几对矛盾的作祟。其一,艺术专业对作者艺术素质的高要求(通常要求作者必须具有良好的书法基础、美术功底、甚至其它诸如摄影、设计、雕塑等综合的素质功底)与当前从事其中综合艺术素质较低的作者群体的矛盾。其二,新型艺术发展中艺术高度建构的需要与进入后现代艺术时期各门类艺术无中心、无目标的艺术大环境的矛盾,导致刻字艺术发展道路的茫然性,以及前景的不可瞻性。其三,创作精英精力或视线的转移导致艺术创作高度和深度的停滞,与新门类艺术急需不停建构艺术高度和深掘艺术深度之间的矛盾。其四,新型艺术需要市场的扶持与市场还未对新型艺术腾出适当位置和空间的矛盾。此外,来自高层提倡的形式蜕变成一个坚硬的躯壳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发展是其一个关键致命的因素。
在现代刻字艺术作品之中,书法线条的灵魂中心地位演变为承载刀法的形体和支起作品构图的结构。在“刀法”的牵引之下,刻字从传统的牌匾之中走了出来,并独立形成一门新的门类。随着时日的推移,前辈“刀法”作为情感或美感代码的功能被后来者继承和发扬,逐渐走向抽象和写意是现代刻字艺术作品的一个走向。当然,在一些前卫的探索者那里也有可能被演变为一种形而上的代言体,这种时刻,语言、思想、主题、内容与传统书法是召其回归的一种天籁之音。由此可见,书法和刀法是刻字艺术作品的骨骼和血肉,色彩则是其皮肤和衣饰,由书法及刀法的张力、字法的形式和作品的内容样式、形体以及色彩的关系构成刻字作品的性格、气质、格致,乃至灵魂所在。
然而,比较尴尬的是,与篆刻艺术不同的是现代刻字艺术并非书法艺术门类中的一个纯血统的家族成员,对这个混血儿美丑的评判失去了寻常的基准,我们也就不难于理解一个纯书法家对于刻字艺术所表现出的纯血统的甚至是贵族式的优越感。此外,如果说现代刻字艺术即将取代书法成为现代人新式的审美对象确是夸大其词了。但某种程度上,书法这种纯抽象艺术的审美因子可以籍现代刻字开拓出汉字美学的另一个维度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现代刻字艺术的原动力是对平面书法艺术的革命或补充,但这门艺术高度的实现又只能求助于书法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以汉字为表征的东方文化的深层次理解而迂回地抵达。书法的体系提供了同时也限制了刻字艺术想象的空间,传统是现代的源和根,但传统往往也是压抑现代刻字创作想象空间之源——在中国文化的世界里没有边界的飞翔只是一种虚无的幻象,数千年发展和传承起来的书法体系及其种种因子是刻字艺术想象的地心吸引力。当然,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现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断裂,这种断裂时常使现代刻字陷入两难的境况,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是一个没有哪一个艺术家能够振臂一挥而形成一呼百应的时代。引领着某种风格、走向代表着时代标高的大师还没出生,也没有哪个能人能对现代刻字艺术的未来作预示的占卜,存在的意义只是某些思想警惕者不得其解的思索与追问。“重大题材”与“宏大叙事”[9]14-15是否就是刻字艺术未来的坦途与大道?这种提倡是一种刀笔当随时代还是另一种流行样式?这都是个有趣问题。在艺术上提倡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背景之下,业内权威们的振臂呼号是否就是一种指向光明的引导?还是不过又一场大而无当的倡议?刻字的内容、形式到载体又能否承载如此份量的重任?或者仍然不过是倡导者的一厢情愿!
不过,这种挣脱了诗书画印樊篱的新型艺术似乎一产生就与西方现代艺术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表现与“民族”和“传统”存在诸多的错位。无疑,现代刻字不可能像怕生的小孩躲避外人一样地躲避在传统书法这个家长的背后,大胆前冲所迎来的有可能是明媚阳光的沐浴也有可能是滂沱大雨的洗礼。形式表现的现代性与内容载体的传统性是一个时常开裂的伤口,不时地舔着伤口或置之不理都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在对传统碑帖刻意模仿的作品上大红大绿色彩涂沫的行为只是后现代人对失去深度的历史进行的一厢情愿的怀旧,犹如站在T 台上染着黄发绿发戴着假睫毛的模特却又穿着古代服装一样的诡异。历史和传统被粗劣的现代形式所腐蚀,厚度和深度因此变得虚幻了起来。
在后现代大行其道的背景下,现代刻字艺术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与文艺复兴人本思想相比,表面上,后现代艺术似乎意欲要把艺术从艺术家的专利手中移交给大众。实际上,后现代艺术的目的不在于实现什么,在于解脱,这是后现代艺术家对工业社会的挣抗,大众可能只是一个幌子。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人人都不是艺术家,继上帝死了之后,应是艺术家也死了,产生艺术的法则坍塌了,传统游戏规则终结了,人本只是新游戏的一个籍口。
当然,“主题”和“地域”的自觉性是否会撑破其形体从而坠入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深渊是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部分前卫的韩国刻字可以印证这一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其作品从“刻字”的框架走了出来,进入了意识与理念的深渊。失去理性的意念与灵光一现交互编织成一张破碎的网,零乱地缠绕在作品之上,杂乱无章且无礼地强迫观赏者的接受。这种用西方地沟油炸出的东西无论其有多美的外包装,都是一种有毒的物品,甄别与摒弃需要美感与智慧。
[1]郭清华.论“主题刻字”艺术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构建[A].全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
[2]吕如雄.全国第二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序[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转引自《全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
[3]王志安.简论中国现代刻字艺术之发展[A].全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
[4]2010 年11 月20 日陈秀卿电话采访,采访人王毅霖.
[5]南帆.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天兵.西方现代艺术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侍少华.中国书刻艺术[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8]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李庶民.主题创作是现代刻字艺术的自觉[A].全国第三届现代刻字艺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