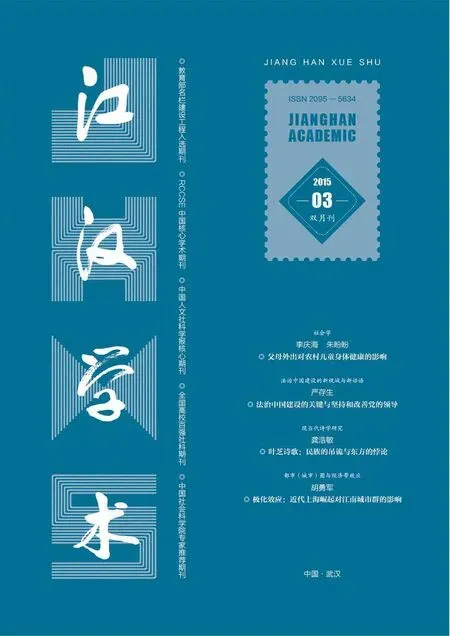为什么
——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段从学
为什么
——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段从学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600031)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细读;符号性主体;死亡
一、一首“透明”的诗?
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以下或简称《枫树》),是近乎完全“透明”的一首诗。一方面,是诗本身的“透明”:通篇上下没有隐晦曲折的表达,词语、意象和诗行,无不以最原始的样态和含义,一目了然地裸露在那里,没有歧义,无需解释。它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作者本人已经不止一次站出来,对创作背景、写作动因等问题做了详细交代和说明,把这首诗放置在了众所周知的透视装置里。所以诗歌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之一二三,很快就被总结和归纳出来,成为了文学史的常识。剩下的,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尤其是学校课堂上——重复其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最终让它从一首诗,变成“诗知识”,消失在无休止的人类知识增长链中。总之,《悼念一棵枫树》就是悼念一棵枫树,一切都已经被“看透”,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根据既有结论和常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枫树》之为“好诗”的理由和根据了。
但这样一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牛汉为什么——要悼念一棵枫树?
正常情况下,悼念的对象不言而喻应该是人。而且,还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任何一个人,而必须是某个做出了重大或较为重大贡献的人。通俗地说,就是“人物”,或者“重要人物”。村上的阿猫阿狗死了,也要开个追悼会的习俗,虽经领袖大力提倡,但至今仍未形成风气,就是这个道理。把植物,把一棵枫树当作悼念对象,确实难以理喻。
再说了,统计学数据无可置疑地表明,我们这个世界上随时都有人在死去。对绝大部分人来说,死亡因此早已经成了不再会引起任何关注的符号和数据。动物的死亡,植物的死亡,那就更无需关心,根本就是不可能被我们留心与看见的事。牛汉为什么要“悼念一棵枫树”的死亡呢?为什么只有牛汉,才为这棵枫树写下了悼词?
二、“这首诗”的结构与节奏
关于一首诗的知识,只能描述性地告诉我们“这首诗”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而不能告诉我们“这首诗”是什么。存在不等于存在者。关于一株小草的知识不等于一株小草。拥有关于一首诗的知识也绝不等于理解了“这首诗”。关于《枫树》的“诗知识”,可能恰好阻碍了我们对《枫树》这首诗的阅读和理解。
理由很简单。关于一首诗的知识,只能在“这首诗”已经在我们面前摆出来、成为对象之后,才能被我们抽象和归纳出来。而理解一首诗,却不能停留在结果上,不能站在“这首诗”面前来作抽象而冷静的观察、分析和归纳。我们必须进入内部,从源头开始,在词语、意象和气息的引导下,体会和触摸“这首诗”从无到有,从开始到终结的过程。只有在这种“入乎其内”的过程中,才能让一首诗从僵死的结果,复活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过程。理解,就是放弃自我固有的位置,进入并体验另一种生命过程,在突破自我中寻找丰富自我、改变自我的可能。面对牛汉这样的诗人,面对《枫树》这样“透明”的作品时,更是如此。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枫树》理解为一个由远及近,再由近入远的过程。“在秋天的一个早晨”,诗人首先在远离枫树的地方,和“几个村庄”、周围的山野、山野中的草木等等,同时“听到了,感觉到了/枫树倒下的声响”。一种巨大的震颤和悲哀,驱使着诗人向着这棵已经倒下了的枫树急切、但却又沉重而迟缓地奔过去。急切,当然是出于对枫树命运的焦虑和关心。沉重和迟缓,则是不愿意相信枫树已经被伐倒的事实,不忍心看见枫树被伐倒的样子。这种不愿,也不忍的心情,让诗人把急切的焦灼变成了沉重的伤痛,变成了走近那已经倒下了的枫树时的疑虑、缓慢和沉重。
焦虑和关心,让诗人迅速抛开一切,把所有的感觉都集中在了枫树上。而因不愿和不忍而来的迟缓,则让诗人在奔向枫树的过程中,敏锐而又痛苦地注视着与之有关的一切:
家家的门窗和屋瓦
每棵树,每根草
每一朵野花
树上的鸟,花上的蜂
湖边停泊的小船
都颤颤地哆嗦起来……
一个以枫树为中心,关联着周围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的世界,由此而被呈现出来,构成了一个亲密的生存整体。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个亲密的生存整体却是以枫树被伐倒,以死亡和消失的方式,才第一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唯其如此,它曾经的亲密性也就更令人痛惜,更加显示为一个巨大的悲剧性存在。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是由于悲哀吗?”这行诗,其实是多余的败笔。最初的版本,将它单独作为一节,尤其显得刺眼。从语义上看,事实就摆在那里,它提出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回答。这个预先设定了答案的问题,其实是把这个亲密生存整体“颤颤地哆嗦起来”多样而丰富的含义单一化了。它如此明显地从诗人的角度来要求和推测一切,其实是把刚刚以死亡和消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亲密整体,再一次压缩到了人的世界里。从整首诗的感情节奏上看,它其实非常突兀地跳出来,打断了由急切和迟缓两种反应交织而形成的厚实而强大的情绪流。牛汉曾经说过,冯雪峰、曾卓等都批评过他不少诗作总是“差那么一点”而难以再往前跨一步,进入“完美的境地”的问题,承认自己有时候确实对技巧和形式存在偏见,对诗意锤炼不够,存在“没有去尽非诗的杂质”[1]的问题。“是由于悲哀吗?”这突兀而多余的一问,在我看来就属于《枫树》“非诗的杂质”。
回到《枫树》上来。在急切和沉重的迟缓两种情绪交织而成的复杂心情的推动下,越来越接近枫树的诗人,首先嗅到了枫树散发出来的清香。这飘忽的清香,证实了诗人不愿、也不忍承认的残酷事实:枫树已经被伐倒,生命气息正在消散。芬芳的清香,袒露了枫树贮蓄在生命内部令人意想不到的美。这种在死亡中才袒露出来的美,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棵枫树之死的悲剧性。正因为这棵枫树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美,它的死亡也就越加令人悲伤。“芬芳/使人悲伤”的理由,就在这里。
循着令人悲伤的芬芳,诗人最终来到被伐倒的枫树面前,近距离凭吊这美丽的生命:
躺在草丛和荆棘上
那么庞大,那么青翠
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
还要雄伟和美丽
正如芬芳的清香更加凸显出枫树之死的悲剧性一样,被伐倒的枫树以它的庞大、它的青翠,它的雄伟和美丽,再一次为自己的死亡,增添了浓厚的悲剧性。而我们的诗人,也最终完成了由远及近地感受和观察枫树之死的过程,最终站在了被伐倒的枫树面前。
接下来,我们分明看见诗人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被伐倒的枫树周围,整整三天,看着这美丽的生命被一点一点地肢解,痛入心扉地感受着一个生命无可奈何的消失。在诗的后半部分,诗人一方面继续追踪着枫树本身,关注着这个美丽的生命如何用“亿万只含泪的眼睛/向大自然告别”,用它“凝固的泪珠”和“还没有死亡的血球”,向世界发出最后的抗议、最后的呐喊。令人痛心而无奈的是:这告别,这抗议,这呐喊,本身却又是枫树的生命走向死亡,走向消失的见证。
一方面,诗人自始至终紧紧扣住在消失和死亡中呈现的枫树的美丽。枫树以美丽昭示消失和死亡的悲剧性这个张力结构,把视野从远处的山野,一点一点地最终推进到了只有近距离的凝视才能看见,才能体会到的枫树“还没有死亡的血球”。这个由远及近的过程,也是一个由外部一点一点渗到枫树内部,细致入微地展示其所有的美丽,用生命的美昭示其消失和死亡之巨大悲剧性的过程。
为了加强高职英语混合式学习方法的应用,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教师必须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好充分的课前准备,可以使教学活动更加完善,教师要对学生的水平、理解能力与接受能力进行调查了解,以此制定具有教学目标,同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完善的微课内容,且要与学生的日常实际结合。二是课中的应用,教师在课堂中要积极的应用该学习方法,发挥其优势与作用。三是课后工作,在教学结束后,教师可以利用微课平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学习兴趣、登陆频率、在线时间等,据此掌握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并据此对教学内容进行改善;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利用该平台与学生进行积极的交流,解决学生的问题和疑问。
另一方面,在紧紧抓住枫树本身,以其生命之美昭示消失和死亡的巨大悲剧性的同时,诗人又反过来以枫树为中心向外拓展,揭示了这棵枫树与周围世界的亲密关联。枫树被伐倒,湖边的白鹤失去了栖息之所,远方的老鹰失去了家园。在《枫树》之前,牛汉写过一首《鹰的诞生》,其中描述鹰筑巢习惯说,“江南的平原和丘陵地带/鹰的窠筑在最高的大树上,/(哪棵最高就筑在哪棵上)”。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棵被伐倒的枫树既然是湖边山丘上最高大的一棵,鹰的巢穴必定会筑在上面。“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的老鹰,必定是来凭吊它消失了的家园。——甚至,是怀着巨大的愤怒和痛苦,前来寻找失散了的亲人。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牛汉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时期留下的一则诗学笔记中得到印证。这则名叫《长颈鹤为什么沉默地飞》的笔记写道:
黎明前后,常常听到嗖嗖的声音,划过静穆的天空。出门仰望,就会看见一只只雪白的长颈鹤急速地从远方飞回来,村边几棵枫树上有它们的窠,雏鹤呱呱地叫个不停。天空急飞的白颈鹤一声不叫,只顾奋飞,我最初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一声不叫,沉默地飞多么寂寞。后来晓得它们的嘴里都噙着小鱼,还有几滴湖水。[2]
枫树已经被伐倒之后,还习惯性地“朝着枫树这里飞翔”的白鹤,无疑就是曾经在枫树上筑巢,哺育过一代又一代幼小的生命的白鹤,就是在这棵枫树的巢穴里长大,长大成为母亲、成为父亲的白鹤。它们的家园,它们的生命记忆,随着枫树倒下而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一棵枫树不是孤零零的一棵枫树,它是白鹤的家,鹰的家,无数生命赖以栖息的生活世界。它的死亡,因此也就不单单是一棵树的死亡,而是一个世界的死亡。诗人对枫树之死的痛惜,和对伐树之举的控诉,最终被同时推向了顶峰:
村边的山丘
缩小了许多
仿佛低下了头颅
伐倒了
一棵枫树
伐倒了
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
诗人既是在悼念一棵枫树,一棵青翠、雄伟而美丽的枫树,更是在悼念一个美丽而鲜活的生命的死亡,一个亲密生活世界的毁灭。
三、诗人的复活
枫树已经被伐倒,被肢解成宽阔的木板,永远地消失了。诗人痛心疾首的悼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变成了只有对人类来说才有意义的行为。这就是说,牛汉之所以悼念这棵被伐倒了的枫树,想要“写几页小诗,把你最后的绿叶保留下几片来”,其实是为了唤醒自我,把生命中的某种感情复活并保存下来。问题,因此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牛汉,究竟为什么——要悼念一棵枫树?《悼念一棵枫树》究竟唤醒了诗人怎样的情感体验?
对此,我们必须遵循诗人的指引,彻底抛弃“通过X表现了Y”的流行思路。诗人牛汉最讨厌的就是“通过(某首)诗表现了什么”的逻辑,“它把诗的语言降低到奴隶的地位,仅仅当成一种工具”,活生生地扼杀了语言和诗人的平等互动关系[3]。写诗不是表达一个已经摆在那里了的观念或世界,而是创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世界。诗人与诗相互发明,相互给对方以生命。他再三强调说:“谈我的诗,须谈谈我这个人。我的诗和我这个人,可以说是同体共生的。没有我,没有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没有我的诗。”“如果没有碰到诗,或者说,诗没有找寻到我,我多半早已被厄运吞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诗在拯救我的同时,也找到了它自己的一个真身(诗至少有一千个自己)。于是,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4]
诗人说得很清楚,《悼念一棵枫树》就是悼念一棵枫树:“我当时并没有想要象征什么,更不是立意通过这棵树的悲剧命运去影射什么,抨击什么。我悼念的仅仅是天地间一棵高大的枫树。我确实没有象征的意图,我写的是实实在在的感触。这棵枫树的命运,在我的心目中,是巨大而神圣的一个形象,什么象征的词语对于它都是无力的,它也不是为了象征什么才存在的。”枫树的死亡,本身就是独立自足的事件,一个应该为之哀悼,为之“写几行诗”,把它“最后的绿叶保留下几片来”的事件。
个中原因,首先当然是牛汉不止一次在回忆中谈到过的这一棵枫树,和诗人在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血肉关联。从1969年9月到1974年12月,诗人被迫在咸宁向阳湖从事最繁重的劳役,“浑身的骨头(特别是背脊)严重劳损,睡觉翻身都困难”。为了减轻身体劳损的痛苦:
那几年,只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我总要到一片没有路的丛林中去徜徉,一座小山丘的顶端立着一棵高大的枫树,我常常背靠它久久地坐着。我的疼痛的背脊贴着它结实而挺拔的躯干,弓形的背脊才得以慢慢地竖直起来。生命得到了支持。我的背脊所以到现在(年近七十)仍然没有弯曲,我血肉地觉得是这棵被伐倒了20年的枫树挺拔的躯干一直在支持着我,我的骨骼里树立着它永恒的姿态,血液里流淌着枫叶的火焰。
特殊历史关联铸造成的生命感,让牛汉在枫树被伐倒之后,“几乎失魂落魄,生命像被连根拔起”。写诗悼念这一棵枫树,就是为了不让“它的伟大的形象从天地间消失”,“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5]。
这一棵枫树长成了牛汉的骨骼,化成了牛汉的血液。它被伐倒了,诗人生命的一部分就死亡了,消失了。写诗悼念这一棵枫树,保存它的伟大形象——请注意“伟大形象”这四个字的质量感——,“把它重新树立在天地间”,就是让死亡的骨骼重生,让消失的血液复活,把它们重新树立在天地间。这是我们理解牛汉何以要郑重地“悼念一棵枫树”,感受汩汩流淌在诗里的沉痛感的入口和起点。
这个理由,足够让牛汉悼念这一棵枫树吗?够了。但问题,似乎不止这么简单。
四、自然之死的生命意蕴
停留在牛汉特殊历史情境中的个人经验层面上,实际上等于把诗人降格成了生活在个人有限的喜怒得失里的自私之徒,一具被个人经验和情感束缚起来了的僵尸。诗歌,也相应地,变成了传达个人生命情感的工具。“通过(某首)诗表现了什么”的死亡逻辑,仍然是诗人、诗歌,和正在阅读《枫树》这首诗的我们的主语。
我们已经看到,即便在诗与诗人的关系维度上,牛汉也极力反对把诗歌和语言当作工具,自始至终在强调诗歌拯救诗人,给诗人带来新生命的积极意义。一首诗之所以能够从作者转移到读者,从诞生的历史语境转移到阅读的历史语境,恰好就在于它超越作者有限的个人情感,创造了一个更为阔大的生活世界。为此,我们必须超越诗与诗人情感经验这个入口和起点,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当时特殊的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悼念一棵枫树》究竟创造出怎样一个新的生活世界而“拯救”了诗人。
为了避免重复文学史的老生常谈,这里不再详述《枫树》的创作背景,而只是立足于理解问题的必须性,把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提炼为这样两点。第一,以对待政治敌人的“革命态度”,把整个世界当作改造和征服的对象,肆无忌惮地把人类的暴力施加到大自然身上,从而造成了自然生命大规模的死亡。第二,活生生的人被要求成为“革命事业”的驯服工具,以便切实保证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革命事业”能够按照权力的指令有条不紊地持续展开。包括牛汉在内的大批文化人,被当作“牛鬼蛇神”,强行送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从事繁重劳役,身心饱受折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造其思想,使之成为“革命事业”的驯服工具。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前者是对待客观世界,后者则是对待人类自身的基本态度。
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根据它所涉及的对象,把这两种基本态度割裂成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而事实上,这两种基本态度乃是同一回事。人类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但把自己当作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主体来看待,却是近代以来才逐渐明确起来的现代性态度。人类并非天生就是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主体。相应地,世界也并不是天生就是客体,就是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客观对象。只有在对世界采取改造和征服性的“革命态度”的地方,人类才变成了主体。同理,也只有在人类成为改造世界和征服世界的主体的地方,世界才变成了客体,变成了客观世界。作为主体的人类,和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事实上都是同一种“革命态度”的产物。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其实就统一在这种“革命态度”里。
“革命态度”笼罩一切,支配一切。这,就是《枫树》诞生的历史语境。在这历史语境中,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越彻底,也就越是要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主体,变成单一可控的行动功能。“劳动改造”,乃是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统一体。延安时期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早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改造自然也同时即改造人性”[6]。在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劳动中,人变成了“劳动力”,变成了“劳动价值”,变成了单一且可计算和交换的功能性符号。
逻辑上,只有首先将人改造成主体,改造成单一可控的行动功能之后,才有可能展开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革命行动”。对人的改造因此而占据优先地位,变成了先于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而展开的“革命行动”。时间上,牛汉等大批“牛鬼蛇神”,就是在被这样那样的“革命行动”打入另册,从活生生的人变成各式各样的“分子”之后,才被发送到向阳湖,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从事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繁重劳役,以此“改造思想”的。
牛汉从改造世界的革命者变成了被改造的“分子”。向阳湖从自然性存在,变成了被改造和被征服的客观世界。作为“分子”的牛汉来到了向阳湖。作为“客观世界”的向阳湖进入了牛汉的生活。向阳湖在毫无节制的主体性暴力肆虐下的死亡,触动了牛汉的诗思。诗人回忆在咸宁向阳湖从事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之“革命”时的情形说:
大自然的创伤与痛苦触动了我的心灵。由于圩湖造田,向阳湖从一九七〇年起就名存实亡,成为一个没有水的湖。我们在过去的湖底、今天的草泽泥沼里造田。炎炎似火的阳光下,我看见一个热透了的小小的湖沼(这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湖最后一点水域)吐着泡沫,蒸腾着死亡的腐烂气味,湖面上漂起一层苍白的死鱼,成百的水蛇耐不住闷热,棕色的头探出水面,大张着嘴巴喘气,吸血的蚂蟥逃到芦苇秆上缩成核桃大小的球体。一片嘎嘎的鸣叫声,千百只水鸟朝这个刚刚死亡的湖沼飞来,除去人之外,已死的和垂死的生物,都成为它们争夺的食物。向阳湖最后闭上了眼睛……,十几年来,我第一次感到诗在心中冲动。[7]
向阳湖的死亡,鱼类、水蛇等自然生命大规模的死亡,触动了牛汉的诗思。这种诗思的真实含义是:以死亡的形式,向阳湖将自身从作为被改造和被征服对象的“客观世界”呈现为鲜活丰富的有机生命,呈现为鱼的生活世界、水蛇的家园、蚂蟥和水鸟的栖居之地。“向阳湖最后闭上了眼睛”,恰好是它之为生命世界的见证。
向阳湖之死,让牛汉从“革命态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以人,而不是以“劳动力”的主体性眼光来看待大自然。向阳湖从被征服和被改造的“客观世界”,转化为有诞生和有死亡的“生命世界”,牛汉也就从符号性的“劳动力”和可计算、可交换的“劳动价值”转化成了“人”,——鲜活生动且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对枫树之死的沉痛悼念,就是在这种把大自然当作生命世界来对待的奠基性态度中生发出来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而把《悼念一棵枫树》理解为对那棵被伐倒了的枫树居高临下的怜悯,把诗人当作大自然的拯救者和解放者。
前面说过,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前提是对人的改造和控制,大自然成为“客观世界”的前提是人类成为主体。只有在预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从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变成了单一可控的主体的地方,大自然才从鲜活的生命世界变成了有待改造和征服的“客观世界”。世界成为“客观世界”,和人类成为主体,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现代人通过把世界设置为“客观世界”而建构了人类之于“客观世界”的主体性神话,以此掩盖自身同样处于现代性“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之中,同样生活在有待改造和征服的“客观世界”里的事实。世界越是成为“客观世界”,人类也就越是成为主体,越是更深地陷入到“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之中,越是从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变成单一可控的主体。“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8],人类也就越是被牢牢地束缚在单一可控的主体性地位上,越是与鲜活的生命世界相隔绝。
反过来,也只有在世界从“客观世界”转变成生命世界的地方,现代人也才会挣脱“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从单一可控的主体转化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诗人牛汉也才会由“分子”,复活而为“人”。
这种转化得以发生的契机,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在“革命态度”将自身设定为世界的标准和尺度,“革命战士”和“正常人”变成了同义词的特殊历史语境中,作为“分子”的牛汉却被从“正常人”的社会秩序里被剥离出来,进入了直接面向大自然,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生存维度。这种被剥夺的特殊经验,为牛汉挣脱“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提供了可能。
人来到世界上,不可避免地要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和他自己打交道。任何一个人,都必然要同时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维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绽现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现代性“革命态度”的问题,就在于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准则,而且是仅仅适用于部分特殊人群的关系准则,强行放大为普遍性的生存原则,施加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完全不同的生存维度上,最终把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扭曲成了单一可控的符号性存在。被剥夺了“革命战士”资格,从“人”变成了“分子”的牛汉,在直接面对向阳湖的时候,也就是在早已经被严重扭曲了的人与社会这个生存维度之外,获得了重新发现大自然,发现自己的机会。牛汉回忆说:“那时我失去了一切正常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卸去了一切世俗的因袭负担,我的身心许多年来没有如此地单纯和素白。我感到难得的自在,对世界的感情完整地只属于自己,孤独的周围是空旷,是生命经过粉身碎骨的冲击和肢解后获得的解脱。”诗人由此真切地触摸到了大自然的生命的脉动,“我觉得一草一木都和我的生命相连,相通。我狂喜,爆发的狂喜!没人管我,我觉得自己就是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从社会历史领域的另类“分子”而成为“天地人间的小小的一分子”,牛汉豁然间恢复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与灵动。“我的生命有再生之感”,他郑重宣告说。[9]
很显然,这种解放感和再生感,仍然局限在诗人一端,没有触及到大自然对诗人的拯救问题,尚不足以构成“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的整体生存论关联。必须将同时发生在大自然一端的变化,即大自然如何将自身展现为鲜活丰富的生命世界而唤醒牛汉,最终引领着牛汉挣脱“革命态度”支配和束缚的问题考虑进来,才能理解牛汉何以要说“我与我的诗相依为命”,才能真正理解牛汉何以要“悼念一棵枫树”。
那么,大自然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将自身展现为鲜活的生命世界的呢?答案是:死亡。向阳湖的死亡。枫树的死亡。
纯粹的大自然本身是匿名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客观世界”或“生命世界”之分。只有在遭遇到人之处,它才从匿名中显现而为大自然。进而,也才有了“客观世界”或“生命世界”之类的划分。而人类,也才能通过对大自然的划分,或者把自己确立为单一可控的主体,或者把自己确立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从“革命战士”的角度来看,向阳湖的消失乃是圩湖造田的“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向阳湖消失得越快,越彻底,就越能激发“革命战士”的主体性豪情,越能证明“革命事业”的正当性。
但对牛汉来说,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死亡是生命世界所特有的事件。“客观世界”不会死亡。“向阳湖最后闭上了眼睛”,恰好说明此前的向阳湖是有眼睛的生命。“死亡的腐烂气味”,恰好说明这一切并非“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是生命在肆无忌惮的人类暴力面前的大规模死亡。诗人瞩目于自然生命大规模死亡,进入并逗留在死亡阴影中的过程,就是从“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中挣脱出来,将自身确立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的过程。自然生命的死亡越是呈现得触目惊心,诗人距离“客观世界”也就越远,也就越深入到生命世界内部,他的生命也就越自由,越丰富,越生动。
具体到《枫树》一诗,就是:被伐倒的枫树,以死亡的形式将自身揭示为“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一个丰富生动的生命世界——白鹤的家,老鹰的家,无数生命的栖居之所。诗人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被伐倒的枫树周围,沉浸在他的芬芳之中,查看他的青翠美丽,感受他凝固的眼泪,聆听没有死亡的血球的呐喊的过程,就是挣脱“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从“客观世界”进入生命世界的过程,就是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的过程。诗人对枫树之死的体验越是强烈,在失魂落魄中逗留越久,拯救和复活也就越彻底。写诗,逗留在枫树之死的阴影中,进而将这种逗留永久地保存下来。
枫树以自身的死亡,引领着牛汉完成了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到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的复活。枫树以自身的死亡,“拯救”了牛汉,让牛汉从“分子”转化成了“人”。因此,牛汉之所以悼念这一棵枫树,绝不是惋惜一个有价值的“客观世界”之消失,更不是因为自己生命之一部分之死而发出自私的哀叹。这种悼念,是对大自然的感激,对世界的感激,对“拯救”了自己的另一个生命的感激。也只有在这里,在对枫树的感激之中,在对世界的感激之中,牛汉才彻底摆脱了将世界当作有待征服和改造的“客观世界”,摆脱了将世界敌视的现代性“革命态度”的支配和束缚。
世界从“客观世界”转化为“生命世界”之处,也正是牛汉从无休止地向他者索取有价值之物的贪婪攫取者复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第一义的诗人”之时。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把世界当作“生命世界”来对待,他就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生命的自由与生动。牛汉当年悼念一棵枫树,我们今天细读《悼念一棵枫树》,意义就在于此。
[1]牛汉.差一点[M]//学诗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36-137.
[2]牛汉.没有形成诗的札记·长颈鹤为什么沉默地飞[M]//牛汉.学诗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157.
[3]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M]//刘福春.牛汉诗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901-902.
[4]牛汉.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M]//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
[5]牛汉.一首诗的故乡[M]//牛汉.梦游人说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36-37.
[6]中央财政经济部关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的通报[M]//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291.
[7]牛汉.对于人生和诗的点滴回顾和断想·诗又在心中冲动[M]//牛汉.学诗手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3.
[8]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M]//孙周兴,译.林中路:修订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94-95.
[9]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81.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
Why to Mourn for a Maple?——Reading Niu Han’s PoemMourning for a Mapleand Commemorating Him
DUAN Cong-xu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00031,China)
The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 to Niu Han’s poemMourning for a Maple,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author's poetic idea,but also difficult to tell clearly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the poem.Placing NIU Han’s mourning behavior in hostil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modern people and nature,by text close reading,we can uncover the modern connotation of the poem.As the object,nature and maple actually wake the poet with a special way of death,raise him from a single controllable subject to a free vivid life.So,the poem is an expression of tribute and thanks from a saved life to his savior.
Niu Han;Mourning for a Maple;close reading;symbolic body;death
I207.209
A
1006-6152(2015)03-0048-07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8
2014-12-10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段从学,男,云南楚雄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