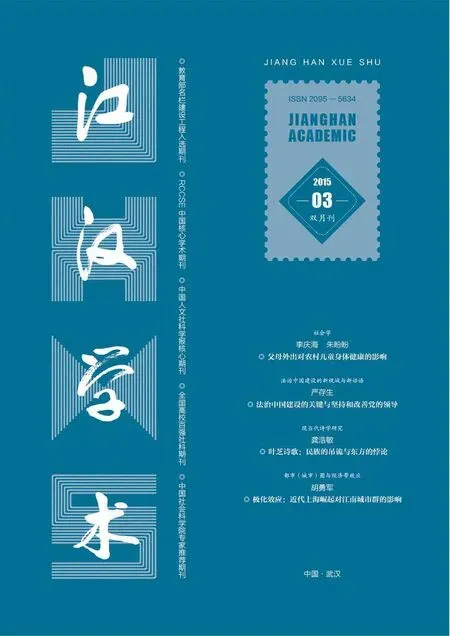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及其正向引导
——对科塞社会冲突论本土化的辩证
杨晓虎
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功能及其正向引导
——对科塞社会冲突论本土化的辩证
杨晓虎
(海军蚌埠士官学校社科部,安徽蚌埠233012)
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交融、分析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助力。但受地域、人文、传统差异的限制,外来理论实现“本土化”是实现正确借鉴的重要前提。当前,在国内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的大背景下,在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引介于中国实践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辩证,既要认识到其“正功能论”前提假设多、过于注重权力要素、理论体系不完备、部分命题有失偏颇的不足,还要看到对冲突原因的多维分析、冲突类型的科学划分、冲突突破底线的警示等重要现实启示。进而辨析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具有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社会制度变革和产生社会治安问题、形成不良示范效应、累积社会负面心理的正负双重功能。对此,要在推进制度化管理、把握矛盾焦点、注重多措并举等几个方面消解社会冲突负功能,加强正向功能引导。
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功能;群体性事件;本土化
近年来,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社会冲突问题研究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可谓著述众多、成果颇丰,但总体上研究视域不够开阔、研究层次不够深入,对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对策等现实表征、实践需要相关议题探讨得多,概念、类型、功能等内涵本质探究得少。尤其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解有失偏颇、国情观照不足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了“食洋不化”的批评,有学者尝试展开“本土化”探讨,但整体上看仍停留在理论框架的宏观思考,有针对性地个案研究还不够。鉴于此,本文以西方政治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为切入点“解剖麻雀”,力求全面认识该理论的得失之处,并结合国情特征提出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正负社会功能以及正向引导的对策思考。
一、对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辩证把握和有益借鉴
西方政治社会学以整合理论(亦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冲突理论为主要代表,二者围绕着社会秩序的建立、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长期的对话和争论。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反战示威等社会冲突频繁发生,传统上注重系统分析的整合理论保守倾向明显,解释社会现实矛盾问题的实践性较弱。正如有关评价所言,整合理论“不重视各种主要的和实际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几乎无法通过系统分析的概念工具得以周详的处理”[1]。在此背景下,擅长于解释政治危机、社会矛盾的社会冲突理论逐步发展壮大,科塞、达伦多夫、科林斯等社会冲突分析学家逐渐占据政治社会学的主流地位,其中尤以刘易斯·科塞最具代表性。
(一)对科塞社会冲突正功能论的辩证把握
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最具创新价值的就是其社会冲突正功能论,当前许多国内学者用之为群体性事件“正名”,但其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必要对其进行辩证。科塞社会冲突正功能论的提出,颠覆了帕森斯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指出冲突对于社会团结、一致、整合同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正功能可分为五个方面,即保证社会连续性、降低社会产生两极对立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尽管科塞花费大量篇幅建构其冲突正功能论,但从其理论推导和结论看,一是存在诸多前提假设。他认为,只有当社会冲突的核心内容不涉及基本价值观、信仰时,社会冲突才具有积极功能;而且只有在“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冲突才会得到制度性的解决,也才能为社会系统的重新整合提供一个契机。此外,涉及有关冲突烈度时,即使是科塞思想的启发者齐美尔也认为,社会冲突过于激烈,将会对社会整合产生消极作用。因此,不加条件限制的、或者有太多假设变量的所谓正功能说,只能是一种理论臆断。如果要做理论移植借鉴,其所要经历的改造将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二是过于注重权力的作用。正如所有的冲突理论一样,“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社会冲突,把复杂多变的社会冲突归因于对权力的争夺,试图以单一的理论原则来解释丰富多彩的人类现象,无疑有一种简单主义倾向”[2]。科塞提出的社会冲突正功能论,目的就在于为社会冲突找到解决之道,并最终通过调整社会权力关系,实现社会变迁。这显然深受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坚持将权力看作是人们的主要目标和社会关系的首要特征,零和博弈的观念始终挥之不去,早已被当今时代社会冲突的化解方法所证伪。
三是理论体系不完备。社会冲突正功能论出现后,理论界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过:如果从“质”的角度看,社会冲突有正负之别,那么从“量”的角度看,社会冲突保有一个什么量,才能保持其正功能呢?能不能计算出冲突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之前让它持续发展并继续发挥正功能?在一个什么样的量的临界点,可以实现社会冲突的质量互变呢?还有的学者提出,当冲突对于一个群体是正功能而对另一个群体是负功能时,会发生什么结果?尤其是面对这样的疑问——既然社会冲突具有正功能作用,那么社会冲突还有必要予以解决吗?这就否定了社会冲突正功能论的存在意义。可见,科塞的社会冲突正功能论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理论模型还不够完备。
四是部分命题有失偏颇。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有利于形成群体意识,建立群体疆界,增强群体的团结,促进群体进一步发展壮大;冲突可以加强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中人与人的联系,促进群体团结。站在某一群体的角度看,社会冲突可以发挥上述正功能。但若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出发,独立成群、拥有较强内部联系、具有强烈抗争意识的群体将会逐步脱离社会规范、制度的制约,另寻一种对其有利或被其认可的价值观,进而引发对当前社会的反感、厌恶乃至对抗。因此,所谓社会冲突强化社会群体团结的命题,必须审慎看待,不可盲目将其定义为社会冲突的正功能。
总之,国内学者通过引入社会冲突“正功能论”,客观上对理论创新、乃至治理方略的由堵到疏均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内涵丰富、地域特征明显,“正功能论”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盲目地宣扬附和或断章取义,不仅不利于理论求解,且在实践中也会引致群体性事件治理走上歧途。鉴于此,有必要对科塞社会冲突论予以批判扬弃,以全面辩证的观点再做探讨,以求为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提供更为准确和科学的借鉴。
(二)对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有益借鉴
尽管社会传统正功能理论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其理论创新价值突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特纳的评价,“科塞的冲突观仍然是当前最富有全面性的成果之一”[3]。尤其是在对社会冲突原因的分析、类型的划分和突破底线的警示等方面,对理解当下的社会冲突仍有积极意义。
1.对冲突原因的多维分析
科塞借鉴格尔(Gurr)的“相对剥夺感”相关理论,并将其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相结合,论证了社会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和临界点。他认为,社会冲突的爆发并不完全在于社会成员对自身利益的“意识觉醒”,而是一种“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这比绝对剥夺更容易引起不平等的感受,也更容易引起冲突。因此,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必然的稳定,而相对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才能带来秩序和安定。其次,还要认识到由分配不公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只有当这种主观感受迫使被剥夺者不再认同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时,社会冲突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冲突发生的临界点在于现存制度合法性的危机程度,冲突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或否定。由此,科塞将“相对剥夺感”的主观社会心理因素与社会制度的客观合法性问题相结合,为冲突发生找到了更为深刻的原因。此外,科塞进一步将冲突发生的根源分为物质性因素和非物质性因素。物质性冲突因素,是指权力、地位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均;非物质性冲突因素,是指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以及制度性的歧视。科塞认为,所谓非物质性的原因(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一致)源于“社会合法性的撤销”,即人们对现有制度的怀疑或信心缺乏,不再认同现有制度的合法性。一般来说,物质性冲突的烈度较小,而非物质性冲突的烈度较大,若前者延续时间较长,可能演化成后者,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伤害。
2.对冲突类型的科学划分
科塞根据不同标准将社会冲突划分为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紧密关系中的冲突、意识形态冲突与分裂型冲突,其中从冲突性质和色彩的角度把冲突划分为“现实性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更具指导价值。前者是指那些由于某种要求未能得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评价而发生的冲突,其目标指向明确,冲突只是手段;非现实性冲突是指基于其中一方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引发的冲突,缺乏明确的目的,具有随意性、多变性、非理性的特点。结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新变化来看,以“非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非现实性冲突越来越多,一些社会成员将个别社会成员之间的纠纷激化为干群矛盾、族际冲突等,如贵州瓮安事件、潮州古巷事件。究其原因,此类非现实冲突的发生是目前社会结构僵化的结果。通过对比两种冲突类型可以看出,在一个对冲突没有提供或未能提供充分容忍和制度化的社会结构里,冲突易于导致社会机能失调。不仅政府机构应对乏力,难以控制冲突规模、冲突烈度,甚至使现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也受到挑战,只有创新旨在推进社会融合而不是人为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社会冲突的发生、恶化。
3.对突破底线的重要警示
科塞在明确社会冲突正功能的同时,也提出社会冲突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变革。若在社会冲突中,双方不再认同社会系统得以合法建立的基本价值,这种冲突就会毁灭社会结构。据此,他认为防止社会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不至于被社会冲突破坏的根本,存在于自身社会结构中,这是由冲突的制度化和承受力提供的。对于当前中国社会频发的社会冲突来说,政府要面对的不是消灭冲突的问题,而是如何消解、缓和和利用冲突的问题。从西方冲突理论得出有益启示,社会冲突的治理更应选择“整合(Integration)”,即通过各种方式将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组成社会结构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功能等予以协调,缓解冲突,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规范、有序的平衡体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及其一般化程度。具体对于社会冲突而言,就应该寻求制度化的渠道,为社会提供一个制度允许、公众接受的利益诉求通道、情绪疏解环境,让社会冲突既能发挥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又能实现社会警示器的功能。
二、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功能辨析
恩格斯说过:“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4]历史唯物主义者始终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客观规律,并认同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泉。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社会转型期,“现代化需要社会所有主要领域产生持续变迁这一事实,意味着它必然因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各种群体间的分裂和冲突,以及抗拒、抵制变迁的运动,而包含诸种解体和脱节的过程”[5]。有学者悲观地认为这是转型陷阱,出现了“社会断裂”,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肌体自我更新的重要契机。对此,必须充分认清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正负功能,合理定性各类社会冲突,有效引导其发挥正功能。
(一)正功能
1.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在诸多抗争政治研究者看来,社会冲突可以起到“减压阀”的作用,对于社会中部分群体减轻或缓解敌对情绪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里的冲突必须在可控范围内,否则这种正功能将不再存在。在当前中国社会屡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抗争一方通过采取各种手段,表达诉求、释放情绪,可防止对抗状态的进一步持续、恶化,避免抗争式的集体行动失控。以广东古巷事件、新塘事件和沙溪事件为代表的外地人与本地人的族群冲突,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后期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置,否则这些外来底层族群在可用资源少、抗争成功率低、自组织空间小的背景下,一旦因打压转入地下,黑恶化带来的矛盾问题将更为严重。这三起事件的爆发,恰好为社会矛盾提供了减压阀,避免其走向激化。
2.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社会冲突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宣泄和利益表达,之所以演化为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反映的就是抗争主体在诉求过程中的无处表达、无法表达和无效表达。从近些年的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来看,不论是信访制度的改革,还是网络监督的积极回应、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建设,甚至包括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显示出党和政府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意愿和努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在社会建设相关章节中着重提出,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6]。
3.推进社会制度变革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7]一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社会变迁本身不会导致大规模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温床。同样道理,群体性事件频发既是深刻社会变迁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管理不及时不到位的“体制性迟钝”的表现。社会冲突对推进制度变革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将其自身纳入制度化轨道,更为重要的在于能够推进政府善治效能的制度建设。如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事件,在网络内外的联动推进下,收容制度最终被废止。潮州古巷事件后,潮州市委书记骆文智表示,要建立外来人员利益诉求表达及优秀外来人员激励机制、工资集体协商及正常增长机制。[8]尽管当前制度性的变革还不显著,涉及领域还比较有限,但变革的步伐已经迈出,剩下的就是沿着正确轨道走下去。
(二)负功能
社会冲突的负功能研究,可以说自社会冲突出现就受到重视。即使是强调其正功能的科塞看来,社会冲突也会产生分裂、破坏群体的团结,引起群体结构的解体,导致社会不稳定等负功能。以中国群体性事件为例,有关研究更为多见。从政府的角度看,“群体性事件的危害”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危害,包括各种暴力行为直接造成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事件处置耗费的大量投入和对当地投资环境和市场秩序的破坏;二是政治危害,包括对政治稳定的负面影响、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可能为敌对势力提供的可乘之机;三是社会危害,包括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干扰、社会危机的加重等。[9]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社会冲突将会产生下述三个方面的负功能。
1.产生社会治安问题
社会冲突一旦发生,不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否面临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政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除少数网络群体性事件外,这已成为中国群体性事件的必经阶段。从广东乌坎事件来看,一些学者鉴于其后期动员组织、分工实施等过程显得相对平和有序,被认为具有标本意义、里程碑价值,但事件前期9月21日—22日的示威游行还是演化成了小规模的骚乱,当地的合泰工业园工地,及丰田畜牧场、海上餐厅、富荣针织厂等部分企业,均遭到打砸,部分民众与赶来维持秩序的军警也发生了肢体冲突。
2.形成不良示范效应
乌坎事件得到初步解决后,同属陆丰市的石碣镇再次因土地问题在市政府门前聚集近百人,要求政府介入干涉。实际上,这是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一旦一个类似议题的矛盾纠纷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解决了,其他相似问题也将遵循此道。如浙江东阳画水事件、福建厦门PX事件、江苏启东排污事件,三者发生时间相继,核心议题都与环保相关,采取的方式也主要是群体抗争。这是由于传统全能政府、单位体制暴露出的责任主体定位和权利实现路径等方面的思维惯性依然存在,逐渐演化成当前国民的一种普遍心态——“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甚至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一种“刁民”理论,“即在某种情境下,由于稳定话语的两面性和过往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绥靖立场,各类社会行动者也许会逐渐意识到,扮演‘刁民’极有可能收获‘刁民’利润”[10]。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某一起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不良示范效应,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效仿,社会冲突问题很难实现和风细雨式解决。
3.累积社会负面心理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11]。也就是说,社会的人必然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心理对人的行为的深刻影响上。在湖北石首事件中,主要参与人群不仅包括作为当事人的死者家属,还包括当地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事发地的周边村民和石首市的普通市民,他们或者抗议事件未得到公正处理、国有资产在企业改制中大量流失,或者抗议企业征地过程中的过低补偿、本地社会治安的每况愈下。在此类群体性事件中,起初爆发的原因仅是群体性诉求中的极小一部分,更多的诉求支持了事件的持续扩大、恶化。这些诉求的过度集中,不仅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更为困难,而且人群之间相互传播,政府公信度受到极大削弱,相对剥夺感迅速上升,甚至人的理性会出现短暂迷失,和平抗争可能会演化为暴力流血事件。此类社会冲突的频发,社会负面心理逐渐累积,社会危机情绪蔓延,普遍价值观陷入困境,执政者的合法性将会受到越来越深刻的质疑。
三、正向引导的若干启示
有学者指出,“要管理中国的社会冲突,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学术任务,也是一项具有深刻政治和政策含义的学术任务。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社会冲突的本质界定;其次是对社会冲突性质的界定”[12]。科塞的社会冲突功能论为全面准确认识当前我国的社会冲突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但对待西方理论需要坚持辩证的观点,既要大胆借鉴、敢于引进,也要全面认识、辩证分析,还原科塞社会冲突理论的全貌,切不可为佐证个人观点而断章取义,否则将不能最大化地吸收其理论菁华。鉴于对上述科塞社会冲突论的理论辨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功能探究,可以在正向引导方面得出一些有益启示。一是从根本上重视制度改革,实现社会冲突的制度化管理。“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13]。当前,对冲突的管理要注重将制度创设从宏观管理层面向过程管理层面推进,注意将预防、预警、中期应对和善后工作制度化;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就要着力提高应对社会变化的制度化能力,将社会冲突管理纳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之中。二是在实践中把握矛盾焦点,充分认清社会冲突的现实特征。正如赵鼎新所言,中国社会在短期内绝没有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或革命的结构性条件,这些集体行动并没有大型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14]。但同时要注意物质利益冲突的不断升级,最终会导致“人民币解决不了人民内部矛盾”,既定政治框架内的改革必须积极稳妥地予以推进,要从利益结构调整、体制机制公正的角度,“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15],消除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三是从环节上注重多措并举,消解社会冲突的负功能。转型期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在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尚有市场,传统左派话语支离破碎的当下,一旦因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导致作为改革受益群体的时代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结盟关系破裂,支撑群体性事件的话语体系甚至意识形态将会很快显现。因此,要对社会冲突事件深入考察群体观念、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因素,防范被敌对势力利用;坚持将直接与非直接利益冲突全部纳入管理视线,防止更大规模的社会危害;同时对社会冲突分类对待,“对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置,同时也对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警觉”[16],做到“因事治宜”与“着眼长远”相统一,在改革策略上运用好“底线思维”,确保社会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
[1]Young O R.Systems of Political Science[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68:15.
[2]王威海.政治社会学: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95.
[3]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99-20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60.
[5]S·Z·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M].张旅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3.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8.
[8]广州市长回应新塘事件流动人口管理滞后敲响警钟[EB/OL].(2011-07-13)[2014-12-19]http://politics. people.com.cn/GB/14562/15146088.html.
[9]编写组.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70-77.
[10]刘能.群体性事件:分类框架及其分析潜力[M]//肖唐镖.群体性事件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16.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12]王敏敏.从帕森斯到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现象认识的深化[J].探求,2010(6).
[13]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6.
[1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98.
[15]习近平.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N].人民日报,2014-01-09.
[16]朱志玲.集体行动与集体行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J].理论月刊,2013(10).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
The Mass Incidents’Social Function and Positive Guidance in China——Discussion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oser’s Social Conflict Theory
YANG Xiao-h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Bengbu Naval Officer School,Bengbu 233012,Anhui,China)
Applying western theory to research problems in China is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exchanges and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But because of geographical,cultural and traditional differences,localization of foreign theory is the important premise.At present,in the context of that domestic mass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Lewis Coser’s social conflict theory must be analyzed when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s practice.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positive features:excessive assumptions,overmuch emphasis on the power,non-perfec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some propositions beneath less biased.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conflict,the dipartition of conflict types,the alerts of breakthrough conflict’s bottom line are very important and helpful.The mass incidents have dual fun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such as avoiding social conflicts,smoothing channels for expressing public opinion,promoting social system change and producing social security cases,forming nega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cumulating negative social psychology.So,we must remove the negative func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guidance in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grasping the focus of conflict and taking all types of measure.
Lewis Coser;social conflict theory;social function;mass incidents;localization
D632.8
A
1006-6152(2015)03-0013-06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02
2015-01-10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杨晓虎,男,安徽蚌埠人,海军蚌埠士官学校社科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