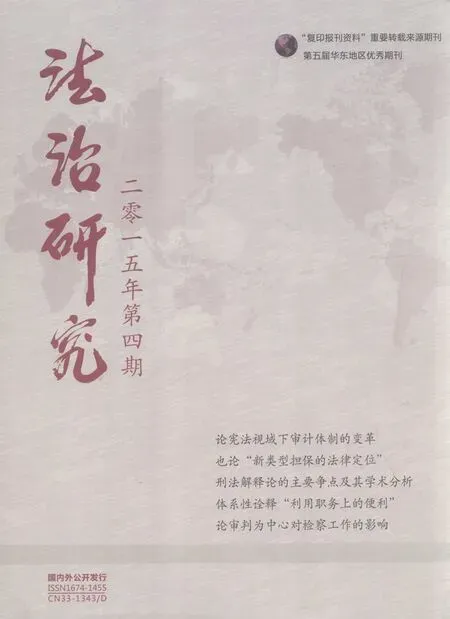可罚性理论: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超越
马荣春
可罚性理论: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超越
马荣春*
因遭遇违法性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分歧以及自身对“可罚性”的视野局限,故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应提升为可罚性理论,从而实现一种超越。在可罚性理论的视野下,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应是“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在可罚性理论视野下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应是一个保障人权功能更加健全有力的犯罪论体系。
犯罪论体系 可罚性 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 有责性
以具体判例为形成契机并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系来自日本的“舶来品”。正如其他“舶来品”,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也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了,表现为国内现有的少量著述先是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作一番脉络交代,接着联系我国《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等具体问题再给出一番所谓“借鉴”。而本文要拷问的是,“香飘中国”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本土语境”中就已经是至善至美的吗?
一、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由来及其理论牵引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形成于日本。按照日本旧烟草专卖法规定,如果烟草不卖给政府,则构成犯罪。但有某烟草耕作者受政府专卖局的委托种植烟草,却把应当向政府缴纳的七分烟叶(价格约一厘)留作自消。①分、厘为旧时日本的重量、货币单位,1厘=1/1000 日元。于是,当局便以违反旧烟草专卖法第48条第1项为由而将之诉至法院。在被一、二审法院均认定为有罪之后,被告人向当时的大审院即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大审院改判被告人无罪,其理由是:刑罚法规是用来规制“共同生活条件”的法规,而维持国家秩序是其唯一目的,故对刑罚法规的解释应参照“共同生活观念”而非“单纯的物理学观念”。虽然对于一粒粟、一滴水的侵害在“单纯的物理学观念”上也应处罚,但不会被“共同生活观念”所认可。那么,立于“共同生活观念”,轻微违法行为不必施以刑罚,而刑罚法规的立法原意也不应包含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刑罚制裁,但能够认定犯罪人具有特殊危险性除外。②[日]垣口克彦:《可罚的违法性论の展开过程》,载《阪南论集》第11卷第2期。对此案,被告人没有上交给政府的烟草仅仅是七分的微小数量,与其不惜费用和精力对之惩罚而有违税法的精神,倒不如不予过问,且被告人也不存
可罚的违法性的定语“可罚的”,最早由宫本英修提出,其所初成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有两个主要强调:一是强调在违法性判断之后再进行可罚性判断,即并非所有的违法行为都要予以刑罚处罚,而只有具备可罚性的违法行为才构成犯罪;二是其将可罚性的实质内容具体化为“可罚类型”,而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事由表述为“可罚类型阻却原因”。⑥宫本英修将“可罚类型阻却原因”大体区分为:①政治上的理由;②传统上的理由;③亲族间的情谊;④被害者的意思;⑤其他情形,包括“依照共同生活上的观念认为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被害法益的价值极为轻微的情形”、“行为的通常性”以及“强要的不当性”(期待可能性)等([日] 宫本英修:《刑法大纲》,成文堂1984年版,第124页)。宫本英修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刑法的谦抑品性为价值核心,故其被认为是最早论述了可罚的违法性。⑦同注⑤,第80页。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为基础,宫本英修结合自己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便提出了规范判断与可罚判断有先后区别的“违法—责任—可罚类型”的独特犯罪论体系。在其所创立的犯罪论体系中,可罚类型必然是违法类型,而违法类型未必是可罚类型。而刑法仅仅把广泛的违法类型的一部分作为可罚类型加以规定,即刑法仅仅必须用刑罚来抑制重大的规范违反类型。⑧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成文堂1995年版,第99页。
在宫本英修的理论基础上,龙川幸辰提出“应罚程度的违法性”概念。具言之,偷摘邻院一朵花的行为虽该当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不能认为成立盗窃罪;法官将用于制作裁判文书的裁判用纸用来书写私人信件该当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但不能认为成立职务侵占罪。只是具有违法的态度尚不能构成犯罪,而只有对法益造成重大侵害,始有刑罚抗制之必要,从而成立犯罪。总之,刑罚应当仅以不法行为中的重大者为目标,且以其他法律手段已经无效为必要条件。⑨[日]龙川幸辰:《刑法讲义》,弘文堂书房1930年版,第83页;[日]龙川幸辰:《犯罪论序说》,大同书院1938年版,第3页;转引自注⑤,第83~84页。“应罚”比“可罚”似乎说明着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力度”加大,同时也说明着“应罚程度的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有着相同的理论构造。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接下来发展与完成主要体现在对违法性本身的理解和把握上。首先是在整个法秩序范围内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二元论的对立问题。宫本英修等以违法一元论为基础来论及可罚的违法性问题。在违法一元论看来,违法性在全体法秩序中是统一的,即其他法领域中的违法行为在刑法中也必具违法性,故民法上的不法行为也应视为刑法上的不法行为,而不科处刑罚仅仅是因为欠缺可罚性而已。⑩[日] 宫本英修:《刑法大纲》,成文堂1984年版,第278~281页。与宫本英修等相对,团藤重光则提出违法相对性论。详言之,违法性虽然应当以全体法秩序为基础予以考量,但仍须根据法领域的不同来承认“法目的”的相对性。那么,其他法领域中的有效行为在刑法中可能具有违法性,而在其他法领域中的违法行为在刑法中也可能具有正当性。⑪[日] 团藤重光:《刑法纲要统论》,创文社1990年版,第136页。再就是对违法性本质的理解分歧。对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中的违法性,佐伯千仞立于客观违法论的立场提出结果无价值,即“违法”是对确认客观生活秩序的实定法律秩序的侵害或威胁。在对违法性的实质作结果无价值把握的同时,佐伯千仞指出,违法性是在根本上与全体法秩序的不相协调统一,同时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类型和轻重不同的阶段。进而,所谓可罚的违法性,就是指行为的违法性具有采取刑罚这种强力对策的必要,并且具有与刑罚相适应的“质”与“量”⑫[日]佐伯千仞:《刑法讲义(总论)》,有斐阁1977年版,第170~176页。。与佐伯千仞相对,藤木英雄则主要将可罚的违法性置于行为无价值论中予以考察和把握。藤木英雄对可罚的违法性的行为无价值论思考主要是假借社会相当性理论得以体现的。在其看来,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不仅仅要考虑实害即“结果无价值”,还应考虑“被害惹起行为脱离社会相当性的程度”即“行为无价值”。这样,藤木英雄在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中引入了社会相当性,并使得两者形成了“表里一体”的关系。于是,在以行为无价值论为基础的社会相当性论中来构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便成为藤木学说的最大特征。⑬同注④,第8页。藤木希望秉承威尔哲尔(Welzel)的“人的不法观”关于社会相当性理论以及行为无价值论的思考路径,突破了过去仅从结果无价值论来讨论可罚的违法性的局限,丰富了可罚的违法性的内容,确立了现在通行的可罚的违法性的二元判断标准。藤木英雄将融入了社会相当性内容的行为无价值论贯彻到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中,其对刑法理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容争辩的。⑭彭泽君:《日本刑法中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可以看出,对违法性是一元还是二元的分歧基本上对应着违法性是结果无价值还是行为无价值的分歧。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发展与完成中的分歧启发着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本身的改造乃至超越,因为分歧映现出不足,而不足隐含着完善。但是,完善不仅可以体现为原有理论架构下的修修补补,也可以或更可以体现为全新的或彻底的重新架构。
联系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为何会遭遇“违法性一元论”与“违法性二元论”亦即“严格的违法性论”、“缓和的违法性论”与“违法相对性论”的分歧,而此分歧又如何消解?这是其一。其二,在当下的犯罪论体系中,三元递进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越来越被认为是最具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犯罪论体系,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最终也是为了解决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即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于是,现有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便因其仅仅将“可罚性”的视野局限在“违法性”上而显示出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本身的严重不足。而我们的目的所在是从前述两点不足之中窥视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旨在追求人权保障价值的出罪功能是否存在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对违法性本身的理解与把握有别,故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出罪功能的发挥也便产生了分歧,甚至自相矛盾。正如龙川幸辰指出,偷摘邻院一朵花的行为虽该当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不成立盗窃罪;法官将用于制作裁判文书的裁判用纸用来书写私人信件该当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但不成立职务侵占罪。而对于“一厘事件”,小野清一郎首先认为这是构成要件的解释问题,即轻微的法益侵害行为原本就不该当各构成要件。构成要件的解释应该是立于社会通念而作出的是否值得刑罚处罚的考虑而非仅仅是形式的和物理学的判断。刑法本是将违法且有责的行为中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予以类型化的规定,故构成要件本来就应当包含“可罚的”这一概念,即可称之为“可罚的违法类型”⑮[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の理论》,有斐阁1953年版,第29~30页。。“可罚的违法类型”说明着构成要件本来应既是违法类型,同时也是可罚类型。于是,当某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则说明该行为便属于“可罚的违法类型”。而既然属于“可罚的违法类型”,又言行为最终不成立犯罪,总让人觉得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第二阶的“违法性”要件在发挥“违法性阻却”功能时显得“底气不足”。那么,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前述不足包括出罪功能的“局促”促使本文来尝试一种既意在消除分歧,又意在弥补不足的具有超越性的理论架构,且名之为“可罚性理论”。本文所提出的“可罚性理论”驾驭着这样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
二、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正如字面所说明的那样,可罚的违法性仅停留在“违法性”来考量可罚性问题。而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则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第一阶来考量可罚性问题,即意味着可罚性视野实现了一种前置。我们可从哪里获得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观念启发呢?首先是日本学者关于违法类型的区分。日本学者将违法的轻微型分为绝对轻微型与相对轻微型两大类。前者是指法益侵害结果或者行为对规范的偏离程度本身较为轻微的情形。此种类型的案件基本上是立于构成要件该当性被否定而被认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一厘事件”萌芽了可罚的违法性观念,而此事件中的可罚的违法性观念正好对应着绝对轻微的违法类型。在“旅馆储购香烟事件”中,被告人为了旅客的方便而私自购置了香烟,然后再转卖给旅客,其行为同样违反了日本的旧烟草专卖法,但法院否定了犯罪的成立仍然体现了可罚的违法性观念,因为被告人的行为系“在社会共同生活上应当被容许的行为”⑯同注⑤,第26~28页;[日]山口厚:《刑法总论》,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181页。。可见,违法的绝对轻微型貌似否定了违法性而实质否定了构成要件该当性。构成要件该当性原本只具有形式性或曰是形式判断,特别是在形式刑法观的片面强调之下,其形式性更为极端,而形式性通常使得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不当地予以扩大,从而导致将实质上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判断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因此,如果说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犯罪成立的第一道限缩功能,则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便使得此限缩功能发挥得实质而具体,如盗窃一张A4纸的行为便可认为不具有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么,如果说构成要件该当性以人权保障为首要价值,则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则是将此人权保障价值落到了实处。
其次,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理论演进隐含着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旨趣。正如我们所知,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起初只是中性无色的、客观记叙的行为类型,即其并不关涉违法的性质及其程度问题,从而对构成要件只能作出形式解释;但随着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违法类型说”的提出,构成要件被视为违法行为的类型和违法性的存在根据,即只要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构成要件该当性便意味着违法性。于是,构成要件的独立性只是在与违法阻却事由的关系上才得以凸显,而在与违法性的关系上则几乎没有独立性可言。这便导致了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中就已经必须考虑实质的违法性,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对构成要件必须进行实质解释。⑰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2页。而在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的前提下,可罚的违法性进一步表现了对构成要件作实质解释所要具体考察的内容,即在行为性质之外,还要确定行为的“量”,亦即“质”与“量”都达到要求才能使得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成立犯罪。⑱同注④,第37页。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从形式解释向实质解释的转变,印证了构成要件从中性无色向价值有色的转变,而构成要件的色彩转变及其解释思维的转变又隐含着构成要件该当性,不能仅仅是形式的该当性,而且同时也是实质的该当性。于是,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便可明确地提出形式的该当性与实质的该当性同时具备的要求,或曰形式该当性前提下的实质该当性需要通过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予以牵引。当然,这里的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仍然包含对构成要件行为的质与量两个方面的要求。可以这么认为,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应该是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演进中的一个或迟或早的“观念萌芽”。
再就是,可罚的违法性的犯罪论体系地位归属问题的讨论,也给予我们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启发。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否定犯罪的成立究竟是通过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还是通过阻却可罚的违法性,仍存有争议。对此问题,以藤木英雄为代表的学者们坚持构成要件阻却说,即立法上只是将具有实质违法性,从而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故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便具有可罚的违法性。相反,若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预设的,达到了可罚程度的违法性,便认为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易言之,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否定某行为成立犯罪,并非因为该行为因实质违法性或可罚程度而具有违法阻却性,而是具有构成要件该当的阻却性,即否定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而非可罚的违法性。⑲[日]藤木英雄:《可罚的违法性の理论》,有信堂1967年版,第20~22页。显然,在藤木英雄那里,可罚的违法性是在判断构成要件时就应当考虑的,被构成要件的类型性所预设的违法性的最低标准。将构成要件作为可罚的违法类型,而不具有罚则所预设程度的实质违法性的行为,便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本身,构成了藤木英雄所主张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显著特征,即“作为构成要件概念之缩小解释基准的可罚的违法性论”⑳同注④,第20页。。藤木英雄的主张本身颇有道理,构成要件阻却说因其在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中一开始就可通过否定构成要件本身来阻却犯罪成立这种适用上的便利性,便可使得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司法实务中获得广泛认可。但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规定的是犯罪的类型性意义,而如果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中连违法性的实质都要予以讨论,就会损害构成要件本来的定型化机能。同时,如果将可罚的违法性置于构成要件层次判断,则会使得实质判断过度导入构成要件之中,从而难免因解释者的恣意而产生适用刑法的主观危险,故其遭到了主张将可罚的违法性放在违法性阶层来讨论的学者们的批判。㉑[日] 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315页。对藤木英雄的质疑和批判也不无道理。然而,如果立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第二阶即“违法性”是“例外性判断”,则藤木英雄的主张仍然是讲得通的,甚至本来就应该作出“藤木式理解”,因为似乎只有作“藤木式理解”,构成要件才真正具有定型功能,从而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第二阶即“违法性”才真正具有出罪功能。而在“违法性”真正具有出罪功能之下,所谓恣意解释所产生的适用刑法的主观危险,便不足为虑。那么,如何消除藤木英雄与其批判者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呢?那就是引入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即用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来解答藤木英雄试图通过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欲在构成要件中所解决的问题,从而避免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前两个要件即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之间摇摆不定或纠缠不清。当然,引入了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则可罚的违法性概念要作出一番新的理解和把握。
最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还能够得到刑法类型化理论的说明。正如我们所知,在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是行为类型,而构成要件该当性“标识”着违法性和有责性。但是,没有定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预示着类型化的泛化性和松散性,而有了“可罚的”这一定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即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便使得构成要件所寄寓的类型化具有确定性和紧密性,从而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中更加能够发挥限缩犯罪成立的人权保障功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将可罚的违法性植入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中或许有损构成要件的定型化机能,但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非但无损于构成要件的定型化机能,反而能够强化这一机能,因为类型化本身排斥着“漫无边际”,而“可罚的”正是对“漫无边际”的紧缩和提防,且此紧缩和提防是通过“可罚的”的“质”与“量”的要求来予以实现的。
其实,小野清一郎的论断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发:构成要件具有对违法性和可罚性的“预设性”。而正是这一“预设性”,可罚的违法性的理论视野应该在拔高之后而俯瞰整个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且应在从左到右的方向上首先注视作为该犯罪论体系第一阶的构成要件。由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视野拔高之后便升华为“可罚性理论”,故被俯瞰的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一环的构成要件便“华丽转身”为“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
三、可罚的违法性
原先的可罚的违法性是在行为已经符合构成要件或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前提下,不仅强调该当构成要件行为是否应具有违法性,而且在违法性程度上还要达到“可罚”的要求,即不仅有质的要求,而且另有量的要求。那么,在可罚性理论架构中,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对应或相呼应的可罚的违法性又应有着怎样的内涵呢?
看来,我们还得从原先的可罚的违法性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问题入手,而从这里入手,即使我们得不到直接答案,也可获得间接启示。在原先的可罚的违法性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问题上,除了藤木英雄提出的构成要件阻却说,日本刑法学者佐伯千仞提出了二元阻却说,即某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时,可能是属于阻却构成要件该当的解释问题,如普通花卉并不该当盗窃罪的“财物”,也可能属于违法性阻却问题,如许多无法利用构成要件解释予以概括的情形就必须在违法性中来判断是否具有可罚的违法性。㉒同注⑫,第182~184页。在佐伯千仞看来,犯罪只是违法行为的一部分,故违法行为要成立犯罪,就必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类型,而此犯罪类型当然应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类型即可罚的违法类型。于是,犯罪即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行为与除此以外的违法行为之间便在违法性本身产生了差别。若此,所谓可罚的违法性就是指行为的违法性具有采取刑罚这种强力对策的必要,并且能够认为具有与刑罚相适应的“质”与“量”。作为“质”的问题,是指违法性要与刑罚相适应;作为“量”的问题,是指犯罪类型各自都预设了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性。于是,效果便有两种情形:一是按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作无罪处理;二是虽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但存在例外的违法减轻事由或可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而作无罪处理。㉓[日] 佐伯千仞:《刑法におはゐ违法性の理论》,有斐阁1974年版,第391~392页。相对于藤木英雄,佐伯千仞将大部分论述着重于第二种处理情形上,故被称为违法阻却说的代表。佐伯的“质”、“量”二分的构想为可罚的违法性概念找到了生存空间,同时也是对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的有力驳斥。在可罚的违法性的体系定位上,佐伯千仞的构成要件阻却与违法阻却的“二元阻却说”获得了多数学者的支持。㉔同注④,第21页。在本文看来,与构成要件阻却说一样,佐伯千仞的“二元阻却说”也隐含着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正如其提出普通花卉并不该当盗窃罪的“财物”所印证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能断然否定这里的普通花卉是“财物”本身,我们只能说这里的普通花卉不具有盗窃罪所要求的,与值得科处刑罚相当的“财物”的“质”与“量”。
当我们能够甚或应该肯定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则可罚的违法性概念既可避免“构成要件阻却说”所招致的将可罚的违法性置于构成要件层次判断而使得实质判断过度导入构成要件之中,从而因解释者的恣意而产生适用刑法的主观危险,又可避免“二元阻却说”所招致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前两个要件即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之间的摇摆不定或纠缠不清。而前述两个避免将使得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在可罚性的理论框架下能够地位明确和“专司其职”。在本文看来,在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对应的可罚性理论框架中,可罚的违法性概念主要是在“可能性”的意义上反面地对应着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因为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一般地”寄寓着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的违法性,而可罚的违法性概念正是在担负着“例外出罪”的功能中“有可能”地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实现对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的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的违法性的一种“抵销”,而此种“抵销”实质就是一种“例外的否定”。那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为已经具备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但可罚的违法性要件能够“抵销”那里的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的违法性,则该行为在可罚的违法性要件这里便可作出无罪结论而无需再作出“有责性”的判断;如果一个行为已经具备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而可罚的违法性要件不能够“抵销”那里的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的违法性,则该行为便要通过可罚的违法性要件而需再作出“有责性”的判断。这里,可罚的违法性概念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关于犯罪成立的消极概念,从而其出罪功能也变得较为“纯粹”,而这是由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的积极色彩较泛泛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概念有所增强,从而构成要件的犯罪定型功能也随之增强所“映现”出来的。
那么,在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对应的可罚性理论框架中,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可罚的违法性来自何方?在本文看来,既然是在可罚性理论的框架中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相对应,则可罚的违法性的来源问题应将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作为问题的参照系,因为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已经“一般地”寄寓着值得科处刑罚的实质违法性。于是,“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和“违法相对性论”便是我们要面对的争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以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为代表,认为在某一法领域的违法行为,在其他法领域便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相反,在某一法领域的适法行为,在其他法领域便不能被视为违法行为。㉕[日]木村龟二:《犯罪论の新构造》,有斐阁1966年版,第221页。与“严格的违法一元论”截然对立的是“违法的相对性论”,认为刑法上的违法性应当以是否值得科处刑罚为前提,故刑法上的违法性判断与其他法领域的违法性判断有所不同,从而违法的判断应当是相对的。持“违法的相对性论”的藤木英雄认为,所谓违法效果应当按照规范各种生活关系的法律法规进行个别的解释,故对同样的生活关系造成侵害,便不能说如果根据某法律是违法的,则就在其他法律上也产生违法效果。如无证行医是违法行为,但医术高超的无证行医并非一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又如金融机关的董事为没有合法借贷资格的合作经营组织提供贷款,董事的违法行为仅此并不足以成立渎职罪。㉖[日] 藤木英雄:《可罚的违法性》,学阳书房1975年版,第107~108页。“违法的相对性论”不仅意味着不同法域之间存在着违法的相对性,即便各个刑罚法条之间也存在着违法的相对性问题,因为每个罚则都有其特定的守备范围和射程距离,故虽然形式上该当某个罚则的构成要件,但如果查明该行为所造成的恶害与该罚则所要禁止的恶害性质并不相同,则可认为该行为在该罚则的守备范围或射程距离之外,从而否定其具有可罚的违法性。㉗同注④,第19页。“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介于“严格的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的相对性论”之间,以日本刑法学者佐伯千仞为代表,认为违法性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故不能认为某行为在民法上适法而在刑法上违法,但是违法性的现实表现却又可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和轻重不同的阶段。㉘同注㉓,第392页。违法性判断问题在不同法域有着不同的解释意义:其一,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容许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其在刑法上是否也具有正当性而无罪;其二,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禁止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其在刑法上是否也具有违法性或可罚性。㉙[日] 曾根威彦:《犯罪论の新构造》,有斐阁1966年版,第221页。“严格的违法性一元论”对上述两种情形的回答均为“是”,“违法的相对性论”的回答则均为“否”,而“缓和的违法性论”对前者的回答采“是”而对后者的回答则采“否”。㉚同注④,第16页。那么,在本文看来,既然三阶层体系是一个关于犯罪成立或犯罪认定的淘汰式或筛选式体系,且该体系潜行着“从一般到例外”的司法认知思维,则在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的即被前置的违法性应“假定”为“严格的违法性一元论”,而在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二阶的可罚的违法性那里,我们应坚持以“违法性的相对性论”为主而以“缓和的违法性论”为补充。所谓以“缓和的违法性论”为补充,详言之,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容许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其在刑法上也应具有正当性而无罪;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禁止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其在刑法上则当然不具有正当性而有罪。之所以提出这种看法,乃因为本文所提倡的可罚性理论终究也是以解决行为是否“可罚”即是否值得科处刑罚为问题宗旨,但在对级层式犯罪论体系的环节性解释中,我们又必须顾及法规范之于公民的预测可能性问题。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禁止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其在刑法上当然不具有正当性即仍然具有违法性,这是符合公民的规范预测可能性即符合公民的规范认知规律的;若民法或行政法等领域容许的行为该当某罪构成要件,则仍认定其在刑法上具有违法性,便难言符合公民的规范预测可能性了,因为刑法毕竟是“后盾之法”和“保障之法”。有人在批判“严格的违法一元论”时指出,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违法性,其功能就是应当限定挑选出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但“严格的违法一元论”从“全体法秩序”的观点出发,在刑法上只能作出一个形式性的违法性判断,并无实际意义。㉛[日] 高山奈佳子:《故意と违法性の意识》,有斐阁1999年版,第290~292页。“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在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二阶的可罚的违法性那里确实没有实际意义,但在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则是有相当意义的,因为在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被前置的实质违法性是被作为“无例外则存在”、“无对立则存在”、“无抵销则存在”的预设性把握的,而此把握完全符合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架构和价值理路。反过来,“严格的违法一元论”在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的重要意义又说明了其在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二阶的可罚的违法性那里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意义空间”的问题。于是,以“违法性的相对性论”为主而以“缓和的违法性论”为补充,便构成了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二阶的可罚的违法性的理论解说。这里需要再予强调的是,“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所“内含”的“实质违法性”和“可罚的违法性”那里所“外显”的“实质的违法性”之所以应分别作“违法一元性”和“违法相对性”的把握㉜实际上,“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也可归入“违法相对性论”。,正好或完全对应了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从“一般”到“例外”的淘汰式或筛选式认知理路。
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第二阶的可罚的违法性,不仅应依托以“违法性的相对性论”为主而以“缓和的违法性论”为补充而实现对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一种“淘汰”或“筛选”,而且同时应在“超法规”之中来担当此“淘汰”或“筛选”功能,因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是客观而普遍地存在着的。
四、可罚的有责性
在讨论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标准问题时,有人指出,日本司法实务中关于可罚的违法性判断的判决理由,体现为一种综合标准,根据即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行为自身的样态、行为人的主观责任程度甚至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等来综合地评价是否应予科处刑罚,如对绝对轻微型案件作出无罪判决,是对违法的大小、责任的大小以及预防的必要性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而对相对轻微型案件作出无罪判决,是对行为的状况、目的和其他相对独立的价值的实现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而认为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㉝[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在日本的刑法理论中,可罚的违法性是作为违法程度问题提出的,而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各阶段的分工来看,可罚的违法性判断不应当包括对责任等其他因素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一元判断标准㉞可罚的违法性的一元判断标准是立于客观违法性论而提出的一种学说。按照客观违法性论,违法的实质是结果无价值,故违法评价只是对一定的结果或是事态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而与行为人的行为样态无关。那么,按照可罚的违法性的一元判断标准,只根据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的程度来判断有无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违法性的一元判断标准立于客观违法性论的立场,重视结果无价值,主张实质违法性的基准仅仅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反对将实质违法性的重点置于行为本身的无价值,否则将导致复归主观违法论的立场而放弃违法与责任之间的区分。结果,立于客观违法性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一元判断标准使得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将属于责任论的主观要素被排除在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之外。同注⑫,第174~177页。,还是二元判断标准㉟可罚的违法性的二元判断标准是将客观违法性论与主观违法性论结合起来而提出的一种学说。按照可罚的违法性的二元判断标准,由于违法的实质需要从结果无价值即法益侵害和行为无价值两个方面来考虑,故可罚的违法性的判断当然需要由此两个方面进行。那么,被害的轻微性与行为的相当性同时具备将排斥可罚的违法性,而如果行为不是明显不相当,但被害法益重大,或被害法益不属重大,但行为极不相当,则不能否定可罚的违法性。同注⑲,第38~40页。,都是符合理论本身逻辑的。而综合判断标准虽然也是以违法性程度的判断为名,但显然已经变换了概念,因为其包含了“可罚的责任性”,故其本质上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最终标准。将琐细的轻微行为在司法实务中予以出罪的技术目的出发,综合判断标准显然是全面和可取的。在理论上,可罚的违法性概念本身原本是为了解决司法中对轻微行为进行非罪化处理而提出的理论途径,但实务中单纯根据实质违法性的大小并不能完全决定行为的可罚与否,有些侵害行为虽然违法程度不是绝对轻微,但行为的主观可责性程度极低或者人身危险性很小,也可以认为不是犯罪,而相反的情形也是存在的。易言之,单纯从行为违法性程度上进行限制,并不能达到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所追求的司法效果。㊱刘士心:《论可罚的违法性》,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3期。可见,可罚的违法性的综合判断标准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此标准直接包含了“可罚的有责性”。那么现今,可罚的违法性的综合判断标准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是:行为的可罚性的判断不能仅仅是违法性层面的,而且还应包括有责性层面的,即可罚性是一个由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和可罚的有责性所紧密构成的完整概念。显然,前述启发能够使得我们去概括或提炼出一种清晰的和有逻辑构造的可罚性理论,且这一理论能够理顺可罚的违法性的综合判断标准的内在肿胀与逻辑杂乱。
“可罚的有责性”的概念形成,不仅可以受启于可罚的违法性判断的所谓综合标准,而且可以得到国内外相关刑法实践的印证,如“处罚故意犯罪是原则,处罚过失犯罪是例外”一直是国外刑法立法所普遍奉行的原则,这里面可以视为隐含着可罚的有责性观念;而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但书”规定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条规定也可视为隐含着可罚的有责性观念,因为“情节显著轻微”可以认为包含着犯罪主观情节“显著轻微”。而在这里,行为人的动机如何与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高低等,都在“可罚的有责性”的视野之中。那么,在可罚性理论的架构之下,可罚的有责性是可罚性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阶层,它在“唯可罚性是瞻”之中实现着先予对“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接力”的“可罚的违法性”的“接力”,即在一种递进的理路之中最终担当着对犯罪成立的“淘汰”或“筛选”功能。
在可罚性理论的总体架构之下,“可罚的有责性”概念有着大于原先“有责性”的理论空间。这里所谓“可罚的有责性”的理论空间,不仅可指期待可能性问题可以放在“可罚的有责性”之下予以展开,而且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即其可罚性问题也可在“可罚的有责性”之下得到说明。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分别是以特定目的、内心倾向和心理过程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而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被称为所谓“主观的超过要素”㊲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274页。。由于有责性是对犯罪成立或行为具有可罚性的一个主观要求,故“可罚的有责性”自然分别排斥没有特定目的、内心倾向和心理过程的行为成立所谓目的犯、倾向犯和表现犯。虽然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起初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那里被讨论的,但最终要到“有责性”那里得到说明,即从“构成要件该当性”到“有责性”说明着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经历了从事实存在到价值评判的说明,亦即从“事实故意”到“规范故意”的说明。那么,这里要进一步点破的是,目的犯的“目的”、倾向犯的“内心倾向”和表现犯的“内心过程”从事实存在到价值评判的认知运动及其所印证的“事实故意”到“规范故意”的认知运用,恰恰说明了在三元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中,“有责性”对“违法性”的递进和“违法性”对“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递进并非沿着水平方向,而是由低到高地进行“攀升”,而“可罚的有责性”通过“可罚”的强调更是外显了这一“攀升”路线。实际上,只有在“攀升”的路线中,递进式犯罪论体系在犯罪认定过程中方具有彻底充分,从而健全有力的“淘汰”或“筛选”功能,即更加出色地担当人权保障功能。
正如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和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这一概念的定语即“可罚的”也明白地说明着作为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一阶并且是最后一阶,“有责性”不仅有“质”的要求,也有“量”的要求,而此两个方面的要求更能体现出可罚的有责性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之中并且是处于最后一阶以发挥旨在追求人权保障价值的出罪功能。如我们可将不具有“特定目的”视为不具有目的犯的可罚的有责性,从而否定目的犯的成立;又如我们可将缺乏期待可能性视为个案行为不具有可罚的有责性,从而否定犯罪的成立;再如,我们甚至可将疏忽大意的过失视为个案行为不具有可罚的有责性,从而否定犯罪的成立。当然,在构成要件越来越实质化的前提下,尽管我们通过“可罚的”来对“有责性”提出“质”与“量”的要求,但体现“质”与“量”的要求的“有责性”即可罚的有责性仍然是在“例外认知”中来担当出罪功能的。
五、结语
在前田雅英看来,如果从正面认可“违法的相对性”,则没有必要使用与“一般的违法性”相区别的“可罚的违法性”,因为违法性在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法域是相对的和多义的,而刑法中的违法性自然是值得科处刑罚的违法性即“可罚的违法性”本身,故区分违法性和可罚性或一般违法性与刑法中的违法性没有实际意义。㊳同注⑤,第340页。而从前田雅英主张应将“可罚的违法性”分解在构成要件的实质化解释和实质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中,我们可看出其有将“可罚的违法性”概念化解在刑法中的违法性即“实质的违法性”概念之中,以最终取消“可罚的违法性”在犯罪论中的独立地位的意图。“可罚的违法性”在阶层式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如何,受制于我们对该体系的逻辑构造与价值理路的认识与把握。在本文看来,阶层式犯罪论体系沿着“递进”的认知理路,在既是“淘汰”又是“筛选”的模式中来解决定罪问题,其认识论上的科学性与价值论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国内外对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以往认识所存在的局限在于:既然定罪问题是最终解决一个行为是否可罚的问题,则“可罚性”思维应贯穿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始终,即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每个环节或阶层都应体现“可罚性”思维,亦即本文所主张的“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体系。而只有在该体系之中,“可罚的违法性”的独立地位才是明确的和牢固的,因为当采用这一体系,则“可罚性”便构成了一个上位范畴,而所谓“可罚的违法性”便与“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和“可罚的有责性”一道构成了下位概念并实现着对“可罚性”范畴所寄寓的刑法价值的逐次担当。笔者曾经论证“应受刑罚惩罚性”应是犯罪成立的“总条件”,而此“总条件”无论对于四元整合的犯罪论体系,还是对于三元递进的犯罪论体系,都是一种“总标准”㊴马荣春:《论应受刑罚惩罚性的犯罪论地位》,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期,第21~23页。。那么,当“应受刑罚惩罚性”可置换为“应罚性”,而“总标准”理应在犯罪论体系的每个要件或阶层都得到贯彻或体现,则“可罚性”作为上位范畴并分解出“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和“可罚的有责性”三个下位概念,且此三个下位概念顺次递进,便使得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可罚性理论”的架构或脉络。
从形成和发展完成来看,原先的“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将刑法的谦抑性、实质违法性和违法相对性作为自身的理论奠基。那么,“可罚性理论”及其架构下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即“可罚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可罚的违法性—可罚的有责性”体系,便更加彰显了刑法的谦抑性,并在充分引入实
质违法性的同时消除了违法是一元还是二元的理论分歧且使得“违法一元论”和“违法相对性”各安其所。“可罚性理论”及其架构下的体系,所展现的是与“法域目的”相对应的“违法二元论”,其立场则是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前提的“行为无价值论”,故其保障人权功能更加强健有力。“可罚性理论”是“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脱胎换骨式的升华。
马荣春,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在危险状况,故其行为不构成犯罪。③[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此即日本刑法史上的一个著名判例即“一厘事件”。在日本明治维新“惩一儆百”的官僚主义时代,本案在极为严苛的法解释的背景下最终得出无罪结论,实难可贵并为后世学说广泛肯定。④王银河:《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刑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此判决被视为体现可罚的违法性观念的最早判例,即体现通过实质判断而不处罚轻微违法行为的思考方式。⑤[日]前田雅英:《可罚的违法性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23~24页。此判决所倡导的轻微违法行为不值得动用刑罚的观念开启了日本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并由宫本英修将此理论予以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