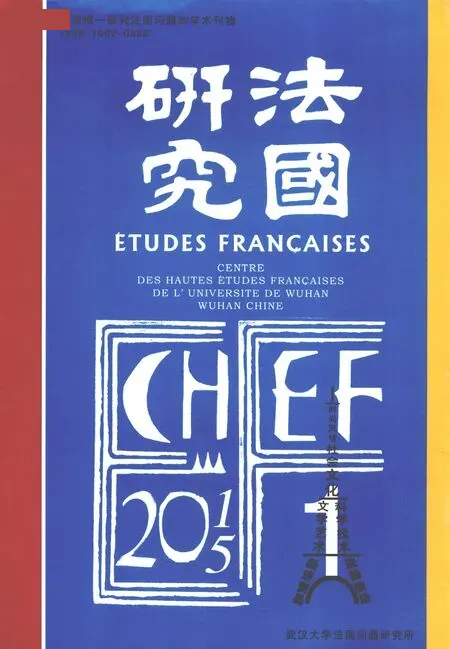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我是查理”:《查理周刊》①据新华社参考消息译名室李学军:《查理周刊》的法文刊名为《Charlie hebdo》, “hebdo” 意为”周刊,按照法语音译规则,Charlie应被译为“沙尔利”,因此,《Charlie hebdo》的正确译法是《沙尔利周刊》。但是,由于《查理周刊》这一转译自英文的译法已经广泛传播,为避免误解,本文沿用,特此说明。的谑虐传统
程 平
“我是查理”:《查理周刊》①据新华社参考消息译名室李学军:《查理周刊》的法文刊名为《Charlie hebdo》, “hebdo” 意为”周刊,按照法语音译规则,Charlie应被译为“沙尔利”,因此,《Charlie hebdo》的正确译法是《沙尔利周刊》。但是,由于《查理周刊》这一转译自英文的译法已经广泛传播,为避免误解,本文沿用,特此说明。的谑虐传统
程 平
【摘要】《查理周刊》继承了其前身《切腹》杂志目空一切、尖酸刻薄的精神,是法国颇具激进自由主义传统的讽刺性杂志。它用大量篇幅刊登一些搞笑、伤人甚至蓄意挑衅的漫画,讽刺极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总统、富商、各种意识形态等。在《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大背景下,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前世今身可以分析《查理周刊》在法国赖以生存的政治土壤和社会氛围,揭示该刊在法国民众中的影响力和象征意义,并表达作者个人对“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这两个貌似矛盾口号的独立思考:前者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誓言,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背后的伦理共识。
【关键词】《查理周刊》 “我是查理” 谑虐
[Résumé] Charlie Hebdo, à l’esprit caustique et irrespectueux hérité de Hara-Kiri, est un journal satirique français de tradition libertaire. Il fait une large place aux caricatures drôles, blessantes ou même délibérément provocantes, qui se moquent de l’extrême droite, du catholicisme, de l’islamisme, du judaïsme, des présidents, des hommes d’affaires ainsi que de différentes idéologies. Au lendemain de l’attentat djihadiste contre le journal, le présent article, tout en faisant l’historique de Charlie Hebdo, a analysé son arrière-plan politique et social, révélé son influence et son image symbolique parmi le peuple français et exposé des réflexions personnelles sur les deux slogans ---- Je suis Charlie et Je ne suis pas Charlie --- apparemment contradictoires:si Je suis Charlie proclame la défense de la liberté d'expression , Je ne suis pas Charlie souligne plutôt les différentes interprétations subtiles de ce principe dans sa concrétisation ainsi que la morale derrière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2015年1月7日,法国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包括杂志主编夏尔伯在内的10名漫画家、编辑和记者及负责杂志社安保的2名警察失去了生命,另有5人身负重伤! 伤亡之惨重、场面之血腥,在战后的法国是绝无仅有的。各路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纷纷使用了“血洗”、“灭门”等令人胆寒的词语,正如总理瓦尔斯所说:“它击中了法国的心脏,每个人都感到恐惧”。
在经历了第一波恐惧、震惊、悲伤的反应后,全球迅疾形成对《查理周刊》的强有力声援力量:众多媒体、普通百姓、甚至多国首脑,喊着统一的口号:“我是查理!”,共同谴责惨绝人寰的恐怖主义,并悼念在《查理周刊》事件中逝去的生命。一时间, “我是查理”、“我们是查理”的口号波及法国各地,并从法国席卷到世界多个城市,以及各大社交网站,最终演进成一场全球性事件:四十多个国家领导人、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支持《查理周刊》的巴黎共和大游行。
“查理”,何许人也?《查理周刊》又是一份怎样的杂志?为什么它是警方的重点警卫对象?为什么该刊物遭此灭顶之灾?解开这些疑问,需要对《查理周刊》的前世今生进行梳理。
1.《查理周刊》的前身
《查理周刊》的前身为《切腹月刊》(《Hara Kiri》),它是创刊于1960年的讽刺性杂志,其创始人及灵魂人物弗朗索瓦•卡瓦纳(François Cavanna)和乔治•贝尔涅(Georges Bernier)相逢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者是《零》杂志的销售总监,后者是该杂志的副总编辑。
50年代末因与老板不和,卡瓦纳决定单干。当时他是创刊于1952年的美国杂志《疯狂杂志》(《Mad Magazine》)的狂热读者,该杂志通过各种讽刺戏谑的模仿,丑化美国社会,嘲笑一切人和一切事,在高兴和愉悦的笑声中,挑战一切固有秩序。这种品味和风格令卡瓦纳颇为喜爱和欣赏,于是,在法国自办一份同类杂志成为他的梦想。经过反复争取,他的计划得到了贝尔涅的支持。贝尔涅不仅自己离开了《零》杂志,还带走了《零》杂志的销售网络。于是,卡瓦纳带领一帮追随他的年轻且不知名的漫画家,贝尔涅率领他的报刊零售商贩,两支队伍合二为一自立门户,成立了新的《切腹月刊》杂志社。
1.1.刊名的来历
这份新杂志的命名,采纳了卡瓦纳的主张——《Hara-Kiri》。该词来自日文的“切腹”,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切腹这一壮烈的仪式,宣告对武士精神的忠诚和坚决。使用这一短促但冲击力十足的外来语,表现出新杂志试图一举颠覆传统新闻标准的强烈、甚至野蛮的意愿和决心。《切腹》完美地集合了新团队对新杂志的全部期许:首先,《hara-kiri》(qui rit)中包含笑声,足以表明“笑”是杂志的主要元素,讽刺与幽默是杂志的最大特征,对于严肃或非严肃的事情,处理方式一律是滑稽的,以博得读者一笑,那“笑”可能是诙谐风趣的,或者尖酸刻薄的,也有可能是厚颜无耻的, 甚至是淫秽下流的,但“笑”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切腹”代表一种接近灵魂的方式。古时候,许多国家和民族认为人的灵魂寄宿于肚腹,如果想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通常会采取剖腹示众的方法和仪式。因此,《切腹》杂志试图通过这一刊名,传递用灵魂与读者交流的目的,希望读者透过嬉笑、戏谑的表象,领略他们不循规守旧,挑战标准、挑战制度、挑战权威的精神和品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切腹”凝聚着杂志为了追求“笑”果,追求“灵魂表达”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自我毁灭的义无反顾,宣示着用生命捍卫灵魂的坚定不移的意志。
1.2. “愚蠢和恶毒”的幽默
《切腹》杂志的创刊号封面:血红的背景里有一位正在开肠破肚的日本武士,“切腹”刊名下印着一行副标题 “Honni soit qui mal y panse”。显然,副标题运用了一个同音异义词的文字游戏,用 “panse”替换了同音的“pense”,让一句话拥有了“未包扎好者遭唾弃”和“有邪念者被唾弃”两层含义。联系画面,既有一种幽默藏在其中,又有提醒读者不要对杂志中过激文字和漫画神经过敏的含义。 而后面几期杂志的副标题先后又用过“开怀大笑”和“讽刺月刊”,直到第7期,副标题成为“愚蠢和恶毒的杂志”(《Journal bête et méchant》),并从此固定下来,似乎成为该刊物自诩的座右铭。
杂志将发展方向定位为“愚蠢和恶毒”,是杂志挑战传统的法式幽默和主动选择读者的举措。从一开始,《切腹》的定位就是小众刊物,卡瓦纳寻求的是少数对幽默质量有“高标准”要求的知音。 根据他掌握的情况,上世纪60年代,法国阅读讽刺幽默类报刊的读者总数约有200万,而《切腹》面向的只是其中的10%。到1966年,《切腹》月刊的每月销售量已经突破了25万①Stéphane Mazurier,Hara Kiri , dans la revue Histoires littéraires, n° 26, avril-mai-juin 2006.,超过了卡瓦纳的预期。
《切腹》的“愚蠢和恶毒”,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权威的象征——宗教、军队、警察等的强烈不满,它会使用极为粗野强暴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反讽,比如,用粪便来隐喻它们的卑鄙和荒诞。1970年11月,甚至刊出了“大粪专号”,封面上的主编卡瓦纳脸上涂满了大便,却仍然哈哈大笑。《切腹》中的幽默就是这样谑而近虐的丑恶、变态、扭曲、疯狂、令人作呕。它追求一种让人在大跌眼镜的同时又被当头棒喝的打击力度。
除此以外,《切腹》中对广告的滑稽模拟、放纵的色情画面以及疯狂的摄影小说等内容,严重扭曲着社会面貌,传播着与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谎言、偷盗、懒惰、仇恨等负面观念。出于对青少年的保护,并反对对老年人和家庭主妇的歧视,1961年和1966年,《切腹》曾两度遭到停刊惩罚。
1.3. 政治转向
起初,《切腹》月刊基本不问政治,从它每月一期的出版频率即可推断出,它与时事政治结合不紧。贝尔涅甚至认为,与时政脱钩的幽默才是真正的幽默。
然而,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切腹》月刊的主要读者不少也是激进的“五月风暴”的参与者,他们不再满足这样一份与政治关联并不紧密的杂志,他们需要的是一份能够对当代政治、社会问题做出积极或及时反应的杂志。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切腹周刊》②《切腹月刊》仍然保留,卡瓦纳将主编的位置让给了热贝(Gébé),自己只担任《切腹周刊》的主编。(Hara-Kiri Hebdo)应运而生,在“五月风暴”之后的第8个月,其创刊号问世,与先前的《切腹月刊》相比,《切腹周刊》的时政色彩明显增强,但与其固有、传统的“愚蠢和恶毒”的幽默手法一脉相承。
1970年11月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科隆贝 (Colombey)的家中逝世。而此前8天,当地一家名为“五七俱乐部”(Club Cinq-Sep)的夜店发生大火,造成146人死亡。11月16日,《切腹周刊》出版了一期紀念专号,标题为《科隆贝的悲剧舞会:一人死亡》。用“1人”换下“146人”,显然在暗讽高高在上的戴高乐。因此,该周刊被內政部责令停刊。 在很多文化中,人们讲究“逝者为大”,法国也不例外。而《切腹周刊》连死人也不放过,可见它“恶毒之至”了。
为了躲避禁令,《切腹周刊》的原班人马,仅在停刊一周后,便以《查理周刊》为名继续出刊。之所以选择“查理”作为刊名,原因大约有二:
一,《切腹月刊》一直持续转载美国漫画《花生》,其中的主人公名叫查理·布朗,他是一名单纯善良的小学生,同时也是一个受人欺负的受气包。他志向远大,但时常碰壁,是作者查尔斯·舒兹(Charles M. Schulz)为取悦读者而创作的一个“失败者”形象。使用“查理”作为刊名,是有意向《花生》系列漫画致敬①Florent Deligia,Quelle est l’origine du nom Charlie Hebdo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108/;二,Charlie同时还是Charles的昵称,而Charles又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名字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以“查理”作为新的刊名,既能继续暗讽戴高乐,又能影射致使《切腹周刊》被迫更名的事件。
从更名过程来看,《查理周刊》重视的是它与《切腹周刊》的关联,努力维护着两者之间的血脉关系,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查理周刊》面对政府的新闻审查禁令所表现出的执拗和倔强。
《查理周刊》从《切腹周刊》脱胎而出,从未换骨,思想自由、挑战禁忌、谑而近虐的“血统”更是一再彰显。它继续以既粗俗又无情,且带有恶意攻击性的幽默方式,搅乱新闻、漫画和幽默传统的道德底线,其尺度大胆充满争议,与其前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2.《查理周刊》的现状
《查理周刊》自诞生之日起,体内就流淌着将“愚蠢和恶毒”进行到底的血液。它以夸张、冒犯的方式,嘲弄宗教或世俗的一切权威,其讽刺对象是全方位的,从穆罕默德、耶稣、圣母、教皇、犹太教教徒到总统、议员、富商、金融巨头以及不同意识形态集权政府,无一不被《查理周刊》挖苦、丑化,其中宗教和政治是该杂志最热衷的主题。
近年来令人们印象深刻的宗教题材漫画委实不少:先知穆罕默德赤身裸体趴在地上,说:“我的屁股呢?你们爱我的屁股吗?”(漫画的上方写着“那部席卷伊斯兰世界的电影”,暗指美国拍摄的《穆斯林的无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曾引发了穆斯林世界的广泛抗议);蹲着的穆罕穆德双手抱头,痛苦地说:“被一帮蠢货追捧太难受了”;正在生产的圣母玛利亚光着并岔开大腿,小耶稣从中爬出;退休教皇搂着一位老太太感慨道:“终于自由了!”……
这些作品显然刻意侵害宗教信仰者的感情,明知伊斯兰教忌讳用图画表现真主和先知的形象,它们却要用恣意夸张的漫画形式来表现他们,甚至用裸体的形式来讽喻他们;因为基督教信仰童贞受孕,它们就夸大其词地予以讽刺;因为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它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地给教皇安排一个老太太,这一切可以说已经到了颠覆宗教传统仪轨的地步了。
对政客的揶揄同样是毫不留情、极富挑衅性的。当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传出“性绯闻”时,《查理周刊》直接让西装革履的总统露着生殖器上了杂志封面;法国政治极右翼的领袖是玛丽·勒庞( Marie Le Pen),她上《查理周刊》封面的画面是一团热气腾腾的,“奉送给勒庞以及给她投票的选民”的大便……,画面极为不雅。
然而,这样一份杂志如何能够在法国生存45年?它如此地百无禁忌,自由表达无下限却没能受到根本遏制,是否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条件和土壤?它是否遭遇危机?它的存在价值又是什么?
2.1.《查理周刊》的政治土壤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法国可以孕育和容忍《查理周刊》这样的杂志,因为,法国一直将“自由”排在国家格言的第一位,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为要冲。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米拉博就向三级会议呼吁:“让法律的第一条永远奉献给出版自由,使它居于神圣的地位。在所有的自由中,它最不能触犯,最不受限制。假如丧失了它,其他自由便永远得不到保障。”①《资本主义国家民权法则及其简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果然,在1789年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法国人用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新闻出版自由、舆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地位,其中第十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是宗教上的意见——而不受打击,只要他的言论不扰乱法定的公共秩序”②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1789, http://www.textes.justice.gouv.fr;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思想和见解的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除非根据法律决定的情形而必须为这项自由的滥用负责,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
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恰好是《查理周刊》40多年来敢于理直气壮地把尖酸刻薄、粗鲁无礼作为办刊特征的政治根源。虽然,法国大革命已过去了200多年,但法国激进主义政治传统并没有渐行渐远。1968年的“五月风暴”给这一政治传统注入新的能量。诞生于“五月风暴”的《查理周刊》,随即被公认为是一份极左翼的激进杂志。年长的和年轻的“查理们”前赴后继、崇尚绝对自由,嘲讽所有道德和宗教权威,毫无顾忌地冲撞各种禁忌。这份杂志能够在法国存在40余年,离不开法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查理周刊》前任记者伊莲娜·康斯坦蒂认为,《查理周刊》意味着“绝对的言论自由”,“我们可以没有阻碍地写任何事情,不需要敬畏任何机构。”“在我们这里,漫画家是老大。”③符遥、王思婧,《<查理周刊>讽刺了谁?》,《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月20日。
除了自由的精神之外,平等的逻辑也是《查理周刊》的重要支点。被写入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生而平等”思想,长期以来在法国深入人心。推而广之,讽刺面前当然是人人平等。以法国前任总统萨科齐为例,尽管他的私生活、相貌、言行、执政,曾都遭到过无情的嘲弄,但是无论嘲讽得多么过分,萨科齐依然认同“讽刺象征着一个自由空间,如果有人阻止,民主就会感到非常遗憾。”这一价值观念。萨科齐还认为,“宗教应该像权力一样,应当善于接受批评、讽刺和嘲弄。这些做法对于所有的宗教——其中包括对于最后来到法国的伊斯兰教——来说,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伊斯兰教在义务上不同其他宗教平等,那么它在权利上也不能同其他宗教平等。实际上,所谓对穆斯林的最大不尊重,不是像嘲笑上帝一样讽刺穆罕默德,而是把法国的穆斯林看作是一些与众不同的公民。”①尼古拉·萨科齐:《萨科齐自述:见证》(曹松豪译),《见证》第二部分:“我的思想遭到过讽刺(1)”,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正因具有由法律支撑的“自由的精神”和“平等的逻辑”形成的双保险,才得以使法国社会对《查理周刊》有着强大的宽容度和接受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饱受羞辱的奥朗德总统,能够在查理惨案发生后1小时以内亲临现场,将血案定性为 “挑战新闻自由”的恐怖袭击,并将此事件中的逝者称为国家英雄,说他们“为捍卫共和国立国之本的自由精神而死”。
2.2.《查理周刊》的坎坷命运
虽然有法律保障,并有“自由的精神”和“平等的逻辑”两大支撑,《查理周刊》的命运仍然历经坎坷。了解《查理周刊》身世的人都知道,它的诞生缘于其前生《切腹周刊》遭到了查禁。改头换面,重出江湖之后,苦苦撑到1981年,由于销量过少,也没有广告收入,经费严重不足,再次被迫停刊。而1992年复刊后至今的20多年间,又接连遭遇到50多起官司,平均每半年1起②« Charlie Hebdo », 22 ans de procès en tous genres,Le Monde.fr – jeu. 8 janv. 2015。
在所有官司中,《查理周刊》与伊斯兰教的积怨最深。一切缘起于2006年。当年,由于转载丹麦《日德兰邮报》 (Jyllands-Posten)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查理周刊》就遭到过穆斯林世界的强烈抗议。2007年3月,巴黎大清真寺和法国伊斯兰组织以违反法国仇恨言论法为由将《查理周刊》告上法庭。尽管法庭最终裁决该刊无罪,但自那以后,周刊常会受到来自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而作为回应,该刊则开始登载更多关于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此后,《查理周刊》经历过网站被黑客入侵、编辑部遭到燃烧弹袭击等恶性事件,为此,巴黎警方将周刊编辑部列为重点保护目标,并罕见地派专人值守(2011年起)。不幸的是,即便如此警卫,执勤的警察也未能保住《查理周刊》的安全,甚至自己也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悲剧,似乎阐述着一个悖论——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摧毁杂志社同时,似乎又“拯救”了这家杂志。1981年的《查理周刊》因经费不足停刊,1992年复刊后,由于它执意秉承独立的办刊理念,拒绝广告③“我们没有广告,没有靠山,查理只有玩家和用户。感谢你们在报摊购买查理。新闻自由,除了你,我们还能指望谁?”《查理周刊》网站首页显眼位置的这句话,无疑是其办刊理念的一种折射。,致使其全部收入只能来源于销售。可悲的是,由于该杂志的“重口味”,它的读者注定为小众,杂志印刷量多为5-6万份,但往往只能售出一半,因此,在经营上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2014年11月,周刊向社会公开求助捐款,希望以众筹方式寻求100万欧元以维持运转,但最终只获得2.6万欧元,似乎濒临破产。而当惨案后的特刊《幸存者专刊》于1月14日如期上市时,当期的杂志印数达到了创纪录的700万。当然,这个印数是暂时的,一个多月后的2月25日,《查理周刊》推出恢复正常发行后的第一期,发行量降至250万,销售情况已经远不如《幸存者专刊》时那么火爆。
从某种意义来说,一个杂志的死亡,大概不是它失去了多少优秀的漫画家、记者、编辑,而是失去读者和市场。由于《查理周刊》的表达方式追求极端化,致使它的受众也逐步仅限于极端人群。受众面的不断缩小,固然可以使刊物日趋“特色化”,但更令它面临困境。
2.3.《查理周刊》的独特身份
《查理周刊》并不是社会主流媒体,这个读者为小众的杂志,运用反教权、反军权、反政权的理念,并用极端的阐释方式来解构一切神圣、一切标准和一切价值体系。它不设任何禁区地恣意妄为,似乎陷入“为否定而否定,为讽刺而讽刺”的虚无主义之中。 法国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客座教授马克·李·亨特(Mark Lee Hunter)写道:“《查理周刊》从来不是事实的反映,但它很好地运用了事实(……)它出售的是一种态度,(……)但一直缺少的是解决方式。”①Mark Lee Hunter,Remembering Charlie Hebdo in the 90s,8 January 2015,https://www.opendemocracy.net。
《查理周刊》追求的根本目的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凸显“表态的自由”,即按自己的方式作出任意表态的自由。 当人们纷纷站出来,喊着“我是查理”的口号时,所声援的其实并非它长期以来所表达的极端内容,以及极端的表达方式,而是它“捍卫言论自由”的立场与勇气。
在当今法国,媒体其实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它们必须迎合各种权力,以此来适应新闻管制,或者获取大额合同,达到经济上的目的。针对这一现象,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西蒙·库柏曾以《法国媒体与权力“同床共枕”》②西蒙·库柏,《法国媒体与权利“同床共枕”》,见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3月26日文章为题撰文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证明法国媒体和权力水乳交融的关系。比如:部长和资深记者的同窗关系;部长与电视新闻女主播的婚姻关系等等,用“利益共同体”来形容法国权力和媒体的关系似乎并不为过。
由此看来,《查理周刊》所持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便显得尤为可贵。它带着棱角、带着挑剔、带着狡黠、带着残酷的激进方式,直面法国政治、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现象,其具有的挑战性和勇气,在略显温顺的众多法国媒体中,可谓非同凡响。
3.《查理周刊》带来的反思
《查理周刊》因对伊斯兰先知的谑虐而招来杀身之祸。此次惨案在发生之时就没有任何疑团,袭击者以“为真主复仇”的名义开枪杀死了他们心目中的仇人,不像有些恐怖事件,通常发生后几小时或几天,才有人或组织出来宣布对事件负责。事件中双方的恩怨由来已久,一方坚持有权挑衅、有权过份、有权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另一方深信宗教信仰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一次是“真主至大”与“言论自由”面对面的拼杀。
《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事件,开启了关于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的激烈讨论。在第一时间,多数人选择站在言论自由一边,喊出“我是查理”的口号,声援《查理周刊》所象征的新闻自由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查理血案后的《幸存者特刊》出版后,这场反思进入第二个富有争议的回合,“我不是查理”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如何解读以上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口号,需要我们将它们置于法国当前政治生态的背景之下认真解读。
3.1.“我是查理”
《查理周刊》的悲剧发生后,社会舆论基本一边倒,从国民到媒体到多国元首,都用自己的声音喊出 “我是查理“的呼声。据《巴黎人报》民调①Sondage Odaxa, réalisé le 13 janvier, auprès d’un échantillon de 1005 personnes interrogées par internet représentatif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âgée de 18 et plus. Méthode de quota.显示,巴黎共和大游行之后,87%的受访者对身为法国人而骄傲,73%的受访者对主要政治党派的反应感到满意。
“我是查理”,一样的口号却蕴含着丰富而多层面、多角度的观点。有些人借此表达对恐怖主义的坚决谴责,他们信奉无论什么原因,血腥屠杀无疑都是可鄙和野蛮的;有的则表达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立场和决心,他们认同不受限制的自由构成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基本内涵,而《查理周刊》用粗俗的语言、裸露的图片来讥讽穆罕默德,也与他们信奉的“新闻自由”相吻合;还有一部分人,通过口号传递对伊斯兰文明的仇视,试图用“查理”暗指欧洲历史上的另一位“查理”②Florent Deligia,Quelle est l’origine du nom Charlie Hebdo ?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108/---查理·马特尔(Charles Martel),其人为欧洲中世纪的名将,其著名之战为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他成功地阻挡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倭马亚王朝侵袭法兰克王国的军队。此战制止了穆斯林势力对欧洲的入侵,因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查理·马特尔以此拯救了欧洲基督教文明。显然,历史上这位查理的名字,寄寓着这部分人意欲抵制穆斯林势力、拯救基督教文明的愿望。
尽管 “我是查理”这一口号能够表达谴责、哀悼、示威乃至声援等内涵,但因为大多受制于情感和情绪因素,且多属于对事件的初始反应,因而局限性显而易见。
3.2.“我不是查理”
相比之下,“我不是查理” 的口号则是渐渐冷静后思考的产物,更多地上升到思想层面,因而包含更多的理性色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1月8日刊发文章直言:“我不是查理”。这位较早喊出这一口号的人认为,查理事件之后的公众反应表明,很多人可以将《查理周刊》冒犯穆斯林的讽刺神圣化,但对于那些冒犯“自己人”的内容却没那么宽容,因此他并不认同《查理周刊》所擅长的用幽默的方式刻意冒犯他人的做法。
的确,在《查理周刊》的历史上存在那种“自己人”碰不得的例子。《查理周刊》的前身《切腹周刊》被查禁的原因,不正是冒犯了戴高乐吗?后来,著名的西内(Siné)解雇案,不也严重抹黑了《查理周刊》以捍卫新闻自由之斗士称名于世的形象吗?西内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担任《查理周刊》的漫画家,名气很大。2008年7月,他在专栏中讽刺了时任总统萨科齐的儿子让·萨科齐,结果遭到当时杂志社总编菲利普·瓦尔(Philippe Val)的解雇,理由是他的反犹言论①相关文字的译文:“让·萨科齐,他爹的好儿子,已经是人民运动联盟的省议员了,交通肇事逃逸,可陪审团竟然免于起诉,走出法庭时,人们还恨不得给他鼓掌!还有:他刚刚宣布,他要先皈依犹太教,然后再和他的犹太人未婚妻、达尔迪(DARTY)家族继承人成婚。这小子,真会为自己铺路啊!”(2008 年7月2日的《查理周刊》)。其后西内将《查理周刊》告上法庭,法庭判西内无“反犹”违法,相反,《查理周刊》侵害了新闻自由原则。此案启示人们,《查理周刊》的“言论自由”其实具有选择性:用于挑衅伊斯兰可以,讽刺“自己人”不一定行。
在《查理周刊》受袭后的《幸存者专刊》出版当口,其主题依然对准伊斯兰宗教,封面上刊发穆罕默德流着泪,手持“我是查理”牌子的漫画。由于题材比较敏感,致使世界各国媒体对于是否转载这幅具有挑衅性的封面态度不一。各国媒体态度明显分化,有转载和拒绝转载者,也有打马赛克转载者,更有拒绝转载并严重抗议者。法国本国读者也不再众口一词地拥护《查理周刊》。据法国《星期日报》1月18日民调显示,认为《查理周刊》不应刊登该漫画者达42%,支持刊登者为57%。另有5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限制网络与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历经时间的积淀与反思,已有半数的法国人开始意识到,自由并非毫无边界。
在自称“我不是查理”的人群中,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支持《查理周刊》新闻自由的原则,但反对它激进、敌意、卑劣的幽默方式。
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其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作为原则,作为观念,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现实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和落差,这些壁垒和落差,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主要产生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则更多缘于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差异,因此,任何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扩张和胜利都不可能实现,它必须保持与其它价值体系的互动。具体到《查理周刊》所捍卫的言论自由,在实践中被“唯我独尊”,被自命为惟一的普世价值,没有对其它价值体系,如伊斯兰教,给与足够的尊重,逐渐沦为嘲弄的自由、冒犯的自由、挑衅的自由,甚至是色情、猥亵和暴力的自由。
这样任性的、排他性的言论自由显然已经偏离了人们所追求的原初的言论自由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是查理”表面上是对粗俗不雅、恶意冒犯的漫画手法的不认可,实质代表了对言论自由原则的不同理解。
二,“我不是查理”,是因为“查理”跟“伊斯兰极端分子”有着太多的共性:
首先,两者皆强迫对方认同和接受自身的文化理念。伊斯兰极端分子从神学意识中寻找安慰,通过杀戮、暴力、精神控制等手段,将他们的世界观强加给别人,而查理们则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以亵渎、侮辱、颠覆破坏等方式攻击别人的精神信仰,同时还要求天下所有人具备欧式幽默感和自嘲精神;其次,两者均不畏死亡,一方愿意为了自己的神杀人而且不惜自身的灭亡,另一方也誓死捍卫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不害怕报复。我无妻无子,没车,没贷款。这也许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生。”②Le monde:« Je préfère vivre debout que mourir à genoux »,septembre 2012.面对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多次受到死亡威胁、甚至被列入基地组织通缉名单的周刊主编漫画家夏尔伯曾向法国《世界报》这样表示。推到极致而言,《查理周刊》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间进行的是一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一方通过武器发言,另一方则把言论当作武器,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暴易暴。“我不是查理”意味着拒绝暴力,反对极端,包括过度的、以自由为名的语言暴力,当然,但绝不包含对恐怖分子的原谅和姑息。如果说“我是查理”是让人团结在“言论自由”旗帜下的号令,那么,“我不是查理”其实并不是它的反腔,后者强调的是对言论自由这一原则的不同维度的微妙理解,探讨的是新闻自由的背后的伦理共识。
3.3.《查理周刊》何去何从
当今的法国,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一个不是移民国家的移民国家,其中,穆斯林占法国总人口的10%左右。但是,很多穆斯林进入法国生活后,却又无法真正融入法国社会,因此,虽然法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元社会却一直没有实现。作为最晚进入法国的宗教,伊斯兰教没有像其它宗教那样,共同经历漫长的世俗化过程,其直接后果就是它与法国的世俗价值观之间(其中包括言论自由、自嘲精神等等)形成激烈的摩擦、碰撞和冲突。这一现状既让穆斯林倍感“被边缘化”,又让法国传统主流社会感到“被伊斯兰化”,甚至在部分社会人群中, 出现“伊斯兰恐惧症”。
法国著名作家乌勒贝克在2015年初出版的小说《屈从》就展望了这一担忧。作者讲述了2020年法国通过选举产生出一名穆斯林总统,从而法国全面进入伊斯兰化的故事。虽然所有描述只是一种文学想象,但是,这已足以用艺术的方式让法国人看到了一种极端的国家未来。
《查理周刊》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拿起捍卫言论自由的武器,并一再挑战穆斯林的敏感神经。但此举不仅无法化解或调和法国社会内部的价值冲突,反而火上浇油地激化矛盾。今天的巴黎悲剧恰恰验证了,《查理周刊》的作法,非但没有令这种文明冲突降温,相反使之更加激烈。
在《查理周刊》事件后的反恐大游行中,游行的行进路线是从共和国广场到民族广场。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专门设计的游行线路似乎正好映射着法国的历史和未来。作为起始点的“共和国广场”,素以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而称名于世,同时也象征着法国传统主流价值。当庞大的游行队伍从该广场出发时,此举别有深意地隐喻着从传统迈向未来的起步;而作为游行路线终点的“民族广场”中“民族(nation)”一词,仿佛提醒每一位参与者,法国已经从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国家,民族的团结、民族的融合是法国当下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民族广场”既是此次游行的终点,更代表法国最终形成多元的、和谐的、新的法兰西民族的终极目标:不同族群、不同种族在法兰西大旗下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再一次向世人证明法兰西文明一再宣称的开放、博大的胸襟。允许并包容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法兰西大地上的相容共生,并行不悖,业已成为这个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这一背景观照下,法国现行的传统政治讽刺以及新闻自由观,当如何与时俱进地适应法国民族融合的进程,具体到《查理周刊》的何去何从,势必不可避免地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必选题。
综上所述,《查理周刊》的前景依然严峻,它绝对无法变更现有风格,形势已将它推到“没有退路”的困难境地。首先,遍布全球的东西方文明冲突不仅没有缓解迹象,反而大有不断激化的趋势,部分热点地区的武装冲突正在给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带来巨大威胁;此外,法兰西本土日益蔓延的民族文化矛盾、因“查理事件”带来的全社会的强大逆反心理,把《查理周刊》推上民族文明冲突的风口浪尖;加之《查理周刊》自身的经营日益风雨飘摇,困窘的经济状况导致其难以为继,而意外的“查理事件”无疑为其注入一剂强心针,这家名声原本有限的刊物,一跃而为称名全球的著名期刊,其带来的不仅是名声,更是可观的发行收益……
可以判断,已经付出血的代价的《查理周刊》,将会在今后一段时期继续捍卫和保持已有的“谑虐血统”,继续以无情嘲讽和有力攻讦作为刊物特色。因为它除此之路,别无他途。只是人们对它的前景存有担忧——戏谑之路还能走多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罗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