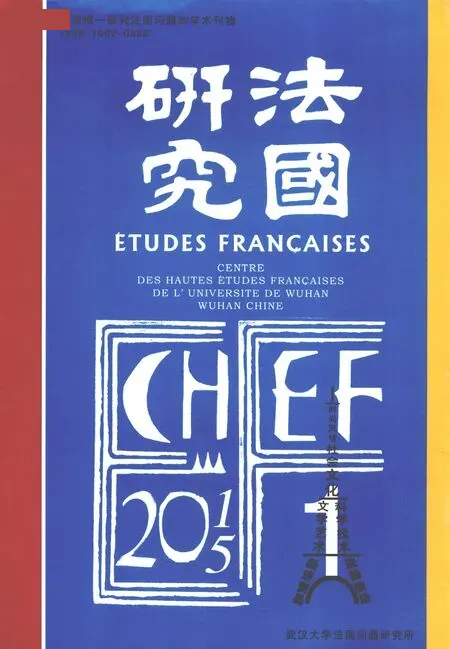法国骑士文化时期女性魅力及其展示——以《特里斯坦和伊瑟为例》
赵 丛
法国骑士文化时期女性魅力及其展示——以《特里斯坦和伊瑟为例》
赵 丛
【摘要】法国骑士文化时期,女性受到异乎寻常的尊敬,这与当时社会父权的加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探讨其中的缘由和挖掘历史的真实,我们从女性自身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来寻找合适的视角,而女性魅力及其展示正好符合了这一需求。通过了解法国骑士文化时期的妇女角色以及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真实看法,我们分析概括出这一时期法国女性魅力的特征,并用《特里斯坦和伊瑟》作为文本例证来近距离观察女性是如何展示其魅力来提升自身价值的,以求破解法国女性的“倾世”之谜。
【关键词】法国骑士文化时期 妇女角色 女性魅力 女性魅力展示 《特里斯坦和伊瑟》
[Résumé] A l’époque chevaleresque de France, l’évidence du respect dont les femmes jouirent fut en contraste avec le renforcement de l’autorité paternelle. Pour fouiller les raisons de ce fait et découvrir la réalité historique, en voulant chercher une possibilité de recherche chez les femmes et dans leur rapport avec la société, nous trouvons que les études sur le charme féminin et son déploiement correspondent bien à notre demande. Après avoir présenté le rôle social des femmes à l’époque chevaleresque de France et les opinions réelles de cette société concernant les femmes, nous analysons et synthétisons des caractéristiques du charme des Françaises de cette époque, et puis en prenant Tristan et Yseut comme exemple, nous observons de tout près comment les Françaises déployèrent leur charme dans le but d’élever leur valeur, de sorte que nous pouvons dévoiler le mystère des Françaises « fatales ».
一、法国骑士文化时期的妇女角色
从公元4世纪下半叶开始,“蛮族”就开始徙居高卢,在此建立国家,其中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克洛维创建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的尚武精神在法国骑士时期被保留下来,特别是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一带,12世纪的时候还流行着骑士比武的习俗。骑士们在为了获得战功而浴血奋战的同时还怀揣着一种特殊的情感追求,即获得心仪女子的芳心。
加洛林王朝末期,男性的优势因为采邑世袭①肯定采邑世袭的法律,法国以877年《凯尔西□令》为准,德国和意大利则以1037年的《封土律》为准。而有所削弱,再加上常年混战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没有男性继承人的现象频频发生,无奈下女性被赋予了继承权。封建家族的贵妇人,因为生活条件和社会处境的改善过着衣食无忧舒适安逸的生活,于是她们开始读书识字来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也千方百计地增加自己的才艺和把握男性世界里的生存艺术来吸引那些风流潇洒的骑士,赢得他们对自己的钟爱,就此,这些贵妇人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来展示这个历史时期所赋予她们的文化魅力,以实现她们现世的追求②事实上,女性在这种现世追求中极大地冲击了当时流行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不可否认这是一种进步,无形中女性实现了对社会束缚的反抗。。
11、12世纪,欧洲开始了“十字军东征”。一方面,骑士们都纷纷奔赴圣战战场,家中的各种重担都落在了妇女的身上,事实证明了妇女完全有能力从事和管理社会生产活动,至此妇女无用的观念不攻自破,妇女也依靠自己的才华赢得了男性的尊重;另一方面,骑士们在参与圣战过程中真切地体会到圣母玛利亚所受到的至诚崇拜,这种崇拜并不妨碍信徒与基督间的直接契合,反而可以促其实现,虽然这种崇拜由来已久,但通过十字军东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玛利亚的圣洁形象开始取代夏娃的堕落形象。由此,现实中的女性和母爱无形之中较从前地位有所提高,有时也会为人所崇拜。
二、法国骑士文化时期的女性魅力
在中世纪法国,女性一直是邪恶的化身,懒惰和淫荡的代表。骑士们如果将传统定义下的女性作为崇拜对象,显然这是有悖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信仰的,因为女人永远是和肉体相连与精神相对。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从社会理想来论,中世纪一直视精神高于肉体,理性优于感性,就像男性强于女性一般。在“骑士之爱”盛行时期,骑士们之所以将女性假想为崇拜对象,是因为他们对女性有着短暂的需求,而且被他们置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女人是被精神化的完美形象。我们要相信,在男性占有绝对优势的父权社会,男性是不可能轻易将手中的权力拱手送给女性,也不会因为一时之需而坦然承认女性的社会价值,骑士们选择的是将理想化的女性和一般女性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让前者成为他们精神与理性的代言人,这样既不违背他们的最高信仰又能够督促醉心于虚幻崇拜中的现实女性心甘情愿地为男性服务。此时,被精神化的完美女性形象所具备的魅力自然成为了男性所推崇的女性最佳品质.显然,男性从根本上认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但就是这种纯粹主观的模糊差距很容易让现实蒙上了一层似是而非的迷雾,现实中的女性只能从这层迷雾中寻找契机,努力通过展示魅力将这层迷雾打造成男性欲罢不能的如梦幻境,促使男性为其一手创造的精神幻想游走在理性与感性的边缘,女性则从中获得生存处境的转机。
由此可见,法国“骑士之爱”盛行时期,女性所要展示的魅力与骑士的精神幻想密不可分。更准确地说,骑士将理想化的女性隐喻为理性交织于感性却又高于感性的事物,来满足他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完成自我超越的目的(为封建主的权力,为宗教信仰而战)。我们从骑士的精神幻想中不难发现该时期女性魅力的两大要素。第一,感性疗伤慰藉功能的具备,即在感性上让男性得以满足。在中世纪,人的天性被极度抑制,宗教里繁琐的教条和封建社会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往往逼迫人们放弃小我(自我)成全大我(超我),长期的身体与精神压抑常常需要得到释放与安抚,特别是在战争与死亡面前。此时女性可以帮助男性找寻到放松肉体与发泄情感的渠道,适时适度地满足男性直觉的渴望,让其感受到现世的愉悦与温存,进而使其愿意为现世奉献出自我。第二,理性压倒性的存在。理想化的女性不同于一般女性,不是纯感性的动物,其所具备的魅力还在于理性对感性有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但是这种理性是遵从男性社会利益的理性,也就是说理想化的女性有着为男性事业彻底奉献的觉悟。在男性看来,现实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受到理性的眷顾,理性对于男性来说是先验性的存在而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后天男性的恩泽,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女性才有机会沐浴此恩泽。这些幻想中的幸运儿通常被锁定在封建贵族家庭,因为血统是判断理性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准,只有继承了父系的优秀血统才可能感受到理性的光辉,传承父系的精神。再者,良好的修养(这种修养往往与当时社会的主导价值观相符)也是成为幻想中的幸运儿的重要条件,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骑士通常将精神幻想寄托在贵妇人身上了,因为贵妇人必须接受严格的道德礼仪教育,而且她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处境的改善,使其有机会接触到男性世界的文字,接触到书本中原本专属于男性的理性认知。
根据这个时期女性魅力的两大要素,我们可以判断,让骑士们行走于精神与肉体、感性与理性之间却让他们诚服其精神与理性的女性很容易为骑士们所钟情,让骑士痛快享乐却又从享乐中获得斗志的女性则极可能被披上神圣的外衣,也就是说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展示魅力被骑士假想成既能满足他们感性需求又能助推他们理想宏图的圣物,或者更直白地说,通过将女性与男性置于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中,制造出看似理想的梦境,“骑士之爱”就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纠缠中呈现燎原之势。
三、法国骑士文化时期的女性魅力展示①为行文方便,我们将女性魅力展示简称为示魅。——以《特里斯坦和伊瑟》为例
根据法国骑士文化时期女性魅力的核心特征,此时的女性正如《玫瑰传奇》中的玫瑰,那喀索斯泉底的魔镜和荆棘利刺筑成的屏障则意味着女性魅力展示过程中符号使用上感性与理性交织存在;玫瑰投射在魔镜中的影像就是女性利用感性营造出的幻影,随即散发的玫瑰香气就是感性打造的细腻多情,而荆棘利刺将玫瑰和情人分离致使情人的欲望愈发强烈则隐喻地表达了理性突显在女性示魅过程中的不可或缺,即使理性的选择会给感性的释放制造一些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但因此女性才能够实现魅力价值的最大化,正如后人评价《玫瑰传奇》时提到:最难采摘的玫瑰正是情人最喜欢的。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骑士时期经典作品《特里斯坦和伊瑟》来了解在这些特征下魅力展示符号的具体使用情况。
3.1 镜中玫瑰②Guillaume Lorris & Jean Meung, Le Roman de la Rose. Paris: 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 FILS ET CIE, 1864, p. 53.—— 亦幻亦真的感性释放
感性的直白表达赤裸而酣畅,给肉体和灵魂都带来无以伦比的快感,但是欢愉过后理性回归,剩下的只可能是百般厌恶,女神随即陨落成女巫。女神想要稳坐神坛,需要的是拥有“魔镜”力量的示魅符号,它们能够让感性释放得真切诱人又神秘朦胧,虚实难辨,耐人寻味。
1)宗教信仰词汇的反复使用
伴随这类词汇的频繁使用,示魅女性往往会进行情感的抒发,这不仅可以为她们打造神圣虔诚的外衣,而且在将感情表露得酣畅淋漓的同时为她们提供了看似合理的情感出口,即来自宗教信仰的依靠,示魅对象既有理由将其看做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以认为是受到宗教信仰的指引,神圣高贵却贴近内心。
我跟您说实话:如果您不相信我且听信那些子虚乌有的谗言,我的真诚最终也会拯救我。……陛下,我是忠诚的。①Béroul, Tristan et Yseut. Éditions eBooksFrance, 2000, p. 9.
这段话发生的前提是伊瑟很清楚国王目睹了她和特里斯坦约会时所演的那场戏,也有一定把握国王已经原谅了他们,所以她可以选择向马克国王(Marc)表达真挚强烈的情感而不会遭到怀疑,并用自己的人格作为赌注为这种情感披上神圣悲壮的色彩,以至于马克国王对自己的猜疑懊恼且后悔不已。
依照奥克汉修道士的建议你将我带回到国王那里并将我归还给他。愿上帝在天堂赐福于你!我也以上帝的名义请求你,我心爱的人儿,在弄清楚国王如何待我之前不要离开这个国家。国王带走我之后,我用全部的爱恳求你当晚前往守林人奥利的住所。就当是出于对我的爱,你先住在那里。……我的爱人,上帝将佑护你!(Béroul: 33)
伊瑟在感叹奥克汉修道士引导他们重回理性道路并将受到上帝赐予的恩泽之后,继而以上帝之名请求特里斯坦能够继续隐藏在她身边,她对特里斯坦的留恋与依赖因为其所突显的上帝的仁慈之心而流露得理所应当且自然流畅。
2)多种称谓的更迭使用
Mon amant - mon bien-aimé - mon ami bien-aimé - ami cher - ami Tristan - ami - Tristan très cher - cher Tristan - cher seigneur - seigneur
以上是伊瑟对特里斯坦用过的称呼,这些称呼在明确亲密关系上程度各有不同。根据称谓的心理学意义,伊瑟不断更换使用的称谓无形地牵制着特里斯坦的内心。就伊瑟而言,浓烈的情感时而因亲密的称呼得以释放,时而又因距离感鲜明的称呼被掩饰;就特里斯坦而言,不同称谓下,关系的忽远忽近和感情的似浓非浓促使特里斯坦对明确的亲密关系愈发渴望,多种称谓的比较中欲望之火燃烧得愈发旺盛。
3)修辞手法的渲染
——提喻
亲爱的特里斯坦,……我只要一看到这个戒指,任何城楼,高墙和堡垒都无法阻止我,我将怀着万分的崇敬与忠诚赴我朋友之请,只要我知道这正是您所希望的。(Béroul: 33)
——夸张
自律法颁给摩西以来,从未有一只动物享如此好的命,睡如此漂亮的床。(Béroul: 32)
——反衬
无论我多么悲伤,只要看到它我就会感到快乐。(Béroul: 32)
在即将与特里斯坦分开并重拾王后身份的时候,伊瑟用这一系列修辞手法将情感释放到了一种爆棚的状态,但是两人的实际处境恰恰只能让这份激情寄托给未来和替代物(猎犬Husdent),于是情感被渲染得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特里斯坦非但无法斩断情丝反而新添更多的不舍与期待。
4)表达技巧上感性与理性的交织
感性在释放的过程中似乎同时在编制一张理性的大网,让示魅对象在感受强烈情感冲击的同时仍然被一根理性的缰绳牵引着,就这样,炽热的情感在理性的网兜里跳动,似乎是随心而生又好像是为理性而生,此时示魅女性就犹如拉网的号手一般,将示魅对象所有期待的情绪一拽而出,在这种情绪的交织中示魅对象在示魅女性身上感受到一种有血有肉的高贵灵魂。
请将你的猎犬Husdent留给我。我保证在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无论我多么悲伤,只要看到它我就会感到快乐。自律法颁给摩西以来,从未有一只动物享如此好的命,睡如此漂亮的床。亲爱的特里斯坦,我这里有一枚刻上标记的绿玉石指环。亲爱的大人,出于对我的爱,请戴上这枚指环。如果有一天您想要求我做什么,请相信我一定会予以满足。……向我出示这枚戒指的人要求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任何国王都无法阻止,不管这是明智的还是疯狂的,只要这不会损害我们的名誉:我以爱的名义向您保证。(Béroul: 32)
伊瑟在与特里斯坦离别之际提出交换信物,并将万般的不舍与依恋赋予这一举动,因此特里斯坦的猎犬成为了她的情感寄托,伊瑟对待那猎犬的态度让特里斯坦深刻地感受到她这份真挚的爱,同时这种爱的表达因为直接接受对象的转移(或者说为真正的接受对象找寻到了一个象征物)而变成了一种含泪的诉说,泪光下的微笑充满了经过理性选择的无奈之后释然的知足感。另一方面,伊瑟让戒指化身为自己爱的见证,但明明是情人之间火热的爱恋却转变成了一种友人间的大爱,爱的誓言因为可以战胜一切不禁让人激情澎湃,同时又因为必须遵从于荣誉与信仰不由使人肃然起敬。就这样,伊瑟将滚烫的情感赋予给了一对象征物,由它们来掌控着感性释放的限度和强度,特里斯坦由此感受到了暗涌的爱恋以及耀眼的大爱,伊瑟也借此化身成了恋人、友人、女主以及女神的综合体。
5)恰如其分的眼泪
国王很清楚她说的是实话。他任其倾诉,然后不断地拥抱亲吻她。伊瑟哭泣着:国王恳请其不要再说了,从此不管告密者说什么,他都会绝对信任特里斯坦和伊瑟。(Béroul: 9)
伊瑟此前一番把握十足的自我辩护已经让国王相信了两人的清白,伊瑟心里也十分清楚已经得到了国王的谅解,此刻的眼泪在显示所承受莫大委屈的同时,还向国王表露出非凡的忠诚。除此之外,在国王表示愧疚的爱抚之下眼泪流露出的情感多少有些暧昧不清,伊瑟用眼泪模糊了自己的立场供对方去想象,国王则可以从中读出他所期待的情愫,因此泪光折射出的话语在当事人眼中清晰可见却又待反复琢磨,以至于国王希望竭尽所能来解读和满足眼泪的诉求。
3.2 荆棘墙包围下无法触及的玫瑰①Guillaume Lorris & Jean Meung, Le Roman de la Rose. Paris: LLIBRAIRIE DE FIRMIN DIDOT FRÈRES, FILS ET CIE, 1864, p. 55.——如歌如泣的理性传递
荆棘利刺筑成的屏障恰恰出现在情人深深被玫瑰吸引,正要不顾一切去采摘它的瞬间,虽然玫瑰与情人之间出现了无法逾越的现实距离,但是玫瑰却更加牢固地扎根在情人心中。因此,感性在想要尽情释放的时候需要被理性拉回来,遭到“绑架”的感性因为理性的束缚得到了升华,伤感惆怅是必然但理性成就了一件最美的嫁衣,女神也因为遥不可及而变得美不胜收。
1)宗教祈祷式的第三人称命令式的使用
当理性与感性发生冲突时,宗教往往被认为起到将人们拉回理性的作用,这种向上帝祈祷的方式一方面在强调所崇尚的价值,一方面是对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的一种安抚,女性通过这种表达突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愿意为其牺牲的觉悟。
大人,承蒙基督慈悲,您不要再继续犯错了。……我的朋友,特里斯坦,我们两个只可能期许万能的上帝可以怜惜我们! (Béroul: 28)
伊瑟和特里斯坦在药效褪去之后,两人对不顾后果的相爱都感到痛苦不已,于是两人在面临艰难抉择之时,伊瑟毅然决然地支持特里斯坦站在理性的这一边,将毁灭了理想的儿女之情抛掷一边,用对上帝的信仰与祈祷来洗涤自己的灵魂,无限放大着自身保持的那道圣洁光芒。
2)修辞手法头语重复的妙用
宗教用语中的头语重复就好像奔腾的情感经过信仰的触摸之后创作的一首理性颂歌,伴随着示魅女性的吟唱,唯美而高亢。
请听我对马克国王的誓言:以上帝,圣伊莱尔,这里神圣的一切,在或不在这的世上所有圣物起誓,除了这个麻风病人和国王,没有任何人曾身处我两腿之间。如果有人要求其他考验,我在这奉陪到底。Ecoutez mon serment, qui est destiné au roi Marc: par Dieu, par saint Hilaire, par tout ce qu’il y a ici de sacré, par ces reliques, par celles qui ne sont pas ici et par toutes celles qui existent dans le monde, entre mes cuisses ne sont entrés autres hommes que le lépreux [...] et le roi Marc [...] si quelqu’un demande une autre épreuve, j’y suis prête, en ce lieu même. (Béroul: 48)
伊瑟的誓言通过par的头语重复显得气势高昂,信仰笃定,同时结合其贵为王后不得不为王室声誉当众立誓以表清白的背景,这种誓言前奏的谱写呈现出悲壮唯美的效果,并与誓言的结尾——伊瑟对一切质疑进行挑战呼应,共同勾勒出虔诚的女殉道者形象,让人由衷臣服赞叹。
3)表达技巧上斗志与柔情的合二为一
以理性为轴,情与义的巧妙转变仿佛让情人透过荆棘墙闻到了玫瑰花香一般,理性的态度表现得坚定却又不失温婉。
陛下,他们都说我什么坏话了?当然每个人都有表达其想法的权利。而我只有您为我辩护: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想方设法地诬陷我。让上帝诅咒他们吧!他们总是陷我于苦恼中!……如果他们想要我宣誓证明自己的清白或是他们苛求我接受审判,那就让他们自己定个日子…… (Béroul: 37-38)
得知国王马克已经开始反感造谣者之后,伊瑟在暗自庆幸之余,仍然需要面对国王一直未消且重新被煽动的猜忌。首先,她既没有一味地诉说自己的冤屈而尽显楚楚可怜之态,也没有锋芒毕露地为自己进行辩护而展现其强硬态度,她只是似乎毫不知情地甚至置身事外地询问造谣的内容,为了从潜意识里就将谣言与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并通情达理地像在为造谣者开脱,于是一个淑惠贤明的王后形象立刻呈现出来,这也为之后伊瑟证明自己的清白进一步表现出不屈不饶的勇士态度作了铺垫。然而此时伊瑟话锋一转,柔情表露无疑,她将国王视为了自己唯一的依靠,并指出这种依靠正是给她带来麻烦的根源,让国王心疼不已,于是接下来对造谣者的指责都变成了这绵绵柔情的载体,辛辣却又甜蜜非常。最后,伊瑟通过接受造谣者的挑战将与国王的情义升华到了一种自我信念与价值的证明,柔情在无畏斗志的装扮下披上了理性的战衣。借此,伊瑟在国王马克心中刻画出了一个理性中深藏款款柔情的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
4)肢体表现与背景环境的强烈对比
体力上女性往往表现出较大的弱势,尤其当受到环境的限制时。而理想的女性时常被认为能够克服生理上的弱势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来完成至高无上的理性目标。可是,在现实中,女性要从肢体表现上完成感性向理性的跨越,心理与生理上都必须接受巨大的挑战,示魅女性更是需要突显其生理条件、环境情况二者与实际肢体表现上的强烈反差,以体现示魅女性理性能够战胜一切的特质。
她靠近坐骑,抓住马镫绳将其系在马鞍架上:御马监和马夫恐怕都无法从这个泥潭中全身而退。她把缰绳放至马鞍下,缩回马前胸并取下马嚼子。她用一只手拎住裙子,另一只手抓住马鞭。当骑至河道处时,她甩一马鞭,这马便越过了沼泽地。(Béroul: 45)
在赴宣誓大会的途中,众多赶赴会场的勇士都纷纷陷入泥潭狼狈不堪。事实上伊瑟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为保险的地方平安渡过泥潭,但是她毅然决定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境地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加上伊瑟身为王后原本就是千金之躯,身体条件的娇贵和环境背景的恶劣因此都被明显放大,此时伊瑟变身为一位斯巴达女战士,所有的不利因素在她面前都望而却步,她通过一系列娴熟的御马技巧展示了与传统女性柔弱形象相对的矫健姿态,放射出了这个时代对女性身体表现所向往的理性光芒。
5)衣着服饰的考究
在等级社会里,衣着服饰一直以来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人们对什么样的场合应该着什么样的服饰都逐渐形成共识。骑士理想中充满高贵气质的女性应该天生就对这种符号有着敏锐的掌控力,于是女性在示魅中有必要突显服饰选择上的理性觉悟,尤其在理性选择看似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恰当的服饰符号体现自身的高贵地位,更是能够将完美女性形象塑造得愈发可歌可泣。
她穿着一件精致的绣金灰色锦缎长袍。头发垂至双脚,系住发辫的饰带也是金色的。看到她如此美丽优雅,只有犹大的心才能做到不怜悯她。(Béroul: 16-17)
这是伊瑟在行刑前的装扮。原本蓬头垢面的罪犯形象被身着锦缎、长发披肩、金光熠熠的圣女形象所替代,这让人们形成极大的心理反差而更加笃定伊瑟不容侵犯的高贵地位。
伊瑟穿着巴格达的绸缎衣服,上面饰有白色貂皮。她的所有服饰,无论是斗篷还是长袍,都有一个拖裙。她那点缀有金粉且中间分开、紧贴双鬓的头发落在肩膀上。她的头上还戴着一个金发圈。她的脸色如何?白里透红,容光焕发。(Béroul: 45)
国王马克受到诽谤者的挑唆,迫使伊瑟在众人面前发誓证明自己的清白。原以为作为审判对象,伊瑟会呈现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但恰恰相反,她选择了一套不失高贵典雅气质的女战士装束,再配上她那如玉的肌肤与焕发的容光,俨然一副为自己荣耀而战的女壮士模样,此时伊瑟将自己塑造成了令男性汗颜的女英雄。
结论
法国骑士制度开始于中世纪加洛林王朝,中世纪也被誉为骑士的英雄时代。在这个骑士文化盛行的时期,法国妇女的地位不仅受到历史传统、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也随着骑士阶层所经历的各种历史遭遇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表面上,骑士对女性的尊重沿袭了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但从根本上来看,骑士所觊觎的女子的芳心就是他们获得的众多战利品中的一种,对女性情感的争夺就好像动物界雄性之间为夺得雌性的交配应允进行的斗争,男性更多的只是将女性当做他们炫耀的一种资本,女子的倾心是他们雄性权威树立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们财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即便如此,女性还是从这种似有似无的崇拜中找到了一种寻求保护展现自我的可能,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再一味地被轻视。更何况,在外征战的骑士长期经历着肉体上的折磨,难免心力交瘁,女性的柔情如母爱般抚慰了骑士疲惫的心灵,女性的怀抱好似谧静的港湾瞬间代替了血腥的战场,目睹太多生离死别的骑士总是在这种感性与理性之间徘徊,也试图在女性身上找寻一种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于是,男性将这种期待付诸在了女性魅力的设想上。
从上可见,历史赋予了法国女性展示自身魅力的特殊条件,相应地,法国女性魅力及其展示也为这段历史贴上了显著的标签。此时的女性魅力并不等同于女权主义者口中的女性气质,而女性魅力展示也不并属于他们所鄙视的男性凝视下的女性作为,相反,法国骑士文化时期女性对自身魅力的准确把握和展示不仅能够让她们巧妙地摆脱男性的控制,而且可以使她们受到男性的尊重甚至崇拜。我们不能说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发生巨变,但至少女性借助这种手段能够有所作为,此后的历史也足以证明法国女性将这种作为发挥到了极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方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