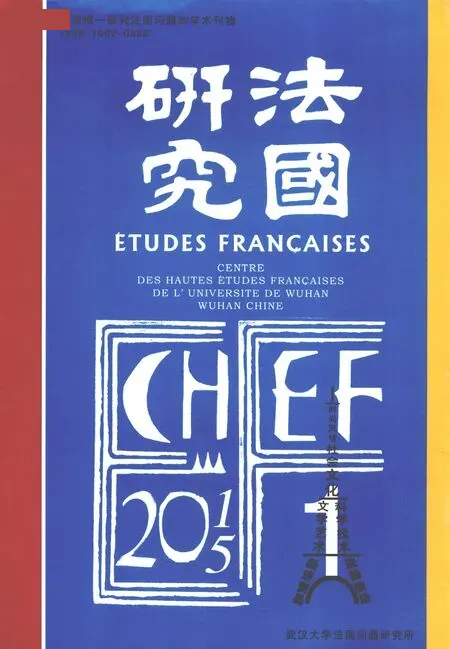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现代性观念的演变
孔建平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美学现代性观念大约形成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法国,相关讨论也大多集中于从司汤达到波德莱尔这段时期。而经常被引用的经典表述是波德莱尔那句评论:“现代性,是暂时的、瞬息即逝的,是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而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的、不变的。”①郭宏安编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3页。然而我们认为,美学领域的“现代性”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作为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中强调“进步”的乐观现代性的悖论,其诸多涵义早已孕育于极具反叛性的法国浪漫主义思潮中。对它的准确理解,更不应该疏漏浪漫主义的艺术实践。为此,本文将截取1800年至1831年之间法国浪漫主义的几部经典理论著作和小说创作,将理论解析和作品细读结合起来加以阐释,以期进一步把握美学现代性观念的来龙去脉。
一
1800年,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发表之后,立刻在法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类及其文学艺术是否必然进步的古今之争。“进步”观念是乐观现代性思想的核心,自文艺复兴以后,它大都基于“进化”的时间观念,即认为随着线性时间的展开,社会和人生都会取得较之过去的长足进步。这正像贡巴尼翁指出的:“连续的、不可逆转的、无限的现代时间观是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进步为模式的,是对权威的否定,是理性的胜利。”①〔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页。这一时间观念在 18世纪被推向高峰,法国启蒙学者普遍相信,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和民主的传播,“进步”的理性必将消除“过去”的蒙昧,人类社会必将有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斯达尔夫人无疑接受了这样的现代性观念。然而,18世纪的革命风潮却带来了未曾料想到的后果,社会动荡使许多人认为现代并未“进步”得更加美好。恩格斯曾这样描绘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②〔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3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18世纪大革命的恐惧和对“进步”观念的厌恶构成了丰塔纳等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要对斯达尔夫人大加嘲讽。在他们看来,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带来的“现代”意味着混乱和堕落,证明了人类进步的不可能。至于文学艺术,文艺复兴之后也更未取得多少超越古人的进步成绩。要言之,18世纪关于“进步”的启蒙信念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丰塔纳直接指出,斯达尔夫人的进步观念是 18世纪启蒙哲学的“残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才是现代的特征。而斯达尔夫人则坚持认为,丰塔纳等人对法国大革命反应过度了,它的确带来了灾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进步”,她在《论文学》第二版中答辩道:“当人们把大革命中的罪恶归咎于哲学的时候,他们是把可鄙的行为跟一些伟大的思想扯在一起了”,“我们应该把这个令人胆寒的时期看成是逸出历史潮流的事件”,历史表明,“人类思想的进步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斯达尔夫人,《论文学》:345)
斯达尔夫人为 18世纪形成的人类必然进步的现代性信念作出了重新辩护,但更重要的是,她把这一问题限制在文艺范围内加以讨论,为浪漫主义文学及关于审美领域“现代性”的讨论打下了伏笔。斯达尔夫人有时将希腊之后的中世纪文学称为现代文学,并以“浪漫”加以命名:“我认为古典诗就是古人的诗,浪漫诗就是多少是由骑士传统产生的诗。这一区分同时也相应于世界历史的两个时代:基督教兴起以前的时代和基督教兴起以后的时代。”③斯达尔夫人:《论德国》,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41页。她在《论文学》的“现代文学的总精神”一章中写道,艺术之本是模仿,模仿本身不可能日臻完美,但“在中世纪取得新成就的不是形象思维,而是逻辑思维”,而“今日的哲学家却在各门学术中,在思想方法方面,在分析问题方面,在概念的概括以及对各种结果的联系的探索方面,比古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斯达尔夫人,《论文学》:123),哲学思维必然推动各门艺术的发展,因此要把文艺领域的进步归功于现代哲学。
斯达尔夫人推崇理性发展引起进步的观点引起了夏朵布里昂的反感。他不仅像他的朋友丰塔纳一样,极力反对“人类是有可能日臻完美的”判断,尤其反对文学艺术因哲学发展而进步的观念。在他眼里,启蒙理性及其实践如同洪水猛兽,是种种罪恶的渊薮,它所带来的,不是人性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全方位的退化,使人变得粗俗,必然造成对文学艺术的伤害。种种现代艺术所呈现的粗鄙风貌,正表明了理性的弊端。事实上,夏朵布里昂是第一个明确地将这种对“进步”艺术的负面感觉称之为“现代性”的,曾经用嘲讽的笔调写道:“海关建筑和护照的粗俗与现代性,与风暴、哥特式大门、羊角号声和急流形成对比。”①转引自保罗·罗贝尔:《法语类比词典》卷4。巴黎:巴黎出版社1959,第607页。他争辩道,历史长河中的艺术或许创造过些许超越前人的美,但这要归功于基督教而非哲学:“我的癖好是看到耶稣基督无处不在,就跟斯达尔夫人看到完美的可能性无处不在一样”,“她把它归之于哲学,而我把它归之于宗教。”②转引自《论文学》,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34页。在他眼里,中世纪艺术所展现的完美与“现代”进步完全无关,它与现代性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二
对乐观现代性的厌恶和批判在夏朵布里昂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在 19世纪初年发表的《阿达拉》和《勒内》,便是记录他在想象中摆脱现代性纠缠的经典之作。《阿达拉》中的主人公沙克达斯到过法国,但法国人让他受到了不公正的遭遇,而真正养育他,让他变得睿智,具有“不屈不饶的品德”的,却是远离现代社会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原始森林。而在《勒内》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现代的判断:“伟大的世纪……已过去了。一个民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惊人和突然的变化。从心灵的伟大和对宗教的崇敬到风俗的严肃,所有一切突然跌到精神的顺从、对宗教的亵渎和世风的腐败。”③夏朵布里昂:《勒内》,载《法国经典爱情小说三部》,曹德明、罗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58页。后文凡出自《勒内》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在他看来,“进步”意味着动荡,现代性的最大祸害,是它玷污了人性的纯洁,摧毁了心灵的安居之所,使人片刻不得安宁。事实上,让夏朵布里昂们“极度失望”的关键,不是国家“伟大”与否,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进步与否,而是在当下法国片刻不消停的动荡现实中,已经找不到让心灵栖息的立锥之地。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性”与“浪漫”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夏朵布里昂笔下的,前者是贬义的、带有嘲讽的意味,后者则改变了原有的贬义——在启蒙时期,“Romantique”的原意是“如同在旧小说中”,其暗示是贬义的,但在夏朵布里昂的小说《勒内》中,患上“世纪病”的正面主人公将自己的性格称为“精神浪漫”,使其带上了褒义色彩。他的所谓“浪漫”,其基本含义正是拒绝现代性,并在绝望中忧郁地寻求心灵居所的精神冲动。可以说,正是在夏朵布里昂这里,“浪漫”第一次取得了与“现代性”相反的意义。
夏朵布里昂否定现代及现代性的真实目的其实既非恢复过去,亦非历史上某一个时段或中世纪,而是要重建某种亘古不变的时间秩序,以安放他的破碎的心灵。回望古代,看看现代,一切都混乱不堪,带给人们只是绝望和忧郁,它们都在时间长河中风雨飘摇、变幻无常,都不能让他的心灵安居。既然在过往的历史和当下的法国现实中,已经找不到让自己的心灵栖息的立锥之地,那么,唯有凭借想象才能进入超越时空烦恼的世外桃源。这也是构成《阿达拉》和《勒内》主人公“浪漫”追求的基本取向。在作者心目中,在变动不居的时空体中,能够给他的主人公破碎的心灵遮风挡雨的只有两片常绿的树叶:与现代性及进步无关的基督教和亘古不动的大自然。它们都是永恒的,都没有被剔出历史的废墟,也都具有完整性,因而都是美的。
事实上,夏朵布里昂小说的主旨正是以基督教昭示的“永恒”、而非简单的过去时来对抗现代社会所躁动的“进步”。在他看来,“现代”的并非是“文明”的,所谓的“文明”,也就是“浪漫”,就是超越时间流逝的“永恒”,就是基督教光照普世。而基督教教义最大的诱惑,也在于它许诺人们有一个超越时间流逝的完美时间之所:“基督教传统正是如此定义的,因为完美是最初的,先于原罪;如果说完美也存在于未来之中,那么这一未来就不被看做那一时间的延续,而是被视作另一个时间,就如永恒。”①〔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夏朵布里昂推崇基督教,所看重的也是其暗含了可以跳出“逝者如斯”的线性时间,规避现世社会纷争和人生烦恼的永恒美。《阿达拉》和《勒内》都曾被收录于《基督教真谛》,所推崇的当然是与变动不居的“现代”相对峙的亘久不变的基督教文明。《阿达拉》的主人公沙克达斯对来自法国的勒内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开宗明义地说道:“从你身上我看到一个文明人变成了野蛮人,而你从我身上看到神灵把一个野蛮人教化成了文明人”,而基督教的真谛正在于它给人以不为尘世所动的精神安宁:“这种安宁在平息感情的风暴时也像风暴那样猛烈:那是暴风雨之夜的月亮。飘动的乌云无法把它带走,它纯洁永恒,它在云层上面平静地向前行进。”它“能净化人的叹息,将容易熄灭的火焰变为永不熄灭之火,将它的安宁、纯洁与希望得到休息的心灵以及正在退隐的生命中残余的不安和嗜欲神圣地结合起来。”②〔法〕夏朵布里昂:《阿达拉》,载《法国经典爱情小说三部》,曹德明、罗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16页。
夏朵布里昂所张扬的浪漫之美,正体现了与资产阶级乐观现代性相背反、相对抗的审美现代性——虽然他讨厌“现代”这一词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文学史家布吕奈尔将夏朵布里昂这个申言抗拒“现代”的小说家称为“第一个现代小说家”,他和他的作品“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③转引自《法国经典爱情小说三部》,曹德明、罗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71页。
三
一般认为,“古代/现代”这一对概念的区分发生在18世纪中期英、法、德等国文艺美学领域,“古典/哥特”、“古典/巴洛克”、“古典/浪漫”等相对概念都几乎同时出现,也都几乎同时存在相互转换、相互说明和歧义丛生的情况。在夏朵布里昂笔下,“古代”和“现代”同时遭遇嘲讽,而在另一些作家那里,“现代”则获取了积极的含义。他们认为,在欧洲中世纪,“哥特”、“巴洛克”、“感伤”和“浪漫”之类的文艺风格都有着强旺的持久生命力,它们在许多方面更崇高、更可怖、更感人,共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都植根于各自民族生活和习俗的与古代希腊罗马相对的思想和艺术传统,这种源自并表现着自己时代的艺术即是“现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浪漫”,也就是要表现自己的时代的,它与“现代”几乎同义,与“古典”相对立。而“古典”,主要指脱离自己的时代和民族性的模仿。浪漫主义的这一观念,斯达尔夫人的表述最为清晰:“在现代人中间,古人的文学是一种移植的文学,而里面的或骑士风的文学在我们这里则是土生土长的文学,是由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一切社会情况使之生长出来的文学。”①斯达尔夫人:《论德国》,徐继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43页。
其实早在20年代,雨果就已经显示出与夏朵布里昂不同的倾向。对法国大革命之“动荡”,他的态度偏于肯定,认为新旧交替是历史必然,”“进步”也是必然的,值得嘉许,它表现在社会历史中,也必然表现在新的文学——即浪漫主义文学中:“它追随着时代而进步,但以一种庄重而合度的步伐。”②〔法〕《雨果论文学》,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16页。在他的理论声言中,“革命”、“新的社会”、“进步”和“浪漫主义”一起,取得了较为正面的含义。
与此相关,雨果逐渐赋予了“现代”一词以褒扬的含义。这在其 1831年发表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明确表达。作品在描述建筑艺术史时明确写道:“到了十六世纪,建筑艺术的弊端日渐明显,基本上不再能表现社会了,可悲地成了古典艺术;从高卢的、欧洲的、土生土长的艺术,变成了希腊和罗马的艺术;从真正的和现代的艺术,变成了假古典艺术。”③〔法〕雨果:《巴黎圣母院》,潘丽珍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180页。后文凡出自《巴黎圣母院》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他在小说中嵌入对圣母院的历史和现状的大段叙述描写,绝不仅仅在于他对中世纪历史的兴趣,而在于他认为,圣母院与后代人模仿的古典建筑既然不同,是完全现代的。他在这里所指的“现代”是与“真实”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能够充分真实地表达自己时代的叙述、描写和刻画,用作品中的话来说,也就是具有“原始性”的。圣母院是现代的,是因为它历经历史上无数次的改造、破坏、磨难,每一个时代都在它身上留下了印记或这个时代特有的原始性,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因而具有多重的原始性及现代性。雨果不相信文学艺术有进步与落后之分,而相信只有好坏之分。在他看来,艺术只要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就是“原始性”的,就是“现代”的,就是好的,永远都不会过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现代”也可以历久弥新:“时间还给教堂的,可能比它夺走的还多:它使教堂正面蒙上数百年积淀的灰暗色泽,而建筑成为文物,唯其古老,才愈显美丽。”(《巴黎圣母院》:106)也就是说,与夏朵布里昂不同,雨果认为,能够永恒的,唯有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现代”和“浪漫”。
与“现代”相对,雨果认为,脱离时代的模仿就是“伪古典”的,不好的,过时的。模仿“古典”是愚蠢的行为,它切断了艺术的原始性,必然导致其衰弱。雨果对现代性和原始性的推崇,不仅与古典主义趣味的“模仿”划清了界限,而且与脱离自己的时代和民族性的一味求新的“时尚”区别了开来。“时尚变得越来越愚蠢可笑。……时尚造成的破坏更甚于革命。各种时尚从形式到象征,从逻辑思维到审美观念都不一样,因此,时尚的破坏是深层的,它们攻击艺术的骨架,伤其筋骨”,而追逐时尚的,都是一些食古不化的模仿者,“都是受人委托,被人指定”(《巴黎圣母院》:107-108),他们必然导致艺术脱离自然和原创性。在雨果笔下,“时尚”与“伪古典”都脱离“原始性”,因而都与“现代”、“浪漫”相对立。
《巴黎圣母院》表达了优秀艺术即浪漫艺术的思想,认为浪漫艺术不仅是现代的,而且与不断变化的“现代”同步发展。按照作品的陈述,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人类最初的艺术是石头的建筑:“事实上,从原始社会到公元十五世纪,包括十五世纪,建筑艺术向来是人类伟大的书卷,是人的力量和智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表现。”(《巴黎圣母院》:172)而建筑艺术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当一种建筑艺术形式趋于模仿,失去现代性、原始性,它立刻就会衰亡。“神权建筑艺术的普遍特征是永恒不变,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因袭传统,关于把人和自然的各种形态,用令人难以理解的象征符号表现出来”(《巴黎圣母院》:178),其死亡不可避免。相反,哥特建筑是市民艺术,“人民建筑艺术的普遍特征,则是不断变化,不断前进,富有创造,五光十色,运动不止。”它始终是现代的,浪漫的,因为“这种艺术紧跟时代,也有了人性,并把人性不断揉入神的象征中,又在神的象征下再生。”(《巴黎圣母院》:508)而当印刷术发明之后,建筑艺术已经不足以表达现代的人性,所以它也成为了古代的,文学创作则成为了现代艺术的代表形式。
“现代”一词还被直接用于小说的人物命名上。《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卡西莫多原文为“Quasi-modo”,它又是法文“Quasi”和拉丁文“modo”的组合,“Quasi”有“准-”、“差不多”及“勉强可以算”等意思;“modo”则是拉丁文的一个副词,相当于现代法语中“maintenant”,意思是“现在”、“现时”,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意思即“差不多是现代的”。①罗国祥:《理性的反动——雨果小说美学的现代性》。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第2期。而“Quasi”和“modo”连用,源自圣彼得在复活节第一个星期天发布的第一封书简的开头用语,所以这一天历来被称作“卡西莫多日”。雅克·塞巴谢就曾指出,它在基督再生瞻礼仪式中也有着特殊位置,圣彼得在书简中写道:“卡西莫多……被上帝选定和珍视的有生命的石头,你也会像有生命的石头一样,进入建筑物的结构。”②〔法〕雅克·塞巴谢:《巴黎圣母院·导言》,载雨果:《巴黎圣母院》,潘丽珍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508页。因此,作品中的卡西莫多,是指有生命的石头,与教堂的钟楼实为一体,他象征着作品描写的年代——中世纪的一四八二年的原始性、现代性。如果说现代性还是指相信人类会随着历史进步而同步前进的意识,那么,雨果从圣彼得的第一封书简“那里面借来一个名字,命名未来人民的神话……使得这部反宗教的绝望的小说,成了一种相信人类宗教前途的最了不起的行为。”③〔法〕雅克·塞巴谢:《巴黎圣母院·导言》,载雨果:《巴黎圣母院》,潘丽珍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505页。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在 1826年提出“美丑对比”原则之后的第一次小说实践,作品所突出的首先就是现代与伪古典及时尚的对比。作品的人物形象设置,就是围绕这一原则结构的。卡西莫多是现代的,是被市民们选举出来的愚人节国王,是中世纪狂欢节的产物,因此具有原始性、浪漫性、现代性,而受到欢迎。诗人格兰古瓦是伪古典的,其特点是热衷于模仿,创作脱离时代的圣迹剧,因此遭遇嘲讽和戏弄不可避免;卫队长弗比斯则是时尚的,他徒有古希腊太阳神的伟岸外表,内心的性情却如低等动物,其脱离原始性的性质与格兰古瓦无异。他们都丧失了原始性,不知情为何物,全无感恩之心,是残害爱斯梅拉达的罪恶帮凶。而卡西莫多身上,像圣母院一样深藏着人性,被爱斯梅拉达送上的“一滴水”滋润苏醒之后,表现出至美的灵魂。卡西莫多实际上就是浪漫艺术品的象征,其外表的丑陋与内在的美的融合,“差不多”完整地表现了中世纪狂欢艺术的现代意味。
与卡西莫多相对,副主教弗洛罗则是想要脱离石头艺术的悲剧性象征人物。他对建筑艺术无比留恋,但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在进步,处于过渡时期,书籍正在侵蚀建筑艺术的地盘,喃喃自语道:“这一个将要杀死那一个!”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属于教堂,属于石头,也曾经有着石头的善良:独力抚养弟弟,收养天生畸形的卡西莫多,都表明了其人性的美,具有原始性、现代性。但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被美色惊动了他被长期压抑的青春,形成欲望与灵魂的错位,脱离了人性的原始状态,使其急欲逃离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教堂,偏离了石头的原始性。他熟谙石头的旧知识,又被书籍象征的新知识所诱惑,他的生命也就像那个时代一样被裁为两截,一截困于行将坍塌的石头世纪,一截倒向未曾夯实基础的书籍年代——从这两方面看,他也“差不多是现代的”。弗洛罗的命运被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现代性“文明状态”所注定,这就是他的浪漫悲剧。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初三十年的历史表明,现代性观念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在斯达尔夫人那里,“现代”意味着进步,理性的发展促使现代艺术超越古代;在夏朵布里昂那里,“现代”意味着混乱,唯有反抗理性的“现代性”,到超越时间性的基督教和大自然中才能寻求到永恒的艺术之美;而在雨果这里,“现代”意味着与历史同步,现代性意味着反映当下时代的同时性,艺术亦唯其现代才能永恒。他们的这些思想,无疑启迪了司汤达、波德莱尔后来表述的现代性观念。甚至可以说,后者的现代性观念,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已经生根发芽。